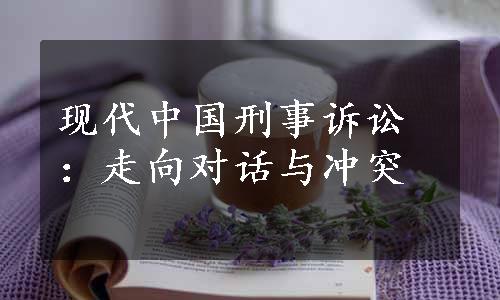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并经由1996年、2012年、2018年的三次重大修改,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尽管在诸多程序设计上各方尚存分歧,但改革的总体理念和脉络是清晰有序的,即在诉讼价值和诉讼结构上日益转向更具保障人权及更富对抗意义的当事人主义,或者至少吸收当事人主义的合理要素。这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诸多代表性学者的作品中均有论及。
如陈光中教授认为,“(中国刑事诉讼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基本上是无法可依,虽然也颁布了一些条例,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一种内部政策。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1980年1月1号开始实施,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经过若干年实施,随着国家形势发展变化,立法部门开始着手进行修改,也就是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1996年的修改力度比较大,条文从164条增加到225条,在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有较大进步,譬如辩护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当时的司法实际上是超职权主义,1996年的法律修改采取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某些做法,形成职权主义框架。第四个阶段应该就是现在的这一次。时隔15年,感觉非常有必要进行修改,此次修改规模上不亚于1996年。”[1]徐静村教授认为,“我国现行的庭审调查程序是所谓的‘对抗制庭审方式’,实行该庭审方式的初衷是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增强庭审的对抗性,提高控辩双方参与庭审的积极性,更好地帮助法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2]龙宗智教授认为,“我国长期实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从其结构上讲,具有强调国家职权主义运用的职权主义特征,由于这种职权赋予及其运用在许多方面超越了现代实行职权主义的欧洲大陆德、法等国在刑事诉讼法中界定的职权范围,如侦查权的缺乏制约、检察官在诉讼中的特殊法律地位等,因此又被称为‘超职权主义’。”[3]并主张“我国刑事诉讼的结构性改造只能继续推进,不能倒退。其基本理由是:继续推进诉讼结构改革反映了依法治国的要求;借鉴对抗制改造诉讼结构代表当今诉讼文化的发展方向;逆传统文化改造诉讼结构是一剂对症良药,有利于克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其运作的固有弊端”。[4]陈卫东教授亦认为,“我国的刑事庭审模式由超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1996年修正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引入当事人主义审判机制,以控审分离、控辩对抗为基点改革了庭审方式,控辩式庭审方式在我国逐渐建立起来。”[5]陈瑞华教授则认为,“刑事审判程序应当同时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真实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为此就必须分别吸收对抗式和审问式程序的优劣,避开其劣势,使这两种程序中的要素都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6]
可见,中国学界对刑事诉讼改革的基本走向几乎是毫无争议的,即认为中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形态是“职权主义”或“强职权主义”,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应是当事人主义或吸收当事人主义的合理要素。但正如左卫民教授在《职权主义:一种谱系性的“知识考古”》一文中所尖锐指出的,“在当下中国刑事诉讼研究中,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已成为参照域外法治国家诉讼模式的基本范畴……姑且不论这种论断是否生搬硬套,就是在基本的层面上,我们似乎对这两个概念尤其是职权主义的内涵缺乏应有认知,很多时候可能是在‘想当然’使用,对于其‘能指’与‘所指’并不明了。由此带来的结果,除了可能会犯潜在的知识性错误之外,还会导致学术研究、交流的障碍;如果考虑到学界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方向所形成的认识对决策层的影响,这甚至会阻碍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真正地朝合理化方向的延展。”[7]这种担忧并非毫无依据,因为时下中国的主流学说已有惯性思维,将职权主义与落后的诉讼形态紧密联系,甚至将诸多违背基本人权的做法如口供至上、刑讯逼供、公权强大、被告卑微等生硬地嫁接到职权主义中去。这其实是对职权主义的误解,中国时下学者普遍的英美法知识背景更加剧了这一“前见”(préjugé)。(www.zuozong.com)
从刑事司法体系的内部观察,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深化已逼近瓶颈,体制内外的各种功能衔接及各主要政法机关利益及资源的分配矛盾日趋尖锐,新旧制度之间的摩擦乃至冲突在刑事司法改革中势必日益明显。[8]在此一背景下,以法学界目前对刑诉改革方向的把握,新法究竟能否取得预期的成效,笔者表示担心和怀疑。实际上,如果不了解职权主义的核心要素,片面强调走向异质化的当事人主义诉讼,那么时下的刑事诉讼改革势必在法律文化冲突中进入钟摆式的轨迹,消耗大量的立法和司法资源。故时下最需要的是对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冷静分析,尤其对刑诉改革进行方向性反思。毋庸讳言,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后,大量学术资源投入对新法实施效果的实证考察,“描述问题—分析成因—提出对策”的应景型研究模式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学术研究自然有其重要价值,但笔者担心,倘若未有正确的方向指引,无法准确把握诉讼形态运行的内在规律,则此一貌似“解决中国问题”的研究所触及的将仅仅是诉讼制度的表层问题,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亦仅是基于利弊得失之权衡的权宜之策,甚至可能导致程序技术杂乱嫁接、诉讼结构混乱无章、制度学理逻辑相悖。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将秉承欧陆法的立场,旗帜鲜明地为“职权主义”辩护,着重探讨与厘清如下几个核心的理论问题:欧陆职权主义概念的起源、职权主义的核心要素、欧陆职权主义的当代发展、对职权主义批判之批判以及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缘何必须走职权主义道路。当然,笔者也必须重申,坚持欧陆法的立场,并非认为欧陆程序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非所谓的“正确知识”,而是认为制度的改革具有文化传承性,任何试图进行异质化、深层次变革的企图,均会导致不可预期的风险。笔者也期待,所有关心刑事诉讼改革的人士都能够对此一基础理论问题产生兴趣、投入精力,并展开讨论,从而为改革的全面深入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