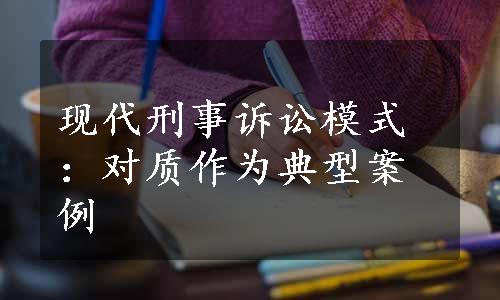
联邦最高法院时下的对质案例经常令人解读为,仿若联邦最高法院相信,适用对质条款是,或者应是,相对简单的事情。联邦最高法院似乎建议,所有我们需要做的仅是不再担心“可靠性”,而只是确信刑事被告得到《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所承诺的权利:与不利证人对质。但“对质”以及“证人”的含义远未清晰。很少有直接证据表明《美国联邦宪法》条款的制定者们心中所真正设想的意图。甚至很少有证据表明《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制定者们所考虑的对质权的轮廓,如果他们曾考虑过这一内容。尽管存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建议,但很少有理由可以认为,《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暂不提第十四修正案)的目的是或最初可被理解为将立宪判例法典化,带着各种巧合和矛盾。18世纪的美国人(尽管并非所有美国人)推崇“普通法”,推崇一系列普遍的原则,而非特定规则及实践的纲要。[311]简单而论,《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的制定者及批准者希望能够保护被告和对其不利证人进行对质的权利,仅此而已。但他们是否认为这一权利正确运行,则并未显得如此清晰。他们多数人并非法律人,也不太可能对这一问题有任何的考虑。《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制定者和批准者更不太可能明确思考,这一对质条款在州刑事诉讼背景下如何运作。
因此,可以理解,联邦宪法法院及其评论者如此频繁地转向雷利审判[312]作为解释对质条款的导向,并招致广泛的批评。这似乎是一个安全的推断,即如果18世纪的美国人对对质条款有所期待,他们希望用其避免诸如雷利审判中的权力滥用,至少在联邦最高法院。而类似的论断亦适用于《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制定者及批准者:如果说他们对对质权有任何判断,那也是认为此一权利可以防止发生在雷利身上的事情。如果探索对质权条款的原始理解被视为毫无希望,或者脱离主题,则可枚举一个极佳的例子予以解释,即在英美法史上对对质权条款臭名昭著的否认。这肯定可以告知我们长期以来在雷利案件这一明显不公正审判所反映的事物。无论是作为一种原始理解的证据(Jed Rubenfeld称之为“奠基性的范式案例”的“核心、准确适用”[313]),或者是作为经历时间考验、传统惩罚的违反对质的案例,[314]雷利审判均可明智地被用来推动对对质条款的理解。
诸如任何范式案例,雷利审判本身需要注解。我们需要精确地研判问题出在哪里,从实践的目的考虑,我们应该怎样构建一个新案例以避免发生于沃尔特·雷利爵士身上的悲剧重演。[315]国王将科巴姆勋爵作为控方证人是否便是失败,或者当雷利要求在法庭上与之对质时国王拒绝如此为之?我们应需要何种类型的“对质”:经宣誓的交叉询问、在法庭上面对面的会见、雷利与科巴姆进行辩论的机会,自由的或无组织的,或者这些程序的某种结合?对质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科巴姆提供了指控雷利的关键性证据,还是因为科巴姆受王室监禁,或者是因为科巴姆据说已撤销了他的指控供述,或者仅仅是因为科巴姆提供的论述可以用于指控雷利?
遵循并扩展威格摩尔的引导,联邦最高法院在最近的对质案件中通过反职权主义的论点审视了雷利案件。如果说雷利的遭遇反映了对英国刑事诉讼职权主义特质的谴责,则雷利的对质要求毫无疑问应该是须经过交叉询问,这是英美法审判中最重要、最著名的特征。毫无疑问,这种自由的、面对面的争辩在欧洲存续的时间比在英国长。[316]因为普通法刑事审判长期以来均被视为以坚持言词性的证人证言为特色,因此不像大陆法系审判中立足审前便已做好的书面卷宗材料,雷利案件中所论及的对质权仅是因为立足书面证据而非言词证据。故侵害对质权的事实已然产生,无论雷利是否请求将科巴姆带到法庭,无论科巴姆在审判时期是否被王室监禁,也无论这一证据至于控方案件又如何重要。
放弃反职权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将雷利的审判作为适用对质条款的典型案例,但这意味着应该重新审查联邦最高法院对案件所作的注释。这意味着应重新审视究竟是什么令与科巴姆的对质变得重要,以及应进行何种类型的对质。回答这些问题均需要明确联邦最高法院在最近对质权案件中几乎完全避免的:讨论对质的潜在目的。有意义有必要的对质类型以及场景部分取决于对质的关键点,即正如联邦最高法院时常说的,它是否是确保准确性的一种手段,[317]或者正如联邦最高法院有时所论及的,它是否为防止政府权力滥用的方式,[318]或者它是否为尊重最基本的公正。[319]
这里我不会继续深究这些问题,但我要说明的是,将“准确、简单和明了”作为对质条款的目的,在更小的范围内可部分重述什么令反职权主义作为更广泛的宪法解释策略变得毫无吸引力。在宪法一般性原则框架下,我们普遍想要的是,作为宪法性原则它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作为在正常民主政治范围之外的一种法律主张。在这一方面论述某些原则最普遍性的正当依据便是,它们(宪法性原则)对于每个民主自治政府的方案至关根本,或者它们反映了选举政治可能低估的价值。避免欧陆审判程序并不意味着便是符合前述两者,除非欧陆程序被认为特别适合于专权滥用,或者特别或错误地吸引民主多数派。同样的事物同样可被认为在刑事审判中需要对质。如果不用对质的问题仅是审判可能没那么准确,那么我们很难理解,为何这一问题(对质权)将提升至宪法水平。准确审判是民主多数派普遍所热衷的。但如果对质的起点是防止一定程度的不准确,以及防止专制权力的滥用,则很容易看到这是为何这一机制需要上升至宪法层面予以保护。专制滥用工具可能也可能不吸引民主多数派的关注,但它们肯定对政府官员(无论选举与否)有吸引力。将对质权重新塑造为保障公正、反对权力滥用的机制,而摒弃反职权主义虚饰的权利,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这一权利的一些特质。这同样也可能令该权利更为可靠,不仅仅是因为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它有意义。(www.zuozong.com)
如果联邦最高法院停止将欧陆刑事司法制度作为“阴影”(shadow),含糊地将其界定为“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一套程序,[320]它可能注意到欧洲人权法院出现的对质判例。已有十余年,欧洲人权法院将《欧洲人权公约》的公正审判条款解释为,作为一个一般问题,证据“应在公开的庭审中提交,在被告在场的情况下”,并且“被告……有充分、恰当的机会向不利的证人挑战或提问,或者在其提供供述的时候,或者在之后的诉讼阶段”。[321]
欧洲人权法院赋予刑事被告这些权利及其他审判权利的内容,便采用了与联邦最高法院完全不同的方法。欧洲人权法院并未通过使用一个反面的程序模型(一个对立的、不言自明的低级法律系统)来界定这些权利,而是通过审理来自普通法系及大陆法系管辖权内的案件,将这些权利定为最基本的权利,无论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均应遵循之。
在起草欧洲人权法院解释和适用的《欧洲人权公约》时亦使用了相同的方法。[322]美国法学者可能感到惊讶,《欧洲人权公约》竟然赋予刑事被告“审查或令人审查对其不利的证人”的权利,[323]欧洲人权法院结合《欧洲人权公约》中“任何人有权获得独立、公正的法院进行公正、公开的审判”[324]这一包罗万象的权利对对质条款进行了解释,为“对质”提供了广义保障。[325]这一保障(对质权保障)被发现是受限制的,例如当提供消息者被询问,但他们的身份未向辩方说明,[326]而声称受儿童性虐待的受害人系由警官而非司法官进行询问。[327]
对于一位美国读者而言,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对质的判决甚至比联邦最高法院在克劳福德及戴维斯案件中对“言词证言”和“非言词证言”供述之间所划分的界限更模糊。[328]欧洲人权法院很少论及什么是对被告不利的“证人”[329]以及何为“充分”对质的机会。在此之上,欧洲人权法院解释道,仅在“视为整体的程序”不公正之时,[330]刑事诉讼控方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因此,仅当有罪判决“决定性”地立足于未经对质的证人证言,对这种结果联邦最高法院方视为违反了对质条款。[331]这一限制意味着非常强势的无过错规则,正当依据不足。[332]
所有这一切都是说,从欧洲人权法院在对质领域判决所获得的指引仍有限,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质上的判例仍应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中获得启发,应当比现有判例更为合理以及更有说服力,而不是如同现有判例根植于对欧陆刑事诉讼作夸张描述。这可能也会成为更加理性的结果。因为欧洲的对质权是确确实实的程序权,而非证据可采性规则,[333]它并不是说明已死亡或其他未出庭的证人所作的庭外供述的可采性问题。换而言之,它并不要求时下在美国很强势的传闻证据规则,这事实上在世界其他国家并不存在。诸如吉尔斯案件,不承认被谋杀的受害人在她被杀前向警察的控诉为证据,[334]这在欧洲人权法院中是不可想象的,[335]对于此,或者是在它所管辖下的所有成员国法院。[336]同样很难想象,这些法院会很难决定是否承认一位已死亡病理学家所作的验尸报告。[337]拒绝使用被谋杀受害人的供述,或者不再能出庭作证的病理学家所提交的验尸报告,这是某种违反直觉的结果,易于成为美国捍卫的当事人主义的重要部分,反映了我们对职权主义司法的排斥。但也因为它是反直觉的,这可能也是我们宪法犹豫作出强制规定的结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