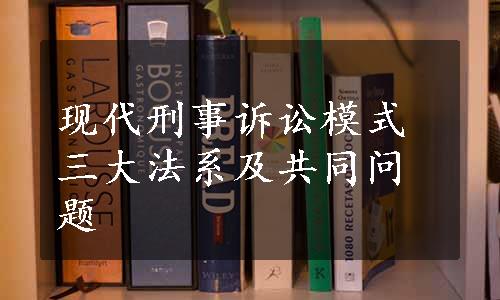
我假定,任何社会结构,即便是最原始的社会结构,都是一种法律结构。因此,法律秩序独立于立法者、法官、法学家、法律作品甚至是言词交流而存在。[64]
依我所提出的动态的、不以西方为中心的分类法,法律系统可分为三种主要法律模式:依专业法律而治的法系,[65]依政治法则而治的法系以及依传统法律而治的法系。这三种模式与主要的社会组织系统(及/或者带有强制性的系统)一一对应。
在此一背景下,本文所使用“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这一术语系广义上的,指对社区日常生活中所有社会互动的管理。这些受管理的“社会互动”包括社会个体成员间的互动,也包括个体与机构间的互动。此外,“组织”不同于政府,前者负责日常生活的低层次规则,后者则负责高层次的决议。[66]我们可在结构层面或者通过解读违反规则之病理来分析组织规则。
第一个假设是西方中心主义不能成为全世界法律系统分类的基础。为达致学术目的,任何分类都必须考虑各种社会组织模式间深层次的区别。迄今为止,大多数的分类都将西方法律传统置于主导地位。此一做法为时下的人类学研究所反对,应予以摒弃。[67]
此外,依法的独立性,试图在学术上为西方法律传统中心主义寻求正当性的法律秩序统一论观点已受到严重质疑。[68]对于“真正”的比较法学者而言,除非研究者意识到其所研究的法律系统具有结构的层次性,否则任何法律层面的评论都不具有分析价值。此一点毋庸置疑。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正迈向法律秩序多元化的观点,而反对被凯尔森(Kelsen)奉为典范的法律秩序一元论。后者依然影响着时下的法律系统分类。
“法律共振峰”的多元化是所有法律系统(从最基本的到最复杂的)的共同特征。据此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法律多元主义自身不能成为区分某种结构法律系统所属宏观比较法系的依据;[69]其二,对于多元化较为明显的法律系统,即便不将其处于优先西方法律传统的位置,但至少也应获得平等的地位。对此类法律系统的研究可揭示掩藏于西方法律传统之后[70]但仍在西方法中发挥作用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来探查这些现象。[71](www.zuozong.com)
把这些现象运用于宏观比较法领域,我们能够看到持续增加的法律移植现象将这些论述运用于宏观比较法领域,我们可以发现不断增加的法律移植现象是如何促成采用三分法这一比以往分类更深层次的标准。我的分类法以正式制度确立前便已存在的标准为基础。这一标准不受因偶发事件而推动之短期改革的影响。此外,一如前述,我所确立的分类法并非僵化的。时至今日,源自西方法传统的要素在所有的法律系统中均存在。[72]例如,尽管苏维埃学者宣称(也一直在宣称)其制度具有独立性,[73]但其也承认罗马法的重要性。又如,一位缜密的学者不会将日本法列入西方法传统的子类型,因为此一分类仅限于日本法的现代图层,这限制了研究方法的有效性。[74]
我所倡导的三分法承认不可能达致完美、严格的分类。[75]三分法立足“主导”理念,承认每个法系都有一些特征亦是其他法系所共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法律系统都是混合的。因此即便在英格兰(依专业法律而治之法系的发源国),倘若审视其司法职业模式,依然可发现依政治法则而治的痕迹。[76]此外,在西欧,除基督教理念发挥重要作用的婚姻家庭法外,其他法域依然存在某些传统法则或宗教法则的痕迹。[77]在特定的环境下(如中国、伊朗、巴西以及一些非洲国家),我们很难区分政治法则和传统法律。[78]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在讨论日本法时将重心置于政治结构而非传统理念。在伊斯兰国家,专业法律与传统法律之间的关系也相当不稳定。[79]
但在学术研究中,归纳和分类是不可替代的研究方法。没有归纳和分类,我们就无法应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归纳和分类仅是达致目的的手段,也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强化我们对法律系统的比较理解提供概念框架。
我所提出的分类法的主要贡献在于它的分析框架。依此一分类法,同一法系内的各个法律系统因其结构差异程度小而很容易进行比较。例如,西方法传统下的合同法很容易进行比较,因为市场经济相对类似。但如果未事先考虑根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要素,则此一论断不能跨法系推及(如德国法和中国法)。如果我们考察实践中的法律,则会发现中国法虽也承认受德国法影响的“法律行为”理念,但这并未使中国合同法与德国合同法趋同。此外,同一法系内的各个法律系统也共同面临一些问题。例如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即法律系统的正式层面受德国法影响,但其潜在亦受儒家秩序及权力观念的影响。[80]
我最后用寥寥数语来说明“依政治法则而治”的意义。在西方社会,法律决定的形成过程往往融入了许多政治因素,例如堕胎或反歧视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政治议题。托克维尔(A.De Tocqueville)早就意识到,较之于法国,美国的许多政治问题都需要由法院来解决。通过法院的处理,政治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81]但政治问题虽可通过法律话语及修辞得以解决却未曾改变。这些热门的政治话题并不是法律的日常运作规则。一系列批判性的史实证明,美国的法院并非完全中立,而总是偏向正在崛起的资本家阶级一方。[82]但我们始终无法提供有力证据以证明(在美国)存在法官与政治权力机关(受经济力量掌控)政治结盟的模式。穷人权利被践踏,富人权利得以彰显。尽管在洛克纳(Lochner)时代可发现此一结盟确实存在,但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法院填塞计划(Court Packing Plan)在政治舞台上陡然重新诱发了法院和政治力量的对抗。[83]在政治法则占据支配地位的法律系统中,日常的裁判进程受政治需求的影响。政治力量与法院的联盟(或者法院屈服于政治力量)是自觉的,且以更高利益的名义理论化。此一利益不受特殊个人权利判决的影响。这样的例子很多,下文将加以谈论。埃塞俄比亚的德格便是一范例。[84]同样,受芝加哥影响的智利经济奇迹使得此一机制(政治法则之治)吸引了许多观察家。[8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