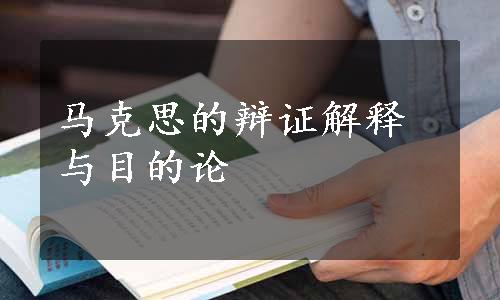
尽管马克思意识到目的论论证当中的问题,但我们却不一定能得出结论说,他拒斥一切目的论解释,或者他无法在目的论的领域内来去自如。不管马克思是否提出过能够被视为目的论的观点或者是提出过已经被视为目的论的观点,他那么去做的方式却不是批评人士与支持者通常以为的那样。[28]虽然我们拒绝对马克思思想当中的历史目的论所作的传统阐释,但在他的著作当中,也确实留下了一些要素,它们引发自我导向的、终极主义形式的因果推理。如果我们要更为全面地了解马克思的进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我们必须具体说明这是怎么回事,这与传统的目的论进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如果剥去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话,那么自我导向和终极主义的因果框架也许还是有用处的。许多人经常假定马克思的用法没有通过这个测试。最为常见的观点是——马克思将历史和共产主义描述成形而上学的和不可避免的目的论——这不是对其思想唯一的目的论解释。此前,卢卡奇(1970:162)就解释道:
……通过劳动,一个目的论的目标在物质的现实中得以实现,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客观性。因此,劳动在某个方面成为所有社会实践的典型。归根结底,劳动总是物质性地实现了目的论的规划——哪怕是通过最宽泛的中介才实现的……[因此]劳动能够充当理解其他社会性规划和目的性规划的典型,因为劳动从本质上构成了它们的基本形式。
在区分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观点的时候,鲍尔(Ball)(1979:471,474)同样认为“马克思的人文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带着激进的……目的论意涵:人类改变自然——并因而根据自己的意图和目的间接地改变自身……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历史的目的论与自然历史的目的论是不同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最多只适用于类人猿,适用于自觉的自然的历史;它不适用于人类历史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类自觉地改变自然和自身”。最后,梅萨罗斯(Mészáros)(1998:420)也看到一种能够让马克思的思想充满活力的目的论形式:
事实上,如果没有某种目的论的话,人类历史就不可索解。不过,唯一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相一致的目的论,就是劳动本身那客观的和辩证的开放性目的论。在根本性的本体论层面上,这样的目的论与人——这个独一无二的“自然的自我中介的存在”(“self-mediating being of nature”)——通过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来进行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的方式有关。(www.zuozong.com)
劳动过程同社会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因而肯定会面对自我导向的和终极主义的问题,就此而言,卢卡奇、鲍尔与梅萨罗斯是正确的。虽然应当推进他们所指出的研究方向,但这些构想依然是有问题的。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将他对劳动的所有分析纳入到一个关于“历史”“社会”或“人类”的未经区分的概念框架中去,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人类社会关系当中,围绕着劳动这一问题的因果关系却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马克思因果推理的转换,就取决于他的制高点是涉及个体层面的劳动、社会阶级层面的劳动斗争还是一般社会层面上的历史发展了。他的这种区分同自然科学家对目的论的区分是相似的,自然科学家的区分,是取决于将目的论运用到个别有机体层面、繁殖种群层面或整体性的物种层面。
虽然卡罗尔·古尔德(Carol Gould)(成问题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形而上学,但她(1978)解释道,对马克思而言,个人的人类劳动是一个涉及自我导向和终极主义的进程。在劳动过程中,个人在头脑中想象出了需要达成之结果的形象,并将自然对象转化成这个预想的目的。目标指引着进程到达终点。不过,在社会层面上,相较于任何一般性的运动、形而上学或其他的普遍主义而言,物质事实和阶级斗争更好地解释了劳动对象的积累,作为结果的劳动分工以及/或者全部社会形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未来针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斗争而形成的制度性或结构性配置的功能性作用,可能并非是当下的实践、制度以及/或者它们的功能首次出现的理由,比如说,金钱不是为了在未来实现资本积累才在过去出现的。正是针对劳动条件以及劳动产品方面所开展的实际斗争,让人们洞悉阶级动态、政治、历史和社会变革机制的本性。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类社会需求,劳动因而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社会关系所涵盖的人类行动者之形状的最初假设。就其本身而言,在牵涉到自我导向和终极主义之实际形式(并非形而上学)的个人层面上,劳动是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层面上,这些形式则变得越来越具有偶然性了。
作为一种解决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阶级斗争的办法,马克思希望共产主义的潜在性在阶级层面上能够是自我导向的,一如劳动在个人层面上是自我导向的那样。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应当始终如一地把对未来目标的愿景与忠诚作为当前政治斗争的方向性路标,从而将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在阶级斗争政治中,马克思认为,向共产主义做社会主义的过渡的革命理念——应当指引行动,这一革命理念本身,就是通过对当下的科学分析以及对潜在的未来可能怎样、能够怎样的愿景而得以形成的。没有什么会保证工人阶级所致力于的斗争(即便是在所难免的)会具有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形式的特征。共产主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取决于工人阶级能否改变政治—经济信念,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写下《共产党宣言》,乃是因为工人并不单纯是由于反映了物质力量(这是形而上学的立场)才具有阶级意识的。组织、教育和行动都因未来可能的愿景而变得生机勃勃,它们都是必需的。在人的劳动和阶级斗争这两个问题上,马克思采取了目标导向的话语形式。无论如何,他的辩证使用方式都是调节式的和定性式的,前者是必要的关系,而后者则是一个偶然的过程,它们都不是形而上学的用法。
自我导向和终极目的论的框架不会外延至诸如整个历史或社会这些更加宽泛的抽象上去。虽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结构的趋势会迫使其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但人们不能预见其确切的未来。由于人类行动的创造性和自觉的方面,再加上与“偶然性”相结合,同人们能够预测自然科学的准确性不同,人们不能预测历史未来的轮廓。无产阶级革命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考虑到马克思假定资本家(正题)会招致他们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出现,从而导致合题或者变革(革命和共产主义),对于辩证法正题—反题—合题的误解,致使某些人相信,马克思视共产主义为必然。马克思以如下言辞批评了这一公式(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他并没有看到超人类的目的论进程,这个进程自动地将正题转化为反题,然后再进入合题。在历史层面与社会层面上的目的论模型总体上与马克思的思想是对立的,因为它们都表现出思辨的以及/或者形而上学的进路,从而是非科学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