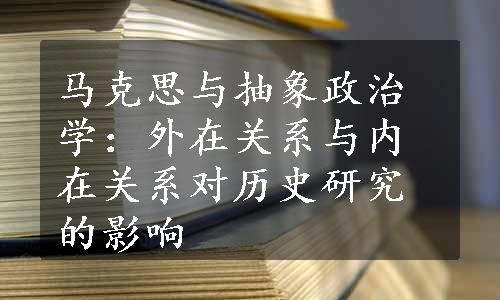
人们可以选择两种分析社会现象的宽泛进路。其一是外在关系进路,该进路将世界视为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作用的部分的聚合体——最常见的是具有功能(例如社会化、商品生产和劳务生产、道德教育等功能)的各种制度(例如规范性法则、家庭关系、经济组织,宗教实践等),以及具有特质(例如收入、态度、技能、价值观等特质)的个人。这种进路将这些部分阐释成彼此间具有偶然关系的事物,是作为社会事实而在不同社会地点上形成的聚合体(即形成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聚合体——互动、家庭、职业、网络、国家等)。这里的因果关系是一些社会事实“碰撞”到其他社会事实的结果。当社会事实“互动”了,研究人员就测量其变化的程度和变化率(通常是统计上的),并将这些相互作用重新构成因果链。
这种观点好像掷骰子一样,骰子的侧面(两个骰子或更多骰子的侧面)代表了某个制度(例如家庭、宗教、经济等)、某段时间(例如月、年、时序等)、某个空间(例如面对面交往、邻里、地区、国家等)以及/或者制度化的行为(例如交往规则、性别角色、尚武精神、似然民主、威权主义等)。随着可能的掷出次数的变化,其结果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便是因果关系(这一描述并非是在说,所有结果都跟掷骰子一样是等价随机的;社会生活并不是一桩风险事业,而且往往一般社会学的确也承认这一点)。随着更多的变量(骰子的各个侧面)及其关联(碰撞及其交互式结果)被定位下来,研究人员将各个部分的效应以及理想类型的效应概念化为抽象的措辞(例如流动性、冲突、政治立场和婚姻满意度等),而且在将变量—概念编排为描述性框架、解释性框架以及/或者类型框架的时候,去考察经验性案例。
内在关系进路可以考察与外在关系进路相类似的经验领域,但内在关系进路却将处在社会现实之间和之内的关系和过程当作优先型变量。外在关系进路将聚合体视为由单独的部分所构成,将这些单独的部分加和,就建构出了现实,但内在关系进路却首先将现实视为总体,它需要我们从思想上将其分解为可供研究的部分(参见第三章)。在这种观点当中,部分并不是作为事物而首先存在,然后社会整体再从这些事物间的相互作用中显露出来。相反,人们是以这样的假设开始的:将概念化的变量视为从总体中抽象出部分这一精神行动的产物。因此,内在关系进路的起点并不在于将社会现实的部分视为事物自体,并将它们重组为相互作用的因果链,而在于将现实分解为历史以及现实所包含的诸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历史和诸社会结构都把自己当成对方的部分,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着的、暂时而系统的运动。内在关系观点不把结果当成由外在而独立的东西构成的偶然事件,而是认为微观制度、中观制度和宏观制度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形成中的和成熟中的关系,上述制度当中的这种内在连接改变了制度性的关系,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制度内部、制度之间乃至制度与更大制度间的强大力量。随着制度本身的变革,从一个制度变为另一个制度,其结果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这以结果是由现实的人在对立的社会关系中所卷入的现实斗争所驱动的。
为什么将关系与过程作为优先考虑的主导变量而不是将事物当成主导变量呢?如果研究从假设现实是事物构成的聚合体为起点的话,那么,就需要研究人员从显而易见的周遭世界开始,在这样的世界中,社会现实之间的各种联系就变成了意识的断层。如果社会探索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地掌握具体表达中的真实人类存在,那么,比起直接而表面的存在层次而言,人的历史发展和它的形式范围起码是同样重要的,或者说,更加重要。从假设人的生存是一个总体开始,便会马上将历史及其社会形式的范围这些问题带入我们的视野。尽管人们不会在这样一个宽泛的层面上终结自己的抽象和研究,但将关系和过程作为优先考虑的主要变量却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好地掌握历史和它所涵盖的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当外在关系进路和内在关系进路成为解释孰者最为优雅、孰者的解释范围最大的竞争对手时,它们就没那么矛盾或者是没那么针锋相对了。尽管它们并没有相互排斥,但各个方法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虽然内在关系进路并未优先考虑事物,但在寻求理解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关系、整体与部分当中的非对称性决定的时候,这一进路的确承认了它们的存在,用恩格斯(1980:476)的话来说,这一进路认识到“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原文着重)。当研究人员接受表象的层级时,也就是说当把关系当作物去把握的时候,整体的观点就变得不那么完整了,甚至是歪曲了的了。
至少是在社会学中,发生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是,“物”设定了明确的界限。当这种方法被带入对制度性世界的理解时,诸如家庭、经济、统治、教育等等这些也就显得是彼此独立的和各自离散的。然而,正如马克思(1973:278)解释的那样:
这种有机制度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www.zuozong.com)
在这里,马克思反对在同一个制度内将诸社会现实视为(本体论上)独立的和静止的物,并且罔顾其历史发展的看法。尽管社会学家经常将制度视为无形之物,就仿佛“宗教”“经济”“政府”和“家庭”都是从远古时代起(就算不见于绝大多数社会学著作,这也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很多社会学著作中的策略)就作为独立的制度(即便是相互制约着的制度)存在了,然而,制度领域的明显分离是现代发展的一个产物,它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如果今天显而易见的、正式的制度领域独立不是像蜂巢中的蜜蜂、堤坝中的河狸、水流中的鱼儿那样,乃是自然的产物,那么人们就不应当根据这样的假设建立起一般社会学。如果从认识论上讲,这个假设会转而在变量之间划定离散性的界限,那么,这样一条进路就在远非必要的程度上重塑了我们关于现实的观点,这种非必要性甚至达到了支持畸形概念的地步。
马克思将体制领域的独立看作历史的发展,而且并未假设在这些制度领域的内部和制度领域之间具有稳定性或相容性(后面那个制度领域不是独立存在之实体的观点与社会学的许多传统相冲突)。进一步来说,对马克思而言,对立并不是简单的逻辑谜题。马克思(1988a:99)说,我们必须这样去思考一个关系:“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原文着重)。在正常运作下,某一关系中的两个对象均产生出相互依赖的关系,但同样也导致了对抗、冲突和否定的时候,这一关系中就存在矛盾了。当常规社会学家将部分与和包含着部分的整体视为独立的物时,哪怕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能看到矛盾,即便他们认识到变量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矛盾也还是外在于他们的变量的。马克思将社会关系置于彼此的内部,彼此关系当中的变化常常是由关系中的矛盾所驱动的,对于关联着的各个部分的内在联系而言,变化是必需的,它并非是由于部分之间的碰撞而形成的偶然事件。马克思也预设了因果力量(causal forces)当中的不平等,在这些因果力量中,如果一个关系比其他关系更能决定结果,那么就要在研究、建模和理论构想中优先考虑它。制度内的主要关系之间、跨域历史的主要关系之间以及各主要关系的内在联系当中,存在着不对称的和矛盾的内在关系,因此马克思的研究路径将这些内在关系优先化和内在化到自己的概念当中去。
诸如一家公司对于资本的具体体现,有鉴于公司与制度中其他基本部分之间的内在关系,因而一家公司这一体现至少包含了处于萌芽阶段的、整体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关系,例如私有制、商品生产、分工、剥削关系、工资、劳动纪律形式、贸易形态以及法律规定和法律关系。此外,资本之间的这些关系也延伸到其他社会关系、制度与实践中去:“关于工场内部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所谈到的这一切,也适用于社会内部的分工。”(Marx 1992b:456)那么,马克思的观点就看到了在部分与整体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人们并不被要求去专注于此类事物来发现模式化了的社会现实,不过,不能专注于这类事物却局限了我们的眼界。于是,任何社会科学家的认识论问题便都是如何从社会现实中发掘出分析的单元,认识要包括什么、要排除什么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做出决定。从观念上讲,勾绘边界当中的程序应当使操作性的本体论假设与所产生的认识论框架保持一致,这就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形成了内在关系,在参照马克思的进路的时候,怎么强调这一点都是不过分的。
埃米尔拜耳文章中的张力源自它处于内在关系进路与外在关系进路之间。一方面,显然他对上面曾概述过的外在关系的一个版本予以问题化:“事务性进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术语或单元之间的关系视为在性质上格外富有活力的关系,好像是展开的、正在进行中的过程,这样的关系不是惰性物质之间的静态关系。”(Emirbayer 1997:289)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替代性办法是:仅仅以部分之间具有动因和变化这种设定去填充模式,其中,部分并未被概念化为在本体论上彼此独立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些部分是具有(简单的)交互关系的外在实体。虽然这一进路比静态的进路更贴近现实,但却未能从概念上将彼此内在的社会对象内在化,它只不过是将静态的外在关系替换为动态的外在关系,这种做法将变化的过程转移到更为切近的观察点,但并未改变概念化对象本身的基本性质。
此外还很重要的是,埃米尔拜耳将本体论从认识论中独立出来的探索却将矛盾的问题弃置于对象—边界的概念模式之外。我们对任何社会实在的研究都是将其从环境中独立出来,而且不管如何简洁,都是通过抽象过程进行的。这个行动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公认做法,即承认诸社会现实在时间(历史)和空间(结构)之内的场所中实现其全部意义。这意味着,任何社会现实都必然与其他社会现实具有内在联系。如果社会现实具有矛盾的特性,那么本体论和认识论必须能够在矛盾特性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上应对它们。尽管可能很是不错,但将“动态”“流动”或“变化”优先为基础性的本体论却推进得还不够远。它仅仅允许在静态的概念和变化的概念之间进行选择,从而导致在概念化之后才进行分析。但为什么应该不选这个就选那个呢?虽然人们能够优先考虑静态或优先考虑变化,并给出如此这般能更好地抓住现实(根据暂时性框架来看,这会是真的)的例证,但是,更好的办法还是在基本的关键社会关系性质上建立起本体论,即在那些处在社会现实核心的关系和过程上建立起本体论。通过将劳动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具决定性的特征,马克思的进路为外在关系进路所遭遇的问题提供了答案,这些问题进入到埃米尔拜耳所主张的框架当中,它们还导致了埃米尔拜耳与之缠斗的认识论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