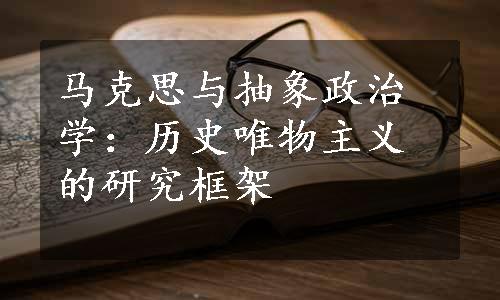
马克思相信,我们必须从经验观察中来发掘出抽象,在他的(1975f:63)博士论文当中,他批评了这样的进路,其中“从本质世界中排除掉的时间,被移置到进行哲学思考的主体的自我意识中去,但却与世界本身毫不相干”。因此,社会结构是诸如“我们必须……认识一般条件对当事人意志的巨大影响”这样的行为模式的创造者,在这样的模式中,行为不能被“仅仅看作上述一般条件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现……”和“当时的强制力量”(Marx 1975g:353-354;原文着重)。[11]虽然这个说法与涂尔干(1982)对社会事实的特征描述很相似,但马克思却又进了一步。在1845年写就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提纲第七条;Marx 1978d:145)马克思的研究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一般社会学。
恩格斯将他和马克思所提出的框架称之为“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与不少公式化的处理联系在一起,所以比起考虑得没那么周到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词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用法更加常见也更加合适,然而这个术语既不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也不是恩格斯提出来的。对于当前的分析而言,我们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我们在历史性的社会制度中所发现的社会规律的考察,例如劳动的主要地位、物质力量和阶级斗争在结构—历史变革中的作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以及国家的起源。在这些变量中,有一些适用于人类的一般层级(例如,从第五层级贯彻到第二层级的劳动主要地位),而其他变量则严格地适用于阶级制度的历史(例如,第四层级和第三层级中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并非静态的先验原则,而是要寻求历史与结构、物质与观念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虽然人类历史和知识既与人类劳动密切相关,又与有关人类劳动的地位和产物密切相关,因为当劳动条件发生变化时,其因果变量的质也就发生变化:“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Marx 1973:88)从这个制高点来看,人们不能假定一个研究环节中的变量会在另一个研究环节中保持所有的相同品质;我们必须注意到,系统中的这些变量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内在变化:“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Marx 1991f:354)因此,作为其自然主义的延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分析运用了历史社会形式的对照比较。例如,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我们发现了对“罗马人的政治制度和私有财产之间联系”的历史分析(Marx 1975c:110-111),这一分析用比较方法去“强调了两种情形,它们与在德国人中所得到的情形不同”[12]马克思的对照比较发现,表面上的社会形式通常包含着实际的具体历史差异,这就避免了普遍的抽象定义、单一化和彻底化。因此,如何、在何时以及用何种方式控制变量就是重要的问题了。[13]
虽然马克思从未写过有关方法论的长篇论文,但是就这一点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却以最为系统的方式陈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进路: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Marx and Engels 1976:36-37)
虽然人类的知识有着通过诉诸意识形态动机以及/或者普遍原则来解释人类具有社会组织形式的显著倾向,但马克思和恩格斯(1976:37)则开始研究“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这个观点需要一个次级规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想去论证每个人的思考、信念以及/或者作为,不过是物质条件的反映,仿佛人类无非是自己周遭环境所锻造出来的机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更广义的层级上提出了一般性的社会规律。也就是说,他们的陈述处于这样一个层级,其中,他们所提出的规律的力量在更特殊、更具体的细节方面(也就是在较低层级上)有着较大的变数。向后退几步——回到将一个时代视为一个时代的层级上去——辨别出法律、思想、观念等的一般模式,辨别出物质条件是如何塑造它们的,这些事情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因此,马克思的研究以如下假设开始:人们无法自由地选择出生的境况,他们是固有的社会存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社会的固有产物。因此,观念论只能是次要的(甚至是第三位的)关切了。(www.zuozong.com)
马克思越来越多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来进行他那更为突出的政治—经济分析,尽管在他的早年著作中,这些晚期研究的形式还未完整地出现。高度成熟的政治经济学必须要等到《共产党宣言》以后才出现,《共产党宣言》可被视为某种类型的过渡,将马克思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它既宣告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分析的变量,又宣告其是政治话语的对象。在《法兰西阶级斗争》(1848—1850)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1869)中,在将阶级分析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的时候,马克思提高了他的历史研究能力,在《法兰西内战》(Marx 1870—1871)当中,他展现了自己的社会—历史敏锐性并向其回归。在这两个时期之间,他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其中的《序言》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而将他的主要思路归在一处。这些众所周知的陈述值得重新审视。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社会生产”生产出“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一关系“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Marx 1911:11-12)
虽说马克思的《序言》表面上看上去是政治经济学的开端性工作,但《序言》却并非是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陈述,而是如恩格斯(1980:469)所解释的那样,它讲的乃是:“历史的唯物主义概念”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基础”。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陈述,《序言》包含了制度内在变化的假设和制度之间变化的假设。它的两个主要原理是:(1)物质基础是影响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主要变量;(2)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导致社会发生内在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将变成新形式的社会。在《序言》中,马克思告诉我们: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要求,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所吸取的教训得以发挥作用,《政治经济学批判》首次对其进行了系统而公开的表达。[1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