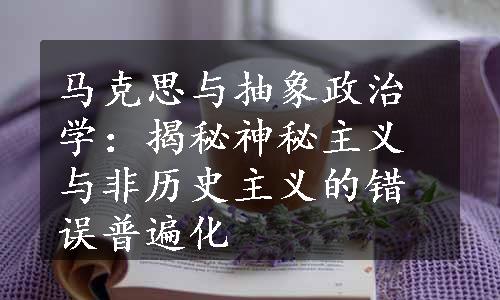
马克思(1975c:12)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黑格尔的“典型特点”是“神秘主义的产物”,也就是一种从根本上曲解探索对象的概念化。在稍后不久的1844年的《德法年鉴》这部作品中,马克思(1975l:144)论证了“分析对其自身而言都难以索解的神秘意识,不管……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政治的形式”。马克思同样警告安年柯夫(1846)不要“发明神秘的原因”和“夸张的表达,例如普遍理性、上帝等等”,不要“永恒真理”,马克思将这些东西描述为“里面没有常识的措辞”(Marx 1982b:96)。
由于神秘主义的知识误解了怎么去分析现实的问题,所以除了某些偶然情况以外,由它开启的知识无法产生出有效的结论。也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1976:28)断言道,黑格尔的传统“不仅其结论,甚至其问题都是神秘化的”。对马克思而言,任何形式的错误推理,不管它是关于抽象观念的还是具体生活条件的,都歪曲了我们所必须掌握的现实,并因此生产出不能让人信赖的知识。
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也就是对不可见的、无法触及的、超越历史的和自动的力量的断言——这是一类形式的神秘主义。按定义来说,超历史的力量超越于时间和空间,是一种必需的形而上学构想,它假定了“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Marx 1982b:102)。如果一种社会力量要么有起源要么有发展,那么它就不是真正超历史的了。进而,自动的力量按其自身的逻辑发挥作用,外在于人类的能动性。任何建立在这样假设的科学,都有赖于不可证伪的断言而不是对资料的搜集,其证实也不过是为了确证它所声称的真值罢了。
马克思在很多地方反对形而上学。在1846年与安年柯夫的通信中,他批评了那些进路,在它们那里,“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Marx 1982b:100)。形而上学并不局限于黑格尔的理论辩证法抽象。在马克思(1992c*:28)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在他们对社会的—辩证的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如果假定社会进程中存在着与之相同的、普遍法则式的规律性,那就不对了。[2]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Otechestvenniye Zapiski)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1989a:200)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还拒斥了如下阐释,即“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如果我们还把马克思在1837年与父亲的通信包括进来的话,那么这种反对形而上学的观点纵贯其一生,超过了40年。(www.zuozong.com)
形而上学命题认为,一切历史都可被视为通过无时间的、自组织的因果与存在范畴所构成的规律而得以展开,如此一来,形而上学命题也就趋向于非历史主义。形而上学地讲,历史是一个事物,而非许多事件。在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视野中,历史包括了一系列处于变革之中的社会关系,并伴有意外的和毁灭性的偶然力量。例如,“财产问题的表现形式极不相同,这是同一般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各国工业发展的特殊阶段相适应的”(Marx 1976b:322)。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中创建了共同的事业,然而马克思还是批评他,因为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着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Marx and Engels 1976:41)。这是由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彼此隔绝:“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Marx and Engels 1976:40-41)当历史唯物主义与/或者历史主义无法结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就用抽象的形而上学命题将自己的主题神秘化(后文有更多探讨)。
这些关注点从马克思对传统辩证法的批评扩展到了他对同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上。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式观念论者的观点是“并且仍是未被领会的,因为它们没有从特定本质去被领会”(Marx 1975c:12)。马克思(1982b:97)将该原则运用到蒲鲁东身上,蒲鲁东“觉得没有必要谈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由此,马克思(1982b:100,102)论证道,蒲鲁东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错误地将其“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而“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马克思(1847:116-117)同样在《哲学的贫困》中批评了自“时间伊始以来”就存在的“不变规律、永恒原则和理想范畴”。
非历史主义的问题可不是单纯地将某个人的抽象过于宽泛地运用而已。它同样有一个政治维度。马克思(1975c:83)在其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黑格尔哲学中神秘的东西”在于它“不加批判的、神秘的阐释方式以及对新世界观而言的旧世界观”(原文着重)。在一个向前铺陈开的世界当中,建立在当下物质现实上的概念也许不但无法充分地掌握过去,而且会将物质条件使其得以存在时的概念误解成永恒范畴,这就错误地描述了当下的历史环节,反而将其当成了普遍的、必然的社会关系的表达。其结果就是,把对现代社会关系的描述视为自然的形而上学产物,以科学的新装将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乔装打扮一番,去为当下的权力关系进行辩护。[3]因此,其政治功能也就不仅仅是建立于概念之中的偏好了。它延伸到社会实践中去。如果当下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表达了超历史的社会事实,那么,对其进行批评并展开对抗行动就必然是天真而不切实际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