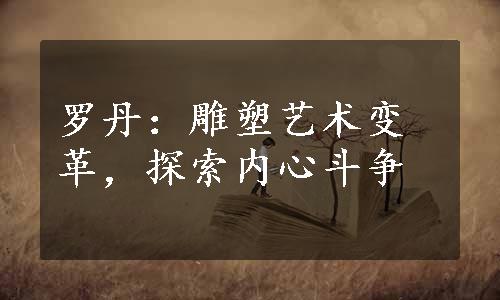
熊秉明
熊秉明(1922—2002),法籍华人艺术家、哲学家,中国数学家熊庆来之子。毕业于西南联大,后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旅居法国50年,被评为法国教育部教授,曾获 棕榈骑士勋章。熊秉明先生集哲学、文学、绘画、雕塑、书法之修养于一身,无论对人 生哲学的体悟还是对艺术创作的实践,都贯穿东西,融合了中国的人文精神。著有《张旭与草书》、《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等。
一般西洋美术史论到雕刻的时候,往往把罗丹作为米格朗基罗(1475—1564)的继承者,把三百年间的雕刻家都忽略过去,忘却掉。其实在这期间,欧洲的雕刻艺术相当繁荣。十六十七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下,欧洲各国的宫廷和教堂都有雕刻家留下大量代表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作品。更近,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法国乌东(1741—1828)塑造了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米拉波的像,还有华盛顿、富兰克林的像。罗丹在“对话录”里盛赞这些肖像是写出了时代、种族、职业和个性的生动的传记。罗丹还赞美过鲁德(1784—1855)在凯旋门上雕的“马赛曲”群像,卡尔波(1827—1875)在巴黎歌剧院门旁的“环舞”群像。卡尔波是罗丹的老师,著名的动物雕刻家巴力(1796—1875)也曾指导过他。罗丹是这个传统所培养出来的,为什么他的出现,大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势呢?我想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来作一些说明。
雕刻的发生源自一种人类的崇拜心理,无论是对神秘力的祟拜,对神的崇拜,或者对英雄的崇拜。把神像放在神龛里,把英雄像放在广场的高伟基座上,都表示这一种瞻仰或膜拜的情操。雕刻家把神与英雄的形象具体化。他的创作是社会交给他的任务。所以雕刻家在工作中,虽然有相当的自由,可以发挥个人才华,但是无论在内容上,在形式上,还要首先服从一个社会群体意识长期约定俗成的要求。有时,我们在庙宇装饰、纪念碑细部也看到日常生活的描写,有趣而抒情,然而那是附带的配曲。
罗丹的出现,把雕刻作了根本性的变革,把雕刻受到的外在约束打破。他不从传统的规格、观众的期待去考虑构思,他以雕刻家个人的认识和深切感受作为创造的出发点。雕刻首先是一座艺术品,有其丰富的内容,有它的自足性,然后取得它的社会意义。所以他的作品呈现的时候,一般观众,乃至保守的雕刻家,都不免惊骇,继之以愤怒、嘲讽,而终于接受、欣赏。他一生的作品,从最早期的“塌鼻的人”“青铜时代”,一直到他最晚年的“克列蒙梭”“教皇伯诺亚第十五”都受到这样的遭遇,只不过引起的波澜大小不同而已。
再举一个例子,如“加莱的市民”。加莱是法国北海岸的一个城市,1347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围城,下令城中选出六名士绅领袖,露顶赤足,穿上麻衫,颈系绳索,持城门钥匙,出城投降就刑,否则将屠城报复。士绅中有六人自愿牺牲自己以救城中百姓。据记载,怀孕的英后在场,恳求英王放赦了六人。罗丹要描写的是这短短的行列走向殉难的情景,六人中,或迈出毅然从容就义的步履,或痛苦踌躇不前,有人回盼,有人苦思。这和英雄纪念碑的体例是大相径庭的。罗丹要在这历史事件中,刻画到个人的内心斗争。他甚至主张取消基座,让悲剧中的人物就走在观众的近侧,使观众能感受到他们的手的颤动,听到他们心脏的悸跳。开初,加莱市的审查组看到初稿,提出批评说,这些人物损坏了他们心目中的爱国英雄的形象。但是最后,他们知道错了,他们期待一座公式化的英雄偶像,罗丹给他们的是更真实的史诗。
罗丹曾经多次参加纪念像的设计竞赛,而往往落选。这也难怪当时评选者的眼光窄狭,因为罗丹的作品是心理的,内向的,个人的,和一般纪念碑的雕刻风格相抵触。他的雨果,与其说表现对雨果的崇敬,不如说对雨果这个人物的解剖、分析,在这一个灵魂中冒险探索的所得。他的巴尔扎克也一样。最后的定稿,雨果是裸体的,巴尔扎克披着及地的睡袍,在学院派看来,可以说“荒诞”“失体”,但是罗丹说:“在我们公共广场上的雕刻,所能辨识的只是些衣服、桌子、椅子、机器、氢气球、电报机,没有一点内在真理,也就是没有一点艺术。”
罗丹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以雕刻的语言说出他认为的真理,这真理是写在人的血肉躯体上的生命历史。
罗丹所要表现的也并不是单纯的“人体美”。
他说过,一般人认为丑的面貌,往往因为更具有个性,更包含丰富的内在真实,而成为艺术更喜爱的题材。又说,在艺术中,有个性的作品才是美的。当然,年轻的、轻盈活泼的肢体会激发他塑造的欲望。只要翻一翻他的素描,就可以看出他带着怎样激动的心,以灵动飞舞的线条去捕捉美妙的形体。他并且说过,女人的一生,青春含花的季节十分短暂,只是几个月的事。但是他也塑造了中年的女人,粗实而沉重的身体;他也塑过老年的女人,两乳平瘪地垂着,腹部积着皮的皱褶。他为巴尔扎克像制作了许多泥稿,都是赤裸的,身体的肌肉强壮结实,用他的话说,“像一头公牛”,鼓着圆肥的肚子,显出暴躁而带世俗气的性格,那是每天深夜披衣起来,啜着浓烈的咖啡,写“人间喜剧”的作者。为了雨果纪念像,他也做了许多裸体的泥稿。那是八十岁老人的躯体,皮下沉积了厚的脂肪,松弛的肌肉在关节处形成纽结。只有如此庞然浑重的体魄才能负载得起一个巨大的创造者的灵魂吧。
欣赏罗丹毕生的作品,我们也就鸟瞰了人的生命的全景。从婴孩到青春,从成熟到衰老,人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爱和欲,哭和笑,奋起和疲惫,信念的苏醒,绝望的呼诉……都写在肉体上。
罗丹的人体不但留下岁月与苦难的痕迹,而且往往是残缺的。在他之前,哪一个雕刻家曾展出过孤零零的一只手?而他雕塑的一只手,如一株茂盛的树,已经圆足,充满表现力,成为“神的手”。两只手合拢来,十指如柱,指尖相接,成为“大教堂”。“行走的人”只有断躯和迈开的两腿,连手臂也删去,面部的表现也成多余。走向前路,是带着振奋?是带着爱护?是乐观?是惶恐?都有吧。那是人的步伐,是全人类的步伐,是全宇宙的步伐。“天行健!”一个中国人心里会跳出这古老的易经里的句子。不纪念任何特定的人物的巨像,而它走在宽阔浩瀚的地平线上,带着无比的动量,带着历历的斑驳,并无所欠缺的残缺,在我们记忆底层烙下棒喝的印记。
在罗丹之前,雕刻家都严谨地、慎重地把完整的雕像安置在神龛里、基座上,留给后世。有一个例外,那是米格朗基罗。
……因为这一个文艺复兴的巨匠,工作到八十九岁,日以继夜制作的,也是心灵的雕刻,肉体的史诗。在早期,他的确也为神龛和基座设计了神与英雄。这时期,他的两件杰作刻出了一人一神:大卫和摩西。大卫是圣经旧约里的人物,年轻时是一个牧羊人,赖他的英勇把非利士军中的巨人哥利亚用石子击杀,为以色列人除了外患。在他和哥利亚决战之前,扫罗王赐给他盔甲,但他穿不惯,脱去了,所以这里的大卫像是全裸的。他立得很直,骄傲又泰然。身体的重量放在右脚上,头转向左侧,通体弥漫着少年的精力和无畏。这石像高高屹立在佛罗伦萨城中的基座上,象征文艺复兴时代都市公民美德,也就是勇武(Fortezza)和爱国主义激起的义愤(Ira)。在西方艺术史上,这该是最能代表“英雄”这个观念的雕像了。摩西是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民族英雄。他并非神,但是耶和华不断指引他,在他之后,再没有谁与神直接对话过。他接受神谕,把戒律碣给他的子民,为这个流亡途中的民族制定了道德律、法典、礼仪、生息的节奏、文化的间架。他的像有如一座坐着的风景:卷发如跃动的焰苗,而长须在胸,卷腾如急湍。两眼若炬,显出惩奖分明的至上权威。他镇坐在神龛中,巨伟而威猛,是呵护并鞭策一个民族站起来的神灵。米格朗基罗在他的额头上加了一双短角,以别于人间的英雄。这两座雕像充满激情,而又是完美的。后世的浪漫主义者醉心于这里的热情奔放;而古典主义者释服于造形的精粹。
到了米格朗基罗晚年,这两种倾向的平衡不再能维持,宗教热忱终决破了古典形式,如罗曼·罗兰所说:“他的所以继续雕塑,已不是为了艺术上的信心,而是为了基督的信仰。”为了达到尽情表现的目的,作品的完整与否,完工与否已不是他所考虑的。就在四十岁左右,他雕的五座“奴隶”都未完成。似乎他有意不去完成,使这些埋在大理石中的男躯成为心灵在物质中挣扎的象征。(www.zuozong.com)
八十岁以后,他的两座“圣母哀子”像却不曾完成。有的部分已经加了精细的打磨,而有的部分还在毛胚状态。我们很难说这粗糙模糊的石面是有意保留的呢?是无意留下的?在对比之下,粗糙与模糊产生一种“不可说”的悲剧效果。圣母的面庞只作了初步的刻画,似乎凿刀到了这里,忽然畏怯,谦卑,迟钝,咽哑。圣母的悲戚埋在石的深处,在我们所不可及的那边。这两件作品不但没有完成,而且已经残损。一座,耶稣缺着左腿,据说是作者在不满意的愤恨中击坏的;另一座,耶稣的右臂在肩部被打断,和躯体脱离开来。这孤立的臂已经琢磨光滑,本已完成,现在像一段被雷击的树桩怪异地兀立着。据说作者准备作大幅度的修改,以致造成基本布局的解体。这是米格朗基罗最后的两件作品,他一直工作到死前一周,如今作品仍以残损而且未完成的状态留下来。
米格朗基罗已经忘却雕像的社会功能、外在形式,忘却要放置在什么地方;他浸沉在人之子的受难与圣母的哀痛中。他的创作已与此受难和哀痛合一,他的铁锤在虔诚中操作,不敢打得太深,唯恐惊动受难者与母亲的沉睡。雕刻本身暴露着被损害的痕迹,一如被钉过、被鞭过的肉躯,而磨光的部分颤栗着悲悯抚慰的清光。
米格朗基罗也在用人体写心灵。他说:“皮肤比衣着更高贵,赤裸的脚比鞋更真实。”
当神从神龛上走下来,英雄从基座上走下来,我们于是看到他们额头上的阴郁,颊边的泪痕,胸前的伤口,脚底的肿泡。我们会像一个母亲抱住他们,抚摸受难的肉躯,而这肉躯即是他们痛苦的灵魂。
米格朗基罗是一个雕刻家,更是一个打凿石头的圣徒;罗丹是一个雕刻家,更是一个雕刻的哲人。他们在大理石里凿出哲学,以青铜锻炼诗句。
从传统雕刻的观点看,从职业雕刻家的眼光看,罗丹把雕刻引入了歧途,引入了绝境。他说“忠于自然”,而在他的手中,人体已经开始扭曲、破裂,他说“尊重传统”,然而他已经把雕刻从纪念碑功能中游离出来。他所做的不是凯旋门,而是“地狱之门”。这是一大转变。凯旋门歌颂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而“地狱之门”上没有英雄。“地狱之门”其实也可以称作“人间之门”,而罗丹所描述的人间固然有鲜美和酣醉,但也弥漫阴影和苦难、烦忧和悲痛、奋起和陨落。罗丹用雕刻自由抒情,捕捉他想象世界中的诸影、诸相。雕刻是他恣意歌唱的语言。在罗丹手中,塑泥变成听话的工具,从此,在他之后的雕刻家可以更大胆地改造人体,更自由地探索尝试,更痛快地设计想象世界中诡奇的形象。现代雕刻从此可能。
艺术史家写现代雕刻史必把他作为第一章。但是大声疾呼“烧掉卢浮宫”的激进派前卫者大概会主张把罗丹的作品归为传统,一并烧掉的。他是一个起点呢?是一个终点呢?这是一个使艺术史家棘手的问题,但是对于普通的艺术爱好者可能并无关紧要。说他的雕刻是最雕刻的雕刻是可以的,因为雕刻本身取得意义;说他的雕刻破坏雕刻的定义,已经不是雕刻,也是可以的,因为雕刻不仅具有坚实的三度实体的造形美,而且侵入诗,侵入哲学。说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见雕刻的源起是可以的;说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到雕刻的消亡也是可以的。因为他的雕刻在生命的波澜中浮现凝定。生命啄破雕刻的外壳又一次诞生。
无疑,罗丹是一个拥有精湛技艺的艺术家,他说过:“没有灵敏的手,最强烈的感情也是瘫痪的。”同时他又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并不认为有了一双灵敏的手就算艺术家。他说:“真的艺术家是蔑视艺术的。”又说:“在做艺术家之前,先要做一个人。”每天有那么多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巴黎罗丹美术馆,在他的雕像之间徘徊、沉思,因为那些青铜和大理石不只是雕刻,那是,用他自己的话:“开向生命的窗子。”
【读后】
贡布里希曾经说过,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什么意思呢?艺术是人的表现,表现人性本身。雕塑艺术从西方走出来,可以说懂雕塑、会雕塑的艺术工作者甚至雕塑大家不计其数,何以人们会把米开朗琪罗(旧译米格朗基罗)和罗丹放在突出的位置呢?
是的,雕刻作为一种艺术固然是表达人们心中的某种崇拜,问题是崇拜谁——神还是人?英雄还是小丑?在米开朗琪罗之前的西方雕塑膜拜的是神,米开朗琪罗开创了西方雕塑摹写大写的“人”的历史。从米开朗琪罗到罗丹之间的365年间,雕刻大师塑造的多是英雄和完美的人,他们“都严谨地、慎重地把完整的雕像安置在神龛里、基座上”。罗丹不只继承了米开朗琪罗开创的传统,并且更进一步。罗丹的作品总是以心灵飞舞的线条去捕捉美妙的形体,少了英雄,多了平凡,这在学院派看来简直就是叛逆,因为罗丹粉碎了他们心中关于英雄形象和完美造型的梦幻和虚妄。在罗丹看来,雕塑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通过雕塑的对象表现对真相的追求和社会意义的把握,脱离了真实,“没有一点内在真理,也就是没有一点艺术”,这样的艺术便谈不上是人的艺术。艺术所要追求的美,应该通过塑型去感受内在的、真实的生命——摹写真实的人本身,这就是“用人体写心灵”。罗丹的伟大恰在于通过对艺术的还原,给了我们生命的棒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欣赏罗丹的雕塑便有阅读一部史诗的感受。
如果说在雕塑艺术领域米开朗琪罗发现了“人”,那么罗丹则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会思想、真实的“人”,从而使雕塑艺术完成了从圣徒到哲人的转型,引领人类的艺术从“凯旋门”来到“人间之门”。从此,雕塑走下了圣坛,不再追求英雄和完美。罗丹之后的雕塑艺术家可以从容地讴歌生命,赞美自由的灵魂。
可见,艺术的价值在于生命,那么作为培育人的教育的价值呢?答案还需要讨论吗?需要讨论的是,通过什么来塑造生命。罗丹告诉我们,“没有灵敏的手,最强烈的感情也是瘫痪的”。换言之,没有厚实的知识素养,没有机智的教学方法,再精致的教育同样也是瘫痪的。教育常常被喻作塑造生命的事业,如果说“塑”的是生命,那么“造”的就是敬畏。在“生命”和“敬畏”面前,“塑”和“造”的原则都可以被改写。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