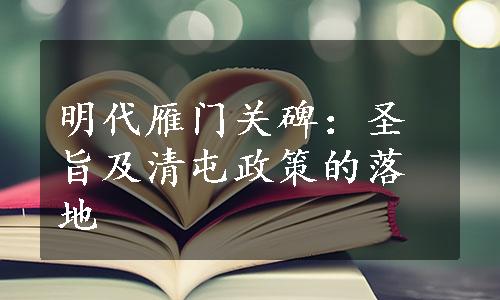
武喜荣
2002年11月底,朔城区文化馆副馆长李柱同志,带领原朔州市外办主任、市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丁福、原朔城区文化局长、平朔考古队副队长雷云贵及新华社驻晋记者丁若亭等同志,找寻前几年李柱等同志徒步考察朔城区南至山阴广武一段长城时发现的一通石碑。下午3时许,在朔城区王化庄村南堡梁找到了这通明代嘉靖二十八年(1549)立的石碑。碑高1.6米,碑文字迹虽遭风蚀剥落,但大部分还是可以辨认的。碑额题“圣旨雁门关”,首行书山西等处提刑按察使、提督雁门关的官员以总督宣(府)大(同)军务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翁(万达)等奉皇上之命,刻立这通石碑的过程。碑文中段是嘉靖帝圣旨的主要内容:“雁门、宁武二关,东西十八隘口,一切禁山,地土退(草)还林……口北应、朔、浑源、山阴、马邑等处,如果禁山内有征粮田,备行大同巡抚衙门,查册处分。各府争占土地,禁山居人,悉照奏内事理施行。等因蒙此,合行刻石,晓谕禁约。今后一应人等,敢有擅入禁山砍伐林木、耕垦地土,参将、守备、守口等官便擒拿解道,问发南方烟瘴地面充军。各官容情故纵者事发,一体参奏,治罪不恕。”碑文后一段内容记述了这一带军事禁区内“退(草)还林”之田的勘界造册之事及执行官员。丁福、雷云贵等同志对这通石碑的史料价值有足够认识,于是,丁福同志把事先准备好的墨汁、宣纸、打刷、拓包等拓印用具取出来,几个人顶着侵肌寒风,首先把碑文拓印下来,保留了资料。之后,在市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参会的魏向东、丁福等同志把这件事直接给市领导作了汇报,时任市长的张建欣同志当即责成市文化局将这通碑运回朔城区崇福寺,妥善保管了起来。李柱是一位热心文物工作的同志,从他1995年首次发现这通碑,到2002年运回保管,前后达7年之久。石碑有了归宿,李柱同志也了却了一桩心事。
这通石碑的碑文《明史》没有记载,但是立这通石碑的起因,《明史》是有确切记载的。就史料价值而言,这通石碑弥补了明代中后期(www.zuozong.com)
雁门关一带防御情况的不足,是任何文献记载所不能替代的。
碑文中有一个关键字是“草”,还是“革”,因风雨剥蚀不很清楚,看起来像个“革”字,即“地土退草还林”或是“地土退革还林”,因为两个不同的字,完全可以诠释为两种不同的内容。有的同志认为是“地土退革还林”,把“革”解释为甲、兵,进而引申为“退军垦之田以植林木”。正史确实有载,不无道理。但是,明朝“退军垦之田以植林木”即所谓“清屯”,当时在山西雁门关一带,不但没有执行,而大张旗鼓地贯彻执行的是山西巡抚上奏,嘉靖帝批准的让边兵耕种余地的策略。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春正月“杨守谦巡抚山西,上言‘偏头、老营堡二所,余地千九百余顷,请兴举劳田堪以内省京运,外资防守'……诏以其法行之九边”(《明通鉴》59卷)。这年二月份,接着就出现了翁万达等上奏“边防修缮事宜”的情况,地土退革还林不符合史实。如果是“地土退草还林”,从语法上讲行得通,因为土地上可以长出草,而长不出“军屯之田”。“退草(包括焚草)还林”是整个明代及明代以前中原汉族统治者“御边”良策之一,“退草”使入犯者骑马无饲草;“还林”使入犯者遇林减速,便于守卫者乘机出击。这就是“圣旨雁门关”碑,为什么把“禁山砍伐林木”“地土退草还林”作为“设重险以固强国事”来抓的原因所在。所以,笔者认为这个“革”字是“草”字之误,就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请识者指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