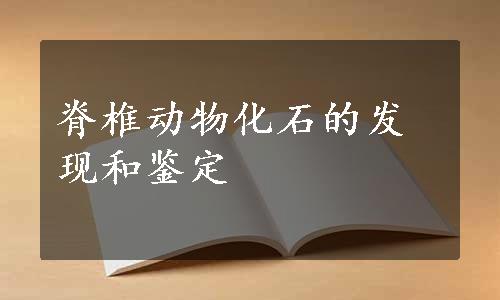
动物化石绝大多数埋藏在遗址的第二层(即文化层)中;在第三层(即砂层)的底部,亦出现极少量的化石(如虎、披毛犀、野马等),化石密集成层,但一般保存情况较差,未见头骨,下颌骨多残破,大多数是单个牙齿和被击碎的骨片。
经初步观察,除一块智人(Homo sapiens)的枕骨外,动物化石计有如下的种类:
鸵形目:
鸵鸟属(Struthio sp.)
材料有几块蛋壳残片,厚度2.2毫米,可能为安氏鸵鸟(S.anderssoni Lowe)
食虫目:
刺猬属(Erinaceus sp.)
材料只有一块左下颌骨的后半部,下第二臼齿(M2)以前部分及喙突均未保存。
食肉目:
斑鬣狗属(Crocuta sp.)
材料只有左下第一臼齿(M1)的后半部,即原尖的后半部及齿座。下原尖的后棱有细微的锯齿,齿座小,下原小尖较发育,呈切割状。特征与斑鬣狗相合。
虎(Panthera tigris Linnaeus)
左股骨的上半段,大小和构造与现生虎的相同。
啮齿目:
鼢鼠属(Myospalas sp.)
只有一个左上门齿,内侧面有些残破,釉质层前面呈杏黄色,构造和鼢鼠的很相像。
偶蹄目:
马鹿(又名赤鹿)(cervus elaphus Linnaeus)
主要由三块残角为代表,一块残角为脱落角,两块带有角柄,在带有角柄的一块残角上,眉叉和第二叉以及第二叉以上的部分均残缺;从保存部分来看,眉叉从基部分出,与主干成直角,第二叉紧接眉叉从主干分出,很清楚,属于马鹿型。有些牙齿也可能属于此种。
河套大角鹿(Megaloceros ordosianus Young)
主要材料为一块残缺的脱落角。眉叉从角环处向前上方伸出,眉叉呈板状,主干断面呈椭圆形,与过去所描述的河套大角鹿的角相一致。角的尺寸较小,属于幼年个体。此外,在鹿类的材料中还有一些比较肿厚的下颌骨,下第二臼齿及第三臼齿(M3)之下的下颌骨厚度为33.5毫米,大于周口店的第3地点的大角鹿(28.5毫米)及丁村的大角鹿(24.2毫米),小于周口店第13地点的扁角鹿(Megaloceros flabellatus Teihard)(35—40毫米),和第15地点的相比(按图测量为30毫米)颇为近似。可惜,峙峪的这一类型的下颌骨的下缘都残缺,由下颌管的位置估计,横断面应为椭圆形。下颌骨上的牙齿也很粗大(左下第三前臼齿的长和宽为20×24毫米;下第四前臼齿为21.5×25.2毫米;下第一臼齿为29×27.5毫米)。此种比较肿厚的下颌骨和大的牙齿应属于河套大角鹿。
普氏小羚羊(Procapra picticaudata Przewalskii Büchner=Gazella Przewalskii)
材料有右角心两个,左角心一个;有些零星牙齿,按其大小也可能属于此种。左角心完整,其余的角心缺尖。角心的大小与萨拉乌苏河的同种动物相比十分接近,左右较扁,向后弯曲,表面有粗糙而深的纵沟;左角前缘的弧长为160毫米,基部前后宽37.5毫米,左右宽26.5毫米。
鹅喉羚(Gazells cf.subgutturosa Guldenstaedt)
有一小块羊的下颌骨(带有下第二臼齿和残破的下第三臼齿)和一个单个的右上第三臼齿。上第三臼齿长和宽为15.3×10.8毫米,下第二臼齿为14.2×7.5毫米;月形脊的前外侧有锐棱,大小和式样与鹅喉羚的牙齿相比颇为一致。
牛科(羊类,未定属名之一)(Bovidae gen.indet.1)
有一些小的羊牙,下第三臼齿的长和宽为20.5×7.5毫米,和鹅喉羚大小接近,但齿冠甚高,高达46.5毫米,远远超过了鹅喉羚下颌骨的高度。
牛科(羊类,未定属名之二)(Bovidae gen indet.2)
另外还有一些巨大的羊类的牙齿,下第三臼齿的长和宽为43.2×13.7毫米,齿冠高57毫米(磨蚀较轻的可达65毫米以上)。
王氏水牛(Bubalus cf wansijocki Boule et Teilhard)
有一件残左下颌骨(保存第一臼齿和第二臼齿)和许多单个的牙齿,另外还有一件残掌骨和一件距骨可归于此种。牙齿的釉质层粗糙而厚,臼齿的第二叶的后部常具有一内距,前后窝较宽,牙齿很大,大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德氏水牛(Bubalus teilhardi Young),与萨拉乌苏河发现的王氏水牛接近,有的尺寸甚至超过。下颌骨也硕大,远超过现生的牛属。
牛属(Bos sp.)(www.zuozong.com)
有三段残破的下颌骨和一些单个的牙齿。下颌骨和牙齿均比水牛属为小,与现生的牛属相比很接近。
奇蹄目:
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 Blumenbach)
有十六个完整和残破的牙齿。从牙齿的大小和磨蚀的程度上看,至少代表幼年、成年、老年三个个体。牙齿的表面多皱纹,原脊(protoloph)、后脊(metaloph)向后倾斜度大,外壁呈波浪状,前刺(crochet)与小刺(crsta)甚发育,特征属于披毛犀类型。完整的成年牙齿中有左上第四前臼齿(P4,齿冠基部的长和宽为44×56毫米)、右上第一臼齿(M1,52×68.5毫米)、右上第二臼齿(M2,59.0×62.5毫米)、右上第三臼齿(M3,61.0×55.0毫米)和左下第三臼齿(M3,62.5×35.5毫米),属于大型。
蒙古野马(Equus przewalskyi poliakov)
以牙齿和少数掌、距骨为代表,根据右上第三臼齿计算,总数至少有120个个体。牙齿的马折(pli caballin)清楚,其大小也与现生的蒙古野马无明显的差异。
野驴(Equus hemionus Pallas)
材料主要以牙齿为代表,臼齿上无马折。在本地点除了蒙古野马之外,野驴的数目也很多,以右上第一臼齿的数目为依据,最少有88个个体。此外,尚有乳齿400余枚。
上列的化石已定出种或与种进行比较的动物共有10种,其中的现生种有6种,绝种的动物有4种,占40%。
峙峪的哺乳动物群和萨拉乌苏河哺乳动物群相比颇为相像,在时代上早于山顶洞,晚于丁村。
丁村的动物群中含有一些原始种,如德永氏古棱齿象和梅氏犀。德永氏古棱齿象最早见于我国更新世早期;梅氏犀多见于我国更新世中期,如周口店第9地点、第13地点、北京人遗址。丁村发现的德永氏古棱齿象和梅氏犀恐怕是这两种动物的最晚的化石记录,因此丁村动物群的时代较早。
与萨拉乌苏河的哺乳动物群相比,峙峪的绝种动物的百分比较大,但这很难说明峙峪的时代比萨拉乌苏河为早,因为峙峪所发现的种几乎都包括在萨拉乌苏河的动物群之内。据此,我们推测两地的动物群是同时的,甚至萨拉乌苏河有可能稍早于峙峪,因为萨拉乌苏河还有我国更新世中期常见的纳玛象,而在峙峪和小南海则未见到。
中国北部更新世晚期主要文化遗址哺乳动物群对比表
(表中所列的化石以定有种名的为准)
关于萨拉乌苏河动物群问题,国内外学者迭有讨论,科兹洛夫斯基最近认为周口店第15地点可以和萨拉乌苏河相比,他说:“第15地点的全部动物在萨拉乌苏河有其副本(野驴、披毛犀、普氏小羚羊、马鹿、翁氏鼢鼠、狗獾和鸵鸟蛋片)……可以推测萨拉乌苏河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与周口店第15地点同时。”我们认为科兹洛夫斯基的意见是很难令人同意的,他在论文中提出的所谓“副本”的材料,是不能作为“副本”来看待的。例如,狗獾(Meles tasus)在裴文中所列的第15地点的化石名单中就没有;马也未定种。披毛犀、马鹿、中华鼢鼠在第15地点和萨拉乌苏河两地虽然都存在,但这还很难用作为“同时”的有力证明,因为绝种的披毛犀在我国更新世早期即已见到,于更新世晚期曾繁盛一时;现在还生存着的马鹿,最近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顶部堆积中也有发现;现在还生活着的中华鼢鼠最早的可靠化石记录也见于华北各地更新世中期地层中;鸵鸟也是一样,在我国秦岭以北的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布的都很广泛,从上新世起到更新世均有化石记录。与此相反,在第15地点发现的变种仓鼠(或称古仓鼠,Cricetinus varianus Zdansky)、简田鼠(Microtus epiratticeps Young)、复齿田鼠(Microtus Complicidens Pei)、似布氏田鼠(Microtus brandioides Young)、翁氏鼢鼠(Myospalas cf.wongi Young)等绝种动物在萨拉乌苏河则未见到;而这些绝种的动物却是北京人遗址哺乳动物群中的成员。因此,我们认为把周口店第15地点归到中更新世末期,在目前来说还是合理的。
与小南海的动物群相比,峙峪的动物群在绝种动物的百分比上大于小南海。小南海的绝种动物的百分比和萨拉乌苏河的很接近,但未见到萨拉乌苏河的河套大角鹿,因此我们同意小南海动物群研究者的分析,小南海的动物群“大致与萨拉乌苏河动物群的时代相当或稍晚”。
至于峙峪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洞沟遗址的时代如何对比问题,根据水洞沟遗址已发表的材料,还很难通过动物群直接得到确切的说明,因为德日进等人谈到水洞沟的地层时,没有发表正式化石名单,只是提到水洞沟发现的化石种类有犀牛、鬣狗、羚羊、羚羊类、牛和鸵鸟蛋壳残片。
根据动物群的性质可以一般地推测峙峪人生活时期这一带地区的自然环境。
在峙峪动物群中有蹄类所占的比例最大,构成这一动物群的主要部分,它们所代表的是比较干燥的草原环境,其中典型的草原动物有蒙古野马、野驴、普氏小羚羊、鹅喉羚等。
在我国,蒙古野马化石首先发现于萨拉乌苏河遗址,最早的化石记录见于丁村遗址。据现代动物地理资料,蒙古野马是一种喜冷的草原动物,分布于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及玛纳斯河流域,沿乌伦古河向东分布到北塔山附近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布多盆地,较我国更新世晚期的分布区的已知南界(丁村)在纬度上约北移了9°在纬度上相当于由北京至海拉尔之差,在年平均气温上相差10℃左右。
普氏小羚羊现在也同样分布于亚洲大陆北部地区,主要产于我国的甘肃北部、河套地区、新疆、青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荒原地带。
亚洲现生的野驴(又名骞驴,Equus hemionus)有五个亚种,其中的西藏野驴(E.h.kiang)产于我国康藏高原,向西分布于克什米尔境内,向北分布于青海地区;蒙古野驴(E.h.hemionus)产区在戈壁沙漠西部,以阿尔泰山为中心,南北皆有,有可能分布到我国新疆、青海等地,生活于丘陵和荒原地带。我国已知的野驴化石记录以丁村遗址为最早,其南界达到河南新蔡(北纬32°40′+)据文献记载,野驴化石在南欧和西欧发现的较多(被命名为asinus hydruntinus),但在东欧北部地区则未发现野驴化石,因此似乎它不甚喜冷。但是,在西欧和东欧,野驴又常常是在喜冷动物群中出现的。目前,关于化石野驴的种的分类和生态特点还不十分清楚。有人认为它适于略为干燥的开阔地带,有人认为它适于不甚干燥的温和的草原环境。
马鹿是一种适应森林和草原环境的动物。它在一年当中随季节的变化在森林和草原之间来往游动,所以马鹿的化石有时发现于森林环境,有时发现于草原环境。现生的马鹿主要分布于冬积雪厚度20—30厘米的地区(蒙古北部、贝加尔湖地区),积雪厚度超过40—50厘米则不见马鹿的踪迹。与此种十分接近的北美赤鹿(Cervus canadensis)分布于北纬32°—60°之间,主要分布于50°左右的地区。
斑鬣狗也是一种偏重于适应草原地带的动物,它经常与有蹄类生活在一个地区,因为它主要以这类动物残骸为食。斑鬣狗现在分布于非洲中部和南部;在我国,目前已知是最晚的斑鬣狗的可靠的化石记录为更新世晚期。但在东欧,在全新世地层中也发现有斑鬣狗。因此,第四纪的化石斑鬣狗的存在并不一定代表炎热带气候,现在虽然生于热带,还依然不畏寒冷。
河套大角鹿是一种很特化的动物,两角间的间距很开阔,它不可能在密林中活动。大角鹿的颈较短,根据头骨位置与脊柱的关系,可以判断它们适于生活在夹杂着灌木的草原环境。
如果从动物群中抽出个别动物的某些性质来推断当时的自然环境,势必得出彼此矛盾的结论。例如根据披毛犀并强调其喜冷的一面,便会认为当时天寒地冻,冰雪漫天;概念水牛并强调其喜湿热的一面,又会认为当时这里暑气逼人,一片水乡;根据鸵鸟并强调其喜干热的一面,甚至会认为这一带平沙无垠。
更新世晚期的披毛犀确实是喜冷的动物,问题在于它喜冷的程度如何。椐欧洲的资料来看,披毛犀最早出现于民德冰湖(Mendel glacial)后一阶段,但化石稀少;在里斯—武木间冰期(Riss-Wurm interglacial),披毛犀在中欧消失,后来在武木冰期(Wurm glacial)又重新出现。有些学者认为披毛犀是冻土地带的典型动物。其实,更新世晚期的披毛犀在总的性质上虽然偏向于喜冷,但它所能适应的环境可能较广,它不一定是冻土地带的标志。在欧洲,披毛犀偶尔也发现于温和草原环境。在德国什图特加特(Stuttgart)附近发现的披毛犀化石的层位中也发现有常见于间冰期的山毛榉的叶子的印痕。从西伯利亚冻土中保存的披毛犀尸体来看,它身上长着棕褐色毛,但毛的长短与现生的欧洲野牛的毛差不多。在萨拉乌苏河遗址,披毛犀也与马鹿、骆驼甚至与水牛共生。在山西丁村遗址,披毛犀与适应温暖气候的梅氏犀共生。
华北更新世初期的披毛犀不一定是喜冷的动物,它在向北亚和向北欧分布过程中逐渐适应了不同的生活环境。
鸵鸟属现在分布于非洲、沙特阿拉伯以及叙利亚等地,生活在沙漠和草原环境中。但是,鸵鸟并不一定只能生活在热带地区,它也能够耐受较低的气温,在比较寒冷的环境中仍能生存。在我国,已不止一次地发现鸵鸟蛋皮与披毛犀化石埋藏在一起,除了峙峪遗址外,还有萨拉乌苏河遗址和哲里木盟化石地点等。
现在的野生水牛(Bubalus bubalis)生活在印度、斯里兰卡、马来亚、缅甸、印度支那等地靠水边的热带低地森林中,但是第四纪的化石水牛并不一定代表热带环境,例如在德国属于民德-里斯间冰期的史坦海姆(Steinheim)遗址发现的水牛以及我国匼河遗址的水牛、丁村遗址的水牛、萨拉乌苏河遗址的水牛、哈尔滨附近的水牛并不完全代表热带气候。我们同意这样的意见:“也许王氏水牛是水牛类中一个能适应于在比较寒冷和潮湿区域生活的种……但更可能的是因为动物随季节而迁居,夏季南方动物北进,冬季北方动物南下,故使化石在同一地方保存下来。”
综上所述,根据哺乳动物群所反映的自然环境,可以认为峙峪人生活时期,峙峪一带主要为靠近山区的辽阔的草原地带,有的地方夹杂着灌木林。冬夏两季温差较大。总的来说,年平均气温应较现在为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