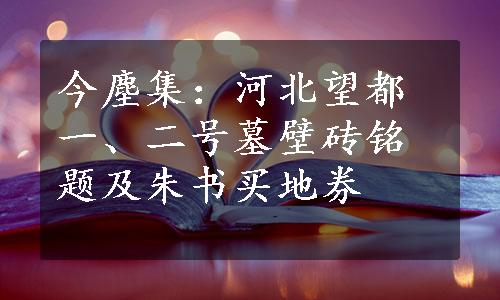
1955年北京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望都汉墓壁画》。书中刊布了河北望都所药村一座东汉晚期壁画墓的资料。该墓为多室墓,其中室顶券和南北两壁的砖面上写有白色字迹(图8.1—3)。字迹情况据该书描述,约略如下:

图8.1—3 望都汉墓砖壁题字,采自《望都汉墓壁画》
券顶中间全是“中”字,其余文字可分为三部分:由东往西,计:第二道至第三十八道券间北侧由下往上为“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南侧由下往上为“作事甚快与众异”;第三十九道至第五十一道券间北侧由下往上为“主人大贤贺□日千”,南侧由下往上为“酒肉日有师不爱手”;第五十二道至第七十七道券间北侧由下往上为“孝弟堂通于神明源”,南侧由下往上为“急就奇觚与众异”。
在中室南北两壁券门过道的顶券上,南券门由北往南,北券门由南往北第一道至第四道券的砖面上,也有白灰字迹。东面由下往上为“一二三四五六七”;西面由下往上为“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左右位置相同的砖,写着同一的字。……可能这些字是起着符号的作用,和起券的工作方法有着关联。[52]
这座墓和所谓的望都二号墓相邻,二号墓略大,但多室结构形式和出土物品颇为相似,壁画风格相同,有可能是时代相近的家族墓。[53]由于一号墓壁题记中有“当轩汉室”之句,二号墓有灵帝光和二年(182)记年的买地券,可证两座墓都应是东汉晚期之墓。[54]
这两座墓发现时间较早,报告都甚为简略,图版不够完整、清晰,十分可惜。[55]此外,可能因为当时出土墓葬尚少,缺乏比对的材料,两墓报告都完全不谈墓主是谁的问题。其实就墓的布局和墓中出土的文字资料,似乎就足以推定两墓墓主都是地位不低的地方官吏。两墓壁上都有壁画,二号墓壁画残损严重,但尚余“□督邮”、“史者”、“辟车伍百八人”等残榜。一号墓壁画保存远为良好,其布局由墓门进入前室,由前而后,左右壁面绘满带有榜题的人物“门亭长”、“寺门卒”、“仁恕掾”、“贼曹”、“追鼓掾”、“□□掾”、“伍佰”、“辟车伍伯八人”、“门下小史”、“门下史”、“门下贼曹”、“门下游徼”、“门下功曹”、“主记史”、“主簿”,在进入中室的过道两侧则绘有“白事吏”、“侍閤”、“勉□谢史”、“小史”。前室相当于前堂后室的堂,乃治事会客之所,布局颇像是墓主生前的官衙各曹。在诸吏之下的壁面上又绘有芝草、鸾鸟、麞子等祥瑞。这是为了彰显墓主生前的文治之功。不难推知墓主应是一位地方官吏。
再者,一号墓前室西耳室的过道南壁下方有朱书四言铭赞,共八句,三十二字:“嗟彼浮阳,人道闲明,秉心塞渊,循礼有常。当轩汉室,天下柱梁。何忆掩忽,早弃元阳。”铭赞东侧有“弟子一人”、“弟”、“弟”的残题,报告推测铭赞可能出自墓主的弟子。[56]题铭的内容和由弟子题铭的方式都和东汉晚期地方官员墓碑上所见的十分类似。凭据这些铭赞应可以肯定墓主为地方官吏。二号墓买地券更提到墓主姓刘,或曾为太原太守。券文谓:“大原大守中山蒲阴助[所?]博成里刘公”云云,又谓为“刘氏之家解除咎殃”。[57]此买地券断为两截,略有残缺。唯券中提及的人物只有这位刘公,其为墓主应无可疑。《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中山国”条有蒲阴县。章帝时改曲逆为蒲阴。望都也是后汉时中山国县名,《后汉书·五行志》谓顺帝阳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阴狼杀童儿九十七人”。望都与蒲阴当为邻县。这墓坐落于今之望都所药村,当是曾任太原太守的墓主刘氏返葬故里之所在。(www.zuozong.com)
如果以上对墓主身份和时代的推定可以成立,则可以进一步分析一下墓中的文字和文字的书写者。如果稍微仔细观察一下两墓中的壁画榜题、买地砖券文字和壁上白色成排重复书写的字迹,就不难发现它们出于不同人的手笔。
姑从一号墓的文字开始。一号墓的文字除了壁画榜题,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成排像是出自《急就》等字书的文字。请先注意一下这些字的书写风格和排列。第一,“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作事甚快与众异”、“主人大贤贺□日千”、“酒肉日有师不爱手”、“孝弟堂通于神明源”、“急就奇觚与众异”这些字重复书写,书风一致,无疑出于同一人之手。第二,书法十分流畅老练,书者喜欢将一字的某一横笔有意向右拉长,表现出书法上的特色。第三,所书内容除“急就奇觚与众异”一句出自《急就》篇,其余或七字,或八字一句,也很像出自某种改编过的字书。[58]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作事甚快与众异”,这无疑改编自“急就奇觚与众异”。第四,排列上,“作事甚快与众异”七字自左向右书,同排的“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八字却由右向左书,两句中间加一“中”字,如此左右对称各有八字。其余“酒肉日有师不爱手”自左而右,“主人大贤贺□日千”自右向左;“急就奇觚与众异”自左向右,“孝弟堂通于神明源”自右而左,情况相同。这种排列方式必是刻意为之,有其用意。用意何在呢?
《望都汉墓壁画》的撰写者认为“这些字是起着符号的作用,和起券的工作方法有着关联”[59]。安志敏在评论这本报告时,也同意这种看法。[60]这种看法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因为在河南等地的确可以看见汉代的空心砖墓中有砖上事先编号,再于墓中按编号顺序组装的情形。[61]如果一号墓壁上成组的字确乎起着编号的符号作用,壁上也书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用简单的数字(例如洛阳的卜千秋墓),岂不更方便?而且为什么当符号用的字仅出现在部分砖面上,难道这部分砖居于特别的位置?为何别的砖不必用符号?由于报告简略,图版不全,我们现在难以判断有字砖是否位于墓室特殊的位置。更令人起疑的是,如果是当符号用,按理成组的字应事先写上,再根据字的顺序在墓中累砌。可是仔细看看一号墓壁面文字的笔画,可以轻易发现许多字总有一笔向右拉得很长,跨过一块砖而写在邻砖上。这似乎只可能出现在砖壁已砌好,而后在砖面书写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先写字,再砌砖起券。
换言之,符号说难以令人信服。那么,为什么会写这些字呢?迄今没有他例可供参照,还不易论定。我的猜想是和墓主生前的工作有关。墓主不仅是一位被吹捧为“当轩汉室,天下梁柱”的官员,也是一位拥有弟子,“循礼有常”的儒师。两汉官吏任官时教授生徒,亦师亦吏,十分普遍。考古报告推测墓中铭赞为弟子所书,有其道理,私意以为墓中砖上的字也可能是由某一弟子所书。这位墓主不但教授《急就》,甚至可能改编过字书之类,因此弟子将这些字句,尤其是第一句“作事甚快与众异”书写在墓中墙上以为纪念。但“主人大贤,贺□日千”、“酒肉日有,师不爱手”等句则比较像是出自弟子的口气,乃为祝福先师而书。总之,这些字都是墓砌好后,才书写上去的。书写笔法流畅老练,似乎不宜简单地看成是工匠所书。为何同时左或右向书写?一时没有好的答案,有待更多类似的材料出土,进一步研究。
老练的书法也见于二号墓的朱书买地券(图9.1—2)。这件买地券书有三百字以上,书法相当工整规范,即使不是墓主的弟子所写,也应出自较为专业的书手或专门书写地券的人,而不是普通造墓的工匠。

图9.1—2 买地券全砖及局部(摹本),采自《望都二号汉墓》
一般民间书师、书手或工匠,并不一定经过像“史”或官府书吏一样的正规书写训练和考试,我们不禁容易去假设他们所书写的比较会有(1)笔画结构随意,不规范;(2)文辞不够通畅,文法不合规矩,不易通读理解;(3)书法粗拙,和公文书上训练有素的隶书笔风相去较远的现象。这个假设不能说错,因为我们的确在汉代石刻、砖刻、器物上看到不少笔画字形不规范,文句不畅通的题铭。实际上却又不尽然。书法和文辞有时并不能绝对反映书手或工匠的读写能力。东汉中晚期书法渐成一门艺术,大儒蔡邕是书法名家,不但为太学书写石经,更为各方礼聘去书碑题铭。东汉碑铭书法之精美常是名家书丹,也就是直接在石上以朱笔书写的结果,石工再据以雕刻。[62]因此许多石工虽在碑上留名,并不能真正反映他们本身的读写能力。当然也有很多砖石上的题刻或壁画文字题榜和名家无关,反映了比较多工匠本身的能力。以下仅举情况不同的两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