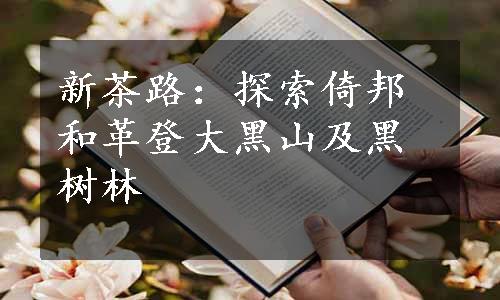
倚邦有两个“大黑”,一个是“大黑山”,另一个是“大黑树林”,二者常被误以为是同一个地方,许多卖茶人也搞不清,在朋友圈里说“大黑山”别名“大黑树林”,就是典型的胡扯,让买茶人厘清二者变得更加困难。
大黑山,属于倚邦弥补村茶地,与之相近的茶园有细腰子、龙过河和叶家寨。弥补村的茶早就受欢迎,近两年,又以大黑山茶最为突出。因其有类似曼松茶的细甜滋味,还有蛮砖茶的浓强度,使之成为倚邦地区价格仅次于曼松茶的存在。
大黑树林靠近曼拱。之所以被称作大黑树林,自然是因为这片茶园隐藏于茂密的森林中,茶树生得高大,在爱茶人眼中就像是倚邦地区的薄荷塘。
大黑山甜柔,大黑树林气韵深厚;同样是倚邦的顶尖代表,一个赛曼松,一个比肩薄荷塘,二者自然不能混为一谈。
大黑树林,道路两边都是茶园
从弥补村到大黑山山顶处有7公里,到离大黑山近一点的位置只有2公里,但路实在不好走。即使是郭龙成这样的茶山老司机,也差点在大黑山把车开翻到山下。
大黑山古茶树并不多,过去砍掉了太多的古茶树,后来栽种的茶树比较多。东一棵、西一棵,不集中。茶树周围还有些散落的野生橄榄树,正是硕果累累时,一颗颗绿色带黄的果实挂在枝头上。我毫不犹豫地摘了一颗放进嘴里,味道很不错,微苦,但很快就是甘甜。茶山乐趣,就在这一点点的回甘中。
跑了很多茶山的郭龙成,坚持认为大黑山的野橄榄最好吃,回甘好,山上吃一颗,到山下还在回甘。这里好吃的还有猴子眼袋果,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这种名字很奇葩的果实,滋味酸甜爽口。后来我查阅了资料,原来其学名叫猴子瘿袋,是桑科波罗蜜属植物。我们还在茶树地里发现一种当地人称为“马鞭草”的草药,即“滇黄精”,主要功能是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用于脾胃虚弱,体倦乏力,口干食少,肺虚燥咳,精血不足,内热消渴。
郭龙成成为茶农前,是位医生,与他逛茶山,总会收获很多博物学上的知识。
大黑山茶的特点是甘甜度更高,苦底不重,蜜香浓郁,润口。这些特点,加上稀少的产量,使得大黑山茶价格这几年来渐涨,大黑山也因此成为整个倚邦古茶山价格仅次于曼松的产区。
先前,大黑山的茶叶都是茶农自己喝,后来茶叶公司收购,茶农才开始卖茶。茶叶卖到倚邦老街那里的茶叶公司。现在,想喝大黑山古树茶就有点难度了,春茶季时茶叶还没有发芽就被预订一空。
龙成号在大黑山有个基地,茶树已经长了齐身高,还需要放养几年才能采摘。刚到基地,郭龙成和曹燕坤动手做饭,一块木板有着多种用途,正面当作饭桌,背面当作砧板,用几块石头支撑好就能开工了;旁边是烧火的地方,找了一些干草点燃几块干柴,火很旺,煮菜、炒菜、烧水……
茶山上的人,最懂得如何利用手边的资源,没有地方坐,就坐在石头上,工人们直接坐在旁边草皮上吃饭;筷子不够,就砍树枝;碗不够,砍一段无花果枝条过来,曹燕坤将碗让给我们,她自己用一片无花果叶子当碗,再将米饭、菜放在叶子上,她就那样吃饭。无花果叶子因为大,形状又像大象的蹄子,当地人称为“象蹄叶”,也叫“大象耳朵叶”。
如今流行的竹筒茶,也是过去人们为存放茶叶而因地制宜的创新。把晒干的茶一边在火上烤一边舂进竹筒中,不仅防潮防虫,还有一股竹子的清香。
江内六大茶山,汉文化痕迹十分明显,无论走到哪儿,都有石碑、石刻留下汉人曾经的印记。大黑山茶园里偶然还能见到散落的石墩,是过去的大户人家留下的。为什么会搬离这里?因为缺水。
著名的曹家大坟也在这里,远远看去,是一处草木茂盛的所在,周边是开满白花的飞机草,中间是高约20米左右的小叶榕,还有些其他常绿植物。
茶地边生活烧水
上山收茶不仅要会炒茶,也要会炒菜
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后的第六年,中央推行“流官管土官、土官管土人”的政策,曹家曹当斋任倚邦土千总,世袭管理倚邦一带茶政兼管钱粮事务。曹当斋祖籍四川,在茶山长大,娶当地头人女儿为妻。对中原文化既有认同感,又了解茶山真实情况,被朝廷任命为倚邦土千总。曹当斋去世后,曹氏家族世袭管理倚邦、革登、莽枝茶山。这一时期是古六大茶山大发展时期,倚邦周围茶园达2万亩,居民有1000余户。
曹家大坟是曹当斋儿媳妇的坟墓,她出嫁没几年,丈夫染病而死,一生未再嫁,当地人还为她立了贞节牌坊。
哪怕到现在,曹家大坟只剩下断瓦残垣,依然能感受到其规模之大。传闻中的数百只石麒麟只找到几只,这里散落着一只,那里散落着一只,并且稍微离远一点还看不到,都被杂草遮住了。与石麒麟一起散落在杂草里的,还有坟墓的基石,留给后来人无尽的遐想。(www.zuozong.com)
散落在山间的石碑
翻山越岭去茶园
曹家大坟核心处,连墓碑都是倾斜着的。其中一块石碑上比较明显的字迹分别是“天承运”“皇帝制曰爪牙(古义是‘得力帮手’的意思,是褒义词)”“土把总曹秀小心尽职”“曹秀之妻陶氏”,另外一块石碑上刻着“大清嘉庆二十二年”。此外,还有很多石雕,图像比较清晰的一块雕刻着鱼和祥云。
当地多位老人说,当时建造曹家大坟,曹家是用大象从远方驮运石材进山的,毕竟古六大茶山并不产石头,这些大石只能从外面运输进来,在交通落后、大坟遗址偏僻、进山之路狭窄而崎岖的情况下,足见其实力雄厚。
当地还流传着一种说法:“曹家大坟雕刻着世界上所有的动物。”说法虽夸张,但完全可以想见雕刻动物种类之繁多。曹家大坟是曹家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更是古六大茶山茶业发展鼎盛的一个侧证——唯有茶业发展鼎盛,曹家才有其地位和财富,也才为营造曹家大坟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与物质条件。
大黑树林在倚邦的另一边,是曼拱茶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循着曲折小路一路往上才能抵达大黑树林的古茶园。茶园不小,在一块陡坡上,与其他乔木类大树共生,乔木类大树比较多,看上去显得茶树比较稀疏。这对茶客来说其实是好事,如此一来,每棵树的根系都能够充分伸展,每个芽头获得的营养供给更为充足,这也是古树茶喝起来滋味往往比台地茶园的茶更丰富的主要原因。
茶农家院子里晾晒茶叶的场所
茶树大小不一,所以高高低低,低矮些的茶树和人一样高,很方便观察;倚邦产区中小叶种的茶树比较多,当地人习惯称为“细叶子”,成熟茶树叶片也仅有半个手掌那么长,与勐海布朗山茶区的大叶种相比,显得十分娇小,而嫩芽就更加明显了,细嫩的芽头一点点冒出来,如针尖一般。
往茶园深处走,高杆茶树出现的频率也增加。这类茶树完全脱离了一般人对茶树的想象。挺拔,颀长,高度可达4米。这些被人亲手栽种下的茶树,在种树人离开之后,便逐渐回归了更为自然的生长方式。阳光,阳光,阳光!在密林中,只有拼命往上才能攫取到足够的阳光。于是茶树的侧枝慢慢凋落,只留下光溜溜的树干和顶部向上的树枝,茶树终于变成了令人陌生的模样。
人为干预少,分枝少,茶树的芽头也少,单片叶获得了比一般茶树更多的营养;密林里的浓荫又使其梗长叶厚,涩度降低,多重因素交织形成了稀有的山野气韵。薄荷塘的独特气质也同样来源于此。
茶园下方还保留了一条较为完整的茶马古道,尽是不规则的石板,有的光滑,有的长满青苔,有的因为路基下陷而倾斜。郭龙成说:“这段茶马古道,一头通往思茅,另一头经倚邦老街通往易武。”昔日马帮里的赶马人,就是沿着这条路驮运茶叶等物资。矮小的云南马,驮起一个个家庭的梦想,更驮起云南普洱茶的辉煌发展史。
大黑树林的石板路
挂满枝头的野生橄榄
茶农正在挑拣黄片(老叶子)
天色黑下来,乌云密布,要下暴雨的样子,郭龙成叫我们赶紧走,前面有一户人家,可以躲雨。
这户人家是彭翠华家,她正在挑拣黄片。看到我们进家里,她放下手头的活,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喝茶。彭翠华家的院子很大,但没有弄平整,摆放着竹竿,方便晾晒茶叶;房子既有传统的木屋,也有新搭建的平房,都是一层的房子,院子外单独搭建了一间离地很高的房子,专门用来仓储茶叶。
彭翠华今年48岁,她说:“大黑树林属于曼拱二队,只有四户人家,之前只有三户,最近有兄弟俩分家,新增了一户。”彭家姊妹五个加上父母,总共七个人,按人口来分茶地,所以分到了很多茶地。
郭龙成抓了一点大黑树林的细叶子冲泡茶叶,虽然黑云压城,但天气还是异常闷热,一杯茶之后,暑气消散,两腋生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