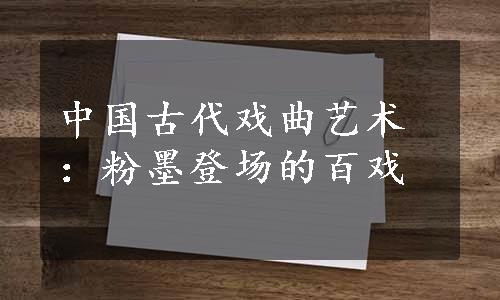
秦统一六国之后,每灭一国,就在咸阳城仿造一座该国宫殿,以该国的女乐倡优充之,又在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大兴宫观,集中演出各地的歌舞艺术。这对歌舞艺术和倡优之技的传播无疑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汉代,随经济的发展和儒家思想的传播,巫觋歌舞也逐渐世俗化为娱乐人的性情的歌舞,“人味”的增加,使这些大型的歌舞表演不必再拘泥于祭神驱鬼的目的,可以更随意地进行表演。在汉代,文化艺术呈现一片繁荣景象,除歌舞艺术大为流行为,还盛行诸如吞刀、吐火、扛鼎、爬竿、走索、角力、扑跌等多种多样的杂技和竞技表演,这些技艺连同歌舞,统称为百戏。戏曲史家普遍认为,汉代百戏与中国戏曲的产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其中以角抵表演为主的《东海黄公》和以歌舞为主的《总会仙倡》便是常常为戏曲史家所引用的例证。张衡在《西京赋》里记述了这两种表演。他是这样描绘《总会仙倡》的:
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箎。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委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而襳衤两。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磅磕象乎天威。
艺人们装扮成豹、罴、白虎等动物,女英、娥皇、洪涯等仙人,载歌载舞。舞台的景物还随表演的变化而变化,摹拟出了飞雪、响雷等戏剧效果。在这里,虽然没有什么戏剧故事,但其不仅歌舞与扮演因素相结合,而且从演出规模、化妆、景物、效果等方面看,其演出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和《总会仙倡》相比,《东海黄公》有了故事的成份,《西京赋》里也记录了这个故事:
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
东晋葛洪整理的汉代刘歆专记西汉轶事的《西京杂记》里的记载更加详尽:
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
根据这两条记载可知,这个表现黄公欲制服白虎又终因饮酒过度和年老体衰而为虎所伤的简单故事,是由两个演员分别装扮成黄公和白虎而进行的依照事先设计编排好的简单故事情节进行的有机的戏剧表演,虽然不能说它是成熟的戏剧,但其中的戏剧因素已相当多了:第一,《东海黄公》已有一个虽然简单却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在这个故事中,人们既可以看出黄公老骥伏枥的不老心,又不能不感触到东汉人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方生术士当道,人们渴望真的能如他们所宣扬的那样,凭借法术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长生不老,然而生老病死这样的现实却是人们不能不面对的;另一方面,“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这样的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来的学说,大大贬低了君主之外的人的地位,在君主和授权给他的神面前,人们不得不自感卑微和软弱。因而在这出小戏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对巫师、术士、神仙方术的讽刺,而是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意识:相对于法术的永恒威力,沉溺于现实生活欲望(黄公所嗜之酒为其象征)中的人是渺小无能的,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衰老和死亡。因为有了这些内容,它就不仅仅是一出角抵戏了。第二,它有台词,虽然不会有后来的完整的歌白,但因要“祝”而厌之,所以念念有词的独白是肯定会有的。第三,有演出的“穿关”——“绛缯束发”。第四,有道具“切末”——赤金刀。“尤其重要的是人与虎斗这个冲突矛盾对立斗争的戏剧行为,这个行为表现了明确的思想倾向性,为纯粹的角抵戏所不曾有而又不可能有的。”[4]
春秋战国之际,我国除有以歌舞祀神的巫觋外,还出现了一大批女乐和倡优(又称优伶、俳优等,多由侏儒充当)。《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了优孟和优旃的讽谏故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优孟衣冠”的故事:
楚相孙叔敖……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为何?”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
优孟因扮演孙叔敖而使孙的后代得以安身立命,这中间的扮演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至汉代,象优孟这样的俳优的滑稽表演也有所发展,但讽刺的对象已转向官吏,使盛行于唐代的参军戏具备了雏形。
在两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里,虽然长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严重影响了民间的艺术表演,但也许正因为战乱使朝代更叠频繁,人们生活朝不保夕,更使各朝统治者全都纵情声色,在各地遍选歌舞。加之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为汉民族文化注入的新的活力;佛教、道教大盛,在各种宗教仪式中也大量采用百戏表演。因为这许多原因,各种歌舞百戏在这一时代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其中那些与后世戏曲形成关系比较密切的带有装扮性的歌舞、傀儡、滑稽等表演,更是大兴于世:(www.zuozong.com)
梁设跳跦剑、掷倒、猴幢、青紫鹿、缘高纟亘、变黄龙、弄龟等伎。陈氏因之。后魏道武帝天兴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戏。造五兵角抵、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白武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人车、高纟亘百尺、长 、跳丸,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北齐神武平中山,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百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后周武帝保定初,诏罢元殿庭百戏。宣帝即位,郑译奏徵齐散乐,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抵之流也。而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鱼龙曼衍之伎,常陈于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5]
窟遊子,亦云魁遊子,作偶人以嬉戏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齐后主高纬尤所好。[6]
石虎性好佞佛,……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又十余木道人长三尺余,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拜,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7]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歌舞百戏还是傀儡戏在南北朝时都有很大的发展,各类表演艺术的充分发展及其中的扮演因素的增加,为中国戏曲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
【注释】
[1]《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2]转引自《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21页。
[3]《中国历代文论述》,第1册,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
[4]董每戡《说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
[5]马端临《文献通考》。
[6][宋]庄季裕《鸡肋篇》。
[7][晋]陆岁羽《邺中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