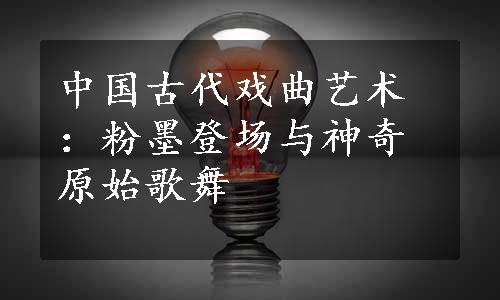
中国戏曲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对于中国戏曲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有“巫觋”说、“源自梵剧”说、“古优”说、“歌舞”说、“傀儡”说等诸种单体起源论点,也有以周贻白为代表的“长期综合形成”论。戏曲作为一种综合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熔各项艺术手法为一炉、至今仍有几百种地方戏曲广为流传的综合性艺术,它的起源不应是单源头的,而应是多源头长期综合发展的结果,它以各种表演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为前提。原始先民为了祭祀和自娱的原始歌舞活动,就是戏曲产生之前已经蕴含了戏曲因素的表演艺术。
原始歌舞几乎被公认为是后世一切文学与多种艺术样式的始祖,其状貌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淹没无闻了,但从古代典籍的简单记载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其中一些与戏曲相关的因素。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尚书·尧典》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革各置缶而鼓之,乃拊石以象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吕氏春秋·古乐》
虽然无从考证当时的原始歌舞的表演场面究竟是什么样的,但仅从一般的逻辑来看,这种百兽率舞的恢宏景象,不可能是真的动物在圣人的召唤下,面对圣人灵光的朝拜,它实际是人类对自己狩猎对象的装扮活动,而被称作“百兽”的各种动物,则可以看作是今日戏曲角色的萌芽。
在原始社会,人们还很难将自己从对象世界中分离出来,处在这种思维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的人们,很容易对他们无法认识和征服的世界产生恐惧和泛神论的崇拜;与此同时,在他们还比较简单的头脑里装着这样一种想法,即人们可以将自己装扮成日常生活中常见到的对象和神灵,通过扮演活动便有了对象和神灵的物性和神性。在这样的装扮活动中,巫觋(女性曰巫,男性曰觋。据《说文解字》解释,所谓巫就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这种专门的神职人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可以通过装扮,代表人向神传达人的意愿和祈求,代神向人传达神的谕示。巫觋的出现,为戏曲提供了虚拟的表演性和心理欣赏性这两种很重要的戏剧因素,因为在巫觋活动中,神由人扮演,用以娱神,同时,这些由人扮演神又可以具有人的感情,可以娱人,可能正因为这样,王国维才确认这种活动为“后世戏剧之萌芽”。他说:“周礼既废,巫风大兴……盖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凭依……或偃塞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1]春秋战国时,巫风极盛,在从事祭礼活动的巫觋中,会有人从衣服、形貌、动作上装扮摹拟神,人们就会把他们看作神的凭依,甚至会直接把他们当作神。这其实是一种雏形的戏剧演出,这里有演员的虚拟表演,有角色的特性(衣服、形貌、动作等)。在下面我们列举的当时比较著名的祭祀活动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戏曲因素的存在。(www.zuozong.com)
傩舞。傩舞周时已十分盛行,主要是用来驱鬼,据说驱鬼时要发出“傩傩……”的声音,所以有了这样的名称。全国上下一起举行的叫大傩,一般在年终举行。领舞者是由人扮成的一个能驱疫避邪的神,称方相。他身披熊皮,戴着四只眼睛的面具,黑上衣,红裤子,一手操戈,一手执盾,率领由人装扮的十二兽等大队人马跳跃呼号,驱鬼遣灾,遍及各个角落。
八蜡。八蜡又称大蜡,是年终时为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祭祀活动,《东坡志林》对此作了较明确的描述:
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祭必有尸,无尸曰奠,始死之奠与释奠是也。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以丧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子夏观蜡而不悦,孔子譬之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盖为是也。[2]
大致说来,蜡祭的场面便是这样:巫觋扮成古君子,驱使禽兽,迎来人扮成的猫和虎。猫虎则是消灭鼠害和凶猛野兽的神灵的象征。这种据传创史于上古伊耆氏(神农)时代的祭祀活动,是氏族成员可以开怀畅饮、尽情欢乐的日子,同古希腊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中古希腊人的纵情享乐相似。在这肃穆的对农业之神、田地之神、禽兽之神和已死的农业官员的祭祀仪式中,还穿插进了一段非常世俗化的罗氏男子把鹿送给心爱的姑娘的故事。可以这样说,在八蜡中,有了虚拟的扮演,有了如痴如醉的观众,还具有了娱神同时娱人的功能和内容成份,这样便在率百兽起舞的原始歌舞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戏剧因素。
《九歌》。先秦诸国中巫风最盛的是楚国。屈原所创作的《九歌》,记载了巫觋祀神歌舞中最接近于戏剧形态的一种范例。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3]屈原据楚民间祭神歌舞加工成的《九歌》共十一章,除末一章《礼魂》为送神曲外,其余各章均各祭一神。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当时演出的情况,但从歌词中,对其恢宏的场面仍可窥其一班:一群男女巫师身着华丽的衣衫,在布置好的场地上,在声箎等乐器的伴奏下,载歌载舞。表演者除了表达对神的热烈礼赞外,更多地是通过让神具有人的情感而表现人世感情,湘君、湘夫人缠绵悱恻的情怀和期而不至的哀婉流连,俨然恋爱中的男女;大司命忧郁伤感;小司命沉默怅然;河伯风流多情;山鬼幽怨情深……这些都是在以祭神、娱神的形式抒发人的感情。人们不再仅仅停留于摹拟神的外貌,而是让神有了个性和人的感情色彩。从《九歌》祭礼演出中,我们可以看出,戏剧中的扮演和观众因素具备而外,还有了角色性格的塑造,这些,都向戏剧的产生迈进了一步。
从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在原始歌舞中,从两个方面体现了一种“神人以和”的文化境界。首先,这些歌舞是以人扮演神,并且用以祭神娱神,人(巫觋等神职人员)通过把自己装扮成神,而有了神的威力,人就是神,从这个意义上看,是以人去迎合神;其次,这些由人扮演的神,逐渐摆脱了其或威严、或恐怖的特性而有了人的感情和性格,鬼神就是人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是鬼神迎合人。神,是原始生民对于自己不了解的外在于自己的世界的人格化。人类的祖先就如同智慧未开的儿童,还不能将自己和对象世界区分开来,在他们的心目中,任何事物都象自己一样具有生命,于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就有了农神、田神、山鬼、河伯……已死的祖先也加入了神灵的行列。在这万物有灵的思想背景下,一些戏剧因素在慢慢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
对于原始歌舞,还应作一点这样的交待:这些原始歌舞也许本身淹没无闻了,但在民间,仍可看到一些它的活化石被保留了下来,比如江西、贵州、云南等地至今仍在上演的傩戏,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远古傩祭的成份。再比如,在边远的农村,还存在着一种“跳大神”的巫术活动。一些被称为“仙翁”、“仙姑”的类似于远古巫觋的人常被邀请到詈受灾难的农家。他们经过一番念念有词、上窜下跳的表演之后,便会开始替他们要请的神灵或附身于病人身上、活动在凶宅之中的鬼怪讲话。“跳大神”作为一种封建迷信活动一再被有关部门反对和取缔,但它至今仍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流行,也许与它来自遥远的古代,其影响已根深蒂固有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