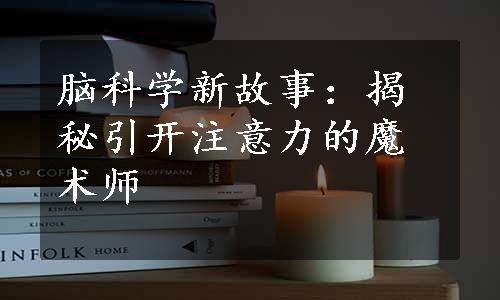
魔术历史久远(图4.6),也许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埃及,是娱乐公众的艺术表演,在各种文明里都有;而脑科学则是近代才蓬勃发展起来的严肃的科学研究,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确实在很长时间里,两者之间很少有关联,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改观,产生了一门新学科——神经魔术(neuromagic)。这是因为神经科学家认识到,魔术师除利用道具和特殊手段之外,还利用了观众的错觉,不仅利用刺激后像等感觉错觉,还利用认知错觉,就像我们上面讲到过的疏忽盲和变化盲。如同视觉科学家利用视错觉来研究视觉系统一样,认知神经科学家也利用认知错觉来研究认知机制。正如克里克所言:“心理学家之所以热衷于研究视错觉,就是因为视觉系统的这种部分功能缺陷,恰恰能为揭示该系统的组织方式提供某些有用线索。”[1]对于疏忽盲和变化盲这样的认知错觉也可以说类似的话。利用几千年来魔术师所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和技术——其中有许多是传统的神经科学家都没有想到过的,结合现代脑成像和其他记录技术,有可能使神经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更加有效地研究注意和觉知的问题。
图4.6 16世纪画家博斯(H.Bosch)的一幅油画《魔术师》(The Conjurer) 请注意当一位观众正全神贯注地观看魔术师的表演时,一个小偷在偷他的东西,而他却浑然不觉——典型的疏忽盲。这幅画现收藏于法国的Musée municipal de St.-Germain-en-Laye。
“变服”的秘密
聚光灯照在魔术师的那位美丽女助手身上,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紧身服,艳光四射,吸引了所有观众的注意。魔术师汤普森(J.Thompson,艺名Great Tomsoni)郑重其事地向观众宣布:他要在一瞬间把她的白衣服变成红衣服!观众俯身向前盯着女助手仔细观看。汤普森轻轻击掌,聚光灯瞬间暗了一下,旋即射出一片红光,女助手遍体通红,当然白衣也变成了红色。观众一片哗然:难道这也能叫魔术?
魔术师站到台前,看上去为他开的玩笑很是得意。他向观众致歉,说是跟他们开了个玩笑。观众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到美丽的女助手身上。他又击了一次掌,灯光再次转暗了一下,然后一片白光大放光明,女助手的衣服当真变成了另一件红衣服!那么,汤普森是怎么做到的呢?
当汤普森向观众介绍他的助手时,她的一身紧身白衣使观众想当然地认为,在这件衣服里面绝不可能再穿另外一件衣服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假定。美艳女郎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这正是魔术师想要的效果,这样观众就注意不到地板上的机关了。另外,观众越是盯着助手看,他们视网膜中的神经元就越是对照在助手身上光的亮度和颜色产生适应。当汤普森在“开玩笑”以后致歉时,观众的视觉正经历着一个适应过程,而当把恒定的刺激撤掉时,已经适应了的神经元会产生某种“回跃”或者说撤刺激“后发放”,因为这时的适应刺激是那件被红光染红了的衣服,汤普森知道观众的视网膜神经元在灯光变暗时会在几分之一秒里产生回跃,所以观众在这段时间里会在女郎身上依然看到这种红色的后像。而就在这时,舞台地板上的一个活门短暂地打开了一下,一条观众看不见的细绳把助手用尼龙搭扣搭在身上的白衣服拖了下去。然后场内重又大放光明。除了撤刺激后发放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使观众上当了。首先是在把白衣拉下去以前灯光非常亮,这时的视杆细胞已经饱和了,所以在灯光转暗时,它们不能起作用,而视锥细胞也只有在强光之下才起作用,因此在灯光变暗的瞬间,观众实际上是睁眼瞎子,根本看不到细绳和白衣的快速运动;其次,当汤普森真正表演时,正在他道歉说开了个玩笑的时候,以至观众都认为这只是其他节目开始之前的一个玩笑,事情已经暂时结束,就在关键时刻放松了注意!也就是发生上节中所说的疏忽盲。
飘失的球
魔术师在台上把球抛向上空,等它掉下来时接了再抛,抛了接,接了抛,从不失手。最后他把球藏在掌中,佯作再次上抛,他的眼睛盯着那个想象中抛向半空的球的飞行轨迹。大多数观众感到,那个其实根本就没抛出去的球在上升,然后在半空中消失不见了。这种魔术也部分地利用了认知神经科学里所谓的“启动效应”。也就是说,以前呈现过的刺激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人对后面类似刺激的反应,受试者甚至可以根本记不起以前看到过这种刺激。例如,在屏幕上很快地显示包括“无巧不成书”在内的一连串成语,每个成语的呈现时间都很短,以至受试者根本不记得看到过它们。然后,要受试者在“无”字后面续上一些字成为一个成语,受试者多半会填出“无巧不成书”,这就是启动效应。同时,魔术师还利用了重复对人产生的心理影响,因为每次他都用同样的姿势向上抛球然后接球,所以观众想当然地认为,后一次也会如此。英国心理学家兰德(M.F.Land)发现,那些自称看到球在半空中消失不见的观众,其视线并没有追随那个虚幻的球。他们的视线从来也没有在他们所声称的自己“看到了”球在半空中消失的地方停留过。所以,使观众产生这种错觉的并不是他们的眼球运动,而是魔术师的头和眼球的运动,因为正是这些运动把观众的注意力(而不是他们的视线)吸引到了他们以为球会经过的路线。使观众上当受骗的是他们的脑,而不是他们的眼动系统!科学家发现,无论是真的有球在上抛,还是观众以为有球在上抛,在这两种情况下同一些脑区活跃了起来。正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激活的是同一些神经回路,无怪乎观众“看到的”上抛的球会那么栩栩如生。而更好玩的是,观众看到球消失时的高度,甚至比前几次它实际达到过的还要高,似乎视觉系统对此还做了外推。
选择盲
瑞典心理学家约翰松(P.Johansson)和哈勒(L.Hall)发现,魔术表演不仅利用了上节讲过的变化盲和疏忽盲,有时还利用了所谓的“选择盲”。他们让不知内情的受试者看许多对头像图,并让受试者说出自己对其中哪一张更有好感。有时候,还会要受试者说出为什么有好感。在受试者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他们偶尔运用从魔术师罗森格伦(P.Rosengren)那儿学到的手法,偷偷地把某对中的两张正好换了个儿。然后再给受试者看,他们选定有好感的图(其实其中有的已经给调包了)。能识破这一点的受试者仅占26%。更有甚者,当他们没有发觉调换而要他们说出挑选这张图的理由时,他们居然都编造出了一套挑选的“理由”(图4.7)!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选择盲(choice blindness)。
图4.7 选择盲 (a)给受试者看两张头像图,问他更喜欢哪一张;(b)受试者挑选出其中的一张;(c)在受试者不加注意的情况下,实验人员偷偷地把两张图对调了一下;(d)受试者取出的其实是他最初不那么喜欢的一张,但是他依然讲得出当初这样挑选的“理由”。(改自Macknik et al.,2008)
街头上的“魔术师”
对于魔术师,我得道个歉——我把扒手也称为“魔术师”了,尽管打上了引号。我这样借用“魔术师”的称号,是因为扒手利用的也是受害者的疏忽盲。其手法和原理跟魔术一样,只不过这是一种引人烦恼的“魔术”而已。在南欧某些国家的街头,当您在一片林荫大道上信步时,突然上空掉下一堆鸟粪样的东西把您的新衣服弄脏了。而正当您为此烦恼之际,“及时”地来了两位“好心人”,他们拿出餐巾纸,打开瓶装水,一面忙着蘸水帮您擦掉污物,一面和您聊起了家常:“您是从哪儿来的呀?”“您的英语讲得真好。”“现在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我喜欢中国人,我真希望能到中国去一次。”……就这样分散了您的注意力——您把注意力都放到弄脏了的衣服上,心存感激遇上了好心人,聊起了家乡……而这时扒手就在您的眼皮底下,从您的口袋或背包里,把您的钱包给偷走了,而您还不知道呢!
上述扒手和扒手“大师”罗宾斯(A.Robbins)比较起来,那又小巫见大巫了。罗宾斯有一次甚至偷了美国前总统卡特(J.Cart)保镖的手表、钱夹、警徽、绝密行程,乃至卡特的车钥匙!他有点像美剧《猫鼠游戏》(White Collar)里那位风度翩翩的盗贼卡夫瑞(Caffrey)。现在,罗宾斯和神经科学家而不是警察合作起来,揭开扒窃、魔术以及注意机制之谜。
2007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意识魔力学术讨论会”(2007 Magic of Consciousness Symposium)[2]上,当着满屋子200多名神经科学家的面,罗宾斯气定神闲地当众表演了他的扒窃术。他从与会者中随便挑了个对象,以为这也是一位科学家,其实他挑的对象约翰逊(G.Johnson)是《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大家都满怀兴趣地看着罗宾斯怎么做。他对约翰逊说道:“现在我要轻轻地碰碰您,这只不过是要看看您的口袋里究竟有些什么。你们这些科学家总是带了很多东西。”他继续絮絮叨叨地说下去:“你们口袋里有那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从哪下手。啊,这是不是您的啊?”他把一样东西往约翰逊手里一塞。约翰逊低头去看。罗宾斯解开了约翰逊的上衣袋,“里面有支笔,这可不是我想要的。那边那只口袋里的是什么呀?”约翰逊不由得抬头去看。“或许是一张餐巾纸或是抽巾纸什么的,您有那么多东西都把我搞糊涂了。您知道,坦白说我不太确定以前是否扒窃过一位科学家。以前我掏人口袋时从来也不曾为这编过目录。”
他这样滔滔不绝,绝不是无的放矢。滔滔不绝地发议论也是魔术师摆弄他人注意的工具箱中的一样重要工具。扒手当然得有一副巧手,但是流畅而亲切的一大串话也是吸引、误导和分散他人注意的法宝。罗宾斯在告诉约翰逊某件事时,他的双手正在做另外两件事呢。这就意味着,约翰逊最多也只有1/3的机会能注意到他有东西丢了,实际上这种机会还要低得多。他不断地碰到约翰逊全身各处:肩膀、手腕、衣袋、大腿……正当约翰逊想要跟踪这一切时,罗宾斯的另一只手已伸进了他的口袋。罗宾斯不断地说话和触碰,把约翰逊的注意力完全从他正伸手去偷的地方引了开去。
就这样,罗宾斯偷走了约翰逊的笔、日记本、数字录音机、钱包甚至手表。当他握着约翰逊的表带时,拼命挤压,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触觉后像,这种后像使约翰逊的皮肤和脊髓中的触觉神经元对表被拿掉不敏感,并且使他产生在表实际上已经被偷走之后表还在那里的错觉;另外,开始时的强烈挤压使受害者的触觉感受器产生适应,而将表偷走后的后像则使受害者更难于觉察。当罗宾斯喋喋不休地转移约翰逊的注意时,他把双臂伸到背后把表戴到了自己手上。(www.zuozong.com)
罗宾斯不时地把他偷到的东西在约翰逊的头后高高举起,这引起了其他人的哄堂大笑,约翰逊窘迫地边笑边朝周围张望,不明白究竟是什么那样可笑,这样反而引起更多的笑声。然后,罗宾斯把约翰逊的东西一一归还他,最后转身对约翰逊说:“我们大家想买块表给您,这块表和您来这儿时戴的非常相像。”然后他从自己的手腕上把表解下来递了过去。可怜的约翰逊目瞪口呆,不明白自己怎么会那样地粗心大意!
形形色色的注意
在本章的一开头我们就介绍过,有两种不同的注意,有意识的、自上而下的注意和不由自主的、自下而上的注意。其实,注意的形式还不止于此,例如有目光盯着目标看的“外显注意”(overt attention)和虽然目光并不停留在目标上,却用余光注意着目标的“内隐注意”(covert attention);另外当您(特别是如果有许多人)把目光专注地投向某个目标时,也会吸引他人去注意这个目标。心理学家喜欢把注意比喻为某种心理上的聚光灯,当您把注意的聚光灯投向某个目标时,其他的一切都被忽略了。魔术师和扒手都是利用了这种忽略。
由于有多种形式的注意,很可能有多个注意控制中枢在协同工作。眼动回路在注意中可能起重要作用,正是它把注意的聚光灯投向目标。魔术师经常通过操控您的视线,让您注意一些无关的细节,从而忽略了他的真正手脚。感觉皮层则接收周围环境中突出的刺激,这是自下而上注意的基础,而前额叶皮层则是自上而下注意的CEO。当您有意识地要注意某个特定目标时,高层次的视觉系统加强了低层次回路的激活程度,增强了它们对感觉刺激的敏感性,且同时抑制了其周围神经元的活动。对某个目标越是注意,对其他的遏制也就越发强烈。当您看魔术时,您越是想揭开其中的奥秘,就越是集中注意力看某个目标,对其他的一切也就越是浑然不觉了。那个目标正是魔术师装腔作势引诱您去看的诱饵,他此刻大动手脚之处却在这个目标之外,然而您对此了无察觉。
罗宾斯正是利用这一点的大师。他从您的上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他问道:“这枚硬币是您的吗?”您明明知道没有人会把一枚硬币放在胸口的衣袋里,但您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去看它。他又问:“这枚硬币是哪一年的?”但是字太小而且字迹模糊,因此您伸手到上衣袋里去摸您的眼镜,而它却早已不知去向了。罗宾斯从自己的脸上取下一副眼镜递给您,并说道:“试试这一副吧!”您一看正是自己的眼镜!当您全神贯注看硬币上的年份时,您对他伸手从您衣袋里取走眼镜一无所知。
扒窃大师的秘密
罗宾斯在“偷”完约翰逊之后,面向观众问道:“现在你们是否想知道,我是怎样偷偷做到了这一切的?”魔术师一般都不愿意透露他们的秘密,不过罗宾斯这次到拉斯维加斯来可不是为了演出,而是向科学家传授他的看家秘技。
罗宾斯把吸引观众去看之处称为一个“场景”(frame),场景可大可小。罗宾斯说道:“您不由自主地会去看我布置的场景。”他边说边表演,他抓住约翰逊的手,装着要把一枚硬币塞到他的手心里去,但实际上他是用他的拇指在约翰逊的掌心里产生挤压的感觉后像。罗宾斯解释说:“要紧紧地挤压。”约翰逊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手,这就是罗宾斯要他看的一幕“场景”。他还在那儿挤压。“您拿到硬币了吗?”约翰逊连连点头,他以为确实如此。罗宾斯说:“松开您的手掌。”手掌里什么也没有。罗宾斯说:“看看您的肩头吧!”一枚硬币正放在他的肩头呢。
罗宾斯解释说,要是一个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某个场景上,那么他对场景之外的一切都茫然不知,比如说把一枚硬币放到他的肩膀上。罗宾斯说,诀窍就是要在适当的时候把您的注意力引到适当的地方。
魔术师利用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一些原理,来操控您的注意力聚光灯。罗宾斯称自己为一个“民间心理学家”,“关键是要有懂得人的心智是如何工作的天分”。其中之一是“感觉吸引”(sensory capture):新奇的、特别亮的、闪烁的以及运动的东西总是会吸引您的注意,想想看从帽子里展翅飞出的鸽子吧!在这种时候,魔术师就可以动他的手脚了,正如魔术师所说:“大动作遮住了小动作。”
魔术师絮絮叨叨地说话,也使您在自己的头脑里跟着进行自我对白,这会降低您的反应速度。另外,放松您的注意力也是手法之一,故意让您以为一切都还不会马上开始,事情或许就已经结束了。本节开始时讲的白衣变红裳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内斯-康德(S.Martinez-Conde)现在和罗宾斯建立起合作关系。她说道:“我希望魔术师所制造的认知错觉,能帮助科学家认识觉知,就像视错觉帮助我们理解视觉一样。”另外,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些在自然界罕见、多半人为制造出来的错觉图像愚弄了我们的头脑,而怪罪人类的头脑不行。我们更应该感到惊奇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我们的视觉系统能够根据不完全的信息,迅速得出正确的结论。对于生存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迅速得出正确的结论(只是偶尔也会犯错误),要比绝不犯错误但是耗费大量时间更重要,须知生死存亡往往取决于瞬间之差!同样,我们也不要怪罪我们的头脑会受到魔术和扒窃的欺骗(当然,无论是谁,如果遭到扒窃,都会非常烦恼),相反,我们应该惊叹在绝大多数自然情况下(除了像魔术和扒窃这样人为制造出来的例外),我们的头脑能够那么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集中处理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而把次要问题弃置不顾。
如果您想一睹罗宾斯的神技,可以登录网站:
http://sleightsofmind.com/media/magicsymposium/Apollo
笔者从里面看到的第一幕也是最简单的一幕,就是罗宾斯把受试者贴在自己额头上的硬币变没了。其内容大概是这样的:罗宾斯把一枚硬币贴在自己的额头上,然后要女性受试者也把一枚硬币贴在她自己的额头上,然后罗宾斯把手伸到她的额头上说,需要把硬币贴牢一点。就在他紧按硬币一会儿之后,当他缩回手的时候,顺手轻轻地把她额上的硬币取走了。由于强刺激的后效应,受试者以为硬币还在自己额头上,而罗宾斯滔滔不绝的话语又分散了她的注意力,使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她额上的硬币已被取走。紧接着罗宾斯要她自己再去摸,自然已经是“钱去额空”而令她惊奇不已了。这一切就那么简单,当然后面的表演可就复杂多了。不过笔者还是卖卖关子,让读者自己去看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