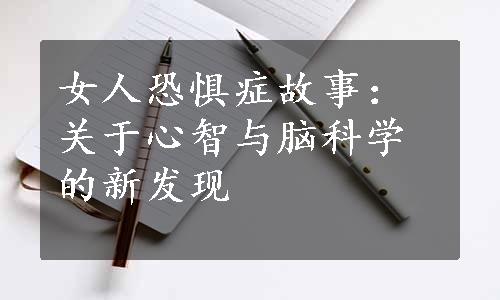
1999年12月初,在一个像早春般的晴朗日子里,当利平(R.Lippin)坐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Columbia-Presbyterian)医疗中心的检查室里等待做脑成像检查时,她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横跨在赫德逊河上的乔治·华盛顿桥。仅仅在不久以前,她只要想到驱车过桥就会充满了极度恐惧。
利平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做过律师,后来当了专门治疗恐惧症的治疗师。她回忆为了避免在桥上被堵塞在车里,“我想尽办法弄到大桥24小时监控室的电话号码,我会打电话给他们,并问他们:‘我知道这听上去有点疯狂,但是我现在正在车里,我在为过桥发愁,我想知道桥上路面是否通畅。’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话,我就不上桥”。这是一种无名的恐惧。如果利平不事先打听好就一往无前,而到了桥中央动弹不得,那么她就会恐惧起来,感到落入了某种陷阱,受到了某种威胁,接着可能会出什么事……简而言之真的像疯了一样。事实上,她确实也有陷在车阵里的时候,然而她从来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但是像她那样的恐惧失常症患者,在生活里老是竭力避免某些情形,他们害怕在那种情况下会出什么其实从来也不会发生的事故。
利平还有其他的恐惧。那还是在1987年的时候,就在她愉快地完成了有关法律的三年学习之后,她听说自己需要到布鲁克林[1]去进行律师考试,这使她惶惶不安,因为这意味着她需要在两件都被她视作噩梦的事情中选取其一:不是过桥,就是走隧道。后来,为了克服她乘地铁的恐惧感,她不得不找了一位朋友,在曼哈顿一会儿向北,一会儿向南转了三次地面车辆,花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才到达目的地。
对于恐惧和焦虑的本质问题,科学家已经研究了一个多世纪了,但是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医学界才正式把焦虑失常归为独立的一类,其中包括恐惧症、PTSD、焦虑等,还常常伴有忧郁。这已成为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一类精神疾病,光在美国就有超过2 000万的患者为此所苦。因此,对此类疾病发病机制和治疗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戈尔曼(J.Gorman)医生是一位精神药物学家,他通过对患者做脑成像,研究当患者感到恐惧时,脑的哪个部位会激活,这些活动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又如何因人而异,以此评估药物或心理治疗的疗效,并研究新的治疗方法。利平就成了这种研究的一名对象。
利平的恐惧症始自1976年夏,当时她还只有十几岁,正在访问荷兰的一个农场家庭。她至今还能想起,那栋坐落在广阔田野中央的小农舍,她能回想起和她的荷兰女主人百无聊赖地闲聊,突然一阵恐惧袭来。她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正坐在田野中央,广阔无垠。我至今还记得这片田野的辽阔。我当时说,想在那天晚上和一些朋友聚一下,女主人说她从不在晚上出去,而正是这些话触发我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立无援的感受,而后……一股肾上腺素一涌而出,光这一点就意味着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然后是汗出如浆、心悸和手掌湿漉漉。这种感觉就好像您刚做完了一场有氧锻炼,您完全筋疲力尽了。”这就是为什么,恐惧症患者总是感到筋疲力尽。
传统的观点认为,恐惧(和焦虑)是有理性的心智和不理智的心智之间的一场战争,也就是在人性的理性和动物性的恐惧之间的一场斗争。这一观点的现代形式是,这是一场在有意识的“自传性”记忆和下意识的情绪性记忆之间的斗争。20世纪末对人所做的实验发现,恐惧感在脑中至少有两条不同的通路:其中的一条要经过脑的高级皮层区(和思维有关的脑区),而另一条则是高速的、不被觉知的通路。神经科学家早就知道,脑处理图像和声音(包括那些有威胁性的图像和声音)的速度是毫秒级的,而要产生即使是最简单的思维,也需要几秒钟。神经科学家通过动物实验表明,脑中非理性恐惧的神经通路都要经过杏仁体[2]。
美国神经科学家卡普(B.Kapp)从1979年开始,研究心率和恐惧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发现,从脑干发出控制心率的神经也传到杏仁体,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这些神经传到杏仁体中比一个针头略大一些的神经核团——中央核(central nucleus)(图3.1)上。这个核团正是当您听到巨响、感到有地震等时立即引起恐惧的脑区。当这个核团兴奋时,由此发出的神经就控制心率、血压、出汗、呼吸、僵住不动等。杏仁体发出的另一些神经,则继续投射到脑的高级区、控制释放应激激素的脑区(它可能对非理性恐惧起到关键的作用)、皮层和感觉区。因此,当有威胁来临而需要及时应对时,警讯传遍脑各处。卡普说道:“我们的一条假设是,这些投射中有许多增强了警觉,您把感觉之门大开,并更为有效地处理信息。”
图3.1 中央核在杏仁体中的位置(www.zuozong.com)
美国神经科学家勒杜(J.LeDoux)从另一个角度对杏仁体进行研究。他先给大鼠听某种纯音,然后施以轻微的电击,他用这种方法建立起大鼠对声音的恐惧条件反射。然后,他追踪脑把声音转换到恐惧反射的神经回路。他发现,听觉信息首先到达丘脑听区,然后继续进入杏仁体中的外侧核(lateral nucleus)(图3.1、图3.2)。对大鼠而言,引起恐惧的声音信息从耳朵传到杏仁体只要12毫秒就够了。他声称,这种核团“学习”和记忆恐惧刺激不仅速度很快,而且非常牢固。一次惊吓的经历可以形成终身不忘的情绪性记忆,而且还很难消除。虽然可通过在以后屡次给予声音时不同时施以电击,来消除这种恐惧反应,但这只是脑对这种反应加以控制的结果,而不是真的清除掉了这种恐惧的记忆痕迹,因为在以后,这种恐惧反应有可能自发地重新表现出来,或是因另一个与声音无关的应激刺激而又死灰复燃。类似地,紧张也能在人身上重新引起已经医治好了的恐惧症。这些都说明,在行为上不表现出恐惧反应,并不意味着关于恐惧的情绪记忆已经完全消除干净了。他们通过毁损鼠的部分听觉皮层的方法,发现听觉皮层对建立此种恐惧条件反射并非必要。但是,如果毁损了中脑听区和丘脑听区,那么就不再能建立此种条件反射。他们进一步发现,丘脑听区的某些部分有神经元联结到皮层下结构,最后发现引起恐惧反射的通路是到杏仁体的通路。他们和卡普有类似的发现:毁损海马中央核之后,当动物受到引起恐惧的刺激时血压不再升高,动物也不表现为木僵状态。与此同时,美国神经科学家戴维斯(M.Davis)研究了另一条恐惧通路:从感觉器官到丘脑,再到达皮层,然后从皮层下达杏仁体。通过皮层的通路使我们能更精确也更细致地看清或者听清危险,但是其代价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自然界中,生死往往就取决于一瞬间(图3.3)。勒杜实验室的摩尔根(M.A.Morgan)发现,如果毁损了部分前额叶皮层,那么就很难再消除情绪记忆。
图3.2 鼠脑中和听觉-恐惧条件反射有关的结构 (a)鼠脑,其中右侧的切面图显示于(c),而左侧的切面图则显示于(b)。(引自LeDoux,1997)
以上研究表明,到达杏仁体有两条不同的神经通路,由此得以形成和恐惧有关的两类不同记忆。勒杜研究的通路并不先进入脑中和思维有关的部分,这就使像利平那样的人下意识地体验和习得许多恐惧性的情绪记忆,而甚至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引起心脏狂跳。脑成像研究也支持了人可能下意识地产生恐惧和焦虑。
图3.3 传导恐惧信息的两条神经通路 当人走在林中小道上时,可能在枯树旁边看到枯枝样的东西——一条响尾蛇!这一视觉形象首先到达丘脑视区(深灰色椭圆)。由此“兵分两路”,一路直达皮层下的杏仁体(黑色椭圆),这会立刻引起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肌肉收缩——人立刻后退!从视丘出发的另一条通路继续上行到达视皮层,经过一系列分析,最后识别出这确是一条响尾蛇。从皮层出发的精确信息继续下行到杏仁体,使人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尽快逃走。当然也有可能视皮层经过分析,最终认出这只不过是一堆枯枝,这个信息到达杏仁体,“警报”解除,使一切恢复正常,人继续前行。如果只有后一条通路,那么人必须认出这确是一条响尾蛇之后才后退,而在此之前,蛇牙可能已经咬进小腿!另外,如果只有前一条通路,那么即使前面确实只是一堆枯枝,也把人吓得掉头就逃,从而错失在前面不远处的野果。(引自LeDoux,1997)
美国医生惠伦(P.Whalen)等人,让受试者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内,同时显示给他看一张恐惧的脸的照片,持续33毫秒,紧接着更长时间(167毫秒)地显示一张毫无表情的脸,这样后者就“掩蔽”了前者。也就是说,受试者并不有意识地觉知到看见过那张恐怖的脸。事后问他,他也记不得有这样的事。但是脑成像表明,在显示恐惧的脸那段很短的时间里,杏仁体被激活了。而当撤掉了这张脸以后,或是一开始时用一张愉快的脸来替换恐惧的脸,那么杏仁体就没有被激活。因此,虽然短暂的恐惧刺激为其后长时间的中性刺激所掩蔽,而使受试者不能有意识地记得看到了它,但是这种刺激依然在脑中留下了痕迹,不过只是处于下意识的状态而已,并且可能在刹那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当利平通过了律师考核,并开业替房客和房东打官司时,她已接受了10年之久的抗抑郁药物的治疗。开始时,这种药物确实缓解了她的症状,不过后来情况甚至变得更加糟糕。她也试过许多种不同形式的心理治疗,疗效也不理想。1987年她偶然被介绍到一位认知行为治疗师那儿去转诊。这种疗法是让患有焦虑症的患者逐渐谈论、接触以至最后亲身体验使他们害怕的事物。这种治疗方法精心设置了一套不断重复的、程式化的自我觉知练习计划,以改变在脑中的联结,并形成有益的新记忆,就像不断地练习弹钢琴,而逐渐形成有关弹琴时运动技巧的记忆一样。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末,利平以每周3天,每天乘2小时的地铁进行“练习”,学习怎样在不断有肾上腺素涌出的情况下生活,这样在她的脑内就产生了新的突触和新的记忆,从而克服了她长久以来所遭受的恐惧。利平说道:“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居然会把10年时间花在不起作用的治疗上,而我是个相当机灵的人。我应该早就得到治疗,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有这种疗法。”
戈尔曼及其同事做了一次大规模的临床调查,比较药物和认知行为疗法对焦虑症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抗抑郁药物和认知行为疗法对治疗恐惧症都有效,但是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差别,这就是药物起作用更快,而认知行为疗法的疗效更为持久。戈尔曼声称,他相信把这两种疗法结合起来的效果更好。药物可能是从生物化学方面减弱了杏仁体的活动,而认知行为疗法则是通过不断练习加强了脑内和认知有关的记忆回路,这种回路告诉患者譬如说乔治·华盛顿大桥一点都不危险。这种“认识”使得理性的脑战胜了杏仁体。
从1997年开始,利平参加了一个认知行为疗法的训练班,并得到了用一种认知行为疗法治疗恐惧症患者的执照。这种疗法要求从业人员陪伴患者到他们感觉恐惧的场合中去。她的患者害怕的场合可谓形形色色:怕独处,怕在交通繁忙之处驾车,怕乘飞机,怕乘电梯,怕到旷野,甚至怕进大商场或戏院或博物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