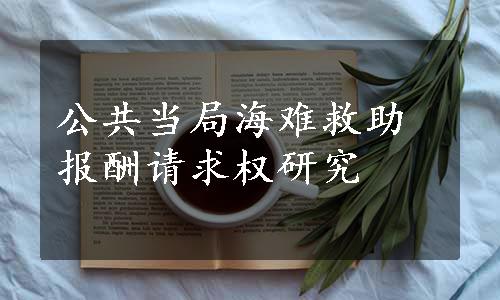
公共当局的从事行为与其他应召救助人的海难救助行为存在极大的共性,两者在本质上都是海难事故发生后,公共当局所协调组织的前来开展救助作业的救助力量。就公共当局从事海难救助的活动,公共当局与遇险船舶或财产的所有人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合意。如上述“港龙运3”轮海难救助中,在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后,宁波港龙公司先后发出4 封书面信函(请求派拖轮前往救助;请求派船前往救助并清除溢油;委托派消防船监控和海事巡逻船监护;在烟台港转驳货油委托安排维护船、消防车、清舱、引航事宜。书面请求中宁波港龙公司副经理朱玉伟签名,前两封加盖了宁波港龙公司合同专用章),请求烟台海事局予以救助,并承诺相应费用由宁波港龙公司负担。烟台海事局在事后提起海难救助报酬主张时,就认为宁波港龙公司上述请求救助的行为,应认定为宁波港龙公司在情况紧急的情形下向烟台海事局发出的要约。而山东省高院在审理案件后也认可了这种主张,认为:“本案中,在船舶遇险的紧急情形下,宁波港龙公司难以逐一向参与救助的各方发出救助要约,烟台海事局一方面行使行政职权组织救助,另一方面针对宁波港龙公司的要约作出承诺,在亲自从事相应的民事行为的同时委托相关单位进行救助是为维护港龙公司的利益。事实上,烟台海事局自身参与了救助,其他施救各方也均是在烟台海事局的组织协调下进行救助,宁波港龙公司对救助行为也予以认可,且除牟平港务局外,其他救助方均委托烟台海事局一并主张权利,因此,应当认定,宁波港龙公司与烟台海事局之间构成了合同救助关系,烟台海事局有权依据救助合同主张救助报酬。”
姑且不论山东省高院的上述论述是否完全正确,但本书赞同其中所阐述的这一观点:“烟台海事局自身从事的海难救助活动与其他施救各方的救助活动一样,都是在与被救助方——宁波港龙公司达成合意的情况下进行的”。(www.zuozong.com)
就作者目前掌握的相关案例来看,对公共当局的海难救助活动安排,包括各应召救助人的救助以及公共当局自身力量开展的救助,鲜有被救助者拒绝的情况。而海难救助法律关系的成立及相应救助报酬的产生,对双方当事人合意的要求仅为“被救助方对救助方的救助活动没有明确而合理的拒绝或制止”[37],因此,对救助方的救助行为,被救助方的沉默构成对双方救助合意的默示同意。此外,实践中,被救助方通常没有必要对公共当局所安排的各应召救助人及公共当局本身的救助行为进行拒绝。首先,根据海难救助的“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只有在救助取得效果的情况下,救助方才有义务支付救助报酬。如果救助完全没有效果,救助方也就没有义务支付救助报酬。因此,接受公共当局所安排的各种力量的救助,对被救助方来说与自行寻找救助力量进行救助的效果是一样的。其次,公共当局运用公权力调集各种力量对遇险船舶及财产进行救助的能力强于被救助方,加之海难救助的紧迫性,被救助方选择接受公共当局的安排实质上是一种“何乐而不为”的行为。最后,如果被救助方不接受公共当局所召集的各救助力量的救助,一是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财产很可能得不到救助而遭受毁损,二是一旦船货毁损、燃油或货油泄漏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或给航道安全造成重大损害,责任方将面临巨大的赔偿责任及行政罚款,对被救助方而言,这种拒绝救助的行为得不偿失。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