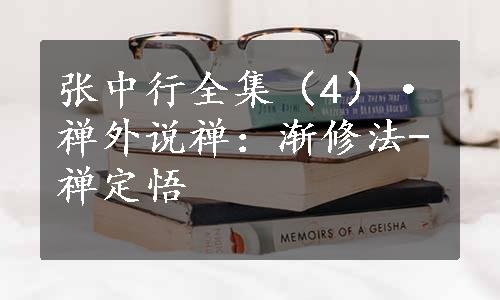
用禅定方法改造思想,求以奇境代常境(解脱),是佛教兴起以前就有的,也是佛教兴起之后许多教派共同的。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家后曾学无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舍弃苦行后渡尼连禅河,在毕钵罗树下结跏趺坐,据说连续七七四十九日,顺逆观十二因缘,终于得无上等正觉,所有这些修持功夫都是禅定。推想佛教早期,信士弟子修习禅定、静虑的所虑都是四圣谛法,即“苦”由于“集”,应以“道”“灭”之。后来,顺随求深奥、趋繁琐的教风,禅定的内容复杂了,讲法很多,这里说说最通常的。大致可以分为“观法”“禅境”“受用”三种,或三个阶段。
(一)观法。这是坐禅时冥想内容的因材施教或对症下药,就是适应不同的心理过失,选用不同的定功来对治。计有五种:一是多贪欲,用不净观法治,就是设想爱而欲得之物都是不干净的。不净分为两种:一种是己身不净,包括九种不净相:死,胀,青瘀,脓烂,坏,血涂,虫啖,骨锁(身肉坏之后骨仍连),分散。一种是他身不净,包括五种不净相:种子(己身宿业和父母精血),住处(母胎),自相(有多种排泄物),自体(由三十六种不净物合成),终竟(死后朽坏)。佛家省察人的情性,知道贪欲,包括最炽烈的淫欲,是走向出世间的最严重的拦路石,所以把不净观法看作最重要的法宝,不只列在观法的第一位,并且用十二分力量实行之,如禅堂用功之外,还要求到丛冢间去看死尸。观法之二是多瞋恚,用慈悲观法治。对于他人,与乐曰慈,拔苦曰悲,就是富有同情心,处处利人达人。他人包括四种:亲属,无大亲疏者,路人,仇敌。因为包括仇敌,要求不怒不恨,所以还提倡忍辱,就是连受到打骂也不当一回事。观法之三是多愚痴,用因缘观法治。所谓愚痴,是认为世间诸法是实,因而迷惑不悟。因缘观即顺逆思惟十二因缘(有“老死”由于有“生”,有“生”由于有“有”,等等;“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等等),最终要求领悟万法皆空。观法之四是多我见,用四界分别观法治。我见或我执,是妄计我(自身)和我所(自身之外)为实。这是诸多烦恼之起因,所以须以分别是妄的道理驱除之。观法之五是多散心,以数息观法治。数息,也说安般,安(安那)是入息,般(般那)是出息,即静坐默数呼吸,使心止于一处。止于一处不是道家的无思无虑,是专注于一理,这理是无我、诸行无常之类。观法分多种,是事理的解析;实际用功,当然不能不兼用,如既有贪欲又有我执,就要兼修不净和四界分别两种观法;而数息观法又像是禅定的入门或基础,是用功时都离不开的。
(二)禅境。这有如世俗的由小学升中学,由中学升大学,定功有成,所得之境也是由浅入深。计分四级:一是初禅。这一阶段,修禅定人的感受,或说讲法,非常复杂,依次序说计有粗住、细住、欲界定、未到定(以上为入门前之相)、八触、十功德(以上为已入门之相)几种。坐禅开始,静坐调息,感到心安稳而不散乱,是粗住。进一步,感到心更澄净安稳,是细住。再进一步,感到空明,己身如云如影,是欲界定。更进一步,感到心地泯然,不见眼前常见之物,是未到定(未入初禅)。此后经过较长时期(日、月或年),入初禅定,身感八触:动触,身起动乱;痒触,身发痒,似无处安置;轻触,身轻如云雾,似能飞行;重触,身重如石,端然不动;冷触,如浸冷水中;暖触,身热如火;涩触,身如木皮,滑触,身滑如乳。入初禅定可得十功德(又称十眷属):空,明,定,智,善心,柔软,喜(粗乐),乐(细乐),解脱,境界相应。还有十八支的讲法(初禅五支,二禅四支,三禅五支,四禅四支),初禅五支是:觉支,观支,喜支,乐支,一心支。这都讲得过细,不如《坐禅三昧法门经》的话简明扼要,那是:“行者呵去爱欲,灭断欲火,一心精勤信乐,令心精进,意不散乱,观欲心厌,除结恼尽,得初禅定。”禅定是求舍世间法,当然是舍得越多,成就越大,境界越高。初禅之境,获得靠思,所得为觉观,为喜乐。舍觉观仍有喜乐为二禅。舍喜仍有乐为三禅。兼舍乐为四禅。四禅是禅定的最高境界,理应称为“悟”。
(三)受用。这是禅定有成所得之善果,是行四无量心,修四念处,明四圣谛,得六神通,都成为易事。四无量心是慈无量(使众生得乐),悲无量(使众生离苦),喜无量(见众生得乐而喜),舍无量(离一切苦乐),总的精神是行功德,以求生梵天。四念处又名四空定或四无色定,是空无边处定(离一切色相,入虚空),识无边处定(虚空因识而有,观识而舍虚空),无所有处定(识亦虚幻,进而舍识),非想非非想处定(有想非,无想亦非,故取非想非非想),这是更高的修持方法。四谛是苦集灭道,明此理就可以成正觉。六神通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都是常识认为不可能的能力。(www.zuozong.com)
以上所讲的修持方法,由坐禅到开悟,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就是说,必须渐修。从禅林的生活方面看,专说六祖慧能以后,也是按部就班以求有成。如百丈怀海的《禅门规式》(以后发展为《百丈清规》)规定:维持“坐禅既久”不容易,因而要有严格的修持制度来保证。这有日日的,是定时坐禅以外,还有课诵,主要是早晚须上殿诵经。还有年年的,是夏日连续修习定功九十日,名为坐夏,冬日连续修习定功九十日,名为坐腊,通名为安居。这用意都是:开悟不易,所以要锲而不舍,一方面用大力,一方面慢慢来。慢慢来是渐修。
所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设长连床,施椸架,挂搭道具。卧必斜床唇,右胁吉祥睡者,以其坐禅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仪也。
时间是个怪东西,有怪魔力。这怪魔力之一是可以化量变为质变。有的宣传术和广告术就善于利用这种魔力,那是如某纳粹头子所说,假话多说几遍就成为真的。这里不是说谁真谁假,是说“渐”有大力,几乎能够变不可能为可能。当然,由时间单干也不成,还要有其他事物(寺院、课诵、衣食等等)陪衬。我比较熟悉寺院的修持生活,深知境由心造和心由境造常常是相辅而行;在初学阶段,力量更大的也许是后者。举两种小情况为例:一种是在殿内或殿外视听课诵,殿宇的静穆,香烟的缭绕,钟鼓梵呗声的清幽,常常使人也略有向往出世的情绪。一种是自己诵经,比如能背诵《心经》,在静夜,心应清净而不清净的时候,默诵:“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诵,未必深思经义,自然也说不上深信或浅信,但这些“无”也会产生一些力量,化心的不清净为略清净,不能舍为略可舍。门外人视听,诵,星星点点的因,也会生星星点点的果,长期坐禅堂,住茅棚,定内定外都默想万法皆空的信士弟子就更不用说了。这是说,大因会有大果。大因来于长时期,这,如果说是一种保证性,似乎只有渐修才能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