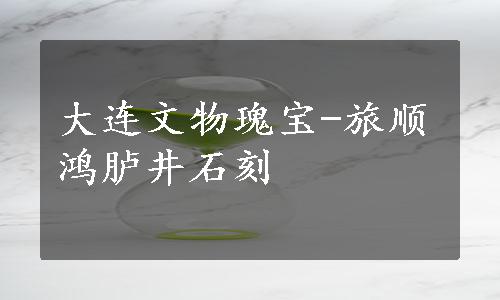
《唐鸿胪井碑》书讯消息
2011年第2期《人民中国》(日文)杂志上刊发了这样一条书讯:韩树英、罗哲文编著的《唐鸿胪井碑》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在2010年4月出版。文中称:“713年,唐王朝派遣鸿胪卿崔忻前往东北,册封‘震国’的大祚荣。崔忻为纪念这次活动,在今天旅顺口的黄金山西北麓刻一石碑,石碑上的文字对研究唐王朝与东北地方政权的关系史具有极高的价值。这块石碑在20世纪初叶,被日本海军劫持,现收藏在日本皇宫内。《唐鸿胪井碑》一书分上下2卷,由32篇论文构成。上卷收录研究中国东北地区及渤海国历史的文章22篇,下卷收录考证鸿胪井石碑历史的相关论文。本书的编著者韩树英希望通过本书,能够进一步推动鸿胪井石碑归还活动的开展。”
查《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有这样的记载:“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而《新唐书》中亦记载有此事,只是时间上未确指“先天二年”,而是说“先天中”。唐“先天”年号是睿宗李旦与玄宗李隆基交替执政时使用的年号,前后只用了两个年头,即712年八月至713年十一月。被后人传称为旅顺“金井”的石碑刻石内容是由29个字组成的——“敕持节宣劳 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里不论是古史典籍,还是历史遗迹,所记述的均为同一件事,即在713年至714年间,唐朝政府曾派遣使者赴东北向
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里不论是古史典籍,还是历史遗迹,所记述的均为同一件事,即在713年至714年间,唐朝政府曾派遣使者赴东北向 (羯)人进行“宣劳”活动。
(羯)人进行“宣劳”活动。
隋唐之际,随着中原战乱的结束,国家重新归于统一。为了巩固政权,统治者推行发展生产、固边安民的政策,各族人民生活于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互相融合,携手进入和平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又是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华民族进入大交往、大融合、大发展的历史时期,生息于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他们或结束自身的分裂,归于统一;或相互融合,重新形成新的更为强大的群体;或内讧不断,走向分裂,日趋没落,直至消亡。 族就是在这种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族就是在这种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族是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
族是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 ”这一称谓,始见史籍《北齐书》所载。“
”这一称谓,始见史籍《北齐书》所载。“ ”的含义,今人解释多有不同,但是达成共识的大概有三点:一指物产,说
”的含义,今人解释多有不同,但是达成共识的大概有三点:一指物产,说 之地盛产宝石,所以为宝石之意;二指装束,即皮帽子;三指居住,说当时生活在东北的勿吉人又名“
之地盛产宝石,所以为宝石之意;二指装束,即皮帽子;三指居住,说当时生活在东北的勿吉人又名“ ”,勿吉就是“窝集”的转音,满语是森林之意。目前研究东北地区古代民族史的多数著作,把肃慎、挹娄、勿吉、
”,勿吉就是“窝集”的转音,满语是森林之意。目前研究东北地区古代民族史的多数著作,把肃慎、挹娄、勿吉、 作为上下传承关系,归为同一族系。史籍的记载告诉我们,南北朝时,
作为上下传承关系,归为同一族系。史籍的记载告诉我们,南北朝时, 人又被称为勿吉。隋至唐朝前期,
人又被称为勿吉。隋至唐朝前期, 人继续栖息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其众多的部落中,有据可考的有几十个,以七大部落最为有名,构成了
人继续栖息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在其众多的部落中,有据可考的有几十个,以七大部落最为有名,构成了 族的主体。按《隋书·
族的主体。按《隋书· 传》等典籍记载,它们分别是粟末部落、伯咄部落、安车骨部落、拂涅部落、号室部落、黑水部落、白山部落。其中尤以粟末部落势力最大,活动区域约在今日吉林省的安图、敦化、蛟河、桦甸、吉林等市县境内。因为这些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较大,发展亦较快。
传》等典籍记载,它们分别是粟末部落、伯咄部落、安车骨部落、拂涅部落、号室部落、黑水部落、白山部落。其中尤以粟末部落势力最大,活动区域约在今日吉林省的安图、敦化、蛟河、桦甸、吉林等市县境内。因为这些地区受汉文化影响较大,发展亦较快。
唐鸿胪井碑拓片(日方提供)
隋至唐初时, 诸部虽依然是“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但酋长的地位不断提高和巩固,已走完了由夫权制向世袭制过渡的历程,开始了“父子相袭,世为君长”的时期。此时,男子普遍成为部落的骨干,在家庭和部落中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由夫妻关系组成的家庭已全面建立起来,妻子成为丈夫的附庸,地位与男人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隋书·
诸部虽依然是“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但酋长的地位不断提高和巩固,已走完了由夫权制向世袭制过渡的历程,开始了“父子相袭,世为君长”的时期。此时,男子普遍成为部落的骨干,在家庭和部落中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由夫妻关系组成的家庭已全面建立起来,妻子成为丈夫的附庸,地位与男人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隋书· 传》中有这样的描述,说在部落内,男人穿的是皮衣,女人则穿布衣,一旦“其妻外淫,人告夫者”,“夫则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行为,自然是因为男子在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中的地位及作用所形成的。而随着财富积累的多寡不同,阶级分化此时已经很明显了,出现了拥有众多家仆的酋长、饲养家猪等禽畜类甚丰的富者,这些都标志着
传》中有这样的描述,说在部落内,男人穿的是皮衣,女人则穿布衣,一旦“其妻外淫,人告夫者”,“夫则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行为,自然是因为男子在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中的地位及作用所形成的。而随着财富积累的多寡不同,阶级分化此时已经很明显了,出现了拥有众多家仆的酋长、饲养家猪等禽畜类甚丰的富者,这些都标志着 人已经进入到了阶级社会。
人已经进入到了阶级社会。
从史籍的记载中可知,至南北朝时期, 人的社会生产活动仍是以畜牧和渔猎生产为主,农业生产为辅。所获得的物品,首先满足家庭的自给,其次再用于社会的交换。在畜牧业生产中,主要以养猪为主。据考,
人的社会生产活动仍是以畜牧和渔猎生产为主,农业生产为辅。所获得的物品,首先满足家庭的自给,其次再用于社会的交换。在畜牧业生产中,主要以养猪为主。据考, 族的养猪业在东北各民族中居领先地位,相当普遍。渔猎业在
族的养猪业在东北各民族中居领先地位,相当普遍。渔猎业在 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资源丰富,虽然渔猎生产手段异常简单,但仍不失为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途径。特殊的环境,使得“人皆射猎为业”,其工具以传统的
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资源丰富,虽然渔猎生产手段异常简单,但仍不失为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途径。特殊的环境,使得“人皆射猎为业”,其工具以传统的 矢石
矢石 为主。捕获的猎物,大部分留作自用,少量的珍禽异兽被用于交换,或作为贡品献给中原王朝。
为主。捕获的猎物,大部分留作自用,少量的珍禽异兽被用于交换,或作为贡品献给中原王朝。 人的农业生产非常原始,靠人力“相与耦耕”,尚未掌握牛耕技术,仅能种植粟、麦等生长期较短的作物,这些谷物除了食用以外,也用于酿酒。据称,
人的农业生产非常原始,靠人力“相与耦耕”,尚未掌握牛耕技术,仅能种植粟、麦等生长期较短的作物,这些谷物除了食用以外,也用于酿酒。据称, 人已掌握了“嚼米为酒”的酿造技术,所酿之酒具有一定的醇度,令人“饮之亦醉”。
人已掌握了“嚼米为酒”的酿造技术,所酿之酒具有一定的醇度,令人“饮之亦醉”。
688年,唐朝大军剿灭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地方政权,一些曾受高句丽役使、钳制的部落开始解脱出来。唐朝灭高句丽后,为了防止其东山再起,也为了充实内地荒疏空闲之地人口,将其大小官吏及强壮人口3.83万户迁往内地。在这一历史机遇下,上千户的粟末 人在其首领大祚荣的率领下,内徙移居辽西地区,被朝廷安置在营州柳城周围。粟末
人在其首领大祚荣的率领下,内徙移居辽西地区,被朝廷安置在营州柳城周围。粟末 人在营州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发展,渐渐成熟起来,在向汉人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社会管理经验。因此说,粟末
人在营州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发展,渐渐成熟起来,在向汉人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社会管理经验。因此说,粟末 人内徙营州,在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跨出了历史性的关键一步,使其崛起的势头愈发不可阻挡。
人内徙营州,在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跨出了历史性的关键一步,使其崛起的势头愈发不可阻挡。
696年,盘踞于营州地区的契丹上层分子发动了反抗唐朝地方官吏暴政的斗争,引起了辽西地区动乱。移居营州一带的粟末 人在大祚荣及其父亲乞乞仲象的率领下,举部东归,渡过辽水回到牡丹江流域的
人在大祚荣及其父亲乞乞仲象的率领下,举部东归,渡过辽水回到牡丹江流域的 故地。《新唐书》载,他们以“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开始割据。尽管唐朝统治者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对
故地。《新唐书》载,他们以“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开始割据。尽管唐朝统治者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对 首领实行封赏招安,封大祚荣之父乞乞仲象为震国公,并赦免其罪,欲使
首领实行封赏招安,封大祚荣之父乞乞仲象为震国公,并赦免其罪,欲使 众部平息下来。
众部平息下来。
崔忻出使渤海路线图
698年,大祚荣率 众部及高句丽的遗民在今敦化市西南二十五里处的城山子一带安定下来,根据唐朝政府对他父亲所加封的震国公的封号,宣布建立震国,自称震国王,以表示愿意承认与唐王朝政权的隶属关系。
众部及高句丽的遗民在今敦化市西南二十五里处的城山子一带安定下来,根据唐朝政府对他父亲所加封的震国公的封号,宣布建立震国,自称震国王,以表示愿意承认与唐王朝政权的隶属关系。
705年,唐中宗李显复位,因忙于应付武则天留下来的乱摊子,对于远离京城的边疆事务,自感力不从心,所以对大祚荣率领 人称王建政一事,继续推行招抚政策,派侍御使张行岌前往慰安。大祚荣为了早日消除来自朝廷的压力,保住既得利益,也欣然接受了李显的招抚,停止与朝廷的对立抗衡。他遣送其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入朝为侍,留作人质,宿卫京师,换取朝廷的信赖和承认。
人称王建政一事,继续推行招抚政策,派侍御使张行岌前往慰安。大祚荣为了早日消除来自朝廷的压力,保住既得利益,也欣然接受了李显的招抚,停止与朝廷的对立抗衡。他遣送其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入朝为侍,留作人质,宿卫京师,换取朝廷的信赖和承认。
710年,唐睿宗李旦即位后,东突厥遣使入朝,请求和亲,言归旧好,表示愿继续臣服于唐朝。而依附于突厥的契丹势力因失去外援,更显虚弱,无力继续与朝廷抗衡,从而使朝廷与 相联系的通道洞开,得以畅行无阻。713年(先天二年)李旦离位,把皇权交给玄宗李隆基(改年号“开元”),从而使唐朝进入“开元盛世”的阶段,对边疆的管辖治理也随之加强。
相联系的通道洞开,得以畅行无阻。713年(先天二年)李旦离位,把皇权交给玄宗李隆基(改年号“开元”),从而使唐朝进入“开元盛世”的阶段,对边疆的管辖治理也随之加强。
李隆基登基之后,便将励精政事的举措推向东北地区,于713年特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卿,充任敕持节宣劳 使,前往
使,前往 故地,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以大祚荣所领地域为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自此,大祚荣不再继续称其所建立的政权为震国,同时又去掉了
故地,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以大祚荣所领地域为忽汗州,加授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自此,大祚荣不再继续称其所建立的政权为震国,同时又去掉了 之号,专称“渤海”,为渤海(郡)国。此时的渤海(郡)国在名实之间,仅是唐朝管辖下的一个州。大祚荣既是唐朝所封的郡王,又是唐朝所任命的都督,在渤海境内他是最高的统治者,而在唐朝全国范围内,他仅仅是一名替代朝廷管理本部的官吏。762年,唐代宗李豫“诏以渤海为国”,晋封大祚荣的后人大钦茂为渤海国王,达到册授封爵的顶峰。(www.zuozong.com)
之号,专称“渤海”,为渤海(郡)国。此时的渤海(郡)国在名实之间,仅是唐朝管辖下的一个州。大祚荣既是唐朝所封的郡王,又是唐朝所任命的都督,在渤海境内他是最高的统治者,而在唐朝全国范围内,他仅仅是一名替代朝廷管理本部的官吏。762年,唐代宗李豫“诏以渤海为国”,晋封大祚荣的后人大钦茂为渤海国王,达到册授封爵的顶峰。(www.zuozong.com)
史籍有记,大祚荣死后,渤海(郡)国曾立即遣使者入朝告哀。唐玄宗李隆基即刻颁诏,以示隆重哀悼,表彰其历史功绩,并赐绢帛五百段以助丧葬之用。同时又派左监门率上柱国吴思谦摄鸿胪卿持节充使,前往渤海吊祭,再次证明渤海与唐同体一家的密切关系。大祚荣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使 人组织了起来,由诸部落分立进入到国家统治时期,为
人组织了起来,由诸部落分立进入到国家统治时期,为 人的发展以及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由于大祚荣接受唐朝政府的册封,积极遣使入唐朝贡,从而奠定了渤海与唐朝密不可分的隶属关系,确保了唐朝疆域的完整与繁荣发展。
人的发展以及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由于大祚荣接受唐朝政府的册封,积极遣使入唐朝贡,从而奠定了渤海与唐朝密不可分的隶属关系,确保了唐朝疆域的完整与繁荣发展。
那么,在713年,郎将鸿胪卿崔忻一行是怎样到达 故地的呢?有史学家认为,713年,崔忻从首都长安出发,一直向东,经山东半岛的登州(今烟台蓬莱),渡海至辽东半岛南端,于黄金山下的旅顺口登岸,继而陆行至鸭绿江口,换乘舟楫溯江而上,到达吉林临江,又经抚松、桦甸、吉林、敦化等地,最后到达了今吉林省延吉市附近的城子山山城,即震国王都所在。
故地的呢?有史学家认为,713年,崔忻从首都长安出发,一直向东,经山东半岛的登州(今烟台蓬莱),渡海至辽东半岛南端,于黄金山下的旅顺口登岸,继而陆行至鸭绿江口,换乘舟楫溯江而上,到达吉林临江,又经抚松、桦甸、吉林、敦化等地,最后到达了今吉林省延吉市附近的城子山山城,即震国王都所在。
唐鸿胪井碑及碑亭原址
翌年(714年)的春夏之交,崔忻一行按原路返回长安,途经旅顺黄金山时,对此行感慨良多,所以命工匠凿水井两口,以纪念此次册封活动。凿井后,便在井旁的巨石上留下了前面所述的29个字。这29个字不仅仅表述了一段珍贵的历史,更因为它是中央政权与东北边陲 族友好往来的信物,而成为研究唐史、东北地方史、渤海国史、
族友好往来的信物,而成为研究唐史、东北地方史、渤海国史、 族史和大连地方史的珍贵文物资料。鸿胪井石刻也因此成为东北地区继毋丘俭纪功碑、好太王碑之后又一著名的历史石刻。
族史和大连地方史的珍贵文物资料。鸿胪井石刻也因此成为东北地区继毋丘俭纪功碑、好太王碑之后又一著名的历史石刻。
当然,今天的人们对于崔忻凿井的时间、井的数量及为何凿井作为纪念之物,仍有许多猜测,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旅顺黄金山有唐代古井石刻这样一个事实。关于碑文文字,清代学者杨伯馨在《沈故》一书中说:“其字结体颇似柳城石刻。”也有学者认为,也许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书法是登科考试的条件之一吧,位居高官的人一般都很擅长书法。这块碑上的书法亦具有相当高的造诣,温雅典丽,尽显唐代的书法风貌。
后人因金山的读音演绎,把崔忻在黄金山开凿的水井称为“金井”,将水井刻石称为“唐鸿胪井碑”。但从文物学上讲,这实在是一错误的定名。碑一般是由碑座、碑体、碑额三部分组成,而旅顺黄金山下的这块石头,既无碑座,更无碑额,只是将文字刻在一块大如驼的自然形石上,所以科学的定名应当是“鸿胪井石刻”。
日本明治三十七、三十八年战役战利品目录一
在鸿胪井石刻诞生后的千余年中,亦曾有达官贵人在巡至旅顺时,观风景访古迹,亲临黄金山鸿胪井旁,俯鉴奇石而留下观感。据称在原刻石之左右,有后人题记铭文五处,时间从明嘉靖年间至清光绪年间不一。1895年冬,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刘含芳随宋庆收复旅顺来到此地,见到唐人铭刻后,就在其旁添刻五行小字:“此石在金州旅顺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未冬,前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刘含芳所提到的石亭于次年8月完工,正面桁上刻有“唐碑亭”三个楷书字额。石亭用料为花岗岩石,柱心间距为260厘米,四角所立之柱呈方形,边宽30厘米。柱的上部嵌接着长方形的桁和梁,桁和梁的末端形成挑斗拱。亭顶显得很重,固于石刻所在的巨石中间立一八角柱,以分担亭顶的重量。“石亭外观颇有沉重感,不能说巨大,但给人以雄浑感,石亭对石碑来说是恰到好处的建筑。”这是日本学者的评述。
日本明治三十七、三十八年战役战利品目录二
现藏日本皇宫的唐鸿胪井碑
鸿胪井遗迹碑
鸿胪井石刻虽仅有短短的29个字,但其意义非同一般。它是现存涉及渤海国历史最早、最具特点的一件历史文物,同时还证明,唐代的旅顺已成为中央政权联结东北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因此,它也就成为后来霸占旅顺的日本人所惦记的对象。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受日本海军省的委托,专程来旅顺考察这一石刻,经过调查、考证,明确了鸿胪井石刻的史料价值。日本海军省随即将鸿胪井石刻和所覆的石亭一并盗往日本,以所谓“日俄战争胜利品”的名义献给天皇。目前,这块铭刻中国唐代重要史实的石刻就收藏在日本皇宫内“建安府”的前庭。或许因为旅顺黄金山下的这块唐鸿胪井刻石盛名远传,做贼心虚的日本人就来了个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把戏。1911年,已离任的日本海军镇守府长官富冈定恭在原刻石所处的位置上又立一碑,在碑的阳面阴刻“鸿胪井之遗迹”,碑阴处刻有“唐开元二年,鸿胪卿崔忻奉朝命使北 。过途旅顺,凿井两口,以为纪验。唐开元二年距今实一千三百余年,余莅任此地,亲考崔公事迹,恐湮灭其遗迹,竖石刻字,以传后世尔云。大日本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海军中将从三位勋一等功四级男爵富冈定恭志”。他通篇没有记述原唐代刻石的去处,反倒以弘扬史迹的“功臣”自居,自我颂扬了一番,真是令人作呕。
。过途旅顺,凿井两口,以为纪验。唐开元二年距今实一千三百余年,余莅任此地,亲考崔公事迹,恐湮灭其遗迹,竖石刻字,以传后世尔云。大日本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海军中将从三位勋一等功四级男爵富冈定恭志”。他通篇没有记述原唐代刻石的去处,反倒以弘扬史迹的“功臣”自居,自我颂扬了一番,真是令人作呕。
今天,岁月的痕迹湮没了唐时的古井,鸿胪井石刻遭盗劫远离故土也已有百余年了,但丝毫没有抹去人们深深的思念。更有有识之士组成了“唐鸿胪井碑研究会”,为促使日本政府归还唐代鸿胪井石刻而奔走呼号。《唐鸿胪井碑》的主要编著人韩树英先生就是推动唐鸿胪井石刻归还活动的首倡者。他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对家乡的土地,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深的感情。他在书序中说:“我们这代大连人就是在这种有力的情结传承的影响下,去探寻金井唐碑的真实历史。”“说到这里,就应该回头倾听并真实对外反映我国人民合情合理的呼唤唐碑回归的声浪。”我们坚信,经过中日双方民间和政府的努力,唐鸿胪井石刻和罩亭的回归一定能够实现。
金州大黑山出土的高句丽 八瓣莲花纹瓦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