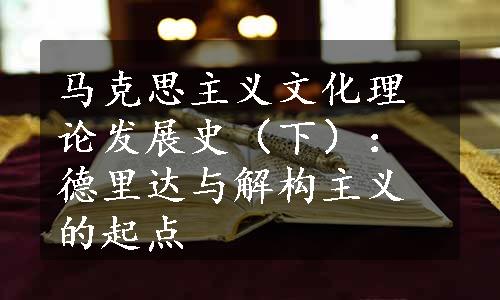
如前所见,“法国理论”在美国的旅途,大都经历了一个“德里达—德勒兹”转向。故假如我们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视为它的一个未必名副其实的起点,应该不是盲目武断。但或许正是对文学的过分热心,致使德里达在本土一时命乖运舛,事实上被排斥在法国主流哲学圈子之外。包括他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满世界文学批评言必称解构的解构主义黄金时代,还舍不得给解构主义的父亲授予一个正教授的职称。在1979年出版,后来被誉为所谓“耶鲁学派”宣言的《解构与批评》一书中,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本文集的五位作者里,布鲁姆、德曼、哈特曼和米勒都是耶鲁大学文学专业的大牌教授,可是他们的“灵魂”德里达,身份其实有点尴尬。该书的“作者介绍”里就说得明白:“雅克·德里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哲学与哲学史,1975年起,他任耶鲁大学的人文访问教授。英语世界中,他因以下著作蜚声:《〈声音与现象〉和胡塞尔符号理论的其他论述》(1973)、《论文字学》(1976)、《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导论》(1978)、《文字与差异》(1978),以及《马刺:尼采的文体》(1979)。”[60]解构主义扛鼎之作《论文字学》英译本1976年由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译出,距离它的法文初版已经过去十年。
德里达的著作走进美国的课堂,《论文字学》的出版是标志性事件。这个译本不仅将晦涩艰深的解构理论译介得通俗易懂,而且有一个长达一百页的译者序言。假如说它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译本,估计也不算夸张。斯皮瓦克的译序中不但系统介绍了德里达的生平、著作和思想,而且就什么是“序言”、怎样来写“序言”大发感慨,被认为从此将写序言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斯皮瓦克早年曾经师承德曼。2007年,她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六十四年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这一最高职称的有色人种女性。但是开始翻译《论文字学》的1973年,这位年方三十的年轻天才女性还在爱荷华大学任职。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捧起德里达的这本大著,出于好奇,大致浏览了一番,当机立断担当起翻译重任,同时说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来出版这部后来被证明是划时代的“法国理论”大著。译序中,斯皮瓦克这样描述她的序言意味着什么:
说某个叫作《论文字学》的东西当初是,现在也是我这篇序言一时兴起的缘起,那是理所当然,可是也并不正确。而且,甚至在我写作之时,我突出此时此刻,当你来阅读的时候,也会在我的序言中发现你读《论文字学》一时兴起的缘起。[61]
斯皮瓦克是不是感染了德里达的文风?这篇序言曲里拐弯,文体明显也是模拟了《论文字学》的迂回曲折。故而称斯皮瓦克这篇大序开启了一个喧宾却不夺主的“法国理论”新时代,一点不算过分。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的作品以此为契机纷纷进入美国课题,成为批评文本的分析对象,但是在“法国理论”的本土,迄今为止拉康、福柯、德里达、德勒兹这一批已故大师们的身份虽然同样得到了确认,但是他们的著作依然被排斥在文学系的课堂之外,尚无出现取代作品分析的趋势。
《马克思的幽灵》1993年出版,德里达与马克思的直接对话可谓姗姗来迟。该书一开篇就说:“现在维护马克思的幽灵。”这句话的法文原文是Maintenant les specters de Marx,[62]开门就是一个双关语,maintenant既是现在、此地的意思,又暗指维护的意思,所以蓓琪·加缪夫在英译文中无可奈何只好把这双关意思同时译出来,是为Maintaining now the specters of Marx。这个开头其实来得突兀,叫人不好理解。它是一个陈述句吗,说作者德里达如今在维护马克思的幽灵?还是它是一个命令句,谓汝等应当维护马克思的幽灵?抑或它就是一个评议句,意谓吾人不论意识到与否,但委实一直是在保养维护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以“幽灵”命名他这部姗姗来迟,一直到苏联分崩瓦解,东欧纷纷易帜之后方才面世的马克思主义专论,当然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从词源上看,它无疑首先取法于《共产党宣言》那一句著名的开场白。再往上推,该书题记引用了《哈姆雷特》第一幕中丹麦王子与老王幽灵宣誓时的一句著名独白:这时代脱节了。
多年以后,德里达本人这样解释过他的“幽灵”情结。他指出,在对马克思的研究中,他之所以重视幽灵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说过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在欧洲游荡的幽灵,也不仅仅是因为哈姆雷特重振乾坤同他父亲的幽灵有怎样的关系,他关注幽灵的原因是“幽灵”的问题也是“幽灵性”的问题。而“幽灵性”的问题、“幽灵性”的概念,如今似乎被用作理解比方说技术、交流变革方法的东西,如电视、网络、电话、手机等等,所以:(www.zuozong.com)
“幽灵性”的概念对于分析我们时代的这些技术、这些新技术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幽灵”意味着既不是真实的,又不是想象物,他既不是生者,也不是死者。他制造传播、印迹、技术的形象。[63]
德里达上述幽灵释义的背景是2000年他访问中国之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报告。德里达称他不知道在中文里如何翻译 spectre、fantôme 和 revenant 这三个同幽灵有关的概念。但是,他对“幽灵”的研究由来已久了,“幽灵”具有它的价值,也具有解构的意义,因为说到底,“幽灵”特点就是非生非死、非在场非缺场、非真非假。至此,对德里达的幽灵我们或许开始看出了些端倪:它是不是同异延、踪迹、补充以及场域(khôra)这类神出鬼没的解构主义概念相知恨晚,愿意形影相随一起叙说在场和缺场、生命和死亡、真实和虚幻之间的那一混沌状态呢?
但是将马克思重读作徘徊在欧洲上空的“幽灵”,无论它被释为20世纪末叶的资本模式也好,弥撒亚式的政治愿景也好,抑或变相取代昔年“异延”的“正义”也好,德里达这一典型的“法国理论”马克思主义阐释模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英美正统,如始终在谴责解构主义是文本主义、反历史主义的伊格尔顿、佩里·安德森、詹姆逊等人,终究还是难合分歧。分歧必然引来反击,方方面面的反击和斡旋后来被汇集到一部不算来得太迟的文集:《鬼魂分割:论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虽然詹姆逊和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等人的评论还算持理解态度,但占据上风的显然是一面倒的批判,诚如该书编者序言中所言:
这本文集里的论者们,对于究竟应该赞扬还是谴责(或者某些情况下干脆不屑一顾)德里达处理马克思文本的方式,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多有分歧的。考虑到大部分撰稿人的政治立场,谴责占据主导地位是可以想见的。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上,他们倾向于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64]
简言之,论者大都倾向于判定德里达对马克思的阅读是误读。皮埃尔·马歇雷的文章是《被分隔的马克思》,伊格尔顿的文章名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标题本身就锋芒毕露。德里达本人的答辩文章《马克思及儿子们》亦收入此书,他却不认为自己是在恣意歪曲马克思,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宗派主义者们的专利,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马克思的儿子,所以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释马克思的幽灵。所以问题依然存在:我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接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