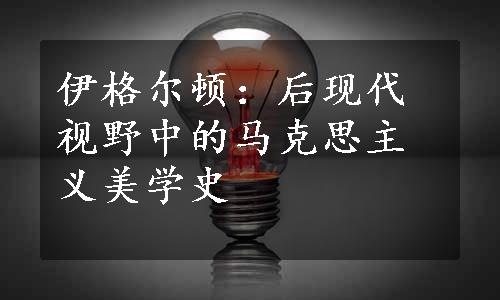
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可以视作一部后现代视野中的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来读。它从夏夫兹伯里和康德开始,一直写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福柯和利奥塔。但是导言部分作者开篇就说,本书不是一部美学史,相反是试图在美学范畴之内,来探索现代欧洲思想的一些中心问题,通过美学发展的线索,来书写不同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在这样一种理论构架之中,美学更像是一种元美学,即美学将以它自身作为描述的对象。伊格尔顿陈述了该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本书亦是一种马克思式的研究——人们既可能认为它过于马克思主义化,也可能认为它过于非马克思主义化。说它过于马克思主义化,是因为人们可能指责本书时常滑入把美学的内在复杂性简化为直接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左翼功能主义”。……另一方面,这类研究之所以过于非马克思主义化,那是因为如果把本书论述的作者的思想置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物质发展、国家权力的形式以及阶级力量的平衡的大背景下来论述,那么对其中任何一位作者的著作作出令人满意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都需要一卷书的篇幅。[47]
这可见,美学的意识形态化或者非意识形态化,在伊格尔顿看来是一个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问题的悖论。他注意到欧洲哲学自启蒙运动以降,始终高度重视美学问题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康德看来美学提出了自然和人应当和谐的问题,黑格尔对艺术也有过大量论述,尼采和叔本华的哲学固然离经叛道,却更以审美体验见出最高形式的价值。到20世纪,海德格尔的沉思终究是在审美本体论中得到完成,而从卢卡奇到阿多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热衷于对艺术作理论说明,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即便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争论不清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也还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字眼。美学在现代欧洲总体思想中占有这样显赫的地位,伊格尔顿认为主要是德国人的功劳,是以他这本《美学意识形态》所讨论的思想家,差不多都是德国人。美学的生命力何以如此顽强,特别是当文化尽失在传统社会中的灵光,差不多沦落为一般商品生产的一个分支之时?这也正是伊格尔顿努力要作解答的。
美学与艺术的大众性质不同,伊格尔顿认为,它一方面固然像艺术一样,是植根于日常经验的领域;但另一方面,美学被认为是自然和自发的表达方式,还必须被抽象化和理论化。不仅如此,美学还必须为人格的完美发展提供一种理式,它不同于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的种种异化了的认知模式,而且永远在向统治意识形态提出挑战。在冷战之后的当代西方,伊格尔顿指出,尤其不能让花样不断翻新的政治形式抹杀和歪曲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丰富遗产。对此作者自称出生而且成长在一个具有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传统的环境之中,自青年时代起,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政治活动,自然坚信当前任何避开社会主义的激进立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正是在这一语境当中,伊格尔顿提出了《美学意识形态》中的肉体(body)主题。作者直言不讳他有意为这个后现代社会中的时髦主题辩护,指出今天的文学文本倘不能提供一个残缺不全的肉体,新历史主义批评便无从谈起。肉体和灵魂不同,它不要求真理只要求快感。不明确这一点,想读懂罗兰·巴特和福柯的后期著作,便是奢望。伊格尔顿认为肉体与审美的密切关系,实在是被康德用理性压抑得很苦。他显然更喜好尼采哲学就是对人体作出解释的说法,而且引《权力意志》中尼采的话——肉体是比意识更丰富、更清晰、更实在的现象。伊格尔顿评价尼采的立场虽有叔本华生理主义的庸俗味道,却是言中了传统哲学的盲点。
赛伊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导言中,曾讲到文化的含义之一就是指一切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活动,就像形式描述、传播和表现的艺术,时常是以审美的形式出现。故而它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快感。后现代文化被认为是一种抽去了理性主义,热衷于感官愉悦的享乐主义文化。但是肉体和快感作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欲望主体的存在形式和追求目标,本身也是后现代美学中一个热门的话题。德勒兹和伽塔利《反俄狄浦斯》中就已指出,他们倡导的“精神分裂症分析”旨在消解自我和超我,再现无意识被压抑的前人格领域,创造后现代的欲望主体。“欲望”是革命的,“肉体”也是革命的。伊格尔顿指出,美学固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因为它萌芽和发育于启蒙运动时期,但《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停止赞扬过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遗产,美学绝不能因此被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帮凶。反之他大力阐明,美学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主体性的秘密原型,作为人类力量的幻象和追求境界,是一切专制思想和工具主义的死敌。
美学标志着社会文化向感性的肉体作创造性转移,也标志着用细腻的法则来强制雕塑肉体。这是一对矛盾,但是这一对矛盾将有可能得到缓和。对此伊格尔顿十分欣赏曾经是解构主义“耶鲁学派”领袖人物的已故批评家保罗·德曼,认为他的后期著作令人振奋地化解了笼罩在美学上面的神秘氛围,以美学意识形态经历了从语言学到感性经验的现象学还原,认识到心灵和世界、符号和事物、认知和感觉原是混沌难分的。这一混沌状,在伊格尔顿看来正是客体潜在的审美诱惑,它的根源在于一种感性实践,它是人类存在的动物性方面,是赐予我们快感、自然和愉悦的源泉,也是久被埋没的审美动因。由是观之,《美学意识形态》的主旨,即是让久被理性压抑的感性开口说话。伊格尔顿背靠肉体来重写美学的底蕴,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局限,应是在所难免。我们不妨来看作者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美学观的阐释。
《美学意识形态》第八章以“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为题,讨论了肉体主题在马克思美学中的地位。伊格尔顿认为迄至马克思,美学的唯物史观还远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据他观之,康德是从审美表现中驱逐了一切感性的东西, 只留下纯粹的形式。他引布尔迪厄《区隔》一书中的评语:康德式的审美愉悦是一种空洞的快感,它本身就包含了对快感的抛弃,是一种纯化了的快感的感觉。同样他发现黑格尔对肉体也颇有挑剔,仅仅认可了在他看来是对理性开放的视听两种感觉。如果说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唯一的策略便是回到起点重新开始。而如何拯救美学中的唯物主义,把美学从窒息它的唯心主义重负下解放出来,伊格尔顿提出,只能是通过一种发生于肉体本身的革命来实现。把目光紧盯住审美中的感性因素,伊格尔顿称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是现代社会中三个最伟大的美学家:马克思是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是通过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是通过欲望的身体,都强调了作为理论基础的物质实践的重要性,三个人殊途同归。
伊格尔顿大量引证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内容),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够说明:人类的身体怎样向社会和技术延伸,逐渐超越它自己的界限而达到空虚,抽空它自己的感性财富,从而把世界转变为它自己的身体性器官。如《手稿》中马克思的这段话:
通过把工人的需要降低到维持生理存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通过把工人的活动降低到最抽象的机械运动……政治经济学家宣布人没有其他的需要,他既不需要活动,也不需要消费……他把工人变成既没有需要,也没有感性的存在,并且把工人的活动从全面的活动中转变为纯粹的抽象的活动。[48](www.zuozong.com)
但是伸张感性的权利并不意味一种庸俗的经验论,伊格尔顿强调说,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倡导一种基础的感性科学,又不陷入经验主义的渊薮,是因为感觉对于马克思而言,一方面是一个较少异化的领域,一方面它作为我们与现实的实践性关系的中介,可以由理性来审视它的“规则”。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感觉都给异化掉了。不说工人的活动被降低到最抽象的机械运动,资本家剥夺工人感觉的同时,也剥夺了他自己的感觉,诚如《手稿》中马克思所言:一方面越少吃少喝,少上剧院、舞厅和餐馆,就越能积攒资本;一方面有资本替代感觉登场,凡人所不能,金钱样样能够帮你办到,它能吃能喝,能上 剧场能去舞厅,能拥有艺术、学识、历史珍品和政治权力。总之资本像个幽灵,在主人睡觉的当儿偷偷地跑出来,机械地享用主人认真抛弃的快乐。这样一种颠倒的镜像,伊格尔顿指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幻觉性的审美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在伊格尔顿看来,在于恢复肉体被掠夺走的力量。而只有推翻私有制,感觉才能回到它们自身。共产主义的理想之所以是必然的,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还不能如其本然地去自由感觉这个世界。而一如伊格尔顿再次引用马克思《手稿》中的名言:
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变成了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却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49]
伊格尔顿对于这段话的评价是,马克思是最深刻的“美学家”,相信人类的感觉力量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无须功利论证的绝对目的。所以可以说,马克思这里是在鲍姆加通为美学命名一个世纪以后,来重新号召确立这门科学。
当然,这样一种感性的丰富展开,只有在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主义之后才能实现。由于人类感觉的主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因此只有通过对象的历史性转变,感觉的主体性才能建树起来,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 “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50]对此伊格尔顿的评论是:美学渗透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政治范畴和经济范畴。
《美学意识形态》第十章“父亲之名:西格蒙· 弗洛伊德”,系统探究了弗洛伊德的美学思想,其展开的视野与我们所熟悉的俄狄浦斯情结、诗人与白日梦一类精神分析的程式多有不同。他认为在弗洛伊德看来,美学既可以成为想象的慰藉,又是一颗能量极度释放的炸弹,它表明人类主体是分裂的,表明人文主义完美的梦想本身就是一种性欲的幻想,这就是传统美学的现实。传统美学由是观之,是在渴求既是感性的又受规则控制的客体,把大量美好的感觉与抽象规则的权威混为一统,然而它仅仅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弗洛伊德对于现代美学的贡献,在伊格尔顿看来,便如马克思无情地从历史的野蛮主义中揭示出文化的隐秘本源一样,是无情地追踪文化的黑暗根源,一直追踪到无意识的深处,即揭示出一种原初的自恋语境。
伊格尔顿对弗洛伊德拒绝求诸理性而欲使分裂人格重归和谐的思想感触深刻。他指出,对于精神和感觉、肉体和理性两相统一的传统美学理论,弗洛伊德的出现无异于晴天霹雳,因为他的理论是肉体根本就不擅长语言,肉体在语言形式中从来就不是自由的。言语和欲望之不可能协调一致,正如意义和存在不断地相互置换。虽然广义的语言揭示了原初的欲望,可是欲望也有口吃和失语之时。欲望本身是崇高的,最终战胜所有的表象。就此而言,伊格尔顿认为,弗洛伊德的思想完全是“审美的” ,因为它涉及的完全是感觉生活的戏剧。假如说古典的愉悦是人性本能冲动的平息而不是它的产物,那么弗洛伊德则是恢复了这一愉悦所具有的粗俗的不快乐性以及它的怨恨、施虐狂等等一切消极的性质。审美可以补偿生存的痛苦,但是无以保护我们不受这痛苦的伤害。在对社会秩序的这一悲观看法上面,伊格尔顿发现弗洛伊德就是一个20世纪的霍布斯,一个激烈的反美学主义者。
伊格尔顿集中分析了弗洛伊德的欲望概念,说明弗洛伊德的启示是,规则及其符号说到底是文化本身,只有在欲望之中,而不是欲望之后得到满足。这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因为它涉及后现代思潮对理性和感性,进而对西方和东方文化的重新认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