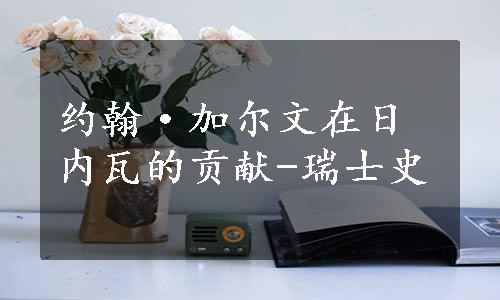
1536年8月5日,西庸陷落时,约翰·加尔文来到了日内瓦。至今,约翰·加尔文的名字依然在日内瓦和以他名字命名的神学领域中流传。1509年,约翰·加尔文出生在法兰西王国北部皮卡第大区的努瓦永。当马丁·路德在威滕伯格的教堂门口张贴他的著名论文[1]时,约翰·加尔文年仅八岁。虽然约翰·加尔文出身贫寒,但他的父亲杰拉德·考文是一个聪明人。凭借自己的才干和能力,杰拉德·考文成了努瓦永地区的地方检察官,从而为子女们营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他的三个儿子都成了神职人员。十二岁时,约翰·加尔文就当上了兼职牧师,并开始有了收入。
1523年,约翰·加尔文跟随一个贵族家庭来到巴黎,并在之后就读于巴黎大学[2]马尔奇学院[3]。后来,他又进入巴黎大学蒙太古学院[4]深造。虽然约翰·加尔文拥有与年龄不符的学习热情,但因为性格孤僻和不苟言笑,他在同学中并不受欢迎。同学们还为约翰·加尔文起了个叫“指控者”的绰号。十八岁时,杰拉德·考文将约翰·加尔文送往奥尔良大学[5]学习法律。约翰·加尔文勤读不辍,结果积劳成疾。在就读奥尔良大学期间,约翰·加尔文曾为一名亲戚翻译的《圣经》译本[6]作序并专注于研究各种文字版本的《圣经》。
约翰·加尔文
1529年,约翰·加尔文返回巴黎。两年后,约翰·加尔文经历了所谓的“突如其来的转变”[7]。约翰·加尔文曾写道:“当我意识到自己的不幸时,一种恐惧攫住了我的灵魂。耶和华啊,我哭泣着祈求你。我将抛弃我所不齿的过往,走上你的光明之路。惶恐不安之中,真理如一束明亮的光,照亮了我的内心。”关于约翰·加尔文对他这段人生的记录,我们已经无从考证。我们也不可能了解约翰·加尔文为何突然信奉新教,我们只知道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天堂的圣光”围绕着约翰·加尔文。或许就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约翰·加尔文和使徒圣保罗[8]一样对神秘的宿命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宿命论后来则成为加尔文主义[9]体系中最著名的学说,并在约翰·加尔文实施的宗教改革中产生影响。
圣保罗
与此同时,约翰·加尔文听从了上帝的召唤。虽然开始意识到反对罗马教廷统治并不等于放弃使徒教会[10],但约翰·加尔文并未像乌尔里希·茨温利那样,想立即将自己的观点传播到国外。约翰·加尔文渴望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以便潜心研究《圣经》。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约翰·加尔文为密友尼古拉·哥普[11]撰写了一篇充满宗教改革思想的就职演讲稿——《新学问》。很快,约翰·加尔文和尼古拉·哥普便引火烧身,并不得不为了保命而逃亡。在逃亡的四年中,约翰·加尔文曾经辗转于多个城市。约翰·加尔文首先来到努瓦永,并放弃了再也不能诚心诚意接受的有俸圣职[12]。在巴塞尔,约翰·加尔文发表了《基督教要义》,这是一部为新教教徒辩护的高尚著作。之后,约翰·加尔文还曾经见过贝亚恩[13]的纳瓦拉王后玛格丽特·德·纳瓦尔[14]和纳瓦拉女王胡安娜三世[15]。作为法兰西王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姐姐和新教教徒的忠实保护者,纳瓦拉王后玛格丽特·德·纳瓦尔和纳瓦拉女王胡安娜三世值得人们铭记。
纳瓦拉王后玛格丽特·德·纳瓦尔
纳瓦拉女王胡安娜三世
之后,在去斯特拉斯堡的路上,约翰·加尔文曾在日内瓦短暂逗留。虽然约翰·加尔文原本计划只在日内瓦住一晚,但那一晚改变了他的一生。日内瓦城四处流传着一条消息——有一个目光锐利的黄皮肤年轻人在一间客店下马留宿,而这个年轻人的长相与《基督教要义》的作者的长相完全一样。于是,威廉·法惹勒立刻前去拜访约翰·加尔文,并请求他留下来帮助自己。约翰·加尔文回答道:“我更擅长理论而非实践,而且我不希望被束缚在任何一个地方。”威廉·法惹勒答道:“你可以继续学习理论,但如果你不肯宣扬基督教教义,那上帝就会诅咒你。”约翰·加尔文仿佛听到上帝的先知在借威廉·法惹勒之口说话,而作为上帝的卑微奴仆,他不应该拒绝威廉·法惹勒的请求。
几天后,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圣彼得教堂[16]开始工作,并做了一系列的神学讲座。威廉·法惹勒撰写了一份信仰告白[17],并将它遍示公众,这份信仰告白立即就被人们接纳。很快,关于改革宗市民生活方式的一系列严苛法律开始在日内瓦付诸实施;关于教会惩戒[18]和礼拜的严格规定也很快生效。地方官禁止民众跳舞打牌。一名理发师因为将一位新娘的头发梳得过于浮夸而入狱两天。日内瓦不再庆祝伯尔尼的四大传统节日[19]。
沉默寡言且天性懦弱的约翰·加尔文很快就发现自己采取的措施过于严厉,因而遭到了大部分市民的反对。约翰·加尔文与日内瓦市当局也发生了冲突。1537年,日内瓦议会投票决定将约翰·加尔文和威廉·法惹勒逐出日内瓦。约翰·加尔文去了斯特拉斯堡。1539年,约翰·加尔文娶了一位再洗礼派传教士的遗孀,并使其信奉新教。约翰·加尔文和妻子幸福地生活了九年,直到妻子去世。在约翰·加尔文和威廉·法惹勒被屈辱流放三年之后,日内瓦议会和优秀市民阶层都希望两位改革者重新归来,他们认为日内瓦需要一个比自由派或放纵派更强大的政府。天主教教徒努力让日内瓦回归正轨,而约翰·加尔文是日内瓦唯一的希望。当约翰·加尔文归来时,百姓和官员们都出城迎接,他们给约翰·加尔文献上新披风,并央求约翰·加尔文别再离开日内瓦。
如今,整个日内瓦政府都在按照约翰·加尔文的意愿做事。和乌尔里希·茨温利不同,约翰·加尔文希望将教会与国家区别开来,或者更确切地说,约翰·加尔文希望教会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由牧师和十二位长老组成的长老会以极其严苛的方式管理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每年对每户家庭至少进行一次巡视。家庭纠纷要接受议会的调查。酗酒的人要受到议会的严厉惩罚。最重要的是,任何在公众礼拜[20]和“布道”中散漫懈怠的行为,一经发现将由议会立即通报并严肃处理。所有儿童不仅要在学校接受约翰·加尔文《教义问答》[21]的培训,反复背诵圣歌和戒律,而且在由学校负责人送回家的途中,不能傻笑或说话。
由牧师们组成的“牧师团”[22]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在会议中,不管愿意与否,牧师们都要相互批评和参与讨论。牧师团还负责审查牧师候选人。牧师候选人必须在个人造诣和品格方面达到很高的标准。自约翰·加尔文往下,牧师们恪守着和他人一样森严的纪律,甚至可能更甚他人。
在制定民法的过程中,约翰·加尔文也发挥了主要作用。以摩西五经[23]为典范,约翰·加尔文试图使日内瓦成为16世纪的希伯来邦城[24]。在约翰·加尔文的严刑重典之下,消遣玩乐成了罪恶,而给孩子们起天主教圣徒的名字则属于刑事犯罪。任何异教神崇拜或亵渎上帝的行为都会招致死亡。1565年,即约翰·加尔文死后第二年,一名女性因为在圣歌中加入世俗言语遭到拷打;一位男士因为读了一本被认为亵渎神明的书遭到监禁;一名儿童因为殴打父母被处死。简而言之,监狱里多年来人满为患。而刽子手们也忙得不可开交。
临终前的约翰·加尔文
随着约翰·加尔文权势日盛,天主教国家将约翰·加尔文称作“新教的教皇”[25],并将日内瓦称为新教的“罗马”。然而,约翰·加尔文却始终安贫乐道。一次,枢机主教雅各布·萨多雷特[26]到约翰·加尔文的住处拜访他。衣衫褴褛的约翰·加尔文接待了雅各布·萨多雷特,并亲自为雅各布·萨多雷特开门。约翰·加尔文本应该很富有,但他死后只留下二百克朗[27]的遗产。
雅各布·萨多雷特
泰奥多尔·贝扎
虽然日内瓦的追随者们将约翰·加尔文尊为“具有神圣权威”的人,但作为一个凡人,约翰·加尔文始终不得人心。尽管约翰·加尔文将精力完全投入到了伟大事业中,为各地的新教教徒殚精竭虑,但他似乎不可能具备马丁·路德那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心。然而,正是这种同情心,让马丁·路德了解到“民生疾苦”。约翰·加尔文排除异己,奉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则,不允许他人信奉异教。此外,持续的健康问题让约翰·加尔文更加急躁易怒。他的一位朋友曾经说过,“与其和约翰·加尔文待在天堂,还不如和泰奥多尔·贝扎[28]一起生活在地狱”。约翰·加尔文认为新教统治者在惩处异教徒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是一种缺乏宗教精神的表现。而约翰·加尔文掌权期间的最大污点之一便是处死了异端人士迈克尔·塞尔维特[29]。迈克尔·塞尔维特是一位聪明但不安分的西班牙人。他曾经写了两本无神论的书籍,也曾致信驳斥约翰·加尔文,还曾以身犯险,冒险进入日内瓦。1553年10月27日,在约翰·加尔文的指使下,迈克尔·塞尔维特遭到逮捕和定罪,并被处以火刑。当时,约翰·加尔文正忙于镇压反对派的武装暴动。尽管约翰·加尔文最终获胜,但他也已经筋疲力尽。
迈克尔·塞尔维特
约翰·诺克斯
人们纷纷辱骂约翰·加尔文,并将街上的流浪狗取名叫约翰·加尔文。一天晚上,有人在约翰·加尔文的房门前开了至少五十枪。在为《圣咏集》[30]所作的序言中,约翰·加尔文无比悲怆地写下了镇压反对派时的冲突场景,而他本来天生厌战胆怯,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约翰·加尔文很欣慰地看到日内瓦没有再发生教派纷争,他创建的教会体制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约翰·加尔文为逃离家园的新教教徒们提供了庇护,甚至连日内瓦也已经成为所有国家受压迫新教教徒的避难所。其中就包括苏格兰宗教改革领导者,伟大的约翰·诺克斯[31]。约翰·诺克斯曾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宗教难民中宣传新教教义,并力图在苏格兰推广新教。1558年,约翰·诺克斯在日内瓦发表了《吹响反对女性邪恶统治的第一声号角》[32],不仅将矛头直指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33],而且激起了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34]的怒火。
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约翰·加尔文对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国内政治影响深远。约翰·加尔文曾致信英格兰王国护国公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35]并谈及新教福祉。约翰·加尔文也曾为英格兰王国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36]的福音派教会联合计划出谋划策。约翰·加尔文还曾向奥地利大公国、波兰王国、遥远的丹麦王国和瑞典王国等地的宗教改革者伸出友谊之手。约翰·加尔文的朋友兼伙伴,温文尔雅的泰奥多尔·贝扎曾经说过,“约翰·加尔文一肩承担了所有教会事务”。约翰·加尔文虽然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依然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托马斯·克兰麦
卧病在床期间,约翰·加尔文仍在关注法兰西王国宗教改革的进程。当感到虚弱无力时,他就命人将自己抬到伯尔尼参议院参加会议。在行将就木之际,约翰·加尔文派人传唤参议院议员们在病榻前举行临终告别。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曾用画作将这一会面的场景呈献给全世界。在这次会谈中,约翰·加尔文向议员们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并请求议员们原谅他屡次大发雷霆。约翰·加尔文认为,尽管自己有缺点,但一心为公,问心无愧。约翰·加尔文曾经告诫属下必须保持警惕和谦卑以避灾祸。在虔诚祷告之后,约翰·加尔文含泪送别众人。
两天后,约翰·加尔文召集日内瓦的牧师并向他们追溯了自己的生平。历经磨难的约翰·加尔文描述了他曾经如何遭人驱狗逐咬,以及如何在睡梦中被敌人的枪声惊醒。约翰·加尔文说道:“想想看,如果我还是昔日那个腼腆懦弱的潦倒学者,面对这样的遭遇将会是何等张皇失措!”约翰·加尔文请求众人原谅他的诸多过错,特别是他那急躁易怒的脾气。至于他的讲授和著作,约翰·加尔文只是说他相信神赐恩典,让自己能够一心一意地为新教的传播鞠躬尽瘁。之后,约翰·加尔文劝诫牧师们恪尽职守并在最后与众人一一握手。泰奥多尔·贝扎说道:“我们与约翰·加尔文诀别,热泪盈眶,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伤。”几天后,即1564年5月27日,约翰·加尔文与世长辞。
约翰·加尔文品格高尚,卓尔不群,正如环绕日内瓦的巍峨群山,但又是如此的粗犷,与脚下的绿色山谷和柔美湖泊格格不入。在日内瓦生活了许多年,约翰·加尔文却从未提及日内瓦的湖光山色。人们对约翰·加尔文更多的是钦佩和崇敬,但缺乏人文关怀。也难怪乔治·戈登·拜伦的诗中并未赞颂约翰·加尔文生活过的日内瓦城,而是赞美了日内瓦城外的美妙景色。
澄澈、透明、如镜的莱芒湖!
你与凡尘俗世迥然相异,
你似乎在静静地告诫我,叮嘱我:
应抛却尘世的苦水,追求纯洁的甘泉。
小船的白帆好似无声的翅翼,
要把我带离烦乱心境。我曾经爱过,
爱过那奔腾咆哮的波澜,
但湖水的温柔细语却像姐姐在轻声嗔怪:
为什么要在危险的波涛里以身犯险。
寂静的夜晚,四周的山岳,
人与周遭融为一团,显得朦胧而柔软。
景色虽蒙上一层夕暮,却仍然看得清晰,
除了那苍茫的侏罗山,它的顶峰,
高耸入云,显得那么峭崄。
船儿靠岸,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www.zuozong.com)
从幼嫩的花丛中传来。只听得见,
收起的橹桨上轻轻滴下的水珠声,
间或蚱蜢夜鸣,打破了寂静。
——乔治·戈登·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注释】
[1]指《九十五条论纲》。
[2]巴黎大学,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坐落在法兰西共和国首都巴黎,前身是建于1257年的索邦神学院,但更早可以追溯到1150年至1160年由天主教修士建立的大学。
[3]马尔奇学院,巴黎大学早期学院之一,约翰·加尔文曾在此学习修辞学。
[4]蒙太古学院,巴黎大学早期学院之一,约翰·加尔文曾在此学习哲学。
[5]奥尔良大学,即法兰西共和国国立奥尔良大学,由罗马教皇克莱蒙五世于1306年创立,为著名高等学府。
[6]指加尔文的表兄,新教教徒奥立韦唐译的《圣经》法文译本。
[7]源自约翰·加尔文的同学们对他的评价。
[8]使徒圣保罗(并非基督十二使徒之一)。1世纪时,他曾四处宣讲基督的福音。《圣经》中记载了圣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听到了上帝的召唤,于是开始信仰基督的故事。
[9]加尔文主义,法兰西著名宗教改革家、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毕生的许多主张的统称。现代神学论述习惯当中的加尔文主义指“救赎预定论”跟“救恩独作说”。
[10]使徒教会,基督教会最早的组织形式。由耶稣生前选定的使徒组成其管理核心,以圣彼得为首,圣约翰辅之。约于1世纪30年代至1世纪40年代形成。
[11]尼古拉·哥普(1501—1540),旧瑞士邦联新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的朋友。
[12]有俸圣职,指依教会规定,附有特殊俸禄的教会职务,也称圣俸。
[13]贝亚恩,法兰西共和国西南部的传统省份之一,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其下的平原。
[14]玛格丽特·德·纳瓦尔(1492—1549),法兰西王国公主,纳瓦拉王国王后,丈夫为纳瓦拉国王恩里克二世,弟弟是法兰西王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15]胡安娜三世(1528-1572),玛丽·德·美第奇之女,曾嫁给纳瓦拉的安托万,1555年至1572年任纳瓦拉王国女王,法兰西胡格诺战争的坚定领导者。
[16]圣彼得教堂,坐落于瑞士日内瓦老城区的标志性建筑。16世纪时,约翰·加尔文曾在此布道并使其成为宗教改革圣地。
[17]信仰告白,也称信经,指信徒加入宗教团体或接受某种信仰时做的信仰声明。
[18]教会惩戒,指在教会成员被认为犯罪后,教会通过对罪人进行谴责以规劝罪人使之悔改的做法。
[19]伯尔尼的四大传统节日,包括天主教祭典、基督圣体节、洋葱节和牧人节。
[20]公众礼拜,又称公开敬礼,指教会对天主之正式敬礼礼仪,以整个教会的名义举行。
[21]《教义问答》,约翰·加尔文于1537 年编写。
[22]牧师团,由教会所有牧师组成,每周四聚集商讨,目的是维护教会纪律。
[23]摩西五经,指《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24]据《圣经》记载,犹太人的族长亚伯拉罕率领其族人从两河流域的乌尔城渡过幼发拉底河和约旦河来到当时被称为“迦南”的巴勒斯坦。此后,这些古犹太人便被称为“希伯来人”。
[25]约翰·加尔文曾被称为“日内瓦的教皇”。
[26]雅各布·萨多雷特(1477—1547),意大利罗马天主教枢机主教和反宗教改革家,因与约翰·加尔文互相通信,并反对约翰·加尔文而闻名。
[27]克朗,中世纪流通于旧瑞士邦联的一种货币,多以硬币为主,早已停止流通。
[28]泰奥多尔·贝扎(1519—1605),法兰西新教神学家、改革家和学者,在宗教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约翰·加尔文的信徒,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日内瓦。
[29]迈克尔·塞尔维特(约1511—1553),西班牙神学家、医生、制图师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参与了新教改革并在后来提出一种三位一体和基督论的异端观点。在遭到法兰西王国天主教的谴责后,他逃到了日内瓦,最后被日内瓦市议会以异端罪处以火刑。
[30]《圣咏集》,指前文的《圣经旧约》中的诗篇。
[31]约翰·诺克斯(1513—1572),苏格兰神学家、作家,苏格兰宗教改革领导者,苏格兰长老会创始人。
[32]《吹响反对女性邪恶统治的第一声号角》,是由约翰·诺克斯发表于1558年的辩论文章。约翰·诺克斯在这篇文章中攻击女性君主,认为由女性统治国家与《圣经》相违背。
[33]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又称苏格兰王国的玛丽女王,于1542年12月14日至1567年7月24日统治苏格兰王国。
[34]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英格兰王国和爱尔兰王国女王,都铎王朝五位君主中的最后一位。
[35]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约1500—1552),萨默塞特第一任公爵,1547年至1549年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护国公。
[36]托马斯·克兰麦(1489—1556),英国改革教会的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对天主教教义、教规和仪式做出了改变,为使天主教英国教会变为英国圣公会进而成为英王私人教会做出了贡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