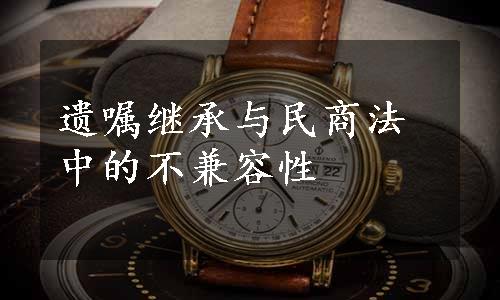
遗嘱继承(Succession testament),早在罗马法《十二表法》中已有规定,该法第四表第3条规定:“凡以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或对其家属指定继承人的,具有法律上的效力。”遗嘱继承在罗马法中的地位远远高于法定继承,例如,当死者以遗嘱指定一名继承人继承时,即使死者只就遗产的一部分指定继承人,那么也绝不可能出现任何“无遗嘱继承人(abintestato)”,也就是说,遗嘱未处分的部分遗产也要归遗嘱继承人所有,这就是“按份设立的遗嘱继承人不能同无遗嘱继承人兼容(Nemo pro parte testatus,pro parte intestaus decadere potest)”的著名规则。
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的不兼容性在罗马人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梅因爵士指出,遗嘱继承表示了“从‘遗嘱人’转移给‘继承人’的是家族,也就是包括在‘家长权’中和由‘家父权’而产生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体。”[1]这为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意大利罗马法学者彼德罗·彭梵得也认为:“遗产继承最初不是用来进行财产转移的,而是用来转移罗马家庭的最高权力的。在任何一个政治社会中,当某人被以某种形式指命为首领时,无法想象人们可以采取另一种形式同时指定另一位首领,这当然也是不相容的。”[2]
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确立了私人所有权绝对和个人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遗嘱被认为是财产所有人自由处分财产的一种形式,这一时代的法学理论也主张“指定或控制死亡后财产处分的权利是财产所有权本身的一种必然的或自然的结果。”[3]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895条宣称“遗嘱为法律行为的一种,依此行为,遗嘱人得处分其死亡后遗产的一部或全部”。遗嘱继承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遂成为大陆法系的一种普遍的法律制度。
一、遗嘱的订立
遗嘱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其设立也应当符合法律行为要件的要求。
首先,立遗嘱人必须具有遗嘱能力。大陆法系国家对遗嘱能力的要求与民事行为能力的要求并不一致。各国一般都规定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才可以订立遗嘱,但也有例外。《法国民法典》第904条规定:“满16岁的未成年人仅得以遗嘱处分其财产,且其处分的限度仅为法律许可成年人处分限度的半数。”但为了防止未成年人的利益受损,第907条又规定已满16岁的未成年人不得为其监护人的利益,以遗嘱处分财产。《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也作了相同的规定。
其次,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遗嘱人立遗嘱存在受欺诈、胁迫或重大误解等情况,那么该遗嘱将有可能被认为无效或可撤销。对于欺诈、胁迫的,德国、瑞士、日本等均规定为无效(《德国民法典》第2339条、《瑞士民法典》第519条、《日本民法典》第891条);对于重大误解,《德国民法典》第2078条规定为可撤销,而《瑞士民法典》第469条规定为无效。
再次,遗嘱的内容必须合法。对遗嘱合法性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遗嘱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或与社会善良风俗相背;遗嘱的内容不得违反关于“特留份”的规定,如《日本民法典》第964条规定:“遗嘱人可以以概括或特定的名义,处分其财产的全部或一部,但不得违反关于特留份的规定”;遗嘱附条件的内容也必须合法,如《法国民法典》第900条规定:“……遗嘱的条款中,不可能的条件、违反法律和善良风俗的条件,应视为未订立。”
最后,遗嘱的订立形式还须合法。《日本民法典》第960条规定:“遗嘱,非依本法规定的方式,不得订立。”
大陆法系国家规定的遗嘱形式一般可以分为普通方式和特别方式,前者如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密封遗嘱,后者包括口头遗嘱、紧急遗嘱、隔绝地遗嘱、海上遗嘱等。
自书遗嘱,它是由遗嘱人亲笔书写,不需要证人见证即可生效的遗嘱,它是大陆法系通行的遗嘱形式,《法国民法典》第970条、《德国民法典》第2247条、《日本民法典》第968条、《瑞士民法典》第505条、《意大利民法典》第602条都对它作了规定。自书遗嘱要遗嘱人亲笔书写遗嘱,并且亲笔签名,注明遗嘱制作的具体时间才能生效。
公证遗嘱,即依公证方式订立的遗嘱。公证遗嘱较自书遗嘱真实性更可靠,证据力较强,也是大陆法系常用的遗嘱形式。如《法国民法典》第969条、《德国民法典》第2231条、《日本民法典》第969条、《瑞士民法典》第498条、《意大利民法典》第603条都是有关公证遗嘱的规定。公证遗嘱要求的条件较为严格。
密封遗嘱,是指遗嘱人将其秘密制作的遗嘱密封后,指定两人以上的见证人,提请公证人公证的遗嘱。[4]法国、日本认为密封遗嘱是一种独立的遗嘱方式(《法国民法典》第976—979条;《日本民法典》第970—972条),而德国、瑞士则将其作为公证遗嘱的一种方式(《德国民法典》第2238条,《瑞士民法典》第500—502条)。
口头遗嘱,又称口授遗嘱,它是遗嘱人在生命垂危或其他特殊情况下,不能依其他形式订立遗嘱时,所采取的一种略式遗嘱形式。大陆法系一般都将它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遗嘱,如《法国民法典》第981—990条,《日本民法典》第976—984条,《瑞士民法典》第506—508条。1900年《德国民法典》开始并没有口头遗嘱的规定,但在1938年的《关于订立遗嘱和继承契约的法律》第23—27条有特别遗嘱的规定,后又被吸收进民法典,成为第2249—2252条的规定。
二、特留份
特留份制度是对遗嘱自由的一种限制,旨在迫使遗嘱人处分其死后的遗产时,给近亲法定继承人保留一定的财产,以尽养老育幼的义务。
特留份制度最早起源于罗马法上手遗嘱逆伦诉(querela inofficiosi testament)。罗马古代,虽实行遗嘱自由,家长可以废除子女的继承权,但当时民风淳厚,家长还是按照习惯,给未立为继承人的子女以一定的财产作为生活费用。至共和国末叶,世风日下,遗嘱人常常不按照传统的良好风俗行事,上不养老,下不抚幼,把财产全部遗给第三人。对此,大法官认为,凡市民都应尽养老育幼义务,若遗嘱人没有正当理由违背人伦道德,不把财产遗给自己的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反而遗给第三人,则遗嘱人的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宣告这种遗嘱不发生法律效力。[5]
至查士丁尼(Justinianus)(公元前483—565年)在位时期,明确地肯定这种遗嘱是“不合人情的遗嘱”,并认为它是“遗嘱人在立遗嘱时,精神不正常”,遗嘱人的近亲属,包括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均可提起“遗嘱逆伦诉”。[6]遗嘱人的近亲属,据此所应享有的遗产份额,就叫作“义务份”(Legitima Pars)[7]。(www.zuozong.com)
在日耳曼法上,为了防止遗嘱人的自由处分而导致家产分散、家族的崩溃,曾明确规定家产分为自由份(Freiteilrecht)和特留份两部分,可供被继承人自由处分的遗产只占家产的很少一部分,扣除自由份后的遗产均为特留份,非法定继承人不得享有特留份。[8]
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立法将家庭组织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德国学者K·茨威格特和H·克茨评价《拿破仑法典》的家庭法时说道:“对家庭组织广泛周密的保护无疑是法国家庭法的特征”,因此“在继承法中对既得家庭财产利益的赠与自由与遗嘱继承自由也有很大的限制:在法国,财产指有人至今也仍然只能对其自有财产部分[所谓‘处分额’(quotite disponible)]自由处分;至于其余部分,即所谓‘保留份’(reserve),各家庭成员不仅就法定义务份额享有一种金钱给付之请求权,而且还享有一种真实的必然继承权(Noterbrecht)”。[9]
古代的和资本主义早期关于“特留份”的规定,是在家庭作为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为主要角色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原有限制家长随意处分财产的意义。但日本学者川岛武宣认为,在现代社会法律生活中,财产皆为个人财产,“特留份”已失去原来的意义,这一制度的重点,已转移在使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人或者期待于被继承人死后仰仗其财产的人,获得生活上的保障。所以,大陆法系各国继承法都还保留关于特留份的规定。《瑞士民法典》第470条、第471条规定了遗嘱的“处分权范围”和“特留份”范围。《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则在继承法中以专章规定了“特留份”。
对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限制。首先,被继承人的直系卑血亲、直系尊血亲一般都享有特留份的权利。其次,兄弟姐妹是否享有特留份的权利,各国不一。《瑞士民法典》第470条采肯定的作法,而德国、法国、日本民法典均将兄弟姐妹排斥在外。最后,配偶一般可以享有特留份的权利(《德国民法典》第2303条,《日本民法典》第1028条,《瑞士民法典》第470条)。唯有法国未将配偶作为特留份的权利人(《法国民法典》第916条)。
在特留份的份额确定上,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
其一,“全体特留主义”(kollektivpflichfeil),即仅确定特留份在遗产总基数所占的部分,典型的是法国和日本。依《法国民法典》第913条规定,遗嘱人如仅有一个子女时,其遗赠的份额(即有权处分部分)不得超过其财产的半数;如有子女两人时,不得超过1/3;如有子女三人或三人以上时,不得超过1/4,可见对子女的特留份份额分别是1/2、2/3、3/4,其子女应当平分特留份。根据其第915条,如遗嘱人并无子女,而在父系和母系各遗有直系尊血亲一人或数人时,其遗赠不得超过所有财产的半数;如仅一系遗有直系尊血亲时,不得超过3/4,也就是说直系尊血亲的特留份是1/2或1/4。
其二,“各别特留主义(Partikularpflichtteil)”,是指以各个法定继承人应继份的基数,确定特留份的数额是应继份价值的若干分之几,[10]《德国民法典》第2303条规定:“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因死因处分而被排除于继承顺序之外的,可以向继承人请求特留份。特留份为法定应继份价额的一半。”该条第2款规定:“被继承人的父母和配偶因死因处分而被排队于继承顺序之外的,享有同样的权利。”可见,直系卑亲属、父母、配偶的特留份都是其应继份的一半,但由于这些法定继承人的应继份不同(《法国民法典》第1931条),所以他们实际取得的特留份份额大小也不一样。同时,第2305条又规定,“留给特留份权利人的应继份不足法定应继份的一半时,特留份权利人可以向共同继承人请求不足一半部分的价额作为特留份”,这一条被称为“补足特留份”。《瑞士民法典》采用的特留份计算方法与德国完全一样。
[1] 〔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9页。
[2] 前引〔意〕彼德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
[3] 前引〔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0页。
[4] 前引史尚宽:《继承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66年版,第410页。
[5] 前引周枬:《罗马法原论》(下),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5页。
[6] 〔古罗马〕查士丁尼著:《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7页。
[7] 前引史尚宽:《继承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66年版,第554页。
[8] 前引李双元、温世扬主编:《比较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9页。
[9] 〔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10] 前引史尚宽:《继承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66年版,第56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