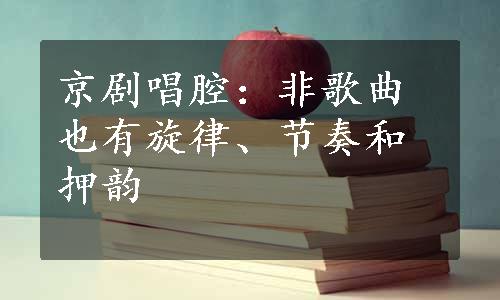
讲过了京剧中的白,就该谈谈它的唱了。
唱,是整个戏曲各种表现手段中最重要的一种。尤其是京剧,过去曾经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国粹,恐怕就和其唱腔蕴涵着的成就密切相关。
尽管京剧唱腔同样有旋律、有节奏、也分句押韵,但唱的并不是歌曲。
我们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寻找原因。
第一,歌曲的内容要么是抒情诗,要么是叙事诗,而京剧的歌词则是剧诗。
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一首歌,就属于抒情诗。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其中没有故事,只有盛情——一串串蓬勃似火的昂扬感情。是谁在抒情?——是没有具体身份的某个人。可以是男,可以是女;可以是大人,可以是小孩儿;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一群人。因此,演唱这首歌时,形式就可以灵活多样。男演员可以唱,女演员可以唱,童声演员也可以唱;独唱演员可以唱,作为合唱也未尝不可;它用大乐队伴奏可以唱,用小乐队伴奏可以唱;用西乐伴奏可以,用中乐伴奏可以;甚至不用任何伴奏也可一试。一般说,唱抒情诗的演员是用第一人称演唱,但这里的第一人称不是具体的人,其中的“我”是抽象的“我”,或者说是大写的“我”。
早年间乐师在台幔前伴奏
比如《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则属于叙事诗。“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其中只有一个朴素的故事,作者仿佛就在淡淡地叙事,感情全都隐藏在那客观的叙述当中。但是听歌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打动,因为就在那舒缓的节奏中,却充满了作者最深沉的情思。演唱叙事诗的演员,一般都是以第三人称演唱。
京剧则完全不同,它的任何一个唱段,都必须是某一出戏中某一个人,在某一个特殊事件发展到特殊阶段时的个人感怀。他(她)是以第一人称在唱,是被他(她)周围的那个环境“挤压”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不得不唱,其中既有抒情诗,也有叙事诗。前者的例子比如《红灯记》[1]中的“提篮小卖拾煤渣”,唱的是父亲李玉和对女儿铁梅的由衷赞叹。后者的例子比如“在粥棚正和磨刀师傅接关系”,唱的是李玉和回忆刚才粥棚脱险的情景。更多的时候,在一些大段唱腔中,唱的是抒情诗和叙事诗的混合,而这种混合又都是从特定人物的独特视角发出的,像“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既有回顾,也有展望,更有对人生、对事业的感慨。这段唱的慢板(从“贼鸠山要密件毒刑用遍……”开始的数句)都属于叙事诗,而后面的原板(“待等那风雨过百花吐艳……”数句)则属于抒情诗。由于京剧的剧诗必须隶属于特定的剧中人,所以演唱者就不能随意更换。李玉和的唱词就不能改由李奶奶或铁梅唱,更不能改由鸠山唱。
第二,从内容上区分唱歌和京剧演唱,又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谈。
(一)歌曲的唱词多是“散文化”了的诗句,而京剧唱段则采用了板腔体。
歌曲唱词都是一句、一句的,可以分成对称的上下句,每四句一个小节;也可以打破对称,随意写成不规则的长短句。前者比如《让我们荡起双桨》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后者比如台湾歌手齐秦的《飞扬的梦》,歌词共分三小节,每一小节句数并不相等,句子也忽长忽短,跳跃性很强——
记忆里/在记忆的梦里/曾经有绚烂的春天/却在一季落叶以后
记忆里/在年轻的梦里/也曾有年轻的故事/却在模糊的泪和无数个冲动的日子里/拾起了生活和自己的悲哀
年轻的希望里/总不忘记提醒自己/没有故事/没有等待/没有太多的悲哀/再一次告诉自己没有神话般的爱情/没有结束/没有开始/只有年轻飞扬的梦
京剧唱词的规格则采取了严谨的板腔体。其文字规格,必须是严格的上下句;每一句都以七字句(节奏二/二/三)或十字句(节奏三/三/四)为基础;每个上句最后的一个字,必须落在仄声上,而下句最后则必须落在平声上。其旋律选择,则不论特定人物有什么特定心情,都只能从下面两个系统中去选择交叉。一个是曲调性能的系统,京剧只有二黄、西皮、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这样很有限的几个大类。另一个是具体的板式系统,如倒板、慢板、原板、二六、流水、快板等。前者供音乐设计者在大的方面加以制约,比如剧中人这会儿心情正难受,沉郁、苍凉、悲哀……行了,就让他唱二黄吧。如果剧中人心情很愉快,或者很愤懑,那么就让他唱西皮吧。在做了大的规划之后,再根据剧情发展的具体要求,去决定是选择一段特定的板式呢,还是安排一大段呈组合状态的综合板式的唱腔。
我们以《文昭关》[2]为例加以说明。伍员一上场有两句唱“伍员马上怒气冲,逃出龙潭虎穴中”——他全家被楚平王所害,如今一个人逃了出来,身后肯定会有千万追兵赶来,看来形势够紧张的。这时需要先从大的方面进行规范——由于情势所迫,似乎以唱西皮为宜;再具体研究这两句应该用什么板式——人物刚刚上场,矛盾还没有完全展开,因此不能选用那些旋律复杂的板式,似乎散板为好。两下里一综合——就成了西皮散板。再讲如何设计大段唱腔的综合板式。《文昭关》的后面,伍员独自借宿在东皋公家中,心神不宁,彻夜难眠。他独自上场,需要唱一小段。坐定之后,打一更,需要唱一大段。起二更,东皋公暗上,唱一小段,下。起三更,伍员再唱一段。起四更,东皋公暗上,唱一小段,下。起五更,伍员愁白了胡子,激愤唱出“叹五更”的最后一段。东皋公上,发现伍员头发和胡子变白,认为可以混出关去,伍员再唱一段,二人同下。根据上述剧情,当初演这一折戏的老前辈所做的安排一直流传、延续到了今天——伍员上场的一小段,唱西皮流水。起更后,整个改二黄。初更后伍员唱变化多端的二黄慢板(十六句),二更东皋公唱规范的二黄原板(四句),三更伍员唱婉转多姿的二黄原板(十句),四更东皋公唱规范的二黄原板(四句),五更伍员再唱激愤多变的二黄原板(十句)。天明后二人相逢,东皋公唱二黄散板上,伍员梦中惊醒,唱二黄倒板转散板,最后再转二黄摇板。这样摆布唱腔的板式,应该说煞费苦心,布局匀称,起承转合,十分妥帖。
近半个世纪,京剧在处理“卖唱儿”的大场子时,已经形成了一种“倒、碰(即回龙)、原(或慢转原)”的习惯路数。现在,搞组合板式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不要千篇一律,二是要努力在相似中追求不同。
(二)歌曲只在一般意义上追求声情并茂,京剧唱腔则讲究一种说不清的韵味儿。
不知能否这样说,歌曲的曲谱是一个确定了的东西。歌唱演员接到它,只能体会它、琢磨它、生发它,却不能变更它。歌曲演唱上的声情并茂,是建立在绝对尊重曲谱的这一前提之上的。同一首歌的曲谱,歌手甲接到它,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加以发挥;歌手乙接到它,同样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去唱。熟悉乐理的听众,只要拿到曲谱,再问一声是谁演唱,就立刻能估计个八九不离十。
京剧则全然不同,曲谱并不能完全表现演员的演唱水平。业余爱好者按照曲谱去学,也是绝对学不出来的。著名演员拿到音乐设计人员编写的曲谱,看几遍便丢开了。这时他通常要想许多问题——第一,他设计的“对”人物的“路”吗?著名演员要重新研究剧本,研究是唱西皮还是二黄,抑或南梆子、四平调什么的,到底哪一个大类更符合人物此时此地的心情。然后再研究选用什么板式最符合传统又最带有新意。把上面两个系统一交叉——如果音乐设计搞的正巧也是这个,那么就无须推倒重来了。还有第二,他设计的“对”我(演员)的“路”吗?因为我是个有影响的演员,所以我每唱一出新戏,就必须给喜欢我的观众一些新东西。这些新东西既不能离开我以前所走的道路,又要能体现我向前迈了一步。注意:这里迈的只能是一步,既不能是两步,也不能是半步!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但凡有成就的京剧演员都会有“自己的观众”,他们习惯“追”着演员看,不管演员演什么戏,不管天气如何和剧场远近,都以“一场不落(缺)”作为骄傲的标志。既然有这样一批戏迷崇拜自己,自己就没有理由让他们失望。
上面我说了著名演员接到曲谱之后的“两步棋”。第一步通常不会有大问题的,如果音乐设计人员连第一步都达不到,大约就应该从剧团里卷铺盖走人了。然而,再高明的音乐设计人员也不能代替著名演员的再创造,正是这“再创造”使那“说不清的韵味儿”明确无误地呈现到观众面前。现在,我准备专门对比着讲讲歌曲和京剧在“韵味儿”问题上的几个差别:(www.zuozong.com)
1.歌曲讲究音色明亮澄澈,京剧则忌讳音色太“光滑”,崇尚声音“摩擦”着出来。京剧中的谭鑫培、余叔岩、杨宝森、程砚秋、裘盛戎,他们的音色就很有“摩擦力”。
2.歌曲吐字张口就出,京剧注意把一个字分成“字头”“字腹”“字尾”三部分,让它们依次而出。比如“家”字,其拼音为“j——i——ā”,京剧总是先吐出字头“j”,再吐字腹“i”,最后再吐出字尾“ā”。请听一下《打渔杀家》 “家贫哪怕人笑咱”中的那个“家”字的唱法。京剧绝不会把已经拼音完成的“jiā”,突然地、“整个”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
3.一首歌曲尽管也可以变速,音量上尽管也有“<”(渐强)或“>”(渐弱),但是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京剧的自由程度。京剧有一个叫作“尺寸”的名词,著名演员根据剧情和自身条件的需要,掌握节奏时忽轻忽重、忽快忽慢,那真是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4.歌曲演唱的乐句分明,因此呼吸换气基本随着乐句进行,讲究自然大方。京剧虽然也分上下句,但是经常有不规则的变化,而且讲究换气不被观众发觉,因此在一大段唱腔中,演员总要偷气数次,给观众一种“一口气唱到底”的感觉。
(三)歌曲不提倡即兴表演,而京剧恰恰提倡即兴表演。歌曲演唱中演员和乐队是什么关系?一般说来,是那个固定的乐谱把演员和乐队都固定住了。不论是哪一方离开了乐谱,对方都可以指责他“出了错”。当然,在排练中,演员和乐队的指挥都可以(甚至都应该)对乐谱做出各自的理解和修正。但是一旦到了台上,“照乐谱进行”就成为一条铁打的定律。
京剧演员与乐队的关系和歌唱不太一样,乐队只是伴奏,是应该“跟”着演员走的。更何况演员到了台上,常常受到同台演员的“刺激”,因而产生新的艺术处理——每逢这时,乐队就格外应该服从演员的即兴创造,紧紧“跟”上,并且“跟”好。从这个道理一引申,我就觉得“京剧卡拉OK”除了帮助普及京剧演唱的优点之外,也存在着一大弊病,那就是违反了“演员牵着乐队走”的京剧演唱规律。如果随着“卡拉OK”唱成了习惯,一旦上台,想再唱得十分舒展、自由,反倒困难了。
(四)歌唱演员通常只出现在晚会的某一个节目里,唱什么和唱多少与整个晚会的规格、档次和票价没有直接关系。京剧演出的规格、档次及票价均因演员而定,和剧目没有直接关系。
歌唱演员分为独唱演员和合唱演员。合唱的不能单独演出,独唱的也很少举行个人的独唱音乐会。从某种意义上讲,独唱演员的个人音乐会只能偶一为之,经常举行绝对没有观众。他们参加到晚会中来,成为晚会中一个节目的主演,其劳动量(两三支歌,十多分钟)基本被固定化了,至于唱什么歌曲观众也不会挑剔。整个晚会的票价要由有多少名哪一等的歌星(以及笑星、舞星)来确定。作为单个歌星演唱两三首歌曲的价值,是不容易计算的。
京剧主要演员本身就有价码。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文革”前,梅兰芳的票价在北京一直是最贵的,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虽然同处一团,但马连良比后面三位的票价也是稍高一些。至于梅和马、谭、张、裘各自分别演什么戏,一般不会影响到票价的变化。但是也有例外,程砚秋在解放前也有自己的固定票价,但是每当演出《文姬归汉》[3]时,票价就要向上浮动20%,原因是这出戏里安排了三段慢板(西皮、二黄和反二黄各一),主要演员很累。观众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客满得比其他戏还快。
向你建议
4—1.有一种介乎歌曲和京剧唱腔之间的“京调歌曲”,正在逐渐风行起来。它可以使听惯歌曲的人,逐渐熟悉京剧唱腔的基本旋律,从而转到喜欢欣赏京剧的道路上来。你可以寻找“京调歌曲”听一听。
4—2.如果你已经到剧场观看京剧演出超过10次,那么,你就可以说一说你喜爱听哪一位演员(包括从电视里、网络上看到的演员)的演唱,以及为什么喜欢他(她)的原因。
请你思考
4—1.从身边的新诗作品集中,找出抒情诗和叙事诗各一首。
4—2.分析一下《智取威虎山》[4]杨子荣的核心唱段“胸有朝阳”当中的抒情诗成分和叙事诗成分。
【注释】
[1]现代剧目。抗日战争时期,铁路工人、共产党员李玉和为保护密电码,不幸被捕;李母将玉和身世告诉孙女铁梅。李母和玉和被日寇杀害,铁梅继承遗志,用智慧保护了密电码,痛击日军。
[2]传统剧目。亦称《一夜白须》。春秋末期,伍员(即伍子胥)逃离楚国,投奔吴国,行至昭关,却因此处有画像缉拿伍员,无法过关。伍员留宿七日,须发尽白,东皋公设计谋,让伍员得以混出昭关。
[3]传统剧目。汉与匈奴战乱之时,蔡文姬逃难被匈奴收留,侍奉左贤王十二年。曹操赎蔡文姬回汉,临行前与孩子诀别,哭拜王昭君之墓。
[4]现代剧目。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解放军某部团参谋长少剑波率队入林海雪原,进攻威虎山座山雕匪帮。侦察排长杨子荣假扮土匪胡彪,以献联络图为名,取得座山雕信任,打入威虎山,伺机将情报送出。正当小分队准备进军时,栾平在座山雕面前指控杨子荣,杨子荣斗智战胜并杀死栾平。座山雕设百鸡宴时,杨子荣灌醉群匪,少剑波率小分队趁机歼匪,大获全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