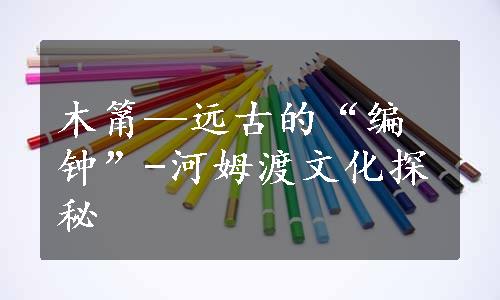
与骨笛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木笛和陶埙。陶埙单孔,已知为古代吹奏乐器。木笛有20多件,在各地出土的文物中可谓绝无仅有,也就是说,属首次发现。
从一般的渔猎工具发展为典型的乐器,木笛比之于骨笛,似有更多的证据证明这一过程。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箱有20余件,均系两头锉磨平整,中间挖空,两端相通,断面呈圆形,上下直径基本相等的筒状物。木筩作何用途?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容器说;二是渔猎工具说;三是乐器说。第一种容器说较易否定。因为作为一种贮物的容器,绝无两端一齐挖通之理,退一步讲,可能原始人在挖凿时出了差错,把本该只挖去一端的木筒把两端都挖通了,但挖错一两件尚说得过去,20余件全都挖通,可见不是疏漏所致,而是一种有计划的行为。容器说不能成立,由容器引申出来的“箭箙”、“滴漏器”之说,终因其构造和使用规范不符而难以令人信服。那么,渔猎工具说和打击乐器说又如何?笔者觉得,木笛的发生与发展历史跟骨笛相似,它的前身应是一种竹筒,无疑是一种渔猎工具;后来又同时应用于娱乐,兼有渔猎工具和打击乐器的双重功能。而发展到木箱,则已衍化为一种典型的打击乐器。
人类对大自然的声音的感知是极为丰富的,如雷霆霹雳,雨滴泉鸣,松涛竹韵,兽吼禽啭,百虫和唱,等等等等,真正是万籁争鸣,绚丽多彩。但探索原始人对制造音响的第一次推动,可能是由于其对获取食物的实际功能。诚然,这关系到音乐艺术的起源,也关系到一切艺术的起源,而这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我们如果不是孤立地看待事物的发生发展,而将它置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大环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音乐源于人类的劳动和生活。河姆渡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开始播种稻谷,便面临着一个与鸟兽争食的严峻形势,当时的鸟兽不知要比今天多出多少倍,人类栽培的这片稻谷,自然也成了它们的“粮仓”。我们在前面有关的篇章中曾经提到过,为了保护人类的劳动成果不受这些天敌的侵害,河姆渡先民们不得不在这片潮湿的沼泽地上立营扎寨,昼夜设防。他们在白天尚可,可以用弓箭、木矛等予以射击驱赶。
但一到黑夜就不同了。
如野猪等为害最烈的动物大都是昼伏夜出,在浓重的夜色里,弓矛根本无法企及,他们只能借助声音来威吓驱赶野兽,除了呐喊、击石,敲打竹筒便成了最重要的手段。而在进行集体围猎时,为了将兽类驱赶至合适的地形予以攻杀,也得借助击石和敲打竹筒等以助声威。人类之所以选择竹子作为最先制作响器的材料,因为竹子中空有节,只要截取一段,敲打起来便会发出很脆的声响。而它之作为渔猎工具,在今天的江南水乡和四明山一带尚能找到古老的遗踪,就是用敲打竹梆以威震潜伏的野兽,使之驱赶到预先设伏的地点。四明山区的庄子多建在山凹凹里,而番茹、玉米、马铃薯等多栽种在岗地上,为了防止野猪等兽类的侵害,山民们就在岗地上搭舍,每到夜晚就派人去管,使用的大多也是这种竹制的响器,但野猪是一种狡猾而又机灵的动物,次数多了,习以为常,梆声响时它潜伏在旁边的密林丛中窥测,稍有松懈,便来个突然袭击。人们就互相约定,推举一个夜晚不大打瞌睡的人作指挥,只要他的梆声一响,所有管庄稼的人一齐敲打响器,深夜里山头处处鼓角,声势颇壮,野猪以为陷入了重围,远遁而去,可得数夜安静。在江河湖泊,渔民们则利用贴近水面敲打竹梆以驱赶围捕鱼群,俗称“敲梆作业”,则是受启发于陆地上之围猎野兽,在时间上自然要稍迟一些。
敲击不但产生了音响,同时也产生了节奏。而人类的许多行为,如举手投足,奔跑跳跃,以及劳动中的采集捕捞,砍伐运输,播种收割,无不包含着人体生理的内在节奏,这种人体内在节奏一旦与敲击的音响节奏相结合,便产生了许多奇特的效果,使原来许多个体的散乱无序的行为变得整齐划一,无序变为有序,从而产生了整体的行动和力量。同时节奏也产生了乐感,于是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以敲打为乐。在此时,石、竹等响器,已从单纯的渔猎工具向娱乐器具转化,成为两种功能并存的局面。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笛,则已从渔狩、娱乐混合中分离出来,成为只具单一功能的打击乐器,可以说,已具有后来的“编钟”和“编磬”相似的性质。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第一,从竹筒到木筩,虽同是打击器具,但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竹筒之作为响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自然物,结构单一,发音单调,除了用于驱赶鸟、兽外,人们虽也利用其音响节奏于娱乐,但随着人类对声音的感知不断丰富,对音色的体察、分辨日益精细,其对人工创造的音乐的要求也愈来愈高,击石、敲竹已远远不能满足。但竹子的自然形态无疑给了他们以启示:有空窍的物器才能发出更大的声响。木笛正是基于上述实践和认识的基础上设计制作的。
第二,河姆渡木第已具有相当复杂的构造,它的设计已具备构成一种发音层次较为丰富的打击乐器的基础。在遗址出土的20余件木笛中,有18件基本完好。其中12件为直筒形,两头直径相等,断面呈圆状;3件为扁筒形,两头大小相仿,断面为扁圆形;另外3件为亚腰形,外壁的两头及中部微鼓,中部至两头间则形成束腰。木筩的外表似皆经过锉磨、削刮,平整光洁。有的还经过髹漆,刚出土时漆色微黄。有的两头扎有藤蔑等箍圈,显然是为了防止敲击时的破裂。木筩的大小以长短完整的17件分,可分为大、中、小三号。大号3件,长度在40厘米以上,其中最长的一件为亚腰形,长48厘米,外径12〜14厘米;小号1件,长27厘米;其余为中号,长度均在30〜40厘米之间。木笛外径完整的20件,外径在6〜13厘米不等,其中10厘米以上的4件,8厘米以下的6件,8〜 10厘米的10件。笛壁的厚度多为1厘米左右。木笛之作为乐器的全部奥秘在于它的内部结构。木笛内壁的加工虽不似外壁精细,但也相当平整。其中筩壁厚度一致、上下平直者约占半数,另有10件在内壁的不同部位镂有凸脊一周,即在通体平整匀称的内壁,在某一部位有一小段凸出,宽度约7〜8厘米,比上下两端内壁厚出1厘米左右。凸脊所处的部位也是一个颇为微妙的问题。有2件处于木笛的中间;5件靠近一端;另有3件距一端约3〜5厘米不等。凸脊作何用途?从3件木笛刚出土时在凸脊上面塞着一个木饼看,应是专为承托木饼而设。在一期发掘时于第四层还发现这样的木饼7件,木饼圆形扁薄,有的一面平整,另一面沿外缘向里斜挖,中间留有一个约1.5厘米的“蒂子”,木饼直径6.37厘米;而木笛的平均内径为6. 69厘米。可以推知这些木饼原来也是栓于木笛内壁的凸脊上的。木饼似采用软木制成,出土时手感弹性还相当好。(www.zuozong.com)
河姆渡先民选择木头作为制作打击乐器的材料,证明他们对材料与音响的关系已有丰富的经验和较深的理解。不同木材纹理疏密相差很大,木质软硬悬殊,不像竹类纹理单一,而多节又使空间受到了限制,木材可以根据需要和制作工具的可能,其空间可以随意延长,而在内壁的某一部位镂有凸脊,栓上木饼,又可将木笛内部任意分割成两部分,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在打击时能够发出清、沉,长、短、高、低等层次丰富的音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木饼也可以称之为音塞。作为打击乐器,经过人工精心设计制作的木筩,比之取之于自然形态的竹筒无疑是有了质的飞跃。
第三,这样制作的木笛,已具备奏出五音的条件。
反映我国古乐五声音阶的宫、商、角、徵、羽,相传黄帝时代的伶戴截竹为管,以管的长短分别声音的高低清浊,以定各种乐器的音调。因此,黄帝时代已能制作出分别表示五声的青、赤、黄、景、黑五钟,“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锺”(“锤”“通”“钟”)(《管子·五行》),大概是关于五声的最早记载。
为了验证河姆渡木筩的用途与功能,不久前,余姚市文化馆音乐室朱德孚等根据遗址出土的木笛的形状和尺寸,仿制出一套七只木筩,敲打演奏时,大号木笛发音宏沉,共振时间长,中号次之,小号木笛发音清脆短促。其精妙之处更在于那个饼状之音塞。木笛加塞之后,敲击时发出之声音不但不同于未加音塞之木笛,而且在同一支木笛的不同部位敲击,其音响也有微妙之区别。木笛加塞之后,打击时能使声波的震荡沿指定方向运动,这使人联想起笛子吹气孔一端的那个小小的塞子,它能使气流也按指定的方向流动。两者有同样的妙用。演奏实践证明,将其中五只不同长度和圆孔不同大小的仿制木笛顺序排列,其所击出之音与钢琴之音对照,近似bB,bA,Fb,E,C(,其唱名可读作2.1.6.5.3,与上面提到的我国古乐中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相似,从而进一步证明,7000年前河姆渡人制造的木箱,是一套典型的打击乐器,已经奠定了五声音阶的基础。
要把20余件几十厘米长的木头中间挖空,而且要在内壁的特定部位雕出一周凸脊,根据当时的生产工具,可以说,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程。它的加工过程,有一种推测认为是用煨红的石锥之类工具,不断刺向木头中间之应镂空部分,使之炭化,然后用石、角凿等工具挖凿、削剐、修整。这个推测当是可信的。但不论怎样,设计制作木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耗去能工巧匠们许多工夫和精力,这就促使我们作更深一层的思考:制作成套木笛是否仅仅为了娱乐,还是当时的氏族已经有了某种比较固定的信仰,与一定的宗教祭神仪式有关?我们在前一章“神巫艺术”中对图腾崇拜已经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许多结论还不得不建立在“合理的推测”上,但是最近从余姚邻市奉化南浦乡茗山后村文化遗址传来的考古讯息则表明,祭神活动在河姆渡文化时代已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奉化南浦乡茗山后文化遗址距今约6000年,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第三层的时代。从出土的釜、盆、鼎、豆等陶器看,同属河姆渡文化类型,该遗址在距今5000年的文化堆积层内,挖出了一个祭台,从实物遗存证明当时的祭神活动已相当完善。这里特别需要一提的是,在河姆渡遗址东面新发现的鳌架山遗址。该遗址距河姆渡遗址仅2公里,其年代相当于河姆渡遗址第三、第二层年代,在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处由红烧土填筑的祭台,祭台直径340厘米。两处遗址如此相近,无疑有一定的血缘关系,其信仰习俗也一脉相承,进而证明河姆渡氏族当已存在祭神(天)活动。在远古,这种筑有祭台的祀神活动往往是全氏族人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他们或跪或拜,或唱或跳,均需乐器的节奏和旋律以统一行动仪式,制造神秘的氛围。木笛正是这类祭拜活动的产物。
从河姆渡木筩特定的型制和专门功能来看,“木筒”应作“木笛”。因为字义训诂虽诠释“筒”与“笛”通,但筩是我国一种古乐器和专用名词,“黄帝使泠戴(一作伶戴)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断两节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箱以听凤之鸣。”(《汉书·律历志上》)可见其有特定的用处。而“筒”的涵义要广得多。我国的打击乐器品类丰富,历史悠久,具有多种性能和生动的表现力,从考占和甲骨文字考证发现,在殷商时代以前的12种古乐器中,以及周代和春秋战国时代所使用的80多种古乐器中,打击乐器即均占到一半以上,其中最为世人瞩目的,当数编钟。这种用铜铸造的编钟,在周朝已有大小不同,以16枚为一簨虡(挂钟的木架)的编钟,河南信阳出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编钟也有13枚。编钟的前身应是“编磬”。编磬用石、玉制成,其状如矩,商代已有单一的特磬和三枚一组的编磬出现,到了周代,已发展到由十几枚大小不等之磬组成的大型编磬。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小不等的20余件木笛,应是一套相当规模的“编筩”(在没有更科学贴切的名称之前,暂以“编笛”名之)。河姆渡编笛既是商、周时代编磬的前奏,而与稍后的编钟在外形和内涵上又有许多相通之处(将加塞的木笛垂直悬挂,犹如一口口悬钟;编笛奏出的五声音阶,又与编钟相近)。编钟→编磬→编笛,使这一在世界乐器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我国古乐器,其起源可追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
利用整块木头将中间镂空作为打击响器,我国古籍上也有记载,“奋木铎以令兆民”(《礼记·月令第六》)之“木铎”,也相当此类响器。在后来更是屡见不鲜,圆状的如和尚敲打之木鱼;长方形的如农村剧团使用之笃鼓,就是将整块檀木中间开孔,敲打时清脆悦耳,这种笃鼓还是民乐队中的指挥乐器。
如果说乐器的产生首先也是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那么它们的发展是由于娱乐功能,而其日臻完善则应归功于宗教活动。
河姆渡氏族定居后已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一方面由于有了稻谷生产,食物来源比较稳定,有了初期的“安居乐业”之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常常面对洪、涝、霜、冻、毒蛇、猛兽、病疫、天亡等灾异。面对不测风云之天,处于旦夕祸福之人而又不可解释,从而萌发出信仰某种超自然力的神的宗教活动,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就这个意义上讲,骨笛、木笛和陶埙的大量发现,绝不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时代内涵。河姆渡文化时代产生的一批图腾之类的神巫艺术品也证明,当时氏族内部极可能出现了某种宗教前期的神巫祭拜活动,而且还是相当频繁的,如日月之食,人的死亡,突发的灾异,等等,氏族里的人聚集起来,举行一定的祈祷活动,并吹奏和打击这些乐器,以祭神驱邪。当然,碰到喜庆的事,如添丁、猎获和丰收,也需要吹吹打打以酬谢神的赐福,并以示庆贺。平常的重大农时活动,比如播种或收获之前,他们也得祭拜太阳神,外出渔猎得祭拜保护神,求丁添口得祈拜生殖图腾。由于那时人类已具有清晰的灵魂意识,也可能已经出现了某种较为确定的宗教信仰。一般地说,进行神巫和宗教活动是离不开器乐伴奏的,因为舒缓低沉的吹打会使人产生一种邈远之感,不紧不慢的节奏又能创造出肃穆的氛围,最容易使原始人陷入玄思冥想,去与想像中的神灵发生一种若有若无的交感。这些神巫活动已经成为原始人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才会制造出这样众多的高质量的乐器来。总之,骨笛和木笛作为吹奏打击乐器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加上陶埙,这三种乐器极可能已发展到群体规模的协奏与合奏,当然也不排除伴以简单的祝祷或咏叹,以及围着圆圈跳跃、扭摆等原始的舞蹈动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