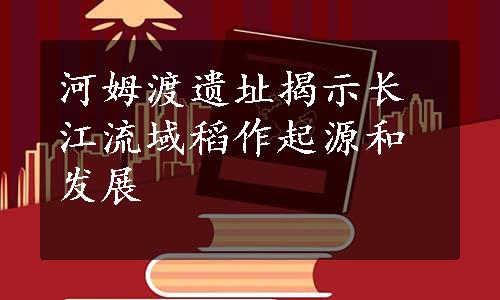
有一位哲人说过,生活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而理论总是显得苍白。其实用它来观照人类的史前活动及有关理论,也同样适用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面对先民们创造的辉煌业绩,一些关于史前文明的理论也变得陈旧和灰色。这应该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如果某种理论成为亘古不变的“常理”,那这个社会(包括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理论)也就凝固了。正是就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欢迎这一变化,并以全新的目光,以阔大的视野,以科学的新方法,去研究和探索这些新发现和新情况,从而孕育出新的理论。
我们之所以将“稻作的起源和演变”放在书的前面部分来叙述,是因为稻作的发生和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它综合了环境、气候、工具·、定居等多种因素。而且,也只有当河姆渡遗址这样内涵丰富的稻作文化发现以后,才有可能以此为时间坐标的“原”点,粗线条地勾勒出长江流域稻作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稻作的起源是整个原始农业起源的一部分,那末,原始农业(包括稻作、粟作、麦作等)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呢,人类从事这些粮食作物栽培的最初动因又是什么呢?对此,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人类原来生活的地方,随着人口的增长,可供渔猎和采集的动植物资源日益减少,免不了常常受饥挨饿,于是,不得不试着去从事谷物栽培等原始农业,以填饱日益空乏的肚子。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可供渔猎和采集的动植物资源十分充裕,依照人类的本性是不可能去从事繁复的农业劳动的。
另一种则认为,谷物栽培等原始农业,只有在可供采集或渔猎的食物资源充裕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因为谷物从播种到收获是一个较长的过程,等到食物资源面临枯竭再去栽培谷物,已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即使播种了,原始人也等不到收获,早已漫游到别处觅食去了。
上述两种观点,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原始农业起源的实际呢?我们如果不带任何偏见的话,不难看出这两种观点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前一种观点是从人类的基本需求出发,后者则立足于可能的客观条件。问题是持上面两种观点的人过于各执一端,因此不能找到两者的结合点。人类萌发原始农业的最初动因,确是在面临饥馑或受饥馑威胁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也只有在采集渔猎食物资源相当丰裕的情况下,原始农业才能获得成功。那末,两者的结合点又在哪里呢。中国有句古话叫“未雨绸缪”,典出《诗豳风·鶗鸮》:“适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意思是说,趁天气晴好,赶快把窗、门修好,将屋顶的漏洞補葺好。但是,萌发“绸缪牖户”(“牖户”是指屋的整体)的念头却是在风雨袭来房屋漏水的时候发生的。这时找到前面两种不同观点的结合点颇有启发。通二稻作的起源和演变常,原始人总得选择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环境作为自己生活的基地,也就是说,有足够动植物资源可充作他们的食物。但是,即使在食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域,比如河姆渡遗址一带,他们还是不能完全避免饥馑的威胁,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天,在大雪封山的时候,因无法获得食物而免不了受饥挨饿。这种年复一年的惨痛经历,促使他们想方设法极力摆脱轮回往复的不幸遭遇。人毕竟是有记忆的高级生命,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他们并未摆脱严冬饥饿的阴影,这大概是人类萌发的最早的“忧患意识”吧。一当有人发现谷物是可以人工栽培的,于是在采集渔猎食物的同时,有意识地开始了谷物的栽培,无疑地,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回报。在实践中他们的认识得到了升华,一年更比一年地重视对谷物的栽培,所得的回报也愈来愈丰厚,逐渐形成了原始农业。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农业(稻作)的起源始于人类对饥馑的忧患意识,而其获得成功则有赖于该地域相对丰裕的可供采集渔猎的食物资源。两者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是相辅相成的。
稻作的起源,则还要上溯到稻谷——野生稻的起源。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的稻谷堆积距今为7000年,按照正常推理,河姆渡先民栽培的稻谷,自是采集于当地的野生稻谷。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有人会问:河姆渡遗址的稻谷堆积中有野生稻谷吗?(www.zuozong.com)
没有,那你怎么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些栽培的稻谷不是来自更远的地方!?虽然从理论上推断河姆渡一带完全有可能生长野生稻,“因为现在野生稻分布的最北界是江西东乡约北纬28°14',河姆渡文化时代(遗址四层)的气候条件相当于现在的广西、海南的条件,即北纬20°上下,当然是野生稻生长最合适的条件。”[1]但理论上的推论毕竟不能替代事实的存在。好在这个推论终于被证实了,中日学者共同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中发现「四颗野生稻谷。[2]
从而证实河姆渡遗址的人工栽培稻谷的种子,最初是从当地的野生稻采摘来的,进而证明长江中下流是稻作发源地。为了搞清楚考古发现的古稻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及釉、粳的属性,许多中外专家利用最新的科技,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如:植物运动中硅酸体的分离技术;用分子遗传学方法分析稻的叶绿体DNA基因片段图谱;出上稻谷夕卜秤乳突的扫描电镜观察;单粒炭化稻DNA片段提取与RAPD扩增……这些研究对于进一步厘清稻谷和稻作的起源,釉、粳的变异和分化,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但一则由于专业性太强,二是大都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很难一一加以详述。本文只打算在“稻作”的“作”字上稍作展开。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不论任何地域的居民,无不受环境、食物、生产工具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环境提供什么样的食物,一当人类选择某种食物构成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并开始人工栽培(或养殖)时,他们都会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工具的改善与食物的增长是成正比的。在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他们总是以发明和改进生产工具作为获取温饱的主要手段。而一项生产内容的完成,如栽培稻谷、建房、纺织、制陶、渔猎等等,需要分解成许多单个的生产环节,都需要寻找相应的材料以制造合适的工具,以代替双手十指,而工具的锋利机巧程度又决定着工作的效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以说是人类很早就领悟到的一个道理。但是,在史前时期,工.具的发明和改进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采集、渔猎漫游生活便是证明,大概到了距今1万年左右,人类才开始栽培作物,逐步过渡到农业定居社会。稻作的起源也当作这个时期。
稻作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1万年左右,这已为学界的共识,而且也为新的考古发现部分地证实。自1973年河姆渡遗址稻谷被发现以后,在1993年和1995年,湖南省道县玉蟾岩(蛤蟆洞)遗址在考古发掘时分别发现了几粒稻谷,经鉴定其中一粒接近野生稻,另一粒则接近栽培稻,该洞穴遗址年代据估计距今为1.2万年。与此同时,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在与玉蟾岩遗址相近年代的地层中,发现了近于栽培稻的花粉与植硅石。当然,这只是一种讯息、,要真正证实稻作的起源地还需有新的发现,然而即使将来被证实了,也并不能证明该两地遗址与河姆渡稻作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河姆渡文化时代已进入成熟的相耕阶段,形成了原始稻作的规模生产,这在前面已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但这样成熟的相耕并非是朝夕之间发生的,而是河姆渡先民在发明了稻谷栽培以后,又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实践,才达到耜耕的水平。这一段时期,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刀耕火种”时期,也是稻作的起源阶段。然而刀何以耕,火何以种,历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解说。“刀耕火种”也称“火耕”或“火耕水耨”。《史记·货殖列传,“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又《史记·平准书》:“江南火耕水耨。《裴骃集解》引应劭的话说:“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井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稻独长,所谓火耕水耨也。《史记》只说:“火耕水耨”应劭是东汉时的一位史学家,他对“火耕水耨”的解释也是很不得要令:先放火烧草,再灌水种稻,等草和稻都长到七八寸高,全部割去,再用水灌溉,这样,草死了,稻就得独长。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矛盾:经火烧再灌水的草,既然能再与稻并生长到七八寸;将草与稻全部割去之后,稻能长,草怎么就会死去而不再生长呢。应劭是河南项城人,可能没有到过江南,只是根据传闻记载的。这样说并非要否定江南在古代有过“火耕水耨”的习俗,因为直至近代,这种习俗也未绝迹。所谓“火耕”,自然是指点火燃去地上之草;“水耨”实际上指水耕或水锄,农民们将地(田)上野草烧去之后,再灌以水,使土壤团粒结构发生分化,土层变软,耕、锄起来省力得多。至于“刀耕火种”,是后来的叫法,是指居住在山地的居民,为了开垦新的坡地以种五谷杂粮,先用刀斧将山坡上的柴木统统砍倒,取去有用的木材,积薪待晒干后点火燃烧,冷却之后再用锄削之类挖孔点播诸如玉米、高粱、豆类等杂粮。由于积薪很厚,被烧过的坡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草木灰,表土也被烧成焦泥,等于施了一次重肥,农民称之为“火力”,头一年往往会获得意想不到的丰收。笔者在童年时也曾亲历过这样的“刀耕火种”,种出来的玉米棒要比普通田地上栽种的大出一倍以上“刀耕火种”实际上是拓荒扩种的代名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它作为原始稻作的第一阶段的耕作方式。这里需要阐明的是,先民们栽培稻谷并非一开始就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初始栽培的稻谷应是小块的、零星的,在他们的食物来源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大部还得通过采集和渔猎获得。这种小块零星的栽培,其最主要“工具”还应是原始人的双手,拔草以整理出小块土地以播种稻谷,收获时大都也得用粗糙坚硬的双手将谷粒捋下。只是当他们发现用火烧地上野草荆蓬比手拔或石砍工效高得多时,才会有意识地去进行“火耕”,再配合木刀、石刀之类的工具,将地面上的杂草弄干净,然后播种上稻谷。也就是人们习惯常说的“刀耕火种”。刀耕火种阶段在原始稻作延续了几千年,在后期,随着播种面积的扩大,稻谷的收获也逐渐增多,稻米在人类的食物比重中也逐渐升高,由此人们对稻作也愈来愈重视,除“火耕”外,对有关耕作栽培工具也时有发明和改进。河姆渡“耜耕”农业就是在这一漫长的孕育过程中一朝分娩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