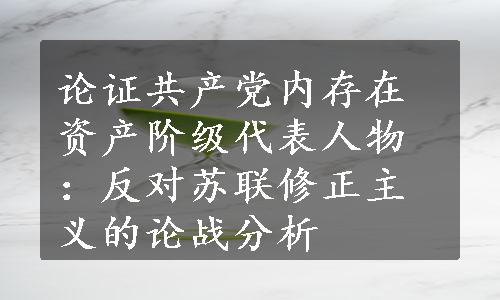
许多研究分析中苏分裂的原因时,都正确指出过苏联存在控制和干涉中国的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也指出过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马列主义正统之争。但是,苏共对中国“三面红旗”运动的批评却多被忽视了,而这才是中苏交恶的直接原因。前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副处长库立克回忆,当时为苏共中央主席团起草建议的一个小组,研究提出了两种选择:或者为了苏中关系而赞扬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或者实事求是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而为了维护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直到1958年12月底)保持沉默态度。后来赫鲁晓夫决定不保持沉默,他担忧中国的影响,他的回忆录说:“中国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说每个国家都应该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的,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的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7]
赫鲁晓夫的第一次公开评论中国内政,是1958年12月4日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作出的:“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1959年1月27日,赫鲁晓夫又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中继续影射中国:是否会有某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到共产主义,而其余国家还远远落在后面呢?“这种前景是很少有可能的。理论上比较正确的推断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效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将大致同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当然,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丰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这些公开讲话是干涉中国内政的。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解释批评中国内政的理由是:“我们感到有必要向我们自己党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的党委会也接受了中国人的这些做法时,我们更感到有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访问时对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再次公开批评,7月21日苏联《真理报》对此作了公开报道。赫鲁晓夫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是组织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美国的《纽约时报》次日就作出评论说:“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1959年12月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七大讲话中又提出:“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地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有利于敌人。”“社会不能够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的这两次公开批评中国内政的讲话正是在庐山会议的一前一后,国内也出现彭德怀的批评意见,尤其是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中苏两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正好走了方向相反的两条路径:赫鲁晓夫是对斯大林体制向市场方向作有限改良,而毛泽东是想向军事共产主义方向突破斯大林体制。中国很快停止大跃进并把人民公社调整到合作社的水平,回到斯大林体制,而苏联却继续在搞“非斯大林化”。赫鲁晓夫批判中国突破斯大林体制为“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则批判苏联改良斯大林体制为“修正主义”。双方都公开指责对方的国内政策,后来苏联把这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内政批评与干涉,概括为社会主义国与国之间的“主权有限”论。“主权有限”论利于大国压小国、强国压弱国,中国承受的压力大得多,因此受到中国的坚决反对,中国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因为中国承受了更多更大的压力,所以中国在国际国内同时举行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运动也更为声势浩大。反对“修正主义”不仅批判苏联的改良,也批判国内经济调整中出现的改革趋向,目的是维护传统“社会主义”即斯大林体制的。近年不少研究将反“修正主义”运动作正面评价,但他们忽略重要当事人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反思中苏关系时所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已有公式。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由他们的实践作出回答。“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8](www.zuozong.com)
中苏论战和“反修”,这是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不讨论隐藏其后的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等原因(这是史学家的事),只探讨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上的这一场正统之争,即何谓正统?何谓“修正主义”?论战的实质,表面是争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实际来之于两国的国际国内政策分歧,即如何看待苏联对斯大林体制的改革。从当时权威文献《九评》和“文革”中的批判文章来看,“修正主义”指“对外缓和,对内搞活”,这些改革只是部分修改了斯大林体制,但并未改变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九评》中的文章,先则认为被斯大林革出教门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出现了一个以铁托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继之则认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自从赫鲁晓夫上台以来,也形成了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说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为什么对苏联这些改良性的新政作如此严重的判断和估计?这与国内形势——从调整性的改革趋向转变为急剧左化,有内在关联。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多数欧美亚国家的共产党站在苏共路线一边,毛泽东在197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判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都不信马列了。毛泽东不怕孤立,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迎接挑战,决心捍卫斯大林所继承的列宁主义原则,而且有更大的手笔,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向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巴黎公社原则回归。这是向左的方向突破苏联模式,以抵制向“右”的方向改革苏联模式。
通过以《九评》的宣传学习运动为形式的“反修”论战,苏联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复辟国家”,论证了共产党高层变质为“资产阶级”的可能性,后果是与苏联同盟关系彻底破裂,中国在“光荣孤立”中彻底独立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