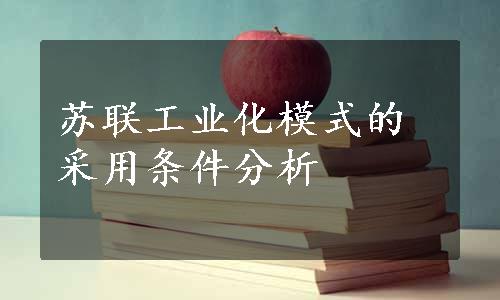
采用苏联工业化模式的主观条件在本文的第一、二节已论及。同时中国当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外部客观条件极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日趋稳定,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朝鲜战场的胜利,使新中国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顺利接收官僚资本奠定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基础,“三反”“五反”打击了民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地位,土改分到土地的亿万农民由感恩心理进而政治服从,特别是占了人口多数的贫农有“极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及苏联实施斯大林工业化战略的强大示范效应。
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政府主导的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导致提前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因。“先求强后求富”的工业化战略成为落后国的上佳之选,从德国、日本到苏联都是优先发展军事重工业。而全世界以苏联重工业优先战略发挥得最好。落后国家工业资本积累阶段,政府有目的配置资源,优于市场的自发配置,政府的效率代替了资本的不足。而政府主导经济的优势,以“计划体制加国有化”为最成功。本来,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盟可以延续下来,转而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同盟,实质是由反帝反封建的同盟转为工业化的同盟。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方案是包含这一同盟的,见之于“限制、利用、团结”的政策。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恰恰不听命于国家工业化的计划,而听命于利润,唯利是图。它偏爱投资少,来利快的轻工业,偏爱投机业而游离于生产。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最初几年的发展中,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远逊于国营经济的发展。这样,在工业化资金奇缺,亟需政府规划一切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亟需全国一盘棋奠定工业基础体系、发展重工业的时候,把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计划体制之中,就成为十分迫切的了。社会主义改造就也基于这种经济上的动因而提上议事日程。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方案,由于不适应重工业优先战略的选择,而必然让位于斯大林工业化模式。
资金积累是工业化成败的关键,“剥夺农民”是导致提前改造个体小农经济的主因。要不要向农民提取工业化资金,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史上的一大争论公案。第一场争论爆发在布哈林、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1924年托派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发表《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既不能向外掠夺殖民地,就只有把国内农业小生产作为“殖民地”。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生产者(指农民——笔者注)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而是……拿得更多。[19]拿的方法是行政手段、超经济强制、提高工业品价格与压低农业品价格。当时斯大林反驳说“把农民经济当做应受无产阶级‘剥削’的‘殖民地’的看法”,是“走上了使工业和农业间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的道路”“在工业利益和农业利益之间造成一种剥削关系,这样就是破坏任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20]但斯大林没有拿出更好的办法解决资金问题。布哈林承认一个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客观事实,但反对称之为“剥削”。他也反对“剥夺”过多,“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既损害工农联盟又缩减农村市场。向农民提取积累的办法只能通过市场商品交换。[21]这一场争论很快演变为权力斗争,没能澄清理论是非。1928年,当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启动之时,工业化资金问题又引爆第二场争论,发生于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斯大林在7月中央全会上提出用工农产品剪刀差向农民征收“额外税”,称此为农民向工业化上缴的“贡税”。[22]布哈林再次作为农民代言人,批驳这是对农民的“军事的封建剥削”,是托派理论的翻版。布哈林的主张合理一些,然而,是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解决了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
当中共发布了总路线决定用同样方法筹集工业化资金时,就发生了“国家工业化与(个体)小农经济的矛盾”,矛盾首先表现为“粮食收购危机”。1952年是大丰收之年,粮食总产达3278亿斤,比上年增10.6%,比1949年增44.8%,比战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9.3%。但1953年粮食年度收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28.2%下降为25.7%。粮食收支赤字40亿斤,几大工业城市居民口粮库存量将近下降一半,粮食供应告全面紧张。主要原因是大规模工业建设展开,1953年城镇人口比1949年净增2061万,达7826万,而农村也由于发展工业需要,大面积改种经济作物,使农村吃商品粮人口增加到1亿。[23]粮食增长高于人口增长,粮食本不紧张,紧张的只是商品粮,由于总人口中吃商品粮人口大增,而农民把商品粮买给私商,不买给国家,因为市价高出牌价20%到30%。粮食是当时中国最大宗的商品,也是国家力求控制的工业化所需的最重要资源,粮食交易又是向农民提取工业化积累的最主要途径。(www.zuozong.com)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这是建立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废弃市场经济最重要、最关键的步骤。国家垄断了城乡经济交流最基本最主要的商品——粮食,后来又加上油、棉、猪等农副产品,从而切断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脉,从而把个体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之中(个体小农经济不能再为市场自发性而生产,只能为国家指令而生产),同时也才可能通过计划强制积累。统购统销政策到198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废止,执行达32年之久。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解决了“国家工业化与小农经济的矛盾”(实际就是积累粮钱),而这又是加快合作化的重要原因。因为每年征粮,大批干部下乡,与一家一户农民直接冲突,效果很不好。而“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这对加快粮食收购进度、简化购销手续、推行合同预购等都带来了便利。”[24]在中国也发生了类似苏联的工业化争论,但不是在党内,而是在政协会议上,没好好学习过《联共党史》的梁漱溟先生为农民请命,被毛泽东叽为鼠目寸光的“小仁政”,而“工业化是大仁政”。
据此,我们也可以理顺:为什么样会从“先化后改”的工业化战略转变为“化、改并举”的总路线,再变而为实际操作中的“先改后化”。社会主义改造本是“工业化的结果和目标”,现在竟不知不觉变成“工业化的手段和积累机制”了。而总路线的表述原本就含有此意,它说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只是带动“主体”起飞的“两翼”。农业所有制变了,小农经济并未由此而变,只是由“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小农经济”。“个体小农经济”本是中共与农民的地权同盟。而“集体小农经济”才成为工业化基础上的工农联盟形式。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大大改变了工农联盟的形式和内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