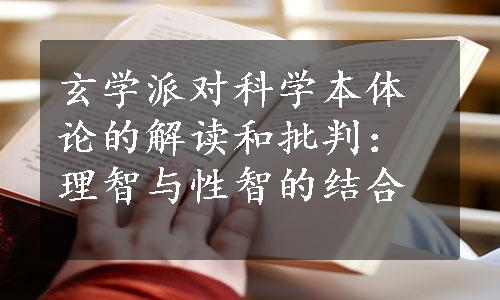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在中国进行了零星介绍[61],但当时并未真正引起人们的兴趣。1923年以后才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介绍和研究[62],1927年以后开始“风行全国”[6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本体论,他们对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64]在思想界、知识界之间终于酿成了一场大范围的唯物辩证法论战[65]。
(一)心性本体论
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玄学派、现代新儒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试图融合西方的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和现代文化来重建正在衰退的“天命”信仰,将人性、心性、仁、生命、意欲、自由意志等作形而上抽象和概括,以构建具有现代精神的新宇宙观。梁漱溟认为“宇宙之生”是中国形而上学的本来议题,宇宙是一个活的“大生命”,一切生物、自然都是这个大生命的表现。孔子是“宇宙之生”学说的典型代表,“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66]宇宙“大生命”是可以认识的,认识的方法只能是直觉而不是理智。
张君劢将自由意志赋予形而上意义,认为人生在于自由意志,无客观标准,“惟有返求之于己”[67]。玄学派的自由意志、生命本体论主要是针对科学本体论而言,他们借助了西方生命哲学理论,倡扬儒家心性之说,藉以批评科学本体论。
熊十力融合唯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以本心、仁心、“宇宙心”为本体,即“心本体”,认为本体“非是离我的心而外在者”,它“圆满至极,德无不全,理无不备”。人类的“性智”可以认识“心本体”,人类的“量智”(亦称“理智”)则可以认识“心本体”外显的物质。“理智”与“性智”结合,形成一种认识外界与本体,探求知识和超越知识的认识活动[68]。
牟宗三将精神性的“仁”作为哲学最高抽象物,它可以通过“觉”和“健”来认识,“觉”是从心上讲,即生命不僵化、不粘滞。“健”是“健行不息”之“健”,也是精神的,不是自然生命或生物生命之冲动,“仁就是‘创造性本身’”[69]。
贺麟把宋明心学与理学相结合,并糅入黑格尔哲学,将“心”“天”“理性”等同起来,认为精神哲学是注重心与理一,心负荷真理,理自觉于心的哲学[70]。现代新儒家的心本体论虽具有传统哲学的“本位”特色,但不是对传统宋学的简单复归,而是融入了西方哲学,进行了现代转换,也是一种现代性本体论。
(二)科学主义解构本体论
严复以“天演”来批判“天命”“天理”观念,建立科学主义宇宙论和科学逻辑方法论,“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71],从而将哲学引向科学化、实证化道路。胡适将科学的实验精神扩大来讲人生,讲宇宙,讲哲学,试图构建一个“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上的”宇宙观,认为物质是不死的,是活的;不是静止的,是动的,宇宙及其中万物运行变迁的原因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72]。
科学主义思潮否定本体论的意义,解构哲学形而上学,以经验实证原则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空前的[73],丁文江批评“不可思议”的“本体”是“玄学家吃饭的家伙”,从伯克莱至张君劢,始终没有大家公认的定义方法,各有各的神秘,说“哲学是假科学”“科学是真哲学”[74]。南庶熙、叶青等认为哲学本体论是根据认识论的,离开认识而独立的本体是乌有的。近代哲学的本体在康德以后就不再有优越地位,本体论降为认识论的一个“分科”,唯物论者将本体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在“古调独谈”,现代科学“根本不问本体”,“认知作用本身即是以表示宇宙本体”[75]。
批判唯物论的另一个致思路径,是将哲学上的物质予以实证化,从而否定物质的本体意义。傅统先认为物质只能是被人认识的物质,它只有认识论的意义而无本体论的意义,“新唯物论者只是用一个本体论上的名词套在一种不健全的认识论上面。这只是名词之争而非真理之争”。唯物论的“物质”与唯心论的“绝对观念”、新实在论的“逻辑的结构”并无多大区别,实在论也主张在人的意识之外有一个独立的外界存在,只是不承认外界即是物质;绝对观念论的“绝对”,也可以解释为独立存在于意识之外,而刺激我们之感觉的”[76]。(www.zuozong.com)
张东荪说辩证唯物论的“物质”,与唯心论的“绝对观念”、新实在论的“逻辑的结构”并无多大区别:“实在论也主张在人的意识之外有一个独立的外界存在,只是不承认外界即是物质;绝对观念的‘绝对’,也可以解释为独立存在于意识之外,而刺激我们之感觉的”[77]。“我们把物理而代替物,便亦正可把生理而代替‘生’,就是有物理而无物质;有生理而无生命;有心理而无心灵。这亦就是说一切都是架构,而无实质。而架构却不是能离开我们的认识”[78]。他又说“所谓机械的唯物论与辩证的唯物论之分别就只是抛弃德穆克里托、霍布士一流的唯物论,而转到自然主义的、实在论的、经验论的进化论,其内容毫无新颖,所有的都是欧美哲学已经早有过的。又可见自从新物理学出来了以后旧式的唯物论(即把物质当作本体的)实在无法维持了”[79]。
陈伯达等批评张东荪、叶青等的“唯物论破产”是没看懂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书中明明提出应把哲学上的物质概念同物理学的物质结构理论区别开来。
(三)民生本体论
孙中山将“民生”看做是形而上的最高存在、宇宙的重心和一切生产、经济、政治活动的中心,涵盖“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80]。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原本存在唯物论的因子和辩证法的要素,但其继承者却以“仁爱”“诚”等儒家思想加以曲解,使民生主义儒学化。戴季陶的“仁爱”说、萨孟武的“生存技术”说、胡汉民的“心物合一”说、陈立夫的“唯生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等,无不以“民生”为最高范畴。民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尖锐对立的两种哲学形态,特别是民生哲学发展到“唯生论”阶段,成为“这些年来在中国与辩证法唯物论相对抗的最主要的思想之一”。他们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以物质环境,来作解决人生问题”是“本末倒置”[81]。
艾思奇之针锋相对批判“唯生论”的心物综合本体论偏离了孙中山的“民生”本意,是“物活论”在中国的再版。他说:“唯生论的哲学,是以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为渊源,以孙中山先生的某些话做为根据,但唯生论哲学本身,并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而只是他的一部分思想的附会夸大的产物”。[82]
(四)物质本体论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本体论问题缺乏思考。陈独秀称“哲学”主要是指“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学的哲学”[83]。对哲学本体论的思考起于瞿秋白,他用“我”与“非我”、“实质”与“认识”、“自然”和“灵魂”等范畴来阐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初步确立了物质本体论。他说:“‘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的关系以及‘灵魂’与‘自然’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一问题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非我”“实质”“自然”是指客观存在,“我”“认识”和“灵魂”则指由客观存在决定的思维和意识。“先有物质,而后发生能思想的物质——‘人’。可见,物质先于精神。”“可以有无精神的物质,而不能有无物质之精神。”“可以断言:精神不能外乎物质而存在;物质却能外乎精神而存在,物质先于精神;精神是特种组织的物质之特别性质。——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84]
艾思奇遵列宁的“物质”定义,认为哲学上的物质是指“实实在在地在我们主观意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独立地运动变化的东西”,“物理学上的物质,在哲学上看来,只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状态,或一个阶段”[85]。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阐释则最早从实践角度来立论,这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高出于苏联教科书的机械论倾向。他认为实践范畴是马克思“建立历史观之唯物论的根据”,马克思“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86]。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都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本体论主要源自列宁主义的物质观。“实践”本体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抽取的一个概念,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主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