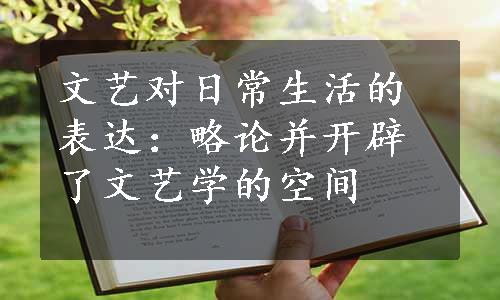
略论文艺对日常生活的表达
李有兵
本文试图讨论日常生活是如何(凭什么)进入文艺这一领地的。讨论这个题目的动力和依据当然来自现实的文艺活动,尤其是一些新兴的文艺形式因为其对“草根的力量”的彰显而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这些都激励理论追随于后,探究其中蕴藏的秘密。
一
本文不拟以时下正在讨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立题——以此处的理解,它实乃讨论的是正在中国城市部分人群中逐渐兴起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态度)之现实影响——甚至在此还要有意与之保持距离。本文所关注的是这样的人生景象:长时间的、缺少变化的机械式劳作,比如抱着钻头持续几个小时地钻探,一镐一镐地挖掘土地,劳累而很少感受到乐趣——这一切只是为了基本的口所需。这是本文所理解的“日常生活”——这种凡俗人们的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生活,这种平常、单调、刻板、乏味的重复生活。本文在此力图证明:这种生活不仅在创造“美”,而是本身就是“美的”。
诸多理论曾将文艺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主将阿格妮丝·赫勒在其名著《日常生活》中,将日常生活和艺术对立并举,比如日常生活的拜物性和因循惯例与艺术的创造性和穷根究底;日常生活的刻板重复与艺术的变化、富有激情;日常生活的直接性与艺术的追求类本质和整体生活描述的超越性等等在本性上体现为对立相反(1)。黑格尔甚至以日常生活为虚幻的“附赘悬瘤”,并以摒弃直接感性现实作为艺术成立的关键一环(2)。亚里士多德主张文艺应该模仿我们身边的人,即不是太好或太坏,而是比我们稍好者的性格,似乎以平常人为表现对象,但是其理性主义思路使他一方面要把人物活动抽象为“情节”,另一方面,他所表现的性格并非“个性”而是“类型”,故而仍然不可说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表达。
日常生活,似因其缺乏光彩而很少入史,甚至野史亦因其缺乏传奇性而多拒绝之。但是,我们的常识昭示着:这正是大多数人真实的生存状况,或曰,此即人民生活的常态。如果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成立,则人类历史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只是它似乎太缺少绚烂的亮色,而不能引人“注目”。以“回到事情本身”为学问主旨的海德格尔,创造性地将人从“主体”降格为“此在”,从而使我们更加接近朴实而真实的人的生存境况,但他亦将“常人”及其生活作为否定性题目而区别于“真实的生活”。但就文艺而言,其只可能是表现人生的。故而在此处形成了一个矛盾:文艺是表现生活的,但文艺必须否定生活才能成为文艺。对此矛盾的化解,一个流行而著名的观点是:文艺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表现人生是文艺成立的最终依据,但文艺揭示的是生活中“有意义的那部分”,或者说文艺只表现生活中“有意义的因素”,平庸、乏味则被摈斥于文艺大门之外。此实即“典型理论”:文艺不表现“一般人”,只表现“典型人”及其“典型的生活”,生活必须经过“典型化”才可能进入“文艺”。此处的逻辑仍然是将生活分为两种:一般(日常)生活,诗的生活(但将“诗”理解为高尚、雅致的东西)。后者是真正的、有意义的生活;换言之,生活只有在“诗”中才葆有其本真性。
矛盾依然存在:文艺是表现生活的,但文艺却告诉人们:只有生活在“别处”才是生活。对此福柯有深刻揭示:
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日常生活要进入话语,其中必须充斥着寓言式非同寻常的东西,并因此发生变形,才有可能;必须由英雄业绩、功勋、探险、神意或恩典,可能还会有恶贯满盈的罪行,使日常生活脱离它自身;日常生活不得不带上一种不可能之事的印迹。只有这时,日常生活才会成为可以讲述的。这样,就将日常生活置于常人所不及之处,作为教训,作为榜样发挥作用。叙事越是远离平常的东西,它的影响就越强,就越有说服力。因此在这出由非同寻常的榜样(fabulous-exemplary)构成的戏中,根本之处就在于真假无所谓。而如果凑巧有人来讲述现实生活的平庸之处,那只可能是为了造成喜剧效果,讲述这种生活只会令人发笑。(3)
福柯的本意是揭示权力如何通过隐蔽的规则实现对日常生活的统治,他认为文学在此正承担着这个功能,因而也揭示了文艺与生活之间的紧张对立。
二
日常生活之进入“诗”,也许应从消除二者之间的鸿沟开始,为此,仍须回到对“美”(诗性)的理解,因为它乃文艺之本质性根据。“美学”从其学科创意来看,即是以研究人心中处于清晰的认识之前的“暧昧”、“朦胧的观念”部分为主题的。为此,鲍姆嘉登在美学与伦理学、逻辑学之间划出了明确界限(4)。后来康德更是将审美判断力作为人心最基本的功能,已经阐明,审美乃人面对世界时的基本感受,它建立着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构成其他一切关系方式(如知识方式、道德方式等)的基础。“美是那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5)“美是那没有概念而被认作一个必然愉悦的对象的东西。”(6)“那规定鉴赏判断的愉悦是不带任何利害的”(7)。“美是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如果这形式是没有一个目的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到的话。”(8)康德关于审美判断的四个契机的分析,实乃表明,审美乃是个体与对象之间的内在亲和关系。海德格尔表述得更加明确:“美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献身方式。”(9)换言之,美乃生机盎然。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氏以古希腊神庙(这一建筑作品)为例,阐明艺术实乃真理(在海氏处实即生活,生生——引者注)之自我运动。石斧和神庙都是用石头制作的,但“石头”硕大、沉重和负荷的本性消失在石斧器具的有用性中,而在建筑作品中则得到了保留。石头的坚固不可能通过砸碎它、穿透它把握到,石头的沉重的分量也不可能通过称量计算把握到,由此得到的只是“表象”和“数字”,石头那种逼迫着向我们袭来的力量则逃之夭夭了(10)。生生实即“人自己”、“物自己”的自由舒展运动,它在艺术中保留着自己的本性,而在知识、甚至道德规则中都消失了。文艺即生活,而不是生活的表现。海氏名言曰:“人诗意地栖居”,表明生活本质上即是“诗”的。今人叶秀山释此为“人活生生地存在着”(11),可谓传其精神。
文艺乃是生活之自我展开(生生)。由此,日常生活凭“什么”进入“诗”便获得了可靠的依据:生活自有其伟大的力量,这是生命朴实光华自由自在的闪耀。“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苟日新,日日新”(《大学》)、“日新月异”,正是对日常生活的描述。日子,活生生的具体现实,是无法被“逻各斯”、知识范畴所规约的。就像河流,散发着无数光彩,展现为无数姿态,它是水的历程,只在“水”里存在,而不在“它处”。河流是河流的真理。人生的真理只来自人生,而不是某种“正确观念”——“正确的”是价值论用语,乃是基于某种抽象为现成物的“精神”的评价活动,恰应以人生、日子为基础——因而,无所谓正确的生活,只是生活(12)。真理就是学习、交往、衣、食、住、行,就是人生,而不是人生的“总结”。日子是日子的真理。日子也许无聊、刻板,但无聊、刻板自有其自身的力量不容忽视。因为在“无聊”、“刻板”中,时间仍在逝去,生命之花仍在绽放,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罢了。
这是“小人物”的生活,常人的生活,不绚烂,不传奇,不典型,但也在人生最基本的层面(诗)上。反倒是“典型”偏离了这个基本的面:言“典型”总是基于某个标准、尺度的判断,比如依“学生行为规则”而有“好”(典型的)学生,依精神病学理论而有(典型的)精神病患者等等。但人首先是“人”,在这个基本层面“之上”(之后)才有所谓的“好人”、“坏人”,“健康人”、“病人”等被衡量、分析出来的“人”。被抽象、分析出来的“人”也因此丧失了本己的丰富性(诗意),成为“单向度的人”。以“审美”为基本性质的文艺则正是要将被知识(科学)“类型化”了的人维持在基本的原初性的维度上(13)。由此,如果承认生活是“日常性”的,则文艺恰以保存这种“日常性”为己任,将“刻板”表现为“刻板自己”,将“无聊”表现为“无聊自己”,以此凸现生活那生生不息的本性。同时,只有将生活“还原”为基本的和日常的,英雄人物才会获得坚实的根基以自身朴实的卓越挺立为传奇——这不是依靠虚构、变型等典型化抽象手段,而是自身力量的自由绽放。至于作为艺术修辞手法的虚构、变型,则是某种具体艺术形式对其与生活间障碍(差异性)——比如镜头画面或语言的次第展开方式与众多人“同时生活”之间的鸿沟——之克服。后文有述。
此处仍须澄清的一点是,本文无意抹平无聊与激情、琐碎与丰富、“小人物”与“大人物”之间的界限,无意也无能消解生活中存在的价值论活动。此处的意思是说,作为表达人与自然最基本关系的文艺,其依据只来自生活,是生活真实性的展示,所以它首先应以“真理”的眼光、态度去记录生活,而不是无批判地坚持某种价值论立场“评判”生活。甚至可以这样说,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拥抱、热爱生活的全部,他热爱邪恶就如同他热爱正义,他热爱敌人就如同他热爱恋人。此前已有述,因为生活无所谓正确、错误,无所谓好、坏,对生活作出正误、好坏等价值判断恰应是在“生活”这个基本的维度之上,并以其为依据的。因此,也只有具备这种不夹杂主体性意志的客观真理态度,才可能体察到那最平常的日子“下面”所蕴含的生命自我运动那巨大的力量来。下文拟以具体作品为例阐释之。
三
影片《大象》是美国当代导演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新近之作,取材于美国某中学发生的一起校园枪杀案。这是一起真实事件。据说事件发生后,照例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政府、媒体、街头巷议从不同角度讨论(评判)之。如检讨国家枪械管理条例、教育体制以及人际关系生态等等。桑特有感于这种“议论”恰恰可能淹没“事件本身”,遂努力以电影形式试图保留之。
整部片子跟踪了一个校园平常的一天,以及这种平静的被打破。上课,体育锻炼,由学生逃课引起的师生谈话,是非议论,个人爱好,友谊,苦恼……这样的内容在任何中学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是一个庸常的日子。但阅读此片,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庸常”所蕴含的爆炸性力量。在此,每个人的生命的每一时刻、每一地点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因而也无法被归纳、抽象为某种情节线索。桑特通过将摄影机的表达力发挥到极致逼出了理性情节的界限。庸常的日子是“我”活在“你”、“他”之中同时“他”、“你”活在“我”之中,是大家“同时”在活着。因而生活更像是一个“浑沌之流”而不是一条“线”,线型单视角(比如一台摄影机一次只能表现一个生活场景)在此失去了原始的表现力,而只能以变型方式多次、多角度表现之。片中出现了大量的画面切碎、穿插,甚至重复。最鲜明的例子是摄影爱好者伊莱亚在走廊里碰到同学约翰,给他拍了张照片,同时有一位同学米雪尔从他们身边跑过。这个画面在片中出现了三次,其实是三个不同视角下的场面,或者说在这个画面中有三个“主角”,谁也无法被客体化,因此谁也无可替代。所以三个看似相同的画面分别是三个学生的生活片段,而非三次“重复”(14)。但影片最具震撼力量的地方来自一种独特的“镜头伦理”:影片主要采用长焦跟拍手段表现人的生活。在此,摄影机就像一个忠实而又沉默寡言的仆人静静地跟随在“主人”身后,关爱地注视着他走远。这种纪实白描的态度使导演尽可能地避免了主观化,也因此尽可能地拉近了电影和现实生活的距离。比如长时间地跟拍某个人物的行走,单调、冷静、缺少变化。但这正是生活的常态,只是我们平常沉溺于此而习焉不察,因此当我们在桑特的艺术中“注意”到这个事实时,甚至不须要以生活的毁灭——死亡——的提醒(桑特在影片中则是以人物简单、平静的死亡映衬出每一个生命无可替代的意义),我们也能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无形力量的压迫。桑特在此冒着牺牲影片观赏性(此乃现代性美学追求)的危险,表达出:凡人无论好坏、贤愚,都是具有个性情感、生存尊严和生命力量的“主体”;同时,每个人的生活都可能成为他人生活的经验片段。所谓“完整生活”,甚至“完整事件”,可能只是一个理性表象。这不仅是指个体无法完全通达“他者”,还因为“我”中亦有“他者”,因此,“我”甚至无法完全通达“自己”。每个人都无法超越自身有限性,因此,所能经验到的都只是人生“片断”(“碎片”)——日子即“碎片”(15)。生活本质上乃生生不息的浑灏流转,“碎片”乃是人对生命浑茫的原初感受,因而它是“诗”。
生命的活力在于葆有诗意(活生生的本性),故对“碎片”之葆贞乃是人生最基本的活动,它是人对此世界的“初恋”(时时处处面对每一个对象的每一次“初恋”),是生命延续性的基点。生命之形成延续必及于“他者”。“他者”也有“碎片”,同样是“诗”:如前述,这是“我”的切身体验,而非凭空想象。承认“他者”同样具有做“诗”的能力和权力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素养——这保证着我、你、他生命的有效关联和生命延续性;换言之,它保证着人之成为人、亦即人生的真实性。以个人意志侵吞“他者”意志,则个人亦没入无根据的深渊;以众人意志侵吞某个个人意志,实乃恶俗的公众消遣。格斯·范·桑特正是为了抵抗这种面对生活事件的消遣性态度,以“大象无形”故而“瞎子摸象”命意自己的作品,道出了人——不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在对“事实本身”把握上无可避免的片面性和盲目性。这似乎是一个悲观的“不可知论”的结论,其实蕴涵着深挚的人道关怀:不可妄发议论,以免伤害自己和他人。我们应该像一台谦恭的摄像机默默地跟随众人身后,不掺杂己意地去听、去看(述而不作)。这应该是我们进入生活真实性的合适态度,因而是文艺自我成立的根据。传统现实主义以客观“再现”生活为理想,后现代主义则发现,将原本浑沌的生活编织成理性“情节”,仍然是主观性的,所以要瓦解“情节”,代之以“碎片”。在认识生活的真实性问题上,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新的深度。桑特即为一例。
此处再论“重复”。日常生活之被诟病为因循、刻板、单调,皆因其重复。人们往往贬低“重复”,应是指其不创造新的价值符号。但正如人迈步行走,“动作”本身的力量在重复中却是累积向前。而“价值论”已如前述,实乃理性主义的抽象执着,而非无条件的绝对判断,它须以生命、生活为基础。但生命本身无所谓重复,农人的田间劳作,母亲的日夜哺乳……生命每天都在创造新境界。所谓“重复”,仍在活生生地记录着时间流逝、生命流淌的沉重步伐。它“重复着不可重复的东西”(德勒兹语)。重复令人生厌,也许根源并不在被观看者,而在观看者自身的态度:不能投入情感。这一点可从“赤子”的行为中映照出来:他们常常无数次呼唤母亲并要求一次次的回答;兴致勃勃地做相同的动作直至身体(生理)疲惫才罢。他们的情趣来自自身,而非某种在先已有的价值论立场,因而生机盎然,无往而非趣也。我们在艺术活动中也能找到例子。张艺谋导演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中,为了寻找走失的张慧科而寻求电视台的帮助,魏敏芝守候在电视台门口等待遇见台长。这是一个茫然甚至几近徒劳的等待,因为她不认识等待的目标,也因此常常出错(认错了人,而显得某次等待的无意义)。但这恰恰崭露出“等待”朴实的真相:一次又一次地守候,一次又一次地寻觅,直至达到目的(16)。张导演在此毫不吝惜地消耗着胶片,这似乎不符合艺术简洁原则和现代艺术制作的成本原则。但当我们猛然想起,一个从未经历“城市”世面的农村孩子正淹没在陌生的人海洪流中等待亲人的召唤、等待回到熟悉的家园时(张导演当然不会忘记通过蒙太奇画面提醒那些“粗心”的观者),则魏敏芝一次次跑过去打听又颓然转身这个重复动作所蕴含的力量急遽向我们压迫过来。高明的欣赏者长时间地驻足于某件艺术作品面前流连忘返,反复涵咏;优秀文学作品令人反复阅读而又常读常新,凡此都在彰显着艺术中“重复”的秘密。
四(www.zuozong.com)
艺术家用艺术形象启示着:当我们以朴实、深沉的情感投入生活时,那“重复”所致的“板结”便悄然融化了。诚挚的情感从两个方面决定着人之成为人的根据:第一,主动应接“他者”影响的感动力、应和力是最基本的人道条件。“道始于情,终于义。”“始者近情,终者近义。”(《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表明具有“发乎情”的能力不仅是人性最基本的内涵,同时也是此世界成立的基础。第二,诚挚的情感乃是共通感,是“我”通达“他者”的通道,它使一个孤立、自在的“我”现实和谐地融进“大家”之中,形成一个天、地、人、神相偕共存的整体生存环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忠恕”之道作为儒学基本原则,康德以共通感为依据阐释作为人心基本能力的审美判断力,都可在此理解为对情感的本体性地位的深刻体会和重大揭示。在此义上,可以说,情感即生活,而真诚地活着即是“诗”。古人表述为“情深而文明”(《礼记·乐记》):诚挚的心灵使天地万物以自由自在的姿态彰显出来。
古人曾经区划出人生三重情感境界:深情执着的“钟情者”,寡情迁移的“不及情者”,博爱天地万物的“无情者”(《世说新语·伤逝》第四节,王戎:“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在现实中我们常常表彰“钟情”而排斥“不及情者”。但是文艺应该站在真理性(生生、无情)立场,以消解前二者的互相对立排斥,将其包容进更广大的超越性境界。圣人无情,以天地万物之情作为自己的情感,物来顺应,物往不留,不迎合,不执着,随物赋形。此态度正是这世间一切存在者——俊、丑、贤、愚,鱼、虫、鸟、兽,山、河、花、草……活生生地和谐共处的基础。文艺不仅要书写“有我之境”,以彰显一个“真我”世界,还应书写“无我之境”,以彰显“小我”之外的天地世界。也许只有以后者的态度,日常生活——这个包容拱卫着“沉默的大多数”的世界才可能焕发光彩,在赢得更多“瞩目”中得到真正的葆贞。
(作者李有兵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注释】
(1)参见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第56—57页,重庆出版社, 1990年版。
(2)参见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福柯:《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中国现象学网·思想散论》(www.xianxiang.com)2005年1月。
(4)参见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第24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5)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第54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第77页。
(7)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第38页。
(8)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第72页。
(9)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孙周兴译,第4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海氏此表述和孟子所谓“充实之谓美”义近之,均可理解为美乃是生命自身力量的绽放。
(10)参见海德格尔《林中路》(修订本),孙周兴译,第31—32页。
(11)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第302页,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12)德勒兹:“无所谓正确的思想,只是思想。”参见《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第4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3)参见叶秀山《美的哲学》,第80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14)因此,同样,我们在此处的“叙述”并不准确,或者说是一个片面的叙述,因为我们在此是以伊莱亚为主角(主体)的叙述,仿佛这三个人的“相遇”是伊莱亚的主动行为,其余二人是其行为客体似的。
(15)其实这个“碎片”已是理性抽象的产物,它是指“意义”之不能连贯成为一个整体性,故而仍属“意义”范畴,仍然是表象。
(16)在此,“目的”通过“动作”而实现,同时“目的”也保护着“动作”的意义。二者内在地融为一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