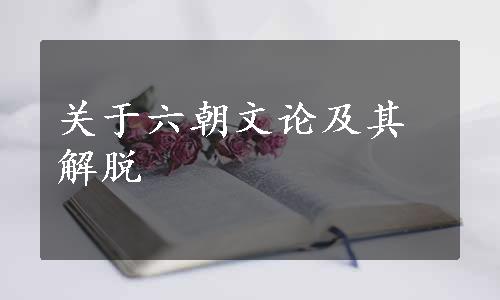
关于六朝文论“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
李顺刚
物(表现的对象)、意(作者的意、构想)、言(语言表现、文)三者的关系,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是伴随着六朝文论对“文心”的论述逐渐明确起来的(1)。从陆机在《文赋》里自觉地提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苦闷开始,文学作为作家个人性质的创作活动,如何完美地运用语言表现个人的情志和客观的外物,就成为魏晋以后文学创作论一直力图解决的问题。这一点,从《文赋》到《文心雕龙》,表现的最为突出,这是较为周知的事实(2)。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是围绕着“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陆机和刘勰等人前后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以物、意、言三者关系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创作论体系。
本文试图从“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这一创作命题入手,探讨其由一般创作经验过渡为文学理论命题的过程,特别是以《文赋》为中心,通过考察魏晋玄学与文学创作论相融合的顺序和途径,进而探讨物、意、言三者关系为核心的六朝创作论的成立和展开。
一
在六朝文论中,陆机的《文赋》占有显著的地位。如果说魏文帝的《典论·论文》,是从文学批评论谈起,建立了作家风格论,成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宣言;陆机则是立足于个人的创作经验,自觉地研求文学的创作规律的(3)。并且,陆机是首次自觉地意识到文学创作中“言不尽意”的苦闷,进而产生了解脱这种苦闷的自觉。从而将文学的自觉深化为创作行为内省式的自觉,开辟了六朝文学理论登堂入室的门径。
《文赋》是《典论·论文》产生八十年后的作品(4)。在这期间文坛的变化对《文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就是说,《文赋》创作的原因,是这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文赋·序》言: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5)。
从这里可以看出,陆机讨论创作之“用心”,得之于二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从前人和同辈作家的作品中揣摩而来的。从现存的资料来看,较为直接言及创作“用心”的,见于《西京杂记》里司马相如的“赋心”之说(6)。但仅限于描绘了作家沉浸于构思过程的“神思”状态。汉代扬雄也有“言不能达于心,书不能传其言,难矣哉”(7)的感叹。以上司马相如和扬雄关于“文心”的议论,理应对陆机有所触发。但是,建安以来诗文创作的实绩,对陆机更有直接的启示。例如,建安诗风的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8);构思的精妙,“驱辞遂貌,唯取昭晰之能”(9)。均在《文赋》中有所反映。降及正始文学,稽康散文的说理细密,阮籍诗歌的含蓄深远,西晋傅玄的拟古之作,张华之文的辞藻温丽等,都给《文赋》提供了创作的经验。
二是从陆机本人的创作体验中得来的。从《文赋》扣紧意和辞的关系,层层推论作文的利害所由来看,实是作者本人创作上的经验之谈。仅以刘勰对陆机作品的批评为例,足见陆机平日锤炼章句的文风。
惟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文心雕龙·杂文》)(10)
陆机自理,情周而巧,笺之为善者也。(《文心雕龙·书记》)
陆机之《移百官》,言约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文心雕龙·檄移》)
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文心雕龙·訑裁》)
人称“二陆”之一的陆云也认为:
云作虽时有佳语,见兄作,又欲成贫俭家。(《与平原书·其五》)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11)。故此,陆机写下了许多创作上用意遣辞的艰难情形。陆机自觉地研求为文之用心,除了自我言明的原因之外,也多少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晋书·本传》称陆机“服膺儒术,非礼勿动”,足见其守成、持重的为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评其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文心雕龙·才略》“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文心雕龙·事类》“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沉密”等等,确是透露了陆机矜持深思的气质。这种气质也就决定了他较容易体悟到“言不尽意”的苦闷,并产生彻底追究解脱这种苦闷的自觉。值得注意的,由《典论·论文》式的外向的人物批评一转而为内向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倾向,其中固然有陆机本人气质个性的因素,但是,由魏入晋的乱世,为了求生避祸,文人们由外向的议论转为内向的玄思,这种创作风气的变化,在当时却是普遍的现象(12)。
在《典论·论文》里,“文以气为主”,强调的是读者的印象批评。“文气”说与“诗言志”论之间,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为文经世的倾向较为明显。至陆机一变,高扬作家个人的创作经验,文人创作的最大苦闷是“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崇意论与缘情说交融在一起,文学由此脱尽了与儒家文学观的关系,开始从新的基础上建立文学的创作论。因此,《文赋》的论旨与曹丕的《典论·论文》截然不同。全文没有一个“气”字,前后却用了七个“意”字。七者之中,除最后“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的“率意”,不是特定的指述语之外,其余六处“意”都具有明确的含意。例如:
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
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
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昇。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
郭绍虞指出,通过构思所形成的“意”,是作家创作活动中的内在意象(13)。陆机认为,“意不称物”和“文不逮意”是创作活动中司空见惯的苦恼,这种物、意、言三者关系的谐调和统一,“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作为作家,陆机更多的从创作经验的层面上讨论问题。因此,与“意不称物”相比,解决“文不逮意”的问题,更是现实而迫切的。从全赋来看,陆机的笔墨大多放在言意关系上。例如,“罄澄心以凝思,渺众虑而为言”,“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要辞达而理举”等文。陆机对言意关系的重视,虽然带有修辞主义的倾向,以至后来被认为是形式主义文风的滥觞(14)。但是明确地从理论上解决“文不逮意”的问题,为六朝文学创作论的成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却是《文赋》难得的贡献。在这期间,文坛上有关言意关系的议论,虽时有所见,如嵇康《声无哀乐论》有“言意无涉”的主张(15)。葛洪在《抱朴子》里,列有《辞义》篇,讨论辞与义的关系。范晔也发表了“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的观点(16)。然而,在诗文创作理论方面,对物、意、言三者关系的认识,还没有超越《文赋》的水平。所以,“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在陆机所论“文心”的基础上,《文心雕龙》进一步以物、意、言三者关系为核心,彻底超越了文学创作的经验层面,建立了完整的文学创作论。
二
汤用彤曾经指出:六朝“文论之发达,因在对于当时哲学问题有所解答也”(17)。诚哉斯言,六朝文学理论的成熟,即从先秦以来印象式经验性的批评提高为形而上学的思辨性的理论,不能排除当时社会清谈玄理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尤其是物、意、言概念的确立,“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明显地是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形成的(18)。但是,魏晋玄学是通过怎样的顺序和途径,对文学理论的成熟产生影响的,特别是对创作论的成立和展开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还停留在现象的泛泛的议论上。从六朝文学创作论的实态来看,“言意之辨”应该是玄学的思辨理论沟通文学的创作体验,进而启发了文学创作论成立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世说新语》里有“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己。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的记载。玄学三理的说法虽始于东晋初年,但是,魏正始前后玄言清谈已在士族中形成风气(19)。与两汉经学相比较,魏晋玄学是具有相当形而上学性质的哲学,它不再把天道变化来附会社会人事的变动,而把天地万物等具体物象及其运动变化仅作为世界的表象,把“寂静”“虚无”作为宇宙万物的本质。因此,玄学的方法并不是就事论事,它在研究宇宙本体时,提出“有无”“本末”“体用”“动静”“言意”等新的哲学的概念来进行抽象的思辨推理。所以,玄学在抽象的思辨方面,不仅超过了两汉经学,也超过了当时素朴的唯物论。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言意之辨”上。
“言意之辨”原由汉魏之际的“名理之学”发展而来。汉人识鉴人物往往由外貌的差别,来推知内在的才性。故有所谓“骨相”之法。在《论衡》中,王充就曾著有《骨相篇》,“察表候以知命,……表候者,骨法之谓也”。王符《潜夫论》列《相列篇》,也有类似的言论。以外貌来评论人物优劣,刘邵《人物志》同样继承了这种风气,以为可以通过外形察知内在的精神,而人的精神常由眼神来表现,故又有“征神见貌,发情见目”(《九征》)。所以,《三国志·魏书》有蒋济之论眸子,以为观眼晴可以知神气的记载。鉴识人伦由外形而认识其内在精神,发展到人物神气的重视。反映在认识论上,就是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由可知到难言之领域的发展。形体可知,神气难言。从而到曹魏以后,“言不尽意”的思想乃大为流行,这是当时思想界发展的自然趋势。
言意关系的问题,在先秦时代就已提出。《周易》、《庄子》等书均有所论述(20)。到魏晋时,这种学说又重新成为论题。荀粲是此间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荀粲,据说好言道,谈尚玄远。“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21)。既然性与天道之思想不能从圣人的言论著作中得知,因此“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劙也”(22)。这显然是站在道家的立场,对儒家经典的嘲讽。在《三国志·魏书·荀犵传》注引《晋阳秋》里引何劭为荀粲所作的传里,有这样的记载:
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因蕴而不出矣(23)。
荀粲认为,言尽的,只是具体的物象,而不是象外之意,系表之言。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才应该是“性与天道”一类的思想。他认为,在一般的言象之外,存在着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它是理之微者,微妙难明,非物象言辞能表达。荀粲的这一主张,与后来的嵇康等人都是一致的。魏正始年间,出现了何晏和王弼两个大家。其中“王弼为玄宗之始,深于体用之辨,故上采言不尽意之义加以变通,而主得意忘言,于是名学之原则遂变为玄学家首要之方法”(24)。《周易·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得而见乎”,实际上是承认言辞能传达圣人之意的。但是,王弼引庄周筌蹄之言,作《周易略例·明象》,对“言不尽意”作了一种新的解释: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言生于象而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25)。
王弼认为,一、言生于意,故可寻言以观意。这就相对肯定了语言的作用。语言可以表达思想,尽意必须通过言,离开言无法尽意。这一点与荀粲是不同的。二、言虽为意的代表者,但非意的本身。故不能以言为意。明确了语言和思想的区别,语言只是传达思想的工具。三、如果执着言,以言为意,则“非得意者也”。故“得意”在于“忘言”,也即“得意”须“忘言”“忘象”,以求“言外之意”。王弼的言意理论,相较荀粲等人之论是细密精致多了。它既肯定了言可达意,又看到了“言不尽意”。语言与思想既是对立的,又是可以统一的。这种思辨方法对文论“言不尽意”苦闷的提出和解决,显然是有影响的。
主“言尽意”论的,以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为代表。
欲辨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随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苟其无二,则言无不尽矣(26)。
欧阳建认为:首先,人类的认识活动是离不开语言的,所谓“物定与彼”“非名不辨”(《言尽意沦》),“欲辨其实,则殊其名”。其次,名与物言与理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在认识过程中,思想对外物的认识必须通过语言和伴随着语言进行。所以,“苟其不二,则言无不尽矣”。应当说欧阳建看到了语言和认识活动的统一性,看到了语言与思想就其产生、深化过程,都是以互为依存为条件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因而对文论中“言不尽意”现象的认识和解决,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言意之间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欧阳建没有看到言意的统一是在对立运动中实现的,相比之下,王弼比欧阳建深刻得多。
“言意之辨”的出现,在美学上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人类思惟活动的认识,尤其是对形象思惟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知道,思惟活动不能离开语言,这是就一般思惟而言的。据近年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人类的语言活动与大脑的左半球的某些部位相联系,控制语言活动的大脑左半球掌管着抽象的概括的思惟,右半球掌管着非语言的感性直观思惟。左半球的语言中枢被破坏后,思惟活动仍然可以进行。这一研究说明,思惟与语言从生理机制上来说是有区别的。特别以感性、个别为基础的直观形象思惟,语言相对来说,是存在局限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思想借助语言进行时,往往又呈现为一种内部语言状态,它是压缩的、跳跃的、模糊的,当它需要表达时,又要转化为明确的、概括的、连续展开的外部语言。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不同性质和需要,决定了两者具有不同的状态。这种差异的认识和解决,既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又是一个理论的问题。特别是形象思惟的文学创作,其创作活动中内在意象的产生,以及其由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的转化,都更具特殊的规定,不同于一般的抽象思惟。它的内部语言的感性、个别、形象、情感的信息量不仅是丰富的,而且外部语言的精炼、独特、生动,又不是一般的达意可以满足的。对这一问题,古人是早有认识的。陆机《文赋》里有:
其致也,情鑗軏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指内部语言)。……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层云之峻(指外部语言的“顺”和“滞”)。……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指外部语言的“随手之变”)。
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里有:
意翻空而易奇(内部语言),言征实而难巧(外部语言)。
苏轼的《答谢民师书》里有: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内部语言),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于手者乎。(外部语言)。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郑燮的《郑板桥集·题画·竹》里有:
其实胸中之竹(内部语言),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外部语言),又不是胸中之竹也。
从物到意,由意到言,是历代文人费尽踌躇的问题。所以,魏晋文论中“意不称物”、“言不逮意”的苦闷,是一个带有普遍哲学意义的文学问题。魏晋文人接受玄学“言意之辨”的理论成果,进而研求“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也就是极为正常的。
三
受汉末社会思潮的影响,魏晋文论的中心,起始便不在社会而在个人,不在环境而在内心,不在形质而在精神。《典论·论文》已初露端倪。及正始之际,随着玄学的兴起,陆机生于此时,风俗习染在所难免。尽管有关陆机撰写《文赋》的年代,在入洛前后问题上,还存有争议(27),但是,《文赋》首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其创作论核心部分的成立,显然是玄学思想影响的结果。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可以说,陆机是以《文赋》的形式,把“言意之辨”的玄理引入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在文学创作论的范围内,参与了“言意之辨”的论争。(www.zuozong.com)
《文赋》从作文之由开始,即从一“伫中区以玄览”(感于物)、二“颐情志于典坟”(本于学)等入手,逐层阐发了意与物、意与言的关系,其中借鉴了许多玄学的理论概念作为思辨论述的出发点,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言不尽意”和“言尽意”的辨证关系,一层层地揭示文学创作的本质规律。例如,“玄览”用玄学的“至人”理应智周宇宙、与道同体之意,“虚无”用“大象无形”之意,“寂寞”用“大音希声”之意。均为玄学喻道名言。并且,善于从“滞”与“顺”、“形”与“状”、“辞”与“意”、“离”与“合”、“多”与“寡”、“巧”与“拙”等对立的现象中,对比辨析文学创作,因而充满了思辨的色彩。尤其是,从玄学的思辨方式来看,以语言为工具和目的的文学创作,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要而言之,被认为是习以为常的文学创作经验,应该是体会“言意之辨”玄理的最适宜的媒介。因此,以此为契机,就为陆机深入地融汇玄学理论,提出和解决“言不尽意”的苦闷,详细地辨析文学的“创作用心”提供了尝试的机会。
从《文赋》的思想倾向来看,陆机是同意“言不尽意”的。但他并不是绝对化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文学艺术毕竟要通过某种媒介来表达,仅就艺术的传达来说,还是“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的(28)。所以,“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这一点,与王弼的观点相接近。王弼认为,言为意象之工具,工具不是目的,因此言难以尽意。但是,言毕竟出于意,滴水非海,然究自海。若真得道,就滴水而知大海。所以关键在于理解和运用语言。这样,言辞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既是尽意的工具,又是创作的目的之一。如果再加上声律的要求,言辞的目的性就更突出了。陆机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表达出的构意要巧妙,言辞要华美,还要有抑扬顿挫的音乐美,这是陆机对言意关系的三个要求。从这个基点出发,陆机对创作中的言和意的两个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
首先,必须有“玄览”的精神准备。而后方能作到“意”能称物。唐李善对“玄览”的注释,引《老子》注为“涤除玄览”。又引河上公注“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所谓“玄览”,意指仅仅局限于具体事物,并不能说明物,只有超出具体的物,净化自己的精神,从而览知万物,才有可能尽物。王弼的《老子指略》也有近似的观点,确知万物“有”,必须把握本体“无”。“象而形者非大象”“音而声者非大音”。然而本体“无”并非在万物之外,“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只有通过具体的物象而又不拘泥于某一具体的物象,才可能把握事物的本体。陆机的“玄览”,有着相近的意义。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提出了虚静说。此外,又要“颐情志于典坟”。这是为了解决“文不逮意”的问题。“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文学教养,才可能善用言辞以尽意。关于这一点,刘勰在《神思》里讲得更全面,“积学以诸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发展了陆机的观点。
其次,在创作构思的阶段,意与物遂渐融合,“情洉龢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内部言语已经完成,创作意象产生以后,就要寻觅确切的语言表现出来。陆机认为,这个过程从构思开始,一直到全文完成修辞之后才告结束。对此,他有个总的要求,在言与意所表现的内容上,是“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要求尽意、尽辞。在言与意的推陈出新上,是“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这是尽美的要求。由此出发,陆机作了一番“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的工作。一是以意为主,言为达意服务。“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在这里,内容(意)虽为主干,还要有繁茂的枝叶(言),文章才会有生气。言与意是互为依存的。刘勰后来看得更清楚了:“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彩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戃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文心雕龙·附会》)。“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龙·情采》)。二是要“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从根本上解决意称物、文逮意的问题。清顾施祯评此条云:“课督于虚无以责求其有,思之凭空而构也。叩击于寂寞而求音,辞之避空而造也,其后以小包远,函其绵邈无际之气势于尺素,辞何不具耶。以微运大,吐其滂沛无竭之文藻于寸心,思何不通耶”(29)。陆机认为,文学创作不能局限于“有”(见到的事物),不可囿于“音”(现有的言辞)。须从“有”而超出“有”,成为“虚无之有”(自己发现的事物)。于“音”而超出“音”,成为“寂寞之音”(自己独创的言辞)。如此,方能称得上意通、辞具。这一理论与王弼《老子指略》略同,“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聆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30)。从“虚无”“寂寞”入手,陆机事实上提出了想象和虚构的问题。“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而尽相”。只有离方遁圆,无拘无束,最大限度调动想象和虚构的能力,才可能确切地把握和表现对象。这是陆机有关解脱“言不尽意”苦闷的一个重要思想。以后刘勰也相继提出了“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的主张。不过刘勰似乎更多地指构思方面,而陆机是兼指构思与表达两个方面的。
最后,陆机从意与辞两个方面说明具体创作时,应该注意的四个问题。一是注意儽裁而使辞和义双美。刘勰后作《儽裁》篇,更详细地作了论述。二是通过警句以突出意象。“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以效绩’。刘勰后来在《隐秀》篇里讲,“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秀以卓绝为巧”。魏晋文论对这个现象的关注不是偶然的,由于语言在表达意象上的限制,往往失落了构思之意的某些部分。然而,如果有生动传神的语言的调节(即诗歌中的诗眼),保留下来的意象,有可能由于警句的作用,使意象更为鲜明而富有张力。这个问题的提出,说明语言的相对独立的美学意义,开始被人们所注意。唐以后出现了许多以警句和秀句为内容的诗选,即为明证。三是戒雷同而求独创,这是兼指意和辞两方面的。四是说明语言的反差和烘托作用。最后,陆机提出了他对意和辞的总体的要求:应、和、悲、雅、艳(31)。
然而,批评家解决“言不尽意”的问题,大多放在现象的分析和技巧的使用上,而诗人解脱“言不尽意”的苦闷,多半是依赖直觉来解决。作为诗人的陆机,是深有感触的。“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一旦灵感到来,则言和意之间的对立就会化然为一,巧意丽言自然而然涌流不止。灵感问题的提出,对解脱“言不尽意”的苦闷,提供了新的认识。
陆机对言意问题的全面探究,虽然是“巧而碎乱”(《文心雕龙·序志》),但具有开创的意义。这为刘勰和钟嵘进一步解决“言不尽意”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四
刘勰直接沿袭了陆机的一些观点,并作了发展。近人已多有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与陆机不同,在言意问题上,他似乎更多地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魏晋“言意之辨”双方的争议,在以儒为主的指导思想下,融汇进他的文艺创作论中。所以,《原道》篇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辞是表现情感的充足的媒介(32)。《神思》篇有:“枢机(辞令)方通,则物无隐貌”,《物色》篇有:“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皎日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夸饰》篇有:“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欼则声共泣偕”。言辞不仅可以尽物,而且可以尽情,这是刘勰总的看法。然而,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行为方式。从表现的对象来看,不仅是物象,而且包含着思想。从表现者本身来说,不仅依赖对事物的认识,而且包含着个人的印象、感觉、情感、情绪。从表现的方式来看,不仅需要文学性的语言,而且要适应文体的特殊形式。这三个环节,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落,都将带来“言不尽意”的苦闷。“半折心始”“疏则千里”的现象是难免的。在这一点上,刘勰采取了比陆机更为精致的方法。非尽儒亦非尽玄,显示了理论上的成熟。
首先,刘勰指出了言辞在构思中的能动作用。《文赋》曾讲到“辞程才以效伎”,多少接触到了文辞在构思中的作用。刘勰则讲得更加深入,“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烜心”。“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神思》)。“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一方面在构思过程中,从意象产生到形成,一直伴随着语言。意象对语言不断地取舍,使之成为意象与情感的落脚之处。另—方面,构思中的意象也在语言的性质和传达方式的作用下发生变化,“辞令管其枢机”,言辞对意象又不断地进行选择,使之适应语言的物化方式。因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这样,整个创作构思的过程,就是意象同言辞之间相互肯定、相互舍弃的过程。言与意的选择如果吻合,即“密则无际”、“物无隐貌”。反之则“疏则千里”。在这里,刘勰一方面认为言可尽意,但以意为主,辞并不一定能达意。另一方面,又认为“言不尽意”,然一旦适应并掌握了语言及其表现手段,言辞的巧妙运用,又会使意象产生难以预期的达意的效果,“得意”则成为“敬言”。基于这一点,刘勰在吸取陆机的有关文学修养的要求基础上,进而提出了“驯致以怿辞”,即要训练自己的情致,以便适应文辞的表现方式。因为,“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神思》)。清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杼轴献功,此言文贵修饰润色。拙辞孕巧义,修饰则巧义显。庸事萌新意,润色则新意出。凡言文不加点,文如宿竘者,其刊改之功,已用之平日,练术既熟,斯疵累渐除,非生而能然者也”。艺术的真实,即意象的忠实的传达,除了想象虚构的作用,语言是最基本的要素,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韵文来说,更是如此。
为解决物意言三者关系的问题,刘勰还从构意和表达上提出了比陆机更为深入的一系列主张。如在构思上,提出了“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神思》)。在表现上,提出了“建言修辞”(《宗经》)、“修辞必甘”(《视盟》)。还从文学的本质规律出发,专列《夸饰》、《比兴》、《隐秀》、《事类》,以成“随物宛转”之法。撰述《丽辞》、《练字》、《声律》,以全“与心徘徊”之术。对言意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较而言,稍后的钟嵘在言意问题上,无论其研究规模和深度都是比不上刘勰的。但是,钟嵘对“言不尽意”苦闷的解脱,却别开了一派。他把“滋味”引入诗的创作理论中,从而将言意问题的讨论纳入—个更广阔的天地。他认为:“诗有三义焉:一日兴、二日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钟嵘对孔子的所谓兴、观、群、怨的诗论,只取其群、怨的部分,强调书写怨情,首先确定了诗歌意象的基本内容。并且,钟嵘把传统的创作方法赋、比、兴,改变为兴、比、赋。以兴和比为重,论及创作中的言意关系。强调言近旨远,形象鲜明。认为诗应以风力(意)和丹彩(辞)并重,乃可耐人玩味。而且,钟嵘把读者的因素(味之者、闻之者)纳入创作的范畴之内。从读者对艺术形象完成的参与作用上,解决“言不尽意”的矛盾。“滋味”,故可求诸于言内,更须求诸于言外,即“文已尽而意有余”。当人们对创作中失落的意味而遗憾,感叹“言不尽意”时,钟嵘却从这里发现了“滋味”。从而,语言传达过程中的限制和空白,无意中促成了作品的内在张力。创作中失落了的意味,经过读者自身经验的补充,反而有可能超过作品中的言内之意,获得言外之意的效果。钟嵘的这一观点,对魏晋以来“言不尽意”的苦闷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方法,提高了语言的艺术的目的性,开了唐以后主“味外”、“韵外”、“景外”,“象外”之意趣,以及主妙悟、神韵的创作流派。因而,给六朝文学创作论的深入探讨,展示了新的可能。遗憾的是,钟嵘在《诗品》里,并未全面展开他的这一思想,真正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那要到唐以后了。
综上所述,“言不尽意”的苦闷和解脱,是六朝文学创作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该命题的成立和展开的过程,正是六朝文论告别传统文论,完成理论化的过程。在这其间,陆机自觉地吸收了“言意之辨”等玄学的思想成果,从文学创作的经验层面上,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命题,成为六朝文论从理论上脱胎换骨的契机。而后经过刘勰和钟嵘的进一步探讨,确立了以物、意、言三者关系为核心的文学创作论。
(作者李顺刚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注释】
(1)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己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愈精矣”。
(2)限于个人管见,笔者认为,六朝文学批评史的著作以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和林田慎之助《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创文社,1979年版)为代表。六朝文学创作论的著作以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兴膳宏《中国の文学理论》(筑摩书房,1988年版)为代表。在日本的陆机研究论中,以高桥和巳《陆机の传记とその文学》(《中国文学报》第11、12册,1959-1960年版)、兴膳宏《潘岳·陆机》(筑摩书房,1973年版)、佐藤利行《西晋文学研究-陆机を中心として一》(白帝社,1995年版)、小尾郊一《陆机の<文赋>-创作论》(《真实と虚构-六朝文学》,汲古书院,1994年版)、安东谅《<文心雕龙>神思篇の周边》(《日本中国学报》第32集,1980年版)为代表。
(3)小尾郊一《陆机の<文赋>一创作论》认为:“陆机の《文赋》上のょぅず论は、文章一般ず论すゐとしなぅょり、自己反省的文章”。(确为至论。立足自身体验,亦是长处,亦为短处。故遭后人褒贬,刘勰评为“各照隅隙”(《文心雕龙·序志》),钟嵘评为“通而无贬”(《诗品序》),均指《文赋》囿于个人之见。然陆机《遂志赋·序》历举前辈作家,言其创作得失,并非不善批评,只是未见于《文赋》而已。
(4)根据冈村繁的考证,《典论·论文》作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为太子时所作(《曹丕の典论·论文につして》,《支那学研究》第24·25期,1960年)。逯钦立的《文赋撰出年代考》(《学原》第2卷第1期)认为,《文赋》为陆机入洛以后,四十一岁(301)时所作。陆侃如《关于<文赋>——逯钦立的<文赋撰出年代考)书》(《春秋》1949年第4期),陈世骧《陆机の生涯と文赋制作の正确な年代》(《中国文学报》第8册,1958年)、周勋初《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文学遗产》增刊第14辑,1982年)、毛庆《文赋写作年代考辨》(《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等均倾向《文赋》是陆机四十岁左右时,入洛以后所作。
(5)本文所引《文赋》原文,均基于《陆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为底本。
(6)《西京杂记》原托名汉刘歆的著作,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考证,为东晋葛洪的历史小说集,所记为西汉时异闻杂事。该书卷二有司马相如论作赋的方法:“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内,不可得而传”。
(7)扬雄:《法言·问神》。
(8)关于建安文风的“通脱”,参照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之变迁》(《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建安文风,以哀为诗,以悲为美。钟嵘称曹操之作“甚有悲凉之句”。王粲、曹植也有七哀诗。七哀者,所谓七情之中,以哀为主。故《文赋》倡导以悲为美。又,建安文风充满人生慨叹,入世之功名代之以生存之真意,故有《文赋》之自我反省。
(9)《文心雕龙·明诗》。建安文风也是追求文采的。曹丕《与吴质书》批评“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又在《典论·论文》中主张“诗赋欲丽”。可见建安文人既求壮气,又不废文彩。
(10)本文所引《文心雕龙》原文,均基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为底本。
(11)杜甫:《偶题》。
(12)林田慎之肋:《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第82页。
(13)参见郭绍虞《论<文赋>中之所谓“意”》,《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14)《文心雕龙·明诗》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晖,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如前所论,陆机未采建安文人的“壮气”之说,偏于“文采”。确如青木正儿所指出:“恰も汉魏の达意主义から齐梁の修辞主义に转换する过渡期の思想を代表するものじある”(《支那文学思想史》岩波书店,1943年版)。
(15)“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因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嵇康集校正,声无哀乐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16)《宋书·范晔传》引《狱中与诸甥侄书》。
(17)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8)这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曾经论及。近年有孔繁《魏晋玄学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专著可参。
(19)据《三国志·魏书·荀犵传》裴松之注和《世说新语》记载,谈玄说理的创始人是裴徽、荀粲、傅嘏等人。据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中文出版社,1979年版)记载,他们活动的时代为228年,而玄学的流行期,为正始时期(240—249年)。
(20)《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以上两段文字,被认为是“言意之辨”的理论根据。
(21)《三国志·魏书·荀犵传》注引《晋阳秋》里所引何劭为荀粲所作之传。
(22)《三国志·魏书·荀犵传》注引《晋阳秋》里所引何劭为荀粲所作之传。
(23)《三国志·魏书·荀犵传》注引《晋阳秋》里所引何劭为荀粲所作之传。
(24)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25)本文所引王弼的原文,均基于《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为底本。
(26)欧阳建,字坚石,西晋人(268—300年),撰有《言尽意论》(《全晋文》卷一0九)。
(27)参见注④。一般认为《文赋》是入洛之后撰写的根据之一,即《文赋》使用了带有玄学色彩的字句。但是,张少康认为陆机在江东时,也有接触玄学著作的机会,是入洛以前的作品。(参见张少康《陆机》,《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陆机作品中的玄学色彩,骆鸿凯《文选学》称“连珠之体,大率先立理以为基,继援事以为证。近世论之者谓有合于印度之因明,远西之逻辑,详加完味,其言非诬”(络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7页)。
(28)张彦远引陆机语,《历代书画记·叙画之源流》。
(29)顾施祯:《昭明文选六臣汇注疏解》。
(30)这里引用的王弼《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的文字,不仅在玄理上对陆机有所启示,而且其文体也与《文赋》极为相似。例:“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聆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31)饶宗颐《陆机文赋理论与音乐之关系》(《中国文学报》第14册,1961年)里,论述了应、和、悲、雅、艳的理论内容和相互关系,并且讨论了与音乐理论的关系。兴膳宏《文学理论史上から见た<文赋>》(《中国の文学理论》,筑摩书房,1988年版)中,进一步廓清了其概念。木津佑子在《美としての乐へ—<文赋>にぉける音》(《中国文学报》第50册,1995年中就陆机使用的音乐理论的概念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作了考察。
(32)参见李顺刚《文与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