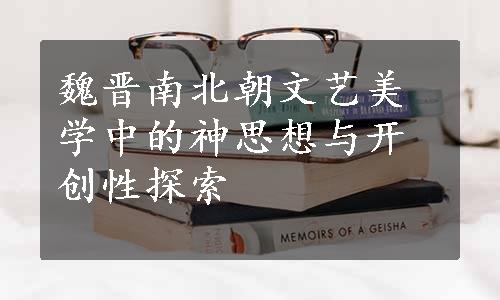
张 晶
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关于“形神”关系的论述,关于“神灭”与“神不灭”的论争,是当时思想史上的一个焦点。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从原初的含义而言,“形”即人的形体、肉体;“神”即人的灵魂、精神,形神关系也就是形体与灵魂或精神的关系。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就已经开始探讨“形神”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介入,“神灭”与“神不灭”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进一步衍为思想界的轩然大波,同时,也使“形神”成为中国哲学史和美学史的非常重要的范畴。范缜、何承天等唯物主义思想家鲜明主张“神灭”论,而佛教思想家慧远(334——416)等人则大力宣扬“神不灭”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哲学史著作中都是着力揭载的。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神灭”论(即“形尽神灭”)属于唯物主义的观点,“神不灭”论属于唯心主义的观点,已成定论。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这场论争的意义就远不止于此。在笔者看来,这场论争大大提高了当时论坛的思辩水平,深化了人们对精神现象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广延性的认识,并且以一种直接的助力,强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美学中重“神”的倾向,并从哲学角度为文艺创作的“神”的范畴提供了理论的动力。魏晋南北朝的著名文论家、画论家如宗炳(375——443)、刘勰(约465——520)、谢灵运、沈约等,大都与此时期佛教哲学中的“神不灭”论的背景有深刻的联系。本文从美学价值论的角度加以发掘,似乎可以认为,以佛教理论为基点的“神不灭”论,却给中华美学的“重神”观念,添注了具有丰富价值的内涵。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不灭”论,虽然有其先秦思想的渊源,但是佛教宣扬“因果报应”的需要和轮回主体的学说,却是其现实的理论动力。南北朝时期“神不灭”论的主张者都是以佛学理论作为其理论根据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慧远,即是当时的著名高僧和佛教思想家,而宗炳虽未出家,但他是慧远的高足,而且其阐述“神不灭”论的经典文章《明佛论》(亦称《“神不灭”论》)更是以佛学为出发点的。其他倡导“神不灭”论者如梁武帝萧衍,更是著名的佛教徒。著名文学家沈约也是佛教的虔诚信奉者。他们以先秦和两汉主张“神不灭”论者为前源,又以佛学理论为其主要的理论支撑,提出更为明确、缜密的“神不灭”命题,他们与辩难的对方主张“神灭”论者如范缜、何承天等思想家一道,使关于“形神”关系的哲学思维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这场论争中,“神不灭”论在对精神现象的重视与论析方面,却是使六朝美学中重“神”的思想有了更为丰富而深邃的内涵的主要因素。
慧远是东晋时期的著名佛教领袖,是当时佛教般若学的代表人物道安的高足,慧远对佛学的精思与敏悟,受到道安的高度评价与赞赏,慧远长住江西庐山东林寺30余年,广泛从事佛教理论的宣传和佛教实践活动,是佛教学者中倡导“神不灭”论的最为突出的代表。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主要是继承了道安的思想,着重发挥了佛教三世报应和“神不灭”的理论。他从道安的“本无”说出发,进一步阐述了佛教所谓的最高实体和最高精神境界的关系,他在《法性论》(残篇)中说:“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这就是说,佛教的最高实体和最高精神境界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由此观点出发,慧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神不灭”理论。《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即有《形尽神不灭》专章,其论“神”的含义云:“夫神者何耶?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塞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致。”慧远认为,“神”是一种非常精灵的东西,是超越于物质形态的。它是无形象的,也无法以形象来表示,圣人也只能说它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东西。
倡导“神不灭”论主要人物还有晋宋之交的宗炳。宗炳既是当时的一位著名的画家,又是一位精于佛理的佛教徒。他曾师从慧远“考寻文义”。宗炳是一个执着的“神不灭”论者,他曾写长文《明佛论》,盛赞佛教,大力阐扬“神不灭”。宗炳在《明佛论》中说:“佛国之伟,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乎?”概括了佛教的宏旨,并以“精神不灭”为佛教的主要精义。宗炳不仅笃情佛教,而且也尊儒家、道家,但他认为佛学可以包容儒、道的精髓,并在对精神层面的洞察上高于儒道。他认为:“中国君子明于知礼义而暗于知人心,宁知佛心乎?今世业近事谋之不臧犹兴丧及之,况精神我也?”他又说:“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高言实理,肃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风,非圣谁说乎?”认为佛经可以包括儒家经典和道家学说的精华。关于形神关系,宗炳是明确反对“形生则神生,形死则神死”的“神灭”论的。他认为“神非形作”,可以超越形体而独存,这自然是很荒谬的。但他对“神”作为精神现象的功能的描述,却是颇有意味的。他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矣。若资形以造,随形以灭,则以形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圣之穷机,贤之研微。”认为“神”是“万物”中最为奇妙的。它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而流布四方,上天入地。宗炳突出地强调了“神”的这种奇妙功能,如云:“夫以法身之极灵,感妙众而化见,照神功以朗物,复何奇不肆,何变可限?岂直仰陵九天,龙行九泉,吸风绝粒而已哉?凡厥光仪,符瑞之伟,分身涌出,移转世界,巨海入毛之类,方之黄、虞、姬、孔,神化无方。”这里是将精神现象的作用夸大到无所不能的地步。宗炳还强调心灵的本体地位,认为心是可以派生万物的,一切都可以从心生出。这对后来禅宗和心学的“心本体”哲学是有相当影响的。他说:“夫洪范庶征休咎之应,皆由心来。逮白虹贯日,太白入昂,寒谷生黍,崩城陨霜之类,皆发自人情而远形天事,固相为形影矣。夫形无无影,声无无响,亦情无无报矣,岂直贯日陨霜之类哉?皆莫不随情曲应。物无遁形,但或结于身,或播于事,交赊纷纶,显昧渺漫,孰睹其际哉?众变盈世,群象满目,皆万世已来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经云:‘一切诸法,从意生形。’又云:‘心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狱。’义由此也。是以清心洁情,必妙生英灵之境;浊清滓行,永悖于三涂之域。何斯唱之迢递,微明有实理,而直疏魂洒沐想,飞诚悚志者哉?”将“心”作为万物产生的基因,认为一切诸法皆是由心而生,当然是典型的宗教唯心主义,也并非独家创造,而是佛教理论的基本观念。宗炳又从因果业报的角度加以论述,更是将慧远的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融而为一。但宗炳对情感业报的论述以及“清心洁情”以生妙境的看法,也是别具美学意味的。
“神不灭”论的这些文章,都是以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为理论依据,亦以业报轮回为理论归宿,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看,这自然是相当荒谬的。这一点,无须多加论证辩驳;但从思想史的进程来看,关于“形神”的论争对魏晋南北朝的美学观念影响却是巨大的、十分深刻的,“神不灭”论者在其间所起的作用是颇为独特的。这些论著中,关于“神”的含义除了与形体相对应的灵魂,在很多地方是谈人的精神境界。而“神不灭”论者对“神”的论述是关于人的精神的,这一点已经跨越了作为三世轮回主体的承担者的灵魂的内涵。如论及“神”的奇妙性、超越性;如宗炳所说的“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精妙地概括了精神超越时空的特质。论及“神”的“感物而动”的特点,如慧远所说的“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等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越出了原有的宗教涵义而对六朝的美学思想起了很大的建构性作用。
二
魏晋南北朝的文艺美学思想中有突出的重“神”思想,这在顾恺之(约346-407)、宗炳、萧子显等人的论著中体现得颇为鲜明,构成了六朝美学的一个特色,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艺术理论的走向,使“形神”成为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重要审美范畴。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是东晋时期的杰出画家,其画深受世人推尊,谢安曾称赞其画云:“卿画自生人以来未有也。”其绘画思想以“传神”著称。他在绘画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传神写照”、“以形写神”等命题。《世说新语·巧艺》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郎有识具,正此有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顾恺之将眼睛视为传神的关键,而在他看来,人物画的价值取向主要不在于形似,而在于“传神写照”。“传神”即是传达出所画人物的特有的神韵;而“写照”也并非一般的外形摹写,而是一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直觉洞照。“照”是佛学的术语,指以佛教的般若智慧来直觉地观照事物,这里引出一段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的有关论述:“在佛学中,所谓‘照’指的是心的一种神妙无方的直觉认知的能力,它是和人的精神分不开的。慧远说:‘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象生焉’(1)。僧肇说:‘智有穷幽之鉴,而无知焉;神有应会之用,而无虑焉。神无虑,故能独王于世表;智无知,故能玄照于事外’(2)。……‘照’既是一种神妙的感知能力,是主体的有‘穷幽之鉴’的智慧(佛学所谓‘般若’)的表现,因而它也就和玄学常讲的‘神明’联到一起了。所以,‘写照’就不是一般所说画像的意思,而是要写出人的神妙的精神、智慧、心灵的活动。”(3)在绘画艺术中,顾恺之所讲的“传神写照”,是说要表现出入物的内在神韵、精神气质。
关于形神关系,顾恺之虽然非常重视“传神”,但他并不认为“神”可以离开形而独立,认为传神离不开写形。因而,他提出了“以形写神”论。他说:“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用之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象之明昧,不若晤对之通神也。”(4)“晤对通神”的命题,我以为是有重要的美学理论意义的,它说明,顾恺之所谓的“神”,在其绘画思想中,是一个最主要的审美价值范畴,绘画的目的不在“形似”,而在于“传神”,“形似”不过是手段、途径而已。而“神”的获得,则是艺术创造的主体与客体相晤对而产生的。主体移情于客体之中,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失”之中,“神”便油然而生了。
顾恺之辩证地处理绘画艺术中的形神关系,并不是脱离形似而单纯强调神似,而是将形似与神似辩证地统一起来。形似只是手段,而“写神”才是目的。“以形写神”,并非现实形象的机械模仿,而是以艺术想象加以补充,所以顾恺之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迁想妙得”。《魏晋胜流画赞》云:“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此以巧历不能差其品也。”“迁想”就是将画家的艺术想象投射到所画的对象中去。“妙得”即是达到传神的目的。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和“以形写神”的命题,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文人画的审美观念中尤其是带有主导倾向的。
宗炳所作的《画山水序》,是中国绘画理论史上第一篇山水画论,在中国美学史上,《画山水序》有着独特的价值。
《画山水序》原载于晚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宗炳在文中提出了“澄怀味象”、“应会感神”、“畅神”等命题,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美学内涵,这些命题的提出,与他的佛学思想有很深的关系。《画山水序》中首先提出“澄怀味象”的命题:“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我以为“澄怀味象”是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主客体审美关系的命题。“澄怀”要求审美主体在审美过程中,排除外物的纷扰,尤其是功利关系的眩惑,而保持虚静空明的心胸以应外物。“味”是特定的审美过程,而“象”则是指观照对象的形象。而“山水质有而趣灵”,是谓山水是物质性的存在,但其中有着整体性的灵趣所在。“澄怀味象”与老子所说的“涤除玄览”,庄子所说的“心斋”、“坐忘”,“虚而待物”,是同一种精神境界,但老庄是讲对天道的体验,虽然可做美学角度的阐释,就其本身而言,则是哲学主体论的,而宗炳的“澄怀味象”,是就山水审美而发的议论,是地道的审美主体论。
“山水质有而趣灵”的美学思想与其《明佛论》中的佛学论述是相互关联的。《明佛论》阐述其“神不灭”的思想即举山川为例,其云:“若必神生于形,本非缘合,今请远取诸物,然后近求诸身。夫五岳四渎,谓无灵也,则未可断矣。若许其神,则岳唯积土之多,渎唯积水而已矣。得一之灵,何生水土之粗哉?而感托岩流,肃成一体,设使山崩川竭,必不与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灭,人亦然矣。”宗炳认为,“五岳四渎”这些山山水水,也是因为有了神灵而成一整体,而有各自的风貌。设使无神,不过是积土、积水而已。这种说法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而从山水审美中所发现的灵趣,则并不能全然归之于唯物与唯心的范畴,而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在相互感应中所产生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所说的山水之神(趣灵),决非客体本身可以独立存在的,而只能是在主体观照的过程中方能产生。作为审美对象,山水是特殊的客观存在。“质有”,不仅是对山水形质的肯定,而且还意味着它的不同的形态差异。“趣灵”是指审美在晤对山水时所感受到的灵趣。这并非是单纯存在于主体方面的,也并非是单纯存在于客体方面的,而是在审美主体与客体的晤对感应中呈现出来的。“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一个很纯粹的美学命题,早已逸出了宗教有神论的范围。
而要体验山水之神,主体方面必须“澄怀”,这与宗炳的佛学思想是息息相通的。宗炳画论中的“澄怀味象”,强调审美主体的虚静的审美态度,一方面通于老庄的“虚静”说,另一方面则是以其佛学思想中的“炼神”说为其渊源的。在宗炳的佛学思想中,“神”是一种虚空抽象的精神实体,“神”存在主体之中,而就客观来说,还有“道”的根本性存在。宗炳说:“今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者,盖谓至无为道,阴阳两浑,故曰‘一阴一阳’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于阴阳之表,非二仪所究,故曰‘阴阳不测’耳。”(5)这是宗炳所谈的神与道之关系。悟道必须练神,“道在练神,不由存形”。宗炳认为,练神就是空诸一切,“心与物绝”,这又是与道家“虚静”说一致的。他说:“夫圣神玄照而无思营之识者,由心与物绝,唯神而已。故虚明之本终始常住,不可凋也。今心与物交,不一于神。虽以颜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钻仰,好仁乐山,庶乎屡空。皆心用乃识,必用用妙接,识识妙续,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焰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识歇,则神明全矣。”空明澄澈的主体心胸,是练神的必要条件。这与《画山水序》中提出的“澄怀味象”是一致的。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应会感神”、“畅神”等命题,也是生自于《明佛论》中的“练神”思想的。他说:“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无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峰岫譾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孰有先焉。”这段内容重在山水之神的获得。山水之神如何获得?是在于审美主体以澄静之心与山水感应的产物。“应目会心”是指审美在体通过眼睛观照对象而会心感通,悟得其神,从而升华为“理”。“这是说山水是以‘应目会心’为‘理’的,只要能把山水巧妙地描绘出来,那么观者目接于形时,心就会领会其‘理’。这种目击心会的欣赏能感发观者之精神,使‘神’超于‘形’而得其‘理’。即使是亲身游于山水之间,求山水之神理,所得也不过如此了。”(6)所论大致不差。而我以为“应会感神”,是主体与山水之形的晤对,在瞬间交融的审美体验中,主体感悟了山水之“神”。宗炳又指出“神”与山水形质的关系,“神”是精神性的,不体现在具体的存在形态中,而是寄寓于山水之形中的。《明佛论》中说:“夫钟律感应,尤心玄会,况夫灵圣,以神理为类乎?”山水是主体感应的对象,可以使人在“应目会心”中悟得“神理”。当人以眼睛来观照对象之时,心灵也在主客相通中获得了山水之神。(www.zuozong.com)
“畅神”则是在观赏山水画时的审美过程中所体验到的高度自由、高度兴奋的境界。宗炳以“畅神”为山水画最为重要的审美功能。“畅神而已”,言下之意是“岂有他哉”!“神之所畅,孰有先焉”是说没有比欣赏山水画更能令人“畅神”的了。“畅”是一种超越于现实缧绁而使精神舒展、飘逸的高度自由的状态。著名诗人孙绰己在《天台山赋》中写道:“释域吕之常恋,畅超然之高情”,在《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中又提到了山水之赏可以使人“神以之畅”。宗炳的说法可能是由此而出,但他将其凝炼为“畅神”的命题,同时,又以之作为山水画审美功能的最高价值体现,这就突出了山水审美“令人解放”的性质。
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中,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提出了“神思”的美学命题。《神思》是《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首章,也是刘勰所提出的关于艺术创作思维的核心范畴。“神思”范畴的提出,也与当时的“形神”关系的论争有内在的联系。刘勰二十四五岁时入上定林寺依僧佑。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神思”是艺术创造思维的核心范畴。《神思》篇中云:“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神思,我以为可以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狭义是指创造出达于出神入化之境的艺术杰作的思维特征、思维规律和心意状态;广义则是在普遍意义上揭示了艺术创造的思维特征、思维过程和心理状态。它包含了审美感兴、艺术构思、创作灵感、意象形成乃至于审美物化这样的重要艺术创造思维的要素,同时,它是对于艺术创造思维过程的动态描述。
“神思”体现了创作主体的自由本质,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想象的翅膀冲破客观时空的云层,上可达天,下可入地;可以回溯于千载之前,可以驰骋于百代之后,刘勰对“神思”的界定明确指出了艺术思维的这种特点。这与慧远、宗炳等人所阐述的“神”的特征是相通的。
慧远、宗炳所倡“神不灭”论,除了“灵魂不死”的含义之外,还相当多地谈到“神”作为精神现象的性质、形态和功能,也即逸出了有神论的范围而具有了心灵哲学的意义。以对精神现象的功能和价值的阐述而言,慧远们所论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建设性意义的。精神现象是无形无相的,却又有无可限量的创造能量。“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致”,可以超越形质、时间、空间的限制而“神机自运”。正是说精神的可以突破时空限制的特点。
刘勰的“神思”在这方面明显是吸取了慧远、宗炳等的思想养料,却以之作为文学创作思维的理论支撑,使之具有了纯粹的美学意味。刘勰在《神思》篇中所说的都是“文之思”,而非泛泛的精神现象的描述。这一点,是吸融了陆机《文赋》中对文学创作思维的描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洉龢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而刘勰的论述则因吸取了慧远、宗炳等人的“神不灭”论对精神现象的论述,更有了哲学的高度。
“神思”的自由性质还在于不拘于成法,变化万端,进入一种自然灵妙的境界。“神”的含义所指的一是神灵和精神的作用,二是微妙的变化。这也是“神不灭”论所描述的“神”的奇妙特性。慧远说:“夫神者何耶?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故圣人以妙物而为言,虽有上智,犹不能定其体状,穷其幽致。”张岱年也指出“神”这个概念的微妙变化的内涵,他说:“以‘神’表示微妙的变化,始于《周易大传》。《系辞上传》云:‘阴阳不测之谓神。’又云:‘神无方而易无体。’又云:‘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说卦》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这就是说:‘神’是表示阴阳变化的‘不测’,表示万物变化的‘妙’”(7)。刘勰所谓“神思”的“神”,首先是微妙变化之意,而“神思”则是变化莫测的运思。稍晚于刘勰的萧子显谈及“神思”时强调的也是这种性质,他说:“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无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8)萧子显认为,神思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思维方式,可以将各种大自然中的情状召至笔下,创造出各具形态的美文。这里揭示了“神思”对文学创作个性化的根本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形神关系的论战,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重大问题,有关哲学史的著作已有许多论述,但多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对“神灭”论和“神不灭”论作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判定。这是正确的,没有什么疑问的。可是如果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美学思想来看,重神的思想是非常突出的现象,而且对后世的文艺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引导作用。后世文论中对于“神”或“神似”的推尊,成为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思潮。美学思想中的“神”,当然和佛学中的“神”并非有全然相同的内涵,但却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神不灭”论认为精神可以脱离形体而独立存在,可以转生于其他形体,这自然是荒谬绝伦的;但他们对精神现象的高度重视和深刻的阐析,却是文艺美学中的“重神”的思想的哲学渊源与土壤。
(作者张晶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注释】
(1)《念佛三昧诗集序》,《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二。
(2)《般若无知论》,《全晋文》卷一百六十四。
(3)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2卷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8页。
(4)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
(5)宗炳:《明佛论》,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0页。
(6)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2卷下,第515页。
(7)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要论》,第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版。
(8)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