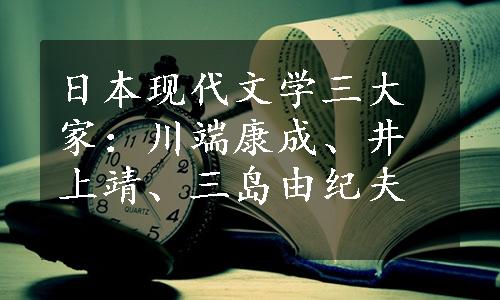
川端康成(1899—1972 )幼失怙恃,成为一个孤儿。直到上小学之前,他“把自己胆怯的心闭锁在一个渺小的躯壳里”,“简直就不知道还存在着一个人世间”。16岁时,他又失去相依为命的祖父。他接连为亲人包括亲姐姐奔丧,参加了无数的葬礼,人们戏称他是“参加葬礼的名人”,孤儿的体验达到了极点。还有,他与四个同名为“千代”的女性,产生过不同程度的感情,有的是相恋,有的甚至已订婚,但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这种畸形的家境、寂寞的生活,导致了川端康成的性格比较孤僻和内向。他埋头书海,广泛猎取世界和日本的古今名著,特别爱读《源氏物语》,手不释卷。在中学时代,开始作和歌、杂文和掌小说。最先发表的习作《千代》,以及《十六岁的日记》、《招魂节一景》、《林金花的忧郁》和《参加葬礼的名人》、《非常》、《处女作作祟》等一系列小说,主要是描写孤儿的生活,表达对已故亲人的深切怀念与哀思,以及描写自己的爱情波折,叙述自己失意的烦恼和哀怨。这些小说构成川端康成早期作品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川端本人说:“这种孤儿的悲哀成为我的处女作的潜流”,“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整个生涯的潜流吧”。
1924年大学毕业后,川端与横光利一等发起了新感觉派文学运动(上章已述),川端发表了著名论文《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但在新感觉派文学创作方面,却没有成功之作。最后他决心走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写下了成名作《伊豆的舞女》,小说描写主人公“我”怀着自身的悲哀来注视女主人公舞女阿薰的命运,而舞女对“我”之入微体贴,把“我”看作是个“好人”,这种不寻常的“好意”,使“我”感到自己是确确实实的存在。这样,他们才得以进行纯粹的心灵交流。“我”对舞女,或舞女对“我”所流露的情感,悲哀是直率的,寂寞也是直率的,没有一点虚假和伪善,如水晶般的纯洁。
川端在《伊豆的舞女》中非常明显地继承了平安王朝文学幽雅而纤细、颇具女性美感的传统,并透过雅而美反映内在的悲伤和沉痛的哀愁,同时也蕴藏着深远而郁结的情感,这是一种日本式的自然感情。作家从编织舞女的境遇的悲叹开始,由幽雅而演变成哀愁,使其明显地带上多愁善感的情愫。“我”之于舞女,或舞女之于“我”,都没有直抒胸臆,他们在忧郁、苦恼的生活中,从对方那里得到了温暖,萌生了一种半带甘美半带苦涩之情。这种爱,写得如烟似雾,朦朦胧胧,作品的艺术魅力就产生在这种若明若暗之间。
此后,川端康成还运用新心理主义和意识流的创作手法,试写了《针·玻璃·雾》、《水晶幻想》,以及无批判地运用佛教的轮回观,写下《抒情歌》、《慰灵歌》,他在和洋文化的摆渡中探索创作的道路,这表明他起初没有深入认识西方文学问题,只凭自己敏锐的感觉,盲目醉心于借鉴西方现代派。其后他自觉此路不通,又完全倾倒于日本传统主义,不加分析地全盘继承日本化了的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最后他开始在两种极端的对立中整理自己的文学理路,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这时候,他深入探索日本传统的底蕴,以及西方文学的人文理想主义的内涵,并摸索着实现两者在作品内在的和谐,最后以传统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学的技巧和表述方法。即使吸收西方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也开始注意日本化。《雪国》就是在这种对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和交流的反复思考过程中诞生的。
《雪国》描写女主人公艺妓驹子经历了人间的沧桑,承受着生活的不幸和压力,勤学苦练技艺,对生活、对未来抱有希望与憧憬,具有坚强的意志,挣扎着生活下来。驹子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还表现在她对纯真爱情的热切渴望上。她虽然沦落风尘,但仍然追求自己新的生活,渴望得到普通女人应该得到的真正爱情。于是她同岛村邂逅之后,便把全部爱情倾注在岛村身上。她对岛村的爱不是出卖肉体,而是爱的奉献,是不掺有任何杂念的。这种爱恋,实际上是对朴素生活的依恋。而岛村把她这种认真的生活态度和真挚的爱恋情感,都看作是“一种美的徒劳”,岛村爱慕叶子。驹子这种苦涩的爱情,实际上也是她的辛酸生活的一种病态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川端对驹子这个人物的描写相当准确。
《雪国》中对日本传统美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更重视气韵,追求“心”的表现,即追求精神上的“余情美”。这种余情美,是悲哀与冷艳的结合,将“哀”余情化,以求余情的冷艳。表面上看似华丽而内在幽玄,具有一种神秘、朦胧、内在的美,感受性的美,而不是外在的、观照性的美。这种冷艳,不完全是肉感性、官能性的妖艳,而是从颓唐的官能中升华而成为冷艳的余情,是已经心灵化、净化了的,蕴含着一种内在庄严的气韵,包含着寂寞与悲哀的意味。应该承认,这种冷艳,虽然有其颓伤的一面,但也不能否定其净化的一面。
《雪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意识流”手法,采用象征和暗示、自由联想,来剖析人物的深层心理。同时又用日本文学传统的严谨格调加以限制,使自由联想有序展开,两者巧妙结合,达到了完美的协调。比如,作家借助两面镜子(一面暮景中的镜子,一面白昼中的镜子)作为跳板,把岛村诱入超现实的回想世界。从岛村第二次乘火车奔赴雪国途中,偶然窥见夕阳映照的火车玻璃窗上(这是前一面镜子)的叶子的面庞开始,即采用象征的手法,捕捉超现实的暮景中的镜子,揭示了《雪国》主题的象征。镜子中叶子是异样美的虚像,引起岛村扑朔迷离的回忆,似乎已把他带到遥远的另一个女子——驹子的身边,接着倒叙岛村第一次同驹子相遇的情景。次日到达雪国,从映在白昼化妆镜中(这是后一面镜子)的白花花的雪景里,看见了驹子的红彤彤的脸,又勾起了他对昨夜映在暮景镜中的叶子的回忆。作家写岛村第三次赴雪国,更多的是与驹子的交往,当他们两人的关系无法维持,岛村决计离开雪国时,又突然加进“雪中火场”,叶子的坠身火海,又把现实带回到梦幻的世界,这时再次出现镜中人物与景物的流动,增加了意识流动的新鲜感。作家运用这种联想的跳跃,突破时空的限制,使人物从虚像到实像,又从实像推回到虚像,实实在在反映了岛村、驹子和叶子三人的虚虚实实的三角关系。同时,从故事的发展来说,从现实世界到梦幻,又从梦幻到现实世界,或者在一个并列的平面上展开,或者时空倒错,但跳跃却很有节奏感。通过跳跃的联想,一步步地唤起岛村对驹子和叶子的爱恋之情,驹子和叶子的内心世界常常是在岛村的意识流动中展露出来。岛村遥远的憧憬,流动于理智的镜中,而镜子又属于遥远的世界,驹子和叶子都是属于岛村的感觉中产生的幻觉,把岛村的心情、情绪朦胧化,增加感情的感觉色彩和抒情风格,表现了川端式的“意识流”这一独特的日本风格。
《雪国》的问世,标志着川端在创作上已经成熟,达到了他自己的艺术高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艺术上开拓了一条新路,在吸收西方文学的基础上,保持日本文学的传统色彩,使两者的结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二,从《雪国》开始,川端的创作无论从内容或从形式来说,都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对人物心理刻画得更加细腻和丰富,更加显出作家饱含热情的创作个性。尽管在其后的创作中,川端的风格还有发展,但其创作始终是和《雪国》所形成的基本特色相联系的。
战后,川端康成对战争的反思,进一步扩展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审美意识中潜在的传统的苏醒。他说过,“我强烈地自觉做一个日本式作家,希望继承日本美的传统,除了这种自觉和希望以外,别无其他东西。”(《独影自命》)也就是说,战后川端对日本民族生活方式的依恋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追求更加炽烈。他已经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思考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问题。他总结了一千年前吸收和消化中国唐代文化而创造了平安王朝的美,以及明治维新百年以来吸收西方文化而未能完全消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且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应该“从一开始就采取日本式的吸收法,即按照日本式的爱好来学,然后全部日本化”(《日本文学之美》)。他在实践中将所汲取的西方文化融合在日本古典传统精神与形式之中,更自觉地确立“共同思考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桥梁的位置”(《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川端康成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作家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量,培育了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气质,并且使之流贯于他的创作实践中,使其文学完全臻于日本化。同时他的作品呈现出更多样化的倾向,贯穿着双重或多重的意识。在文学创作上,继《雪国》之后获得最大成功的,可算是《千只鹤》、《名人》、《古都》和《睡美人》等作品。
审视川端康成创作的全过程可以发现,他从追求西方新潮开始,又回归传统,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运用民族的审美习惯,来挖掘日本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汇合,形成了川端康成文学之美。用川端本人的话来说,日本文学“既是日本的,也是东方的,同时又是西方的”。可以说,川端康成这种创造性的影响,超出了日本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艺术性方面,这一点对促进人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作用。可以说,川端康成为日本文学的发展,为东西方文学的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69年诺贝尔基金会为了表彰他“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而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井上靖(1907—1991)生于医学世家,其父从军后辗转各地,三四岁的井上靖便离开父母身边,被送回静冈县伊豆汤岛乡间,由艺妓出身备受村里人冷眼的庶祖母抚育。井上与这样一个孤老相依,过早地体味人生的凄苦,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另一方面,他置身于山林之中,接触到旖旎的风光,又孕育了他对大自然的敏锐感觉。这对于井上作为一个诗人的直观和感觉的特质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井上在大学攻读英国文学,从创作诗歌起步。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积15年的记者生活体验,人过中年,于1949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斗牛》和《猎枪》而立足文坛。井上靖早期的代表作还有中篇小说《暗潮》,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美国占领军当局为使日本成为他们的朝鲜战争后方基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以嫁祸于日本进步力量,“下山事件”便是其中之一。这部作品就是以这一真实事件为背景,描写新闻记者速水卓夫在调查采访过程中逐渐成长和成熟的历程,并以含蓄的手法,揭示了事件的真相。故事大意是:速水已过不惑之年,工作上不得志,婚姻上又很不幸,因而身心受到严重创伤,他痛感人际关系的冷酷无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生产生了厌倦情绪。但是,他在接受了采访“下山事件”的任务以后,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与良知,使他的心中燃起了执拗地追求事实真相和伸张正义与真理的热情。小说展现了速水在来自各方面的,甚至被指责为“共产党的吹鼓手”的巨大压力下,从彷徨、困惑和畏惧至愤怒、坚定、奋斗的思想转变过程。最终速水经历严峻的事实考验,没有退缩与屈服,坚持了经过认真周密调查得出来的实事求是的结论。这说明作家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面对现实的巨大勇气,来塑造速水这个人物的。他所塑造的速水这个人物,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积极面对现实,却怀着某种程度的孤独和哀伤情绪,然而决不悲观、消沉。作品通过展现人物的苦楚和际遇,揭示人间的不平,寓委婉的批判于平静的气氛中,然而这种批判却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和睿智的人生哲理。
继这几部小说之后,井上靖探索着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构建一种新的小说模式——中间小说,使之兼具纯文学的艺术性和大众文学的趣味性。其成功之作有:《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射程》、《冰壁》、《城堡》、《夜声》等,题材多样,无论在主题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达到了圆熟的程度,从而确立了井上靖小说的定式。
井上靖的文学功绩,表现于他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继承日本文学的优秀传统,赋予作品以强烈的民族气质。同时,博采现代各流派的技法,既重视叙事,又注意心理分析,既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又有诗的素质,创造了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新世界,形成作家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将中间小说创作推向了最高潮,为迎来战后日本中间小说的全盛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井上靖的第二创作期,以创作历史小说为基本特色。井上的历史小说涉及的时间比较久远,空间比较广阔,上至一两千年前,下至十七八世纪,既创作日本历史小说,也推出中国以及俄罗斯、高丽、印度、波斯和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小说。但艺术成就最高、作品比重最大的,还得数中国历史小说,尤其是西域小说,成为井上靖文学的一根重要支柱。井上靖的这些历史小说的特点,就是充分发挥诗人丰富的想像力,将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尊重史实而又不拘泥于史实,充溢于文中的,是史实所不能完全涵盖的诗意。《天平之甍》、《楼兰》、《敦煌》、《洪水》、《苍狼》,是具有不同手法和特色的代表作。
《天平之甍》这部作品,主要根据日本奈良时代文化名人淡海三船所著《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的史实,改编而成。小说以史实为主,辅以虚构,将鉴真应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的恳请而东渡传法的全过程,以及当时日本奈良的佛教状况和日本留学僧在唐朝的动态,以形象的艺术手法,真实地再现出来。作者完全尊重历史的真实,但又没有囿于史料,而是跳出历史,对《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只留其名而无事略的人物玄朗,根据当时日本许多留学生或留学僧以种种理由长留唐土的散见史实,进行了艺术塑造。小说中的另两名留学僧业行、戒融,史书里并无其人,是作者为了表达小说的主题而虚构的,但作者根据主题和情节的需要,赋予他们以特定性格,使这两个人物有血有肉,形象栩栩如生。
接着发表的《楼兰》,则是以《汉书》、《晋书》等有关史实为本,间以某些虚构情节。在叙述历史时,并不是史书的翻版,而是运用形象思维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尤其是调动诗的瞬间的美,加以灿烂多彩的描写。但是,小说中没有出场人物,没有爱也没有恨,只有在席卷的风与沙之中,小国楼兰的一切——两千年前的国土、湖泊和沙漠,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埋没在远景之中。西域楼兰国兴亡史在作家的笔下,就像海市蜃楼般地艺术重现。然而,它不是简单的历史复述,而是诗的苦吟。(www.zuozong.com)
井上靖这种历史小说的叙事诗性格,在《敦煌》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作者以虚实相间、收放自如的笔致,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了落第书生赵行德与王女的悲恋故事,还虚构了赵行德把大批珍贵的经卷藏入千佛洞的情节,再将这些虚构人物和故事情节,编织在发现敦煌千佛洞藏经的历史传说中。这种虚构,无论故事情节的安排,还是主要人物的塑造,都是符合历史生活和时代气氛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可能产生的。就以赵行德的形象来说,他虽然是个虚构人物,但当时秀才考试落第而被西夏看中,受聘于西夏的大有人在,也是有历史记载的,作者不过是根据这个史实,加以集中概括罢了。小说中的西夏李元昊、敦煌太守曹贤顺等人物以及千佛洞的开凿、封闭与再发现,都是真实的历史,有史料可查。小说的情节结构、故事发展都符合小说艺术的一般规律,历史人物的描摹也注入了生命力。《敦煌》具有叙事诗的浪漫性格,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三岛由纪夫(1925—1970)在东京一个高级官僚家庭出世,自祖父辈起家道中落。祖母受到娘家家风的教养,自然而然地养成一种武士的骄矜和皇族的孤高气质。三岛出生第49天,就被祖母从母亲的怀里夺了过去,受到祖母的严格管教,“被闭锁在两三重隔离的状态下。首先是与母亲的隔离,其次是与户外自然的隔离,第三是与同年代的游戏伙伴的隔离”,这决定了他那奇异的、阴暗的一生的命运。
年幼的三岛,在这种异常的生活中,试图从图画、童话里寻求某种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的东西。他看见法国童话的圣女贞德图,便幻想着骑士的下一瞬间将会被杀掉,对骑士的死作了一番美妙的幻想。他读到安徒生童话《玫瑰妖精》中的一个年轻人正在亲吻情人留下的遗物——玫瑰时,却惨遭坏人刺死的故事,读到怀尔德童话《渔夫和人鱼》中紧抱着美人鱼被冲上海滩的年轻渔夫的尸体,以及童话《被杀害的王子》中王子那身紧身衣裤所显露出来的体形等等,都与残酷的死结合在一起来空想,竟然产生一种神秘的快感。在现实生活中,他发现掏粪工身穿紧腿裤把下半身的轮廓清楚地勾勒出来,一个东西优美地活动着;地铁检票员身上弥漫着橡胶般的、薄荷般的气味;打靶归来的士兵身穿肮脏的军服发出一阵阵汗臭味儿,对此他都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倾倒。屋内的童话世界和屋外的现实世界交织的这些幻影,执拗地追赶着他,而追赶他的这些“异样性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已含有某些悲剧性,有了某些血与死的幻影。后来这些东西,成为他的一种特殊的嗜欲和浪漫的憧憬,并构成他的文学生命体。
中学时代,三岛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习作《酸模》,国文教师清水文雄发现了他的天才。在清水文雄的指导下,他热心学习古典文学,尤其是欣赏《源氏物语》的原罪的主题,以及非个性的、抽象的《古今和歌集》的纯粹美,从那里吸收了古典文学的营养。同时他也主动涉猎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唯美派作家王尔德的作品,以及拉迪盖的《魔鬼附身》等作品。16岁时,他发表了第一篇正式的小说《鲜花盛时的森林》。这时候,他特别喜欢文艺复兴时期新古典主义的《塞巴斯蒂昂·圣殉教图》,被塞巴斯蒂昂殉教的肉体、官能性、美、青春、力量乃至残酷的美所刺激,产生了性异常和自我陶醉。这是他幼年时刻印下的“悲剧性的东西”的形象的延长。确切地说,在他体内埋下的倒错的爱与性的种子,渐渐地在他的体内萌芽,他第一次陷入了自恋。
三岛由纪夫采取了与战后派作家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接受日本战败的事实,他在精神上处在一种混沌与清醒、绝望与希望参半的状态中,开始了战后的生活和创作,写就了短篇《中世》、《香烟》及长篇《盗贼》等。《盗贼》出版后,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他毅然辞去大学毕业后仅任职八个月的大藏省的官职,全身心地投到长篇小说《假面自白》的写作上。这部自传体小说的文学结构分三个层次:一是写了主人公“我”的诞生和家庭状况以及家族中人际的心理纠葛,展现了幼时的“我”那光怪陆离的内心世界,激起一种官能的欲求、一种逆反的心理,引发出第一次“性倒错”的冲动;二是写了“我”发现男学友近江的健全身躯,壮实的完整无缺的美的幻影,由憧憬近江的男人野性的肉感,而联想到塞巴斯蒂昂被乱箭射杀,由爱上近江的力度与肉感,而爱上塞巴斯蒂昂的充溢的血,这时候“我”已经不满足于自己的肉体的成长,而转向追求自我的“精神锻炼”,出现了第二次“性倒错”;三是写了“我”与女性园子的初恋,由同性恋转向异性恋,“我”对自己的气质抱有一种不安感,尝试与异性恋爱,接近园子,但又自觉欠缺肉体的能力,难以成为现实的东西,“我”忘却了园子,视线内出现一个粗壮而野蛮却无比完美的肉体,于是出现了第三次性倒错。
《假面自白》获得成功,三岛更醉心于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和法国诗人莫里亚克的《爱的荒漠》的艺术结构,即表现古典主义的文学传统与现代主义潮流的对立与统一的结构,以此作为他探索新创作的出发点,用他从未有过的自信和热情,写了长篇小说《爱的饥渴》、《青春时代》、《禁色》,进一步展开更为怪异的文学和美学世界。
以1951年第一次出访欧洲,特别是希腊的体验,三岛由纪夫构筑起自己的特异的文学模式,即将肉体的改造与文体的改造放在同一的基准上,写下了《仲夏之死》、《潮骚》、《金阁寺》等优秀作品,将三岛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可以说,他对希腊的体验,使他觉得比起内在的精神性来,更应重视外在的肉体性,重视生、活力和健康,于是他效仿古希腊朗戈斯,创造出一个东方的“达夫尼斯和赫洛亚”的纯洁爱情故事——《潮骚》诞生了。
《潮骚》在神岛的自然与风俗画面上,展开了新治与初江的渔歌式的纯情故事。三岛将人物的生活、劳动、思想、感情镶嵌在大海的自然画框里,以大海寄意抒情,创造了一种自然美的独特魅力。尤其对于青春的描写,朴实自然,极力提高爱情的纯洁度,达到肉体与精神的均衡,并在这种均衡中创造了美,从而使这对恋人的爱情得到了绝对的纯化,推向至纯至洁的境界。在这里,美的艺术创造者,同创造美的艺术,具有同一的伦理基准,即神岛古老共同体的基准。这不仅回归日本传统的深层,而且使渔歌的理想之乡的传统的古朴美,保持完整无损而再现于现代。
三岛在《金阁寺》中,撷取一僧人焚烧金阁寺的历史事件作为素材,独创性地运用作家独立的思想和文体的力量,即从素材的现象独立出来,通过对主人公沟口的绝对的美与丑之展现,凸现其非人性的反社会行为,构建起纯粹的观念性的艺术世界。正如他所说的:“人类容易毁灭的形象,反而浮现出永生的幻想,而金阁坚固的美,却反而露出了毁灭的可能性。像人类那样,有能力致死的东西是不会根绝的,而像金阁那样不灭的东西,却是可能消灭的。”此后三岛更是陶醉于希腊古典式的男性艺术,在《阿波罗之杯》中是这样记录的:“希腊人相信美的不灭。他们将完整的人体美雕刻在石上了。而日本人是否相信美的不灭呢?这是个疑问。他们顾虑有一天具体的美会像肉体一样消灭,总是模仿死的空寂的形象。”这种希腊的体验,对三岛其后的创作影响是很大的。
以1960年的日本战后史又一次转折为契机,三岛由纪夫逐渐形成自己新的“文化概念的天皇观”,并以此作为其创作的中轴,辐射出《忧国》、《十日菊》、《英灵之声》三部曲,这些作品将其破坏性的冲动与危险美的情趣结合起来,并运用了冷嘲热讽的、保守的乃至反动的言辞,来构建其新的文学模式。以《忧国》为例,它着重描写中尉夫妻在悲境中自觉地捕捉生的最高瞬间,追求至福的死,并将他们肉体的愉悦和肉体的痛苦完美结合,使夫妻爱达到了净化的境地。但是,三岛却将这个美的世界置于“2·26事件”的背景之下,目的在于表现比夫妻爱更为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大义与至诚,即将中尉对天皇和国家的忠诚抽象为纯粹的美。但是,在文学上并非愈抽象就愈纯粹,更何况注入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让人悚然的愚忠。实际上这反映了三岛的一种明显的右翼国家主义的倾向,三岛试图将政治置于文学中,又将自己不可思议的美学置于文学中的政治。不过,这一切都是冠之以爱与死的主题来完成的,这是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主题而采取的一种巧妙的艺术手法。这就使三岛文学模式中的文学基因裂变,产生新的因子,演绎而形成三岛由纪夫特异的精神结构——“文化概念的天皇”和“文武两道”,这成了三岛文学生涯及三岛文学的一大变化和转折。
作为三岛绝笔的超长篇巨作《丰饶之海》,是由《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四部曲组成的。这是三岛由纪夫毕生的文学创作的缩影,他将唯美、浪漫和古典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又着眼于与复古的国粹主义的微妙接合,并在接合点上确立其历史的独特性。可以说,它是三岛文学、美学的集大成,也是三岛的“文武两道”的艺术作品化。三岛本人曾总结说:“《丰饶之海》四卷的构成,第一卷《春雪》是王朝式的恋爱小说,即写所谓‘柔弱纤细’或曰‘和魂’;第二卷《奔马》是激越的行动小说,即写所谓的‘威武刚强’或曰‘武魂’;第三卷《晓寺》是具有异国情调色彩的心理小说,即写所谓‘奇魂’;第四卷题未定(注:即《天人五衰》),是取材于时间流逝某一点上的事象的跟踪小说,导向所谓‘幸魂’。”简单地说,三岛试图在这四部曲中表达“和”、“武”、“奇”、“幸”四魂,实际上是集中表现“文武两道”。三岛对各卷的不同主人公松枝清显、饭沼勋、小月光公主、安永透四人,赋予了不同的性格特征,使他们各自成为一种“魂”的体验者;而他们彼此的联系完全仰赖于梦与轮回的主题,并由副主人公本多繁帮贯串始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故事系统,这是作家的独具匠心。
《丰饶之海》四部曲的四个主人公的人生,都结束于风华正茂的20岁,在人生不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了。女主人公聪子和本多已经老迈,聪子对尘世的一切已经了无记忆,本多走向老丑的绝境。作家情不自禁地道出:“人是要死的,肉体是要衰老的,为什么要等到老丑才死呢?这时候,他们两人什么也没有,既没有记忆,也没有过去,直面的是宿命的孤独,已成为虽生犹死之人。”这部超长篇最后的一切存在都化为乌有,导向了绝对虚无和绝对空寂之境,梦与轮回的主题也空无化了,这里就浸润着东方艺术的神秘色彩。
三岛由纪夫创作活动是多样性的,除小说以外,在戏剧和评论方面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戏剧创作来说,包括话剧、歌舞伎、能乐、文乐(木偶净瑠璃),乃至广播剧、音乐剧、舞剧和翻译剧等近代剧和古典剧,还涉足电影。可以说,小说与戏剧是三岛文学的两根支柱。尤其是在近代能乐的创新上,三岛出色地完成了他的诗剧性理念,其成果表现在《近代能乐集》上。该集收入《邯郸》、《绫鼓》、《卒塔婆小町》、《葵姬》、《班女》、《道成寺》、《熊野》和《弱法师》等八出戏,其中《绫鼓》和《卒塔婆小町》与三岛小说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从不同视角表现了爱、死与美。
三岛的评论包括文学论、艺术论、美学论、戏剧论、作家论、作品论以及社会文化论,共千余篇。其中《文化防卫论》和《太阳与铁》两篇评论,不仅反映了其文学艺术、哲学美学的思想,而且描绘出其整个精神结构。在《文化防卫论》中,他既反对美军制定的象征性天皇制,同时也反对“复古主义者只希望复活政治概念的天皇制”,因为战后“总算维持下来的天皇制,使这两个侧面的任何一方都变得软弱无力”。所以他力图恢复“惟一能对抗左右全体主义的观念——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即恢复“作为文化整体性的支配者天皇的形象”。所以,三岛的天皇观是非常矛盾的,正如奥野健男所说的:“三岛对天皇抱有一种两面价值的感情,恰似对近亲抱有的爱与憎的极限的两面价值的感情一样。(中略)三岛对天皇的思想和感情,正像一把双刃的剑。”(奥野健男《三岛由纪夫传说》)
三岛在《太阳与铁》中,着重论述了“发现其奥妙而暧昧的领域”——“文武两道”。他的“文武两道”的焦点,就是如何整合肉体与精神的背离问题,即在战后所有的价值颠倒的时代,如何调和现实、行动、生活的肉体系列的价值,与想像、语言、艺术的精神系列的价值这两个体系的对立问题。也即是如何在艺术与生活、文体与行动伦理方面达到使“文武”相反的欲求均衡于一身的境地。了解三岛运营的这一机制,对于理解三岛文学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他所说的“从太阳与铁中领会到的,不仅用语言描摹肉体,而且用肉体去描摹语言的秘法”,就是他悟到作家作为“观察者”,如果总是将自己置身于想像、语言、艺术的精神系列之内,也就是等于将自己置身于现实、行动、生活的肉体系列之外,那么就没法到达事物的本质,于是要谋求让“观察者”变为“行动者”,进入肉体系列的价值体系。正是从这里出发,三岛试图首先通过太阳与铁来创造“行动者”的肉体。这样,他就在更深层面上思考太阳与肉体的关系,发展到肉体的思考之一就是“武”。从而强调肉体训练的必要,并且严格要求自己进行希腊古典式的肉体训练。而他的所谓“古典式的肉体”或“肉体的思考”是包括肉体与精神两个方面的,是将肉体与精神放置在两个秤盘上微妙地计量其平衡,在平衡中酿造一种“对死的浪漫的冲动”。然而他认为要面对“浪漫主义悲壮的死”,还需要有健壮的雕刻般的肌肉,过去自己没有机会实现这种“对死的浪漫的冲动”,原因就是自己不具备肉体的条件。于是他追求的,不仅要借助太阳进行肉体训练,而且要借助铁来完成他的肉体与精神两者的绝对统一。“太阳与铁”便成为其完成肉体与精神统一的最重要的两个要素。
三岛在《文化防卫论》和《太阳与铁》所表述的观点,成为他独特的思想方法论,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对语言、文体、肉体痛苦、死等进行了三岛式的分析。这些理论十分生涩难懂,有时甚至故弄玄虚,但从中可以了解三岛文学、美学的主体,及其行动的深层意识。最后,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自杀,正是他这种人生观、文艺观和美学观的最终总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