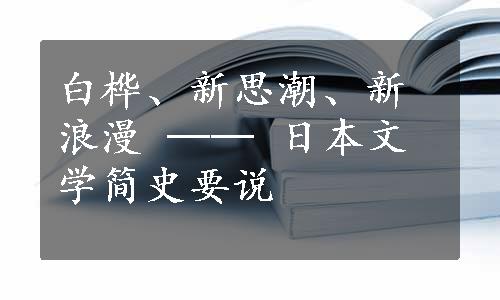
面对1910年自然主义式微的文坛沉闷形势,作家兼诗人石川啄木发表了题为《时代闭塞的现状》一文,提出这个时期自然主义已经丧失其前期暴露社会的积极态度,转向更多地暴露自我和肉欲,失去了初期反封建传统、追求自我个性解放的性格,自然主义的初衷是克服人生苦恼,最后却变成制造人生苦恼,因此必须抛弃自然主义。文章的发表促进了反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于是,一批青年作家举起反自然主义的旗帜,先后掀起了白桦派的理想主义和新思潮派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但是,两者反对自然主义的出发点不同,白桦派是对自然主义的“无理想”的反拨,主张恢复理想,故称理想主义;新思潮派则是对自然主义的“无技巧”的反拨,主张恢复技巧,故又称技巧主义。这一时期,白桦派、新思潮派与新浪漫主义一起,迎来了近代文学史上三派鼎立的时代。
白桦运动主要由一批贵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作家发起,主要成员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以及长与善郎、有岛生马、里见弓享等。他们的基本特色是:(一)尊重人的个性和肯定自我,主张人的价值是艺术的源泉;(二)肯定人生,以善为本,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三)强调“调和”与“和谐”,以无抵抗作为其文学的中心思想。可以说,白桦派确立近代的自我、个性和肯定人生的热情,是反对封建主义遗制、反对旧价值秩序,表达了继续完成明治维新未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强烈愿望,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期市民社会和文艺的向上的气氛、感情和理想,注意艺术的良心和艺术家的气质,并在文艺上发挥了作家各自的特殊个性,创作倾向各有侧重。
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处在白桦派指导地位,出身于公卿华族家庭,入贵族学校——学习院就读时,倾倒于托尔斯泰在文艺上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思想。他在《白桦运动》一文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人生与文学的问题,其主要论点是:(一)强调热爱文学,就要忠实自己的艺术良心;(二)主张从事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将自己的内心活动铭刻人类,将爱奉献给读它的人,并接受读它的人的爱;(三)认为文学的价值,与个人的价值是成正比的,如果个人没有作为个人的使命,那么文学这种东西就没有价值;(四)赞美天才,认为受人类的意志支配而从事工作的,都可以称作天才,读天才的作品,可以获得无限的喜悦和充实生命,而人类的意志是通过个人和个性才能发挥出来的。
他的前期创作积极肯定人生,并且表现了绝对的优越感。这种信仰自己的精神一直贯穿在他的剧本《他的妹妹》、《人类万岁》、《爱欲》等中,这些作品塑造了众多的“不知绝望的、明朗幸福的”、“相信爱、相信美、善、真一致的”,或“追求人类永恒的理想的”人物形象,热烈地礼赞生命的力量。他还写了长篇小说《幸福者》、《友情》、《第三隐士的命运》和《一个男人》等。
代表白桦派的理想主义的典型作品《友情》,它的主人公剧作家野岛暗恋着友人的妹妹杉子,野岛向挚友大宫谈了这件事,大宫抱着真挚的友情祝福了野岛。大宫经由野岛认识杉子后,也逐渐为杉子所倾倒,爱上了杉子。当大宫发现杉子也爱自己,悟到这样会背叛对野岛的友情时,便决计离开日本到法国去。杉子写信给远在巴黎的大宫,表明她感到野岛对她的爱恋,只是一种困惑,野岛虽赞美她却不想理解她。最后,杉子为了与大宫结婚到了巴黎。大宫用小说的形式写了自己无可奈何地背叛了友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以主人公野岛在日记中写下“我自己好不容易地忍受了孤寂。难道今后还必须忍受吗?我已是孤身只影的人。神啊,助我吧!”这样一句话就结束了。其主题突出了自然赋予的东西是不可抗拒的,爱情最终战胜了友情。
志贺直哉(1883—1971),出身于藩主家庭,就读于学习院初高等科,毕业后考入东京大学,由于志向当小说家,于1910年中途退学,当年在《白桦》杂志上,发表了《到网走去》等。志贺因为选择从事文学道路,以及与女佣的婚姻问题等,与其父长期不和,几经曲折,最后终于和解。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和解》,以冷静的态度,描写了主人公与其父从决裂到和解的经过,对于骨肉亲情和对父亲的抗拒进行了自省,并着意凸现了人与大自然、人与人和解的重要性这一主题。他还发表了《在城崎》、《一对父子》、《11月3日下午的事》等众多作品,与前期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作者表达了对于将人导向调和世界的异常感动,以及暗示性地表达自己对人生的观点。
志贺惟一的长篇小说是《暗夜行路》,描写主人公时任谦作在母亲死后,与祖父的妾阿荣一起生活,他发现自己对祖父的妾产生了性意识的念头后,便到足道旅行去了。可是当他知道自己是祖父的儿子后,便移居京都,与直子相恋而结婚,然而爱子出生七个月后便夭折。此时,阿荣在天津经营的艺妓馆失败,经朝鲜回国时,谦作赴朝迎接阿荣,其妻直子与他的表兄发生了关系。他虽然原谅了妻子,但在感情上还转不过来,此时又为阿荣所动心。他为了摆脱母亲和妻子的过失所造成的苦恼,净化自己的心灵,便又外出旅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寻求一种和谐的氛围,以达到自我的心理平衡,进入一个包容善与恶、幸与不幸、光明与黑暗的调和世界。
战后的志贺发表了《灰色的月亮》,小说描写一个少年工的饥饿的情状和自己无能为力的心境,具有反战的色彩,鲜见地给人一种时代感。但对于志贺来说,如果要进一步超越,显然存在不可逾越的困难,这是由于他阶级出身的局限,以及他一生创作所设定的狭窄视野的惰性作用所造成的。此后除了写些小品和书简以外,他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小说创作,只是过着作为作家的漫长的“余生”了。
有岛武郎(1878—1923),作为原萨摩武士,大藏省官僚的长子,自幼即受到娇宠,进入贵族学校学习院学习。他学习成绩优异,并尝试习作历史小说。在从事创作之初,虽然是白桦派的一员,却与同属白桦派的武者小路实笃沉湎于乐天的空想世界完全不同,与志贺直哉囿于狭窄的个人天地也不相同,而是力图在现实生活中探求人类的博爱和社会意识。他的处女作《除锈工》,就将目光投向社会下层的人物,描写了港湾船坞的一群除船锈工人的种种苛酷生态,表达了对他们深切的同情并批判了资产者的非人性和体制的非变革性。之后,又写了《阿末之死》,描写了一个贫民窟少女的悲剧命运。
他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是以国木田独步的妻子信子为模特儿创作的。信子与国木田独步离婚后,迫于经济原因,准备赴美国与武郎的友人森广结婚,但在赴美的轮船上,认识了另一个男子,两人坠入爱河,遭到世人的非议。信子的这段恋爱生活遭际,对武郎的思想冲击是非常巨大的,他不愿割舍这原始的素材,于是怀着巨大的激情,重新构建这部《一个女人》的故事,将主人公置于日本的现实生活中,从根源上探索潜藏在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各种矛盾,艺术地再现了一个热情奔放、富有个性的女人叶子追求恋爱自由,但她的行为不为社会所接受,虽然身处孤立的世界,但仍忠实于最纯粹的爱的本能的故事。小说描述了一个具有近代自我觉醒的女人的追求与失败的生涯,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多层挑战意味的女人:向封建的伦理和社会的束缚挑战,向以男人为中心的旧生存状态挑战,向传统的好女人的标准挑战,向世俗的偏见和伪善挑战。小说细腻地表达了一个女人追求自我的解放和发展的心路历程。作者以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揭露了社会的偏见与伪善,宣扬了个性自由思想,蕴含着丰富而素朴的人文精神。
《一个女人》受到广泛好评之后,武郎试图将其在小说中关注的这个问题提升为理论,于是在长篇随笔《不惜夺爱》中,他试图从肉与灵、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性二元论的困扰中解放出来,创造一种没有二元对立的本能的生活。
与白桦、新思潮鼎立的新浪漫主义的兴起,是以上田敏的译诗集《海潮音》介绍西方高踏派的诗和象征派的理论作为开端的。1907年1月在森鸥外的支持下,由上田敏等人创刊《昴星》杂志,其周围结集了吉井勇、木下木

在文学上,日本经历了明治初期的欧化运动。在日俄战争之后,一方面继续引进西方的文化与风习,陶醉在西欧现代文明的幻想之中;一方面转而对本国和本国文化传统盲目狂信,高扬国粹主义精神。在这种情况下,近代文学丧失了初步确立的主体性,也削弱了批判的精神。作家对现实和人生抱着消极的态度,逃避社会与政治,走向自我封闭的道路,一味追怀过去和沉溺于唯美之中,以寻求文学的自由。当这种欲望遭到压制之后,就转向了颓唐主义。后期浪漫主义者高山樗牛在幻想破灭之后,便倒向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本能主义,提出所谓幸福,就是本能的满足,人性的自然要求。
日本新浪漫主义论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一)主张“第一是艺术,第二是生活”,认为文学应该游离于生活现实,追求超然于现实生活的所谓纯粹的美;(二)主张唯美的属性就是享乐主义,文学应该以享乐作为目的;(三)强调生活就在于玩味,艺术也绝对在于玩味官能主义,以官能的开放来改变一切价值观念,这一论点,与(一)、(二)的论点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否认思想、感情的普遍性,认为艺术之美的首要要素,就是求得最彻底的享乐;(四)追求所谓真正的自我,以为享乐主义的精神主体,就是本能的自我,因而将自我看作是集中快乐感觉的实体而主张尊重个人主义和人性的自然;(五)尊重西方异国情调,憧憬西方的风习,同时又追求都会情调、江户情调,认为其美的激情受到江户情趣的强烈刺激,是通过江户时代的一切人情风习来体味的。(www.zuozong.com)
在这种唯美文学理论的指导下,日本新浪漫派更加积极开展创作活动。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是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两根有力的支柱,这将在下章论述。此外,颇具代表性的作家还有:佐藤春夫、铃木三重吉、近松秋江、田村俊子等。但是,从整体来说,新浪漫主义文学的成就,与其说在小说方面,不如说更多的是在诗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歌人是北原白秋、木下木
北原白秋(1885—1942),生于经营酿酒业的家庭,中学时代就喜爱诗歌。于1906年参加新诗社,他与其他新浪漫主义诗人一样,既憧憬异国的情调,又执著传统的情趣。他的诗集《邪宗门》就反映了诗人追求东西方艺术精神合成审美意识的强烈愿望。诗人在诗集卷首特别写道:
经过这里,面对一团旋律的烦恼
经过这里,面对一份官能的愉悦
经过这里,面对一种麻醉神经的痛苦
这三行“扉铭”,可以视作是一篇代表新浪漫派的“唯美主义宣言”。那就是表达诗的象征意义的同时,诗人的目的是以西方的异国情调来编织出刹那的官能享乐主义的主题。白秋的这种努力还表现在抒情小曲集《回忆》上,他将柳河的乡土风俗,以及自己儿时奶妈背他去观海潮、少年时代性意识觉醒的生活诗化。尤其是对他少年期的官能所抱的怀疑和神秘感的抒发,充满了浪漫的气氛和抹上了浓重的颓唐色彩。第三诗集《东京景物诗》充分展开唯美诗风的同时,采用了都会新时代的一些新事物,用近代的感觉,表现了近代的色彩、观念和感情,反映了都会的颓唐、感伤、情痴情绪的一个侧面。这些诗集,确立了白秋在唯美诗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北原白秋还著有诗论集《艺术的圆光》,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他的文艺观,主要论点是:(一)提倡诗的品格和气韵,品位是艺术美的品格,气韵则在人世间的善恶之上;(二)诗是诗人自身的纯洁无垢的创造物,诗要有充实的个性的表现,才有艺术的魅力;(三)诗的个性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完美地表现出来;(四)诗的韵律,犹如林泉在静中而生音,言语不断,飘荡于缥缈之中;(五)诗的价值在诗本身中产生,其艺术的价值应完全用艺术的鉴赏眼来评判。也就是说,他认为就诗来说,真正必需的东西,是品格,是韵律的至妙至美。诗人要通过这科学神圣美的最高诗品,最终将自己提高到神圣的绝对之境。就是达到戴上圆光——金色光环之境。这就是艺术的诗的圆光。
木下木
EAV DE VIE DE DAHTZICK
啊,五月,五月,小酒盅,
我的酒铺的彩色玻璃,
降在街上的雨的紫。
女子啊,酒铺的女子,
你已经穿上丝绸洋服了吗?
现出了淡淡的蓝条纹,
素白的牡丹花,
不许触摸,花粉要散落,花香要飘散的啊!
诗人将诸如小酒盅与彩色玻璃、蓝条纹与丝绸洋服等日本和西方两种特异的东西,作为诗的素材,创造了一种现代的享乐情趣,从而向读者展现了走向现代化的东京,混杂着江户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情景,暗示他所创造的“新的世界”的情调。
在他们的后继者中,佐藤春夫(1892—1964)则兼及新浪漫主义的诗歌和小说,而且还从事评论和翻译工作,为新浪漫主义的创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春夫出身于医生世家,自少年时代起就接受文学的教养,参加了后期新诗社的活动,并结识了与谢野晶子,接受了他们的古典情绪和唯美的浪漫主义的熏陶,这些激发了他的唯美的诗情。春夫最典型的作品是《殉情诗集》,其中收入的《水边月夜歌》就咏道:
恋爱的苦恼,
让月影的寒冷渗入我心。
正因为知物哀,
才面对水月兴叹。
即使我觉得虚幻无常,
但我的思绪却非泡影。
我尽管卑微,
但也要驱散哀愁,
为了你。
这种物哀、风雅甚或风流的古典的诗美,引起了诗坛的注目。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与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同时被认为是通晓古典的作家。由于他对传统的诗美非常敏感,故素有“第一古典抒情诗人”之称。
佐藤春夫在小说创作方面,以短篇小说《田园的忧郁》和中篇小说《都市的忧郁》为代表作,充分地体现了新浪漫主义的唯美精神。这两部姐妹篇将田园和都会的“忧郁”发挥得淋漓尽致,被谷崎润一郎誉为“那种忧郁的一字一句侵蚀着读者的神经”(小说集《受伤的蔷薇》序)。
概括地说,新浪漫主义在艺术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荒诞、丑恶、颓废中提取美,拓展了艺术的表现空间,在美学上维护了艺术的独立与真实,在培养人的美感和美的享受方面,并非全无其文学价值。但是,他们又都全面否定艺术的社会功能,只醉心于形式美的追求,从而走向纯粹的形式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道路,并最终走进文学的死胡同。可以说,日本新浪漫主义创造了美,也毁灭了美。正是这种美的幻灭,致使谷崎润一郎也不得不发出“异端者的悲哀”的慨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