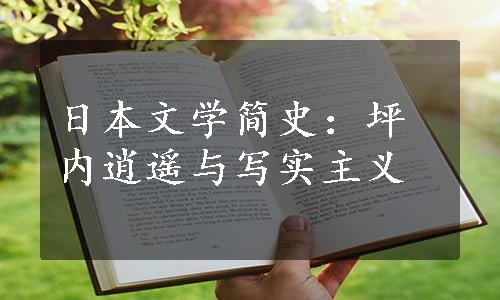
因此,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并没有像西方近代文学那样,以浪漫主义文学作为开端,而是以写实主义文学的诞生,迎来了近代文学的曙光。写实主义文学的创始者,是坪内逍遥(1859—1935)。他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少年时代起爱欣赏歌舞伎和江户戏作文学,尤其是曲亭马琴的书。就读名古屋英语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之后,更多地关心西方文学,尤其是注意并涉猎西方的文学评论,这便成就了他的文论《小说神髓》。
《小说神髓》开篇是“原理篇”,首先明确提出小说的定位是一种艺术形态,有其独立的价值,为小说确立了它在艺术上的地位。同时强调小说的主体性,认为小说只受艺术规律的制约,而不是用来为政治、宗教和伦理道德服务的,而且还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江户时代的文学观。其次,强调小说的内容,应以写人情为主,批评马琴的劝惩主义,指出,小说的主要目的是写人情,其次是写世态风俗。他还补充解释,所谓人情就是“人的情欲”,就是指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写“世态风俗”就是写现实。
接着是“技术篇”,提出小说内容形象化的方法问题,提倡写实主义的方法是近代小说的基本创作方法。认为小说写人情必须穿其骨髓,尽力促其逼真。也就是说,小说要写人的真实,写人的心理活动的真实,作为方法论则提倡对人物心理的剖析。
最后是“文体论”,将文体分为雅文体、俗文体和雅俗折衷体三种,认为平安朝的雅文体不适合描写现代的人情世态,戏作文学的俗文体又容易流于鄙俗,所以提倡“雅言七八分的雅俗折衷文”。
总之,从整体上来说,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从内容到形式提出了变革的主张,对于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的诞生,无疑起到了催生的作用,但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实际上,他的写实理论,是朴实的现实反映论,只停留在现象的、凡俗的写实方面,虽然也提出“穿其骨髓”,但却又认为“只应当旁观地如实模写”,其缺陷是:(一)只强调把握写“真实”的技巧,主张如实地描写现实的外表现象,而没有提到须深入地写出内在实质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忽视了真实与典型的关系。(二)强调对现实的真实描写,却又认为作家不应解释自己所描写的现象,更不应评判它,从而排斥现实主义的表现理想,将现实与理想对立起来。(三)强调写人的“情欲”,主张文学论和心理学原理结合,即运用心理学来模写人的内心世界,这是一种进步。但在创作方法论上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如何运用心理学原理。运用心理学原理从事创作是近代写实主义小说的一种重要表现之一,这是构成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揭开了近代文学的序幕,奠定了近代小说论的基础,反映了逍遥在转型期对传统和现代的矛盾思想和探索两者结合的强烈欲求。这一点,在以《小说神髓》为理论依据创作的实验性小说《当代书生气质》中也反映出来。它写了几个从事自由民权运动的书生与封建专制斗争与妥协的侧面,描写了他们的种种不同的柔弱性格,来展开转型期东京书生的风俗画卷,但贯穿了“没理想”的精神。也就是说,他的写实主义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是屈从于现实而产生的。它不能算是写实主义的成功之作。
近代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构建新的近代文学理论体系——写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任务,是由坪内逍遥的后继者二叶亭四迷来继续完成的。二叶亭四迷(1864—1909),是武士出身,少年时代爱好中国古典写实主义文学,对曹丕、魏叔子的作品尤有兴趣,耳濡目染地接受“建安风骨”的精神影响。入东京外语学校专攻俄语,开始接触俄国文学作品和文艺批评,以俄国的文艺理论为指导,总结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和《当代书生气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经验和教训,写就了《小说总论》。(www.zuozong.com)
《小说总论》从批评逍遥的《当代书生气质》出发,在文学论上具体阐明了文学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主张文学的主要目的是真实地描写生活现实,揭露生活现象偶然性的外壳所掩盖的实质,强调作家不应脱离现实,歪曲现实,或根据自己的理想来粉饰现实,但同时在描写生活的某些现象时,又不能没有自己的观点。所以说,文学是人们认识生活的方法之一,它的作用和社会意义也在于此。他扬弃了逍遥的朴实的写实论的偏颇,深化了近代写实主义理论,并在创作实践上加以体现,这就是《浮云》的诞生。
《浮云》通过官僚机构的小办事员内海文三洁身自爱,宁可忍受被撤职的痛苦而不愿充当附庸,和同是小办事员的本田升为了一官半职而寡廉鲜耻,出卖自己的灵魂这两种对官僚体制的不同态度,以及文三的婶母逼着女儿阿势同失去官职的文三中止恋爱关系而嫁给本田升的故事,揭示了明治社会在“文明”的背后所隐蔽着的种种丑恶现象和不合理制度。
二叶亭所选择的这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放在封建制度出现动摇、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形成、新旧事物新旧思想错综交织和复杂斗争的典型环境里加以塑造,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达到了某种典型化的高度。比如,在二叶亭的笔下,内海文三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是时代留下的烙印:一个只悠闲地思索和感觉而不行动,又不肯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他肯定是赶不上时代的潮流,甚至作为一个“多余的人”而存在的。他就像一片浮云度过一生,可以说他就是一片“浮云”。
《浮云》最大的成就:(一)首先突破了当时占文坛主流地位的戏作文学的旧框架,选择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权机关这个典型环境,通过内海文三这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再现了明治社会的生活世相,直接批判了明治的官僚制度,抨击了官僚的特权思想和官尊民卑的庸俗观念,具有积极的批判现实的力量。(二)突破旧文学的创作技巧,描写了人物的心理活动流程,有时通过人物自身的内心独白,有时作为第三者进行心理剖析,有时又利用客观的生活形象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几种方法交错兼用,相得益彰。(三)实践言文一致,创造了新的文体。《浮云》不仅内容新、体裁新,而且文体也新,创造了以近代口语为基础的言文一致体,为表现新思想、创作新文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对于日本近代文学走向通俗化,以及近代文学语言的创立,准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
在《浮云》之后,日本近代文学,虽然断断续续地出现过山田美妙的《武藏野》、坪内逍遥的《妻子》、木通口一叶的《大年夜》、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德富芦花的《不如归》等写实主义或具有写实主义倾向的作品,但都没有达到《浮云》那样批判现实的高度。可以说,在《浮云》之后失去了进一步向批判写实主义方向深化的机会,从而近代日本写实主义没有像西欧写实主义那样得到充分的发展,就此告终了。
日本近代文学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由于日本的近代写实主义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本国近代化具体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首先,明治维新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使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中残存着浓厚的封建性,此外日本近代文学形式的后进性,以及西欧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过早冲击和写实主义理论的准备不足等等,也都造成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存在着诸多软弱性格。其次,日本近代文化精神结构未能完全确立以人本主义为基调的近代自我,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成立的政教社,宣扬了国粹主义,强调个人要绝对服从天皇制绝对主义,并以此建立自我与社会的新关系。自我意识与前近代的现实所造成的矛盾,使日本近代文学,尤其是写实主义文学虽然重视文学上的自我觉醒,但未能正确地把握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未能把自我的问题作为社会的问题来加以探求,常常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作为静止的,这样势必出现一般化形式而无法创造出典型的作品来。再次,日本资本主义社会尚未发展成熟,就向封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所以日本浪漫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还未能形成一种文学理论体系,近代日本文学就首先朝写实主义方向发展了。但是,当时文学战线上的砚友社所标榜的“写实主义”,即拟写实主义,其实是追求“似是而非”的无思想性的纯技巧论,在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出现之前,由它统治了日本文坛。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未能建立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期的追求近代性社会和引进欧洲近代文学来适应人和文学近代化的基础上。同时,日本近代写实主义理论未能充分展开,就将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译介过来,这对写实主义是一个严重的冲击,以致日本评论家、作家常常将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混淆,给写实主义理论带来很大的暧昧性。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学时期,要贯彻批判现实的精神是非常困难的,更失去进一步开拓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最后一点,日本近代启蒙文学是从改良文学开始的,未能达到根本性的文学革命,其朴素的写实理论,将写实与理想对立,因而在创作实践中,只追求真实地描写生活,而不要求表现作家的理想,不要求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中体现作家的理想。因而日本近代写实主义文学作品所写的,不是理想人物,而是“多余人”。从整体来说,日本近代写实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不足和缺陷,使其主流具有明显的软弱性格特征,这是近代日本现实主义文学不成熟的根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