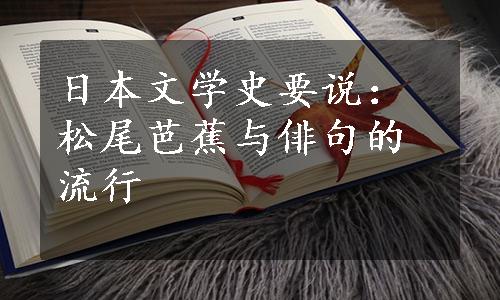
松尾芭蕉不仅是著名的随笔家,而且更以俳句而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出生于伊贺上野乡,生平未详,一说他已娶妻成家,一说他终生独身,因为他的著述和门人的记述都无涉及他的家庭生活情况,故难以定论。芭蕉自幼丧父,家境清贫,受俳人北村季吟的启蒙,开始作句。29岁时,他来到江户,亲眼目睹了当时武家政权和町人金权的统治,不满金权政治横行于世,于是决然离开了这一权力中心,来到荒凉的隅田川畔的深川,甘于忍受在底层生活的清贫与困苦,隐居草庵,从此参禅,彻悟人生,潜心作句,并将此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芭蕉从草庵生活开始探索新的句风,草庵也成为芭蕉开展俳谐新风运动的据点。其具有新风的《富家食肌肉,丈夫吃菜根,我贫》中有一句:
清晨冬雪彻骨寒
独自啃食鲑鱼干
芭蕉以富家食肉,贫家吃菜根来作对比,说明人虽清贫志不移,在寒冷的早晨,独自啃鲑鱼干,也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这一句写出了他人,也道出了自己的贫苦景况。芭蕉的句,还写了贫穷渔家的清苦、耍猴汉的苦楚、可怜歌女的悲哀、路人的饥寒、贫僧的凄苦等等。这些句,已孕育着“诚(まこと,真实)”与“闲寂(さび)”的审美意识,从中可以感受到芭蕉的新句风——蕉风的胎动。
晚年的芭蕉以旅行来抚慰自己孤独的心,同时观察自然与人生。隐居草庵的人生体验,以及旅行中对大自然的切身感受,成就了芭蕉,写下了代表蕉风的不朽名句《古池》,句曰:
闲寂古池旁
青蛙跃进池中央
扑通一声响
这一句写于芭蕉居庵之后。如果从表面来理解,古池、青蛙入水水声三者似是单纯的物象罗列,不过如果从芭蕉的“俳眼”来审视,古池周围一片幽寂,水面的平和,更平添一种寂的氛围,但青蛙跃进池水中,发出扑通的响声,猝然打破这一静谧的世界。读者可以想像,水声过后,古池的水面和四周又恢复了宁静的瞬间,动与静达到完美的结合,表面是无穷无尽无止境的静,内里却蕴含着一种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和大自然的无穷奥秘,以及俳人内心的无比激情。
这说明芭蕉感受自然不是单纯地观察自然,而是切入自然物的心,将自我的感情也移入其中,以直接把握对象物生命的律动,直接感受自然万物内部生命的巨大张力。这样,自然与自我才能在更高层次上达到一体化,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进入幽玄的幻境,艺术上的“风雅之寂”也在其中。
还有,芭蕉旅行奥州小道,来到山形藩领地的立石寺,心神不由得清净起来,作句一首,以慰藉他的孤寂悲凉的旅心:
一片静寂中
蝉鸣声声透岩石
这一句的俳谐精神与《古池》是相通的,都是具现了芭蕉的“闲寂”的典型佳句。芭蕉以“闲寂”为基础,将自然与人生、艺术与生活融合为一,达到“风雅之诚”、“风雅之寂”。这个“诚”与“寂”,较之物质的真实,更是重视精神的真实,是作为精神净化的艺术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俳谐的新风。
芭蕉热爱大自然,对自然美的感动,成为他追求的“风雅之诚”、“风雅之寂”的原动力。他的“风雅”,不是风流,也不是物质和官能的享乐,而是一种纯粹对自然景物的享受,向往和憧憬闲寂的意境。
在旅途中,芭蕉不止一次地说过:“若死于路上,也是天命。”旅中病倒,大概他已预感死期将至,临终前四日,还满怀闲寂风雅的情趣,写下一首辞世名句《病中吟》:
旅中罹病忽入梦
孤寂飘零荒野中
据其弟子其角记载:“师悟道:‘荒野之行,心中涌起梦般的心潮,正因为执迷,切身感到病体已置于风雅之道。’”可以说,芭蕉的俳句展现了一种闲寂美、风雅美,这种美是在永恒的孤绝精神之中产生的。而这种孤绝的精神又是在自然、自然精神和艺术三者浑然一体中才放射出光芒的。
芭蕉一生写了千余首俳句,他在创作实践中发现“风雅”、“闲寂”之美,开拓了一个时代的新俳风,完成了创造一个时代的日本美。芭蕉在传承与创造俳句的传统美方面,的确是个“登峰造极者”,世人尊称他为俳圣。
芭蕉不仅在俳句创作方面,而且在俳论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既扬弃贞门、谈林俳论只注重“俳言”和“滑稽”的旧风,以及超越贞门、谈林俳谐的观念性,又摄取上岛鬼贯从新的视点来思考“真实(まこと)”文学论的生命,以及运用禅学“本来无一物”的哲理思想,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鬼贯的“诚”的俳论,在“诚”的自觉的基础上,探寻俳谐的艺术本质。(www.zuozong.com)
芭蕉的俳论是通过对上述传统俳谐思想的自觉和本人严格的艺术实践建立起来的。他在俳谐创作实践和俳谐理论两个方面,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闲寂、风雅的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芭蕉生平很关注从理论上指导其弟子进行俳句的创作,但他生前未系统整理和发表过一册俳谐论著,大多数论述都是只言片语,散见于他的随笔、俳文、序跋、评句、书简中,尤其是集中反映在俳谐纪行文《笈小文》上。同时,他殁后由其主要弟子记录在自己的论著中,主要代表作有去来的《去来抄》、土芳的《三册子》等。芭蕉俳论包括俳谐的本质论和美学论,主要内容由“风雅之诚”、“风雅之寂”、“不易流行”三部分构成,是融会贯通,不可分割的。而且三者其本为一,都是建立在“诚”即“真实”俳谐思想上。三者之中,“风雅之诚”是基础,是根本。它不仅将自古以来的“真实”文学美学思想提高到一般艺术的真实性上,而且使这一时期的俳谐获得更高更深刻的艺术性,大大地丰富了俳论的内容,形成当时俳谐的全新理念,成为一个时代的俳谐新趋向。革新俳谐,便成为这一时代文艺思潮的中心。上述《富家食肌肉,丈夫吃菜根,我贫》,就是他的真实论的重要艺术实践。可以说,芭蕉的“风雅之诚”是对人生的深刻思考的结晶,同时贯彻了写实的“诚”的俳谐理念。
作为日本文学传统基本精神的“诚(真实)”,是融贯于各个时代的。芭蕉强调“风雅之诚”正是继承了这种传统的“真实”精神,但他并没有把“诚”精神绝对化,而是与时俱进,提倡“风雅之寂”。这是在禅思想和老庄思想的导向下,在全面参与的关系中,深化“风雅之诚”,从而使“诚”的内涵获得更大的延伸。因此,芭蕉的俳论同时主张“风雅之寂”,强调风雅与禅寂相通,具有孤寂与闲寂的意味。
芭蕉在《笈小文》中强调“风雅乃意味歌之道”,写道:“西行的和歌,宗祇的连歌,雪舟的绘画,利休的茶道,其贯道之物一如也。然风雅者,顺随造化,以四时为友。所见之处,无不是花。所思之处,无不是月。见时无花,等同夷狄。思时无月,类于鸟兽。故应出夷狄,离鸟兽,顺随造化,回归造化。”
从芭蕉这些论述来看,芭蕉俳谐的风雅精神,首先是摆脱一切俗念,“出夷狄,离鸟兽”,回归同一的天地自然,采取静观的态度,以面对四时的雪、月、花等自然风物,乃至与之相关的人生世相。其次,抱着孤寂的心情,以闲寂为乐,即风雅者也。文中所说“顺随造化”、“回归造化”的“造化”,就是“自然”,是“以四时为友”,人与自然的调和。芭蕉认为心灵悟到这一点,一旦进入风雅之境,就具有万般之诗情,才能在创造出“风雅之诚”的同时,也创造出“风雅之寂”来。
换句话说,风雅本身,就是孤寂,就是芭蕉的所谓“俳眼”。从这点出发,以静观自然的心情静观人生,则人生等同于自然,达到物我合一,真实的物·心与纯粹的感情相一致,即入物才能得“物之心”,达到“物我一如”之境而显其真情,这样才能把握物的本情。
然而,自然是随着四季推移而变化的,所以把握自然的本质,不应是眺望原来的自然,而是要将凝视自然所获得的本质认识,还原于原来的自然之上。这样凝视物象所把握的东西,就是“闲寂(さび)”。“闲寂”就成为芭蕉自然观照的根本。“闲寂”是当时流行的美理念,它继古代写实的“真实(まこと)”、“物哀(もののあはれ)”和近古的幽玄“空寂(わび)”之后,而成为近古流行的新的文学理念和美学理念。
上述芭蕉的名句《古池》,就是通过“闲寂”的独特表现力,产生艺术性的风雅美、余情美的。换句话说,“风雅之寂”的精神基础是“禅俳一如”,以禅作用于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精神。芭蕉在旅次以“四时为友”,“顺随造化”,通过对自然观照,自觉四季自然的无常流转,进而感受到“诸行无常”。因此他竭力摆脱身边一切物质的诱惑,以“脑中无一物为贵”,“以旅为道”,以及将大自然作为自己的“精神修炼场”,在俳谐思想中培植“不易流行”的文艺哲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易流行”成为其“闲寂”的思想结构的基石。
芭蕉俳论的“不易流行”是芭蕉风雅观即“风雅之诚”与“风雅之寂”的中核。
关于“不易流行”说,按芭蕉本人的解释是:“万代有不易,一时有变化。究此二者,其本一也。”土芳在《三册子》中按其师的本意作了如下的说明:“师之风雅,有万代不易的一面和一时变化的一面。这两面归根到底可归为一。若不知不易的一面,就不算真正懂得师之俳谐。所谓不易,就是不为新古所左右。这种姿态,与变化流行无关,坚定立足于‘诚’之上。综观代代歌人之歌,代代皆有其变化。且不论其新古,现今看来,与昔日所见不变,甚多令人感动之歌。这首先应理解为不易。另外,事物千变万化,乃自然之理。作风当然也应不断变化。若不变,则只能适应时尚的一时流行,乃因不使其心追求诚也。不使其心追求诚者,就不了解‘诚’之变化。今后不论千变万化,只要是发之追求诚之变化,皆是师之俳谐也。犹如四时之不断运行变化,万物亦更新,俳谐亦同此理也。”
由此观之,“不易”是万古不变的东西,即现象千变万化,然其生命是万古不易的。从文学美学思想来说,也是贯穿于日本文学美学历史长河的“真实(まこと)”之中,这是有其传统的。而“流行”是随时代推移而变化,自然也是随着四季流转而变化的。所以,把握自然的本质,不应是眺望原来的自然,而是以凝视自然所获得的本质认识,还原于原来的自然之上。
芭蕉的结论是:
句,有千载不易之姿,也有一时流行之姿,虽为两端,其根本一也。之所以为一,乃是汲取风雅之诚也。不知不易之句难以立根基。不知流行之句难以立新风。(去来·许六记录,《俳谐问答》)
可以说,芭蕉主张的不易的“诚”与流行的“寂”,正是根基与新风的关系。穷究芭蕉俳论都归为这两者,而这两者又归于同一根源,就是不易的风雅之道,这样,松尾芭蕉从根本上解决了俳句不断革新的理论问题。芭蕉这一俳谐的根本文学理念和美学理念为俳句带来了重大转机,在近古俳谐史、文学史上建立了一座丰碑。
蕉风从理论到实践的形成与发展,松尾芭蕉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不过,这又不仅是芭蕉以个人的力量所能达成的,是通过其弟子的共同劳作,尤其是他的俳论,是通过其主要弟子著书论说,而传承下来,发扬光大的。蕉门弟子凡两千以上(其角《枯尾花》),其中有俳谐史称的“蕉门十哲”,但留传下来十哲的名字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宝井其角、服部岚雪、森川许六、向井去来、各务支考、内藤丈草、杉山杉风、立花北枝、志太野坡、越智越人,这是见诸与谢芜村的画赞《续俳家奇人传》的,也就是由芜村根据自己的标准选定的;一说前六人无异,后四人则为河合曾良、广濑惟然、服部土芳、天野桃邻。享宝十一年(1726)举行的芭蕉33周年忌辰时,陶工一瓶、石田久光为祭祀俳圣芭蕉而创作的“一翁四哲像”,芭蕉像坐其中,其角、去来、岚雪、丈草等四塑像则分列左右,故其后又有“蕉门四哲”之称。这都是后人评说的,许多地方上的杰出俳人,比如凡兆并未列名其中,实际上留下伟大业绩的佼佼者,首先是其角、岚雪、许六、去来、土芳,其次是各务支考、山本荷兮、野泽凡兆、河合乙州、浜田洒堂(珍碛)等。无论对“蕉门十哲”如何评定,他们在蕉风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存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