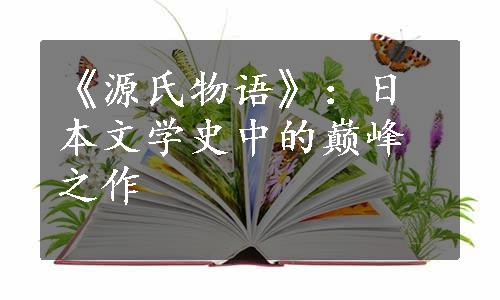
《源氏物语》是日本物语文学的高峰之作,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并继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作者紫式部,本姓藤原,原名不详,一说为香子。紫式部出身中层贵族,其父兼长汉诗与和歌,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研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世家。式部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博览其父收藏的汉籍,特别是白居易的诗文,很有汉学素养,对佛学和音乐、美术、服饰也多有研究,学艺造诣颇深,青春年华已显露出其才学的端倪。式部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26岁的地方官,婚后生育了一女。结婚未满三年,丈夫因染流行疫病而去世。从此芳年守寡,过着孤苦的孀居生活。她对自己人生的不幸深感悲哀,对自己的前途几乎陷于失望,曾作歌多首,吐露了自己力不从心的痛苦、哀伤和绝望的心境。其中一首悲吟道:“我身我心难相应,奈何未达彻悟性。”
其时一条天皇册立太政大臣藤原道长的长女彰子为中宫,道长召紫式部入宫,给彰子讲解《日本书纪》和白居易的诗文。紫式部的才华深得一条天皇和彰子的赏识,因而也受到中宫女官们的妒忌,甚至受到某些女官的揶揄。可是,式部在宫中有机会更多观览宫中藏书和艺术精品,直接接触宫廷的内部生活。当时摄政关白藤原道隆辞世,其子伊周、隆家兄弟被藤原道长以对一条天皇的“不敬罪”而遭流放。道长权倾一时,宫中权力斗争白热化。紫式部对道隆关白家的繁荣与衰败,对道长的专横和宫中争权的内幕,以及对妇女的不幸有了全面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对贵族社会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和衰落的发展趋向也有较深的感受。但她又屈于道长的权威,不得不侍奉彰子,于是作歌一首“凝望水鸟池中游,我身在世如萍浮”,以抒发自己无奈的苦闷的胸臆,还赋一首“独自嗟叹命多舛,身居宫中思绪乱”,流露了自己入宫后紊乱的思绪。她在《紫式部日记》里也不时将她虽身在宫中,却不能融合其中的不安与苦恼表露出来。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紫式部长期在宫廷中生活,经历了同时代妇女的精神磨练,这些孕育了她的文学胚胎,厚积了第一手资料,为她创作《源氏物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源氏物语》一书的创作时间,一般认为是作者紫式部于长保三年(1001)其夫宣孝逝后,孀居生活孤寂,至宽弘二年(1005)入宫任侍讲前这段时间开笔,入宫后续写,于宽弘四五年完成。这部作品产生的时代,是藤原道长摄政下的平安王朝贵族社会的全盛期,表面上一派太平盛世,实际上却充满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皇室内外戚之间、同族之间展开了权力之争。加上地方势力迅速抬头,庄园百姓的反抗,使这些矛盾更加激化,甚至爆发了多次武装暴动。整个社会危机四伏,已经到了盛极而衰的时期。《源氏物语》以这段历史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隐蔽式地描写了当时贵族的政治联姻、权力的腐败与淫逸生活,并以典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和特征。
首先,作者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特别是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的争斗。作品所描写的以地位最高的妃子——弘徽殿女御及其父右大臣为代表的皇室外戚一派政治势力,同以源氏及其岳父左大臣为代表的皇室一派的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正集中反映了这种矛盾和斗争。主人公源氏是桐壶天皇与地位次于女御的妃子——更衣所生的小皇子,母子深得天皇的宠爱。弘徽殿女御出于妒忌,更怕天皇册立源氏为皇太子,于是逼死更衣,打击源氏及其一派,促使天皇将源氏降为臣籍。天皇让位给弘徽殿所生的朱雀,右大臣掌政,源氏一派便完全失势。弘徽殿一派完全得势后,进一步抓住源氏与右大臣的女儿胧月夜偷情的把柄,迫使源氏离开宫廷,并把他流放到须磨、明石地方。后来朝政日非,朱雀天皇身罹重病,为收拾残局才不顾弘徽殿的坚决反对,召源氏回京,恢复他的官爵。冷泉天皇继位以后,知道源氏是他的生父,就倍加礼遇,后源氏官至太政大臣,独揽朝纲。但是,贵族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纷争并没有停息,源氏与左大臣之子围绕为冷泉天皇立后一事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紫式部在书中表白:“作者女流之辈,不敢奢谈天下大事。”所以作品对上述情节的反映,多采用侧写的手法,少有具体深入的描写,然而,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出上层贵族之间的互相倾轧,以排斥异己、政治联姻等手段进行的权力之争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主人公源氏的贬谪晋升、荣辱浮沉都与之密不可分。
在《源氏物语》中,作者以上述社会政治生活为背景,描写源氏的爱情生活,但却不是单纯描写爱情,而是通过描写源氏的恋爱、婚姻,来反映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欢乐、愉悦、哀愁与悲惨的命运。作者笔下的众多妇女形象,有身份高贵的,也有身世低微的,但她们的处境都是一样,不仅成了贵族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成了贵族男人的玩物。小说着墨最多的是源氏及其上下三代人对妇女命运的拿捏。源氏的父皇玩弄了更衣,由于她出身寒微,在宫中备受冷落,最后屈死于权力斗争之中。源氏倚仗自己的权势,糟蹋了不少妇女:半夜闯进地方官夫人空蝉的居室玷污了这个有夫之妇;践踏了出身卑贱的夕颜的爱情,使她郁郁而死;看见继母藤壶貌似自己的母亲,由思慕进而与她发生乱伦关系;闯入家道中落的末摘花的内室调戏她,发现她长相丑陋,又加以奚落。此外,源氏对紫姬、明石姬等许多不同身份的女子,也都大体如此。在后十回里出现的源氏继承人薰君(他名义上是源氏与其妾三公主之子,实际上是三公主与源氏的妻舅之子柏木私通所生)摧残了孤苦伶仃的弱女浮舟,并且与两位女公子有暧昧关系,因怕事情败露,便把她们弃置在荒凉的宇治山庄。在这些故事里,不难看出这些乱伦关系和堕落生活是政治腐败的一种反映,和他们在政治上的衰落有着因果关系。尤其是作者描写了源氏营造的六条院原是被世人誉为琼楼玉宇,源氏逝后“必然被人抛舍,荒废殆尽”,并慨叹“此种人世无常之相,实在伤心惨目”,更证明作者对贵族社会走向崩溃的趋势是有一定预感的。
总之,《源氏物语》现实地反映了时代与历史的潮流,虽也写了源氏等的好色和风流,但也是为了折射与之相伴而产生的矛盾、人心的嬗变、世间的无常、荣华背后的衰落,从内面揭示了这个贵族社会盛极而衰的历史趋势,堪称一幅历史画卷。应该说,这是有深层的历史意义、深邃的文化内涵的。
《源氏物语》在艺术上也是一部有很大成就的作品,它开辟了日本物语文学的新道路,将日本古典写实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全书共54回,近100万字。故事涉及3代,经历70余年,出场人物有名可查者400余人,主要角色也有20~30人,其中多为上层贵族,也有中下层贵族,甚至宫廷侍女、平民百姓。作者将人物描写得细致入微,使其各具鲜明个性,这说明作者深入研究了不同人物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和曲折复杂的内心世界,因而写出来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富有艺术感染力。小说的结构也很有特色。前半部44回以源氏和藤壶、紫姬等为主人公,其中后3回是描写源氏之孙丹穗王子和源氏之妃三公主与柏木私通所生薰君的成长,具有过渡的性质;后半部10回以丹穗王子、薰君和浮舟、大小两位女公子为主人公,铺陈复杂的纠葛和纷繁的事件。它既是一部统一完整的长篇,各章节也可以成相对独立的故事。全书以几个重大事件作为故事发展的关键和转折,有条不紊地通过各种小事件,使故事的发展和高潮的涌现彼此融会,逐步深入揭开贵族社会生活的内幕。
与此同时,作者以她的博学多艺,在书中尽展宫廷春夏秋冬四季的活动和自然景物。日本宫廷的仪式多从中国传入,为适应日本平安朝贵族社会生活而加以洗练化。在《源氏物语》中大量描写了这些宫廷活动,有的她没有参加,是根据文献记载;有的她身历其境,亲自耳闻目睹。在小说故事的转换和内容的展开中,她都巧妙地采用了这些宫廷四季举办的活动情景,以描绘出一个宫廷生活的真实世界和追求贵族人物的真实存在。比如对白马节、踏歌节会、灌佛、佛名会、迎神赛会、赌弓、内宴、花宴、赏月宴、菊花宴、新尝节、大尝节、贺茂节、五节等四季的重要活动都有出色的描绘。尤其是对白马节、踏歌节会和五节的描写非同凡响,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对于四季自然景物的描写,成为四季活动场景描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出现在这些叙事场面中,以增加抒情的艺术效果。而且一年春夏秋冬的各种风物,都是随人的感情变化而有所选择,其中以秋的自然和雪月景物为最多,这是与《源氏物语》以哀愁为主调直接相连的,因为秋天空濛、忧郁、虚无缥缈的景象,最容易抒发人物的无常哀感和无常美感,最能体现其“物哀美”的真髓,同时也可以让人物从这种秋的自然中求得解脱,来摆脱人生的苦恼和悲愁。最典型的是“浮舟”一回的小野草庵明澄的秋月之夜,庭院秋草丛生一节的描写,映衬出此时浮舟栖身宇治的孤苦心境。然而“桥姬”一回则是例外,将薰君与女公子们交际中所展现的人物的风流情怀,尽倾在“夜雾弥漫的朦胧淡月”下,使自然带上人情的或悲苦或喜乐的多种色彩。尤其是在“帚木”一回的“雨夜品评”中描写与源氏等贵族青年男子在景淑舍里品评宫廷女官们的容貌风姿和心理状态时,以岑寂的长长夜雨下庭院残菊颜色斑斓、红叶散乱的颇有情趣的景色,使人联想起古昔的哀情小说,并作歌一首“争妍斗丽百花发,群芳不及常夏花”,以烘托他们的闲情逸趣,制造出一种儒雅风流的氛围。(www.zuozong.com)
在描写雪、月物象上尤其泼洒浓重的笔墨,因为雪、月蕴含一种无常的哀感。开卷的“桐壶”一回,皇上的“徘徊望月,缅怀前尘”,想起弘徽殿女御冷酷对他和他至爱的更衣,吟出“宫中泪眼映秋月,焉能长久居荒野”句,寄托于月来抒发自己的感伤和悲戚情怀。“花散里”一回源氏顿萌厌世之念,与丽景殿女御回思往事时,描写了“缺月升入天空中,树木阴影深沉沉”,来托出源氏对世间万事都感忧恼之情,这些描写使人与月之间产生一种精神的律动。“总角”一回写到与浮舟的命运一样被薰君等置于荒凉宇治山庄的大女公子病逝时的“飞雪蔽天,竟日不息”的场面时,薰君即景赋歌嗟叹“人世无常久难住”,揭示了人生寂寥至极之心,体现了一种“物哀”的洗练的美感。
这些宫廷举办的四季的活动和季节景物的描写,在“末摘花”、“须磨”、“萤”、“铃虫”、“夕雾”、“法事”、“总角”等章回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总之,作者将四季自然和物象,与自己的思想、感情、情绪乃至想像力相协调,表现了自然美、人情美,进而升华为艺术美。它们与上述的“历史画卷”相辅相成,富有更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艺术地展开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四季画卷”,给人更多美的享受。
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结构上,某些章节略显庞杂、冗长,相同的场面描写重复过多,多少有损于作品的艺术完美性。
值得一提的是,《源氏物语》深受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它一方面接受了中国的佛教文化思想的渗透,并以日本本土神道的文化思想作为根基加以吸收、消化与融合;另一方面广泛活用了《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文选》等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引用了它们的原文,将《白氏文集》、《诗经》、《游仙窟》等二十余种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神融贯其中,尤其是吸收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的精神,并把它们结合在故事情节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文学观来看,白居易强调文章是“感于事”、“动于情”而产生的,主张走写实与浪漫结合的道路。紫式部则强调她的《源氏物语》是“写世间真人真事”,“一切物语,都是写人情世态,写种种心理,读物语自然了解世相,了解人的行为和心理,这是读物语的人首先应该考虑的”。紫式部这种文学观,以及根据这一文学观的创作实践,固然源于日本古代文学的“真实”文学思想,但也不能否认她受到白居易的文学观的影响,在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不难发现两者的近似性。
(二)从思想结构来说,白居易的《长恨歌》的思想结构是两重性的,即讽喻与感伤兼而有之。这对于《源氏物语》的思想结构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成为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长恨歌》的讽喻意味表现在对唐明皇的荒淫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种种弊政进行揭露,开首就道明“汉皇重色多倾国”,以预示唐朝盛极而衰的历史发展趋势。《源氏物语》也与这一思想相呼应,通过源氏上下三代人的荒淫生活,以及贵族统治层的权势之争,来揭示贵族社会崩溃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写到源氏从须磨复出,官至太政大臣,独揽朝纲,享尽荣华时,痛切地感到“盛者必衰”的道理。作者不无感叹“这个恶浊可叹的末世……总是越来越坏,越差越远”。《源氏物语》与《长恨歌》的相似,并非偶然的巧合,紫式部是有意识地模仿白居易的《长恨歌》的。
(三)从作品的结构来看,《长恨歌》内容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写唐明皇得杨贵妃后,贪恋女色,荒废朝政,以致引起“安史之乱”;一部分则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唐明皇对死去的杨贵妃的痛苦思念。《源氏物语》也具有类似的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描写桐壶天皇得更衣、复又失去更衣,把酷似更衣的藤壶女御迎入宫中,重新过起重色的生活,不理朝政;一部分则描写桐壶天皇的继承人源氏与众多女性的爱情生活。白居易和紫式部所写的这两部分都是互为因果的两重结构,前者是悲剧之因,后者是悲剧之果。他们都是通过对主人公渔色生活的描述,进一步揭示各自时代宫廷生活的淫糜,来加强对讽喻主题的阐述。所不同的是,白居易是通过唐明皇贪色情节的展开,一步步着重深入揭示由此而引发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即指引发了安禄山渔阳(范阳)起兵叛唐之事,最后导致唐朝走向衰落的结果。而紫式部则通过桐壶天皇及其继承人的好色生活,侧面描写了他们对弘徽殿女御及其父右大臣为代表的外戚一派的软弱无力,最后源氏被迫流放须磨,引起宫廷内部更大的矛盾和争斗,导致平安朝开始走向衰落。从这里人们不难发现白居易笔下的唐朝后宫生活与紫式部笔下的平安朝后宫生活的相同模式,而且他们笔下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也是互为参照的。更确切地说,紫式部是以白居易的《长恨歌》的唐杨的爱情故事作为参照系的。
(四)就人物的塑造来说,《长恨歌》对唐明皇的爱情悲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比如白居易用同情的笔触,写了唐明皇失去杨贵妃之后的思念之情,这样主题思想就转为对唐杨坚贞爱情的歌颂。《源氏物语》描写桐壶天皇、源氏爱情的时候,也反映出紫式部既哀叹贵族的没落,又流露出哀怜的心情。既深切同情妇女的命运,又把源氏写成是个有始有终的庇护者,在一定程度上对源氏表示了同情和肯定。也就是说,白居易和紫式部都深爱其主人公的“风雅”甚或“风流”,其感伤的成分是浓重的。比如,在《源氏物语》中无论写到桐壶天皇丧失更衣,还是源氏丧失最宠爱的紫姬,他们感伤得不堪孤眠的痛苦时,紫式部都直接将《长恨歌》描写唐明皇丧失杨贵妃时的感伤情感,移入自己塑造的人物的心灵世界。最明显的一例是,紫式部写到源氏哀伤紫姬之死时,引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夕殿萤飞思悄然”的诗句,将主人公内心深处荡漾的感伤情调,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源氏物语》借用、引述白居易的诗共计80~90首(句),可见其接受白氏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从《源氏物语》与白居易诗文的比较中,不难看出白居易诗文对《源氏物悟》的影响。川口久雄指出:“紫式部没有停留在模仿《(白氏)文集》的零星词藻,或照搬《文集》诗的体验上,而是继承了《文集》那种(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真正的诗精神,连同消化《史记》的精神,以及特别运用《长恨歌》那种叙事诗形式,将颓废的现实形象化,并加以批判,而且将这种精神具现在自己的作品上。”(《平安朝日本汉文学的研究》(中),第674页,明治书院1982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