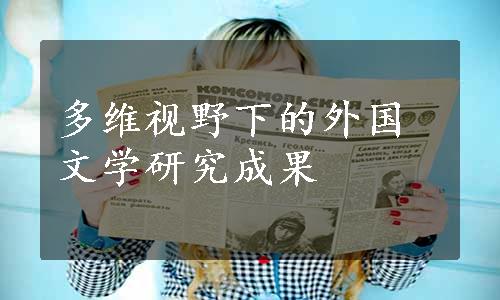
王诺[1]
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于21世纪初,虽然仅仅走过十余年的短短历程,但由于我国生态危机日趋严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类研究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态势,已然成为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显学”。
从研究内容上看,我国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目前有三个主要方面: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生态审美及生态艺术特性研究、生态思想文化维度的研究。其中生态思想文化视域的研究是我国此类研究最突出、成果最多的部分,多数研究者致力于发掘外国文学作品的生态智慧,部分研究则批判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反生态思想,通过外国文学研究寻找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试图为当今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思想资源和经验教训。从研究对象来看,我国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1960年代以来涌现的生态文学的研究;另一类是对古往今来所有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特别是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学名著的研究。后者侧重于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解读、重新评价文学名作,揭示以往被人忽视的生态思想价值和生态美学价值,并对其中的反生态思想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艺术表现展开批评。
我国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成果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其影响不仅辐射到中国文学研究(直接推动了生态批评视角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而且渗透到生态哲学、生态史学、生态经济学乃至整个生态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一些研究者还直接参与了国际学界的生态文学研究,参与国际会议,与国外同行对话、争论,在国外文学研究刊物发表论文,得到国际生态批评界的关注与好评。与此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生态批评还不成熟,其思想基础还没有稳固建立,其基本术语、研究边界、主要原则和主要方法还没有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很多学者还不能明确区分生态批评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相当数量的以生态批评视角的研究或生态批评命名的研究著述严格说来是名不副实的。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这十几年来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做一番梳理,总结其成绩,找出其缺失,汲取其经验与教训。
一、兴起与发展
Ecocriticism这个术语1999年第一次出现在外国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中国学界。当年第4期的《外国文学评论》在动态栏里发表了“司空草”的一则短讯“文学的生态学批评”。作者介绍了几部重要的国外文献,指出这类研究在西方批评界方兴未艾,值得我国学者重视。不过作者将这个词翻译成“生态学批评”。[2]同年,王诺在《外国文学:人学蕴涵的发掘与寻思》(科学出版社1999)一书里用了一章6万字的篇幅探讨了“外国文学里的人与自然”,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生态批评的主要视域——初步梳理了外国文学作品。
200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程虹的专著《寻归荒野》,该书由其博士论文《自然与心灵的交融——美国自然文学的缘起、发展与现状》(2000年)修改而成,作者是国内最早从事美国自然书写研究的学者,虽然她并没有使用“生态批评”或者“生态文学”等术语,但其研究方法和一些观点与此后的生态批评相当近似。同年,我国学者第一次使用“生态批评”这个中文术语——出自王宁选编并主持翻译的《新文学史I》,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论文选包含国际知名的文学研究期刊New Literary History 1999年生态批评专辑的几篇文章,这也是我国学界第一次翻译国外生态批评文献。
2002年,王诺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论文《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首次以论文形式系统评介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与主要成就,同年他还在《国外文学》第2期发表论文《雷切尔·卡森的生态文学成就和生态哲学思想》,此乃我国学界第一篇外国生态文学研究论文。2003年,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专著。作者在这本书里首次界定了“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这个术语,并将其与“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等国外学界的常用术语做了区隔,论述了生态文学的特征、哲学基础和生态思想蕴涵。
自此以后,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著述井喷一般地涌现,研究论文不计其数,博士硕士论文数以百计,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课题多达近百项,主要的研究专书有二十余部,包括: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朱新福:《美国文学中的生态思想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杨素梅、闫吉青:《俄罗斯生态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鲁枢元主编:《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王诺:《生态与心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王晓华:《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
李美华:《英国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
苗福光:《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程虹:《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夏光武:《美国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
周湘鲁:《俄罗斯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
陈茂林:《诗意栖居:亨利·大卫·梭罗的生态批评》,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袁霞:《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
韦清琦:《绿袖子舞起来——对生态批评的阐发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高歌、王诺:《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研究》,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
江山:《德语生态文学》,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
南宫梅芳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谭晶华:《薇拉·凯瑟的生态视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宁梅:《生态批评与文化重建——加里·斯奈德的“地方”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吴琳:《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刘青汉主编:《生态文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薛小惠:《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堪称一部总结性著作,该书作者辨析回答了这一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争论不休、困惑不已的99个重要问题,系统论述了生态批评的特征、对象、任务、方法、优势、局限以及生态文学和生态审美,初步建立了作为生态批评思想基础的生态整体主义理论体系。
此外还有一批相关的国外研究著述被编选翻译引进,主要有:
〔美〕斯科特·斯洛维克:《走出去思考:入世、出世及生态批评的职责》,韦清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www.zuozong.com)
〔美〕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美〕格伦·洛夫:《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胡志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美〕利奥·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马海良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李庆本主编:《国外生态美学读本》,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
以上主要成果有一半以上的作者或译者是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的学者或兼职教授。成立于2004年的厦大生态文学研究团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发挥了引领性作用,这个国内学界首个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汇聚了二十余位生态文学研究者,出版了学界第一套生态文学研究丛书“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七部专著),编撰了第一本国家级生态文学教材(“十一五”规划教材《欧美生态文学》),自2008年起每年在报刊发布国内外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年度动态。
二、优势与特色
与欧美主要国家的生态批评或生态/环境文学研究相比较,我国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首先,我国学者在生态批评理论方面有独特的创新。国外多数生态批评家采用“环境文学”或“自然书写”等术语,而我国多数学者则采用“生态文学”这个术语,一些学者还进一步指出“环境”(environment)一词带有浓重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与生态批评视角的文学研究之基本精神相抵触;而“自然书写”或“自然文学”的外延太小,不能完全涵盖生态文学所要表现、生态批评所要探讨的文学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国很多学者在何为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的指导思想这一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认为生态整体观、生态联系观、生态动态平衡观、生态友好观(即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是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之思想基础,反对将环境主义甚至弱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批评的指导思想。我国学者对美国环境批评家布伊尔有关生态批评第一波、第二波乃至第三波发展的论断提出了质疑和批驳,对英国生态批评家贝特有关生态作家代言自然的论述提出了不同看法;对美国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所倡导的“叙事学术”(narrative scholarship,一译“叙述性学术研究”)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辩证性论述;对“处所”(place)理论展开了不同于美国生态批评家海塞、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和环境批评家布伊尔的论证,坚持从生态的视角而不是人类文化的视角论述生态处所观,揭示处所性(placeness)、处所依附(place-attachment)、处所感(sense of splace)、处所剥夺(place-deprivation)、非处所(non-place)与生态危机、人的异化、生态的身份认同(ecological identity)的关系。
其次,我国多数学者十分重视通过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发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反思人类文明,批判反生态的思想文化,传播生态思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应当说,这也是拉美、南亚、南部非洲等地区生态批评的主导倾向,也是欧美早期生态文学和早期生态批评的主导倾向;然而,在1990年代到21世纪初这十几年里,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少生态批评家则把注意力转向探索人的自然审美和人与自然交流的心理机制,转向人的诗意生存,主张减弱甚至超越生态批判。与之相比较,我国的生态文学研究者有着更为强烈的生态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特别是我国学者很多人都明确主张文学研究要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贡献,明确主张文学研究要介入现实,要为本民族和全人类摆脱生态危机探索出路,这种建设性——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在国际生态批评界堪称独特。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从2005年开始,欧美的生态批评和环境批评又呈现出向生态批判和社会批判回归的态势,越来越多的生态批评家关注毒物污染、反生态的都市文化和消费文化、生态非正义与环境非正义、消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反生态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并与中国等第三世界生态批评家形成了呼应。
第三,我国学者十分重视探索独特的生态审美与生态艺术表现,重视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理论的建构,并对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截然不同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进行了初步探讨,论证了生态审美的自然性、整体性、交融性和主体间性等原则与方式。相比之下,欧美生态批评家的多数著述都局限于思想蕴涵方面,对于有没有或者有哪些堪称生态的审美方式和艺术表现手法很少关注。而且,他们与生态美学家的交流合作也较少,分别在不同的学术圈子活动,在不同学科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而我国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不仅从一开始就与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研究者一起探讨问题,而且还受到较早研究生态问题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的深刻影响,影响最大的生态美学与文艺学著作有:徐恒醇的《生态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陈望衡编选并主持翻译的“环境美学译丛”(这是我国第一套环境美学译丛,翻译了国外环境美学五部代表性著作,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文学与生态学》(学林出版社,2011年)和《陶渊明的幽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等。我国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研究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生态批评研究者有相同的立场,他们多数人都主张“生态美学”而非“环境美学”,倡导生态的整体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重视对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的挖掘与批判。
与其他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批评流派相比较,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有其重要的、独特的、不可替代、与当今生态语境和社会语境密切相关的优势。这类研究最大的贡献,是对地球生态的贡献,是对大自然的贡献,是对缓解乃至消除生态危机的贡献。文学和批评的功用绝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内部,它还可以通过人而作用于非人类,作用于整个世界。这就是文学的自然功用——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理论所忽视的功用。从文学的自然功用的角度来看,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的文学研究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原因之一,因而批评的生态转向也应当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之一;如果认可生态危机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最大的危机,那么生态批评就是当代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研究最紧迫的任务。生态批评对于人类生态的、永续的生存和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其重要贡献——启迪和普及生态意识,倡导和鼓励生态的生存方式,挖掘和批判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的存在有了新的意义。生态批评所倡导的就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它促使人们认识到:人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自我(小我),也不仅仅是为了全人类(大我),还要为了这个地球上所有生命和非生命存在物的生态共生(超我)。人类不仅仅需要超越极端个人主义,超越性别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为普天下人的幸福做出贡献;而且还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谐、稳定与永续存在做出贡献。
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在2005年指出,当今西方国家文学研究界的情况是:多数批评家都产生了“我怎样才能跟上这个新工作(指生态批评和环境批评——引者注)的步伐”[3]的紧迫感。这种发展态势值得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高度重视。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是在生态危机逼迫下和文学研究内部规律的作用下兴起和发展的;它前所未有地大大强化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自然功能,即有助于保护自然、有助于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维持其永续存在的功能;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大大强化了外国文学研究对人类走出生态危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变革反生态的传统文明并创建新的生态文明的社会功能;它为外国文学研究的均衡、健康发展带来了整体上说是全新的理念——生态主义思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理念,提供了新视角,开拓了新领域,填补了老空白,生发出新课题,输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三、缺陷与未来发展
在国际生态批评的大背景下考察我国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既可以清晰地看出其特色与优势;亦可以明确它的缺陷和未来努力的方向。除了参考文献不够全面、作家与文本研究不够深入细致、具有一定程度的唯洋是从倾向、独立创新和理论建构缺乏之外,还有几个特别明显的不足;而这类研究未来能否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弥补这些不足。
首先是缺乏对国外生态批评及其支撑思想的辨析。生态批评是新兴的、尚不成熟的、尚未形成完善理论体系的、尚未达成基本共识的文学研究流派或走向,复杂多样、众说纷纭是其突出特点。因此,对国外生态批评及其依托理论的借鉴一定要建立在充分辨析的基础之上。然而,目前存在的现象却是:对这一领域的国外著述缺乏整体把握和对比分析,不善于发现国外学者的误区和缺陷,不善于发现国外不同著述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往往是抓住几本外文著作就当成不容置疑的依据,不加辨析论证就选择和坚持国外学者的观点与术语,进而又将其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依据。很多中国学者混用“环境”与“生态”、“环境批评”与“生态批评”,未能弄清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根本差异,这与西方主流生态批评家混淆“生态”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我国今后的生态批评视角之外国文学研究首先需要在核心思想上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选择与“生态”的本意相匹配、与生态文明诉求相一致的生态主义思想,建立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自洽性的理论体系,确立明晰的生态思想和生态审美评价标准,与环境主义指导下的环境批评严格区隔开来,不再盲目地、没有主见地追随西方主流生态批评家,把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混为一谈,不再在特定的研究中传达并倡导相互矛盾的生态观与环境观。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各有优势也各有缺憾,两类批评虽然都与自然有关,但其出发点、最终诉求和路径选择完全不同。从学理上说,最佳的态势应当是在划清界限的前提下共存和竞争,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而不是把思想依据绝不相容的二者混在一起,将双方的精力浪费在无止境又达不成共识的争辩之中,使得双方都难以形成自洽的评价体系,从而制约了双方的健康发展。既然选择了生态批评视角,就应当展开真正堪称生态批评的研究,就应当以真正具有生态主义倾向的理论和研究作为主要支撑资源,同时广泛借鉴包括环境批评在内的其他研究,汲取其中与生态思想不相矛盾的、有益于生态批评的营养。同理,既然选择了环境批评视角,既然确信环境主义真的能够解决当今人类的环境危机,就应当自信地坚持环境论和环境批评评价标准,并以环境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自我命名;而不是人与亦云地跟着“生态热”跑,也自命为生态批评,打着“生态”的旗号做着“非生态”甚至“反生态”的环境研究。
其次是缺乏对反生态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学术批判。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要关注传统作品中的反生态思想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对人类反生态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比如《浮士德》、《鲁滨孙漂流记》、《白鲸》等,揭示这类作品对人类走上与自然脱离和对立的道路所发挥的历史作用。然而,目前的情况则是:大部分此类研究都在寻找和阐释作品的生态意义,批判性的研究却很少见。生态批评并不拒绝历史地、发展地看待传统文学的非生态和反生态的内容。它充分理解反生态作品产生的原因和产生的语境。人类在20世纪后半叶之前的几千年发展过程中,虽然一直在对自然进行开发、控制和改造,但总体上看,并没有突破生态承载限度,还没有造成生态系统的全面恶化,还没有出现生态危机和生命供给系统全面崩溃的征兆。因此,生态批评并不是要以当代的生态思想苛求过去的作家和作品,也不是要脱离作品产生的语境而苛责它们。但是,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对于“历史地看文学”也不能片面理解——仅仅将“历史地看”理解为放到特定历史语境中去看,仅仅考虑文学现象的时代合理性和时代必然性;却忘记了“历史地看”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考察视域,那就是放到整个历史进程中看,不能将文学现象与整个文学发展史乃至文明发展史割裂开来。简言之,所谓历史的考察,既要有特定历史阶段的考察,也要有置于整个历史进程中的考察。具体来说,对待非生态和反生态的文学现象,“历史地看”应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不脱离时代语境、客观地讨论作品的反生态性,深入理解文本的非生态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在其产生时代的合理性;二是要分析和评价该作品在人类反生态的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反思人类的文明进程究竟在哪些地方出了错,判断特定的作家作品在那些错误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生态视角的传统文学重审,虽然不是以当代的生态思想苛求过去的作家和作品,但也不能以特定时代的必然性为理由,否定过去的作家作品对人类文明走上非生态的道路所发挥的历史性的负面作用。
此外,还要特别重视对当代反生态的文学作品的批判。生态批评从一开始就是介入性、批判性很强的文学研究,这是因为促使它产生的最大驱力并非来自学术领域,而来自生态危机的逼迫和文学研究者强烈的生态使命及社会使命。因此,生态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绝不能在当代反生态文学面前沉默失语。美国作家克赖顿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影响极坏的反生态小说《恐惧状态》,将生态保护者描写成散布恐惧的人,伪科学大骗局的炮制者,甚至是自私、无知、傲慢、欺诈和不择手段的环境恐怖主义分子。作者无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严谨的科学家通过大规模、认真负责的研究所达成的科学共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直接相关,无视这一事实:此结论“来自大量世界顶尖级科学研究,经过了极为细致的审核并备有详细的证明文件,是目前所研究过的最大、最长、最昂贵、最国际化、学科跨度最大、最彻底的科学议题”[4];却采用少部分反对气候变化说的科学家的说法,并且很不科学地使用人们的一些日常感受来抨击全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污蔑生态保护者的行动。作品中的人物说:“每一次下雪人们都会忘记所有关于全球变暖的说法,或者认为暖一点结果也许挺好。在雪地里步履艰难地走一遭,人们会希望全球变暖一点儿。”作品这么描写,有意无意地用局部的、一时的寒冷偷换了气候变化研究的结论——全球总体气温升高、两极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海洋洋流平衡被打破、极端天气频发等,进而又以非科学的感受否认科学研究的结论。作品里的一席话透露出了作者这么描写的内在秘密:“你所需要做的……就是组织好这些信息,于是不管是哪种天气出现,总是可以证明你的预言的。”[5]大千世界,变化万端,谁都可以找出一些表面上与自然大趋势不一致的、局部和一时的具体事件和感受。不经过长期严肃的科学研究,难以发现其变化的总体趋势。作为一个应当对自然、对人类负责任的作家,用局部的情况和个人的感受误导读者,麻痹读者,使之丧失对气候变化的警惕,其社会良知和生态良心何在?然而,就是这个极不负责任的作者,这个写出了被气候学家称为“从科学角度看完全是垃圾”的小说的克赖顿,居然还被同样反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美国参议员因霍夫邀请到参议院作证反对为气候变化立法,而且还对美国国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居然还获得了美国石油地质家协会颁发的新闻奖!石油地质协会给文学作品颁奖,给小说颁发“新闻奖”,荒唐得意味深长!
生态批评的介入性甚至进攻性未能充分显示,生态批评对文学创作乃至社会文化的影响还不够强大,与反生态文学批判的缺乏,特别是对当代反生态文学的批判不足,有直接的关系。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未来应当特别重视对反生态文艺作品、反生态的文学批评著作展开思想性和学理性批判,揭示其巨大的危害性。唯如此,才能更快地趋近它的终极目标——普及生态意识、推动生态文明、消除生态危机、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再次是对传统文学生态蕴涵的阐释表现出孤立化、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孤立化的主要表现是脱离传统作品的创作语境和文本语境,孤立地认知和反思作品中的生态思想,进而又脱离时代特殊性地讨论其当代意义——对构建生态文明的借鉴意义。许多人津津乐道于古代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生态思想,却很少具体分析其历史局限性,忽视其在古代社会的适用性和在当代社会的适用性之间的巨大差异;更多的人将传统文本的部分描写孤立出来,抽取——甚至是断章取义地抽取文本片段甚至语句,将其与文本语境(上下文关系)割裂开来讨论其中的意义。这些常见的错误做法很容易扭曲文本含义,诱导人们孤立地、片面地理解传统文学的生态思想,也难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其普适意义。
比如,人类各个文化圈在原始时代都产生了许多有关敬畏自然、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学作品。埃及神话、希腊神话、印度神话、美洲印第安神话、大洋洲神话和非洲布须曼神话当中,都有许多这类故事。其中所流露出来的自然观和生态的生存观,表面上看似乎与当今的生态思想主张十分相似。对于这样的作品,不能满足于其思想与今日生态思想在表面上的相似,不能将其与产生语境割裂开来,直接地、不加分析地古为今用;而应当结合原始时代人与自然的实际关系、结合当时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状态来思考它,特别需要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作品产生于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意识尚未确立的时代和人的能动性尚未充分开发的时代,这些生态智慧的出现是被动的、无奈的,不是生发于人的主动意愿,也不是建立在人对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整体特性的认知把握之基础上的,它背后支撑的不是生态责任和生态伦理,不是人主体对自然物主体真正的、平等的尊重。当今生态批评的语境已完全不同于原始时代。当今人类的主体性高度张扬,张扬到了虚妄的程度;凭借科技的巨大发展,当今人类的能力高度强化,不仅可以保证为人类越来越奢侈的生活而攫取甚至榨干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不仅可以保证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征服、控制和改造自然,而且还完全能够,并且正在迅速趋向于彻底摧毁自然。只有充分考虑了作品产生的语境和我们当今的言说语境,才可能客观而不夸大地探讨传统生态文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当代人接受,实事求是地分析它们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多大程度的借鉴意义。原始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绝不同于当代人所面临的生态困境,原始人类的生态理想绝不同于当代人的生态理想,原始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途径也绝不同于当代人在更高的阶梯上重新达至与自然和谐的途径。原始人用附魅的方式激发人对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当代人对自然的爱与责任义务,主要不应建立在想象、幻想、附魅、再神化之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对自然的准确认知、对自然规律的恰当把握、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性超越和价值论超越、对生态责任和生态伦理的理性恪守之基础上。去魅—复魅理论对于以感性力量和形象思维见长的文学创作来说有其有限的价值,但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生态哲学观和实践论,则不仅不具备可行性,而且还有严重的误导性。我国学者对这类外来理论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批判借鉴的态度。
片面化的主要表现是忽视作品思想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片面地认识、思考和评价传统文学作品的生态思想。对于这一点,斯洛维克在与中国作者进行学术对话时做了特别强调:“要防止突出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难以避免、但又必须努力避免的倾向。生态视角的重新解读和评价,目的是丰富传统文学的生态含义或揭示传统文学的生态局限,但绝对不是以一个新的亮点掩盖原来的亮点。”[6]孤立化和片面化倾向不仅表现在认识具体作家作品上,还表现在对生态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基本走向的整体把握及其研究方法上。迄今为止,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片面地集中在对生态文学或者具有生态蕴涵的文学这一支流上,并且往往割裂了主流文学的影响,孤立地考察支流。这样的考察和描述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存在着两条平行的、互不相干的文学发展线索。因此生态视角的文学重审,最好能将非生态的主流文学与生态的支流文学结合起来作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考察,同时重视这两类文学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主流文学对生态文学的影响和生态文学对主流文学的挑战。
最后是一些学者未能清楚认识到生态批评的限度。生态批评不是无边的,不是万能的,生态批评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应当严格限制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思想(包括生态审美思想)的范围内。“生态的”这一限定语决定了生态批评不是一般的文学批评,更不是所有的文学批评;它只是文学批评的一部分,有其特定的视域和目的。然而在当今国内外生态批评界,却有不少自称为生态批评的著述超出了其应有的范围,偏离其应有的目的。比如,在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讨论文学作品里的环境正义之时,有些研究最后的落脚点不是如何通过促进环境正义而有效地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不是如何消除生态危机,不是如何建设生态文明;而变成如何争取与生态有关的人间正义,争取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公平,其重心已经从自然转向了人类、从生态转向了社会。这样的“生态批评”已经越界了,异变为借生态说社会、说人类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了。生态批评家既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探讨文学与生态、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根本目标,就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研究,不断地扪心自问:我到底是要为拯救地球和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友好关系而批评呢,还是要为了争取社会公平公正而批评呢?虽然这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联,但侧重点和目标的差异将决定研究和批评之属性的不同——是生态批评还是社会批评。追问目的是必要的,特别是在认识到各种批评流派的关联之后,更需要明确每一种批评的目的何在。基本目的和主要诉求上的辨析,是将特定的批评进行学理性归类的必需。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的目的完全不同,虽然无论出于哪一种目的都有推动整个文学批评发展的价值。
同理,在讨论所谓生态女性主义的时候,也需要扪心自问:到底是为人(女人)而批评,还是为自然而批评?布伊尔就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观念的出发点——性别差异的重要性,一般来看,与深层生态学在诸如‘自然’或者‘人’或者‘人类’方面做整体主义思考之倾向不一致,与强调通过认同自然来实现自我认同的观念也不一致”。[7]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确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有一些相似的对应(比如人类征服、蹂躏、占有、贬低自然与男人征服、蹂躏、占有、贬低女人),生态批评不仅为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新的参照,拓宽了女性批评的视野,而且其整体观、和谐观、相互依存观还有助于女性批评走出困境,走出源自女性的性别对立倾向、来自女性的文学文本片面解读、源于女性的性别偏见以及无法彻底摆脱绵延数千年的男权话语等困境,走向追求相互依存的、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所谓“后女性主义”新阶段。因此,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交叉影响是必然的。但是,交叉并不意味着交融,并不意味着两者任何一方主体性的消解,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合二为一——一方吃掉另一方。为了双方都能在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与核心特征的前提下共生共荣,需要仔细辨析所谓生态女性主义的目的,不能仅仅因为它自称“生态”、涉及生态就简单地将其研究归类于生态批评;也不能仅仅因为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有一些相似之处就简单地将其归属于女性主义。需要从学理上确定:究竟是从女性的角度探讨导致生态危机的社会原因、思想文化根源,从而丰富强化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推动生态批评的发展,进而为缓解人与自然的对立、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做出贡献呢;还是为了从更广的范围、更新的角度,结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生态危机,来进一步探讨人类社会压抑女性的思想、文化、传统、制度,从而更加推崇女性主义,更好地弘扬女性意识,更有效地凸显女性主义批评的价值呢?如果是前者,可以说那是一种生态批评,具有女性主义特色的生态批评(简称女性主义的生态批评,中心词是生态批评);如果是后者,则要说那仍然是一种女性主义批评,结合了生态批评某些观念的女性主义批评(简称生态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心词是女性主义批评)。在“生态”成为学术和社会热词和时髦词的当下,这种学理性辨析是必要的。划清了这一界限,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方能都明确自己在做什么,要什么,为的是什么。而对于真心致力生态批评视角的文学研究的学者和学术著述,有理由要求其不能逾越关乎生态批评本质属性的界限,不能重心旁落。
由此看来,明确生态批评视角的文学研究之边界,还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它的骄妄,防止它的无边化;也是为了保持它的独立性、独特性和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文化决裂的彻底性,为了保持它的生态思想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诉求的唯一性。生态批评彻底的反人类中心和倡导生态整体价值,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人类文学批评的主流。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领域,生态批评家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生态批评在当今的崛起和风光,主要是因为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促使人们不得不关注与生态相关的生态思潮,而并非多数人都愿意接受生态思想,更不是生态批评已经取得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产生了多么了不起的影响。人类的文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人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由人创作的艺术性的人学。无论是从创作者和批评者的本性,还是从文学及其理论数千年的发展和积淀来看,文学和批评主要关注人、关注人类社会,主要从人的价值和人的利益之角度考虑问题,都是有充分理由和必然性的,更何况生态意识迄今为止还没有成为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文人)的共识,生态的价值还没有成为人类的普适价值。
因此,生态批评在很长时间里不仅不会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而且还必须与作为主流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批评和谐相处,共生共存。在拓开文学研究新领域的同时,生态批评并不否认也不可能否认文学研究其他领域、其他流派、其他方法的重要性,并不想也不能取代其他的文学批评。生态批评倡导的是生态整体内部的多元共生,绝对不是一元独大,也不是二元对立。因此要充分尊重和理解非生态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并把自己的领域严格限定在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范围内。生态批评只是希望向越来越多的人证明:生态问题在当今极其重要,重要到关乎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存亡和命运,文学家和批评家可以也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发出声音,可以也应当为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做出贡献。
注解:
[1] 王诺,厦门大学教授。
[2] 司空草:《文学的生态学批评》,载《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第134—135页。
[3] Lawrence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1.
[4]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王玮沁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5] Michael Crichton, State of Fear.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4, pp. 295, 314.
[6] 王诺、斯洛维克、王俊 :《我们绝对不可等待》,载《读书》,2006年第11期,第118页。
:《我们绝对不可等待》,载《读书》,2006年第11期,第118页。
[7] Lawrence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10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