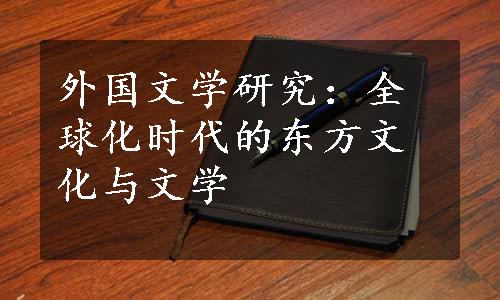
麦永雄[1]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数字化,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各种既有的文化板块和学术范式进入了全面转型。对人类文明或文化体系作粗线条的二元划分,如传统的东西方分野,已显示出许多弊端。因此,在进行东方研究时,尤其需要一种宏观与微观、历史与逻辑、常数与变量相结合的辩证学术眼光。从全球化宏观视野审视东方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前景,是一项具有挑战性意义的研究课题。
第一节 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审视中国东方研究的三重视野
当我们面对当代西方文艺美学的全球“理论旅行”和东方诗学的“失语症”的世界诗学形态时,中国东方文学界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以跨语境的当代学术意识为基础,以西方诗学为参照,重视以东方理论话语探索与阐发东方文学作品,让古代东方文艺思想的智慧焕发青春并且进行理论反思及重构。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跨语境框架中,我们可以从比较诗学的三重视野[2]审视中国东方学的梳理与建构问题:其一是内文化视野(intracultural perspective),强调从东方文化内部探讨以东方理论话语研究东方文学如日本俳句、印度文艺作品的理论与实践;其二是交叉文化视野(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重视东西方之间文艺思想互为参照的学术意识,旨在克服文化偏至的障碍,破除西方“东方学”理论概念存在的“规训”与“学科”的纠结;其三是跨文化视野(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寻求一种新型的、包容差异的宏阔视界,以东方文学史论为例,探讨东方学的“轨迹”和未来发展定位。
一、内文化视野:以东方理论话语研究东方文学
内文化视野的特征是:强调探讨自身文化内部传统嬗变的根由与模式,而不与其他传统进行明确的比较,由此,以东方理论话语研究东方文学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试以日本与印度为个案予以阐发。
1.日本审美文化范畴与俳句阐释
日本俳句的阐发是以东方理论话语研究东方文学的一个佳例,同时也是一种富于东方韵味的国际性的文化与文学传播现象。近代以来西风东渐,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开国门,全盘西化。当代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不断地提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英文的“俳句”(Haiku)一词就已经流传至西方,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仿照俳句形式以本国语言写成的“俳句-Haiku”文学,在各不同国家,以不同语言被吟咏也快近一百年。二次大战后,随着日本的政治、经济复苏,国际上“俳句”文化的广为流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甚至出现“世界俳句协会”(World Haiku Association)。[3]欧美人士不乏俳句爱好者和相关专门网站,如http://www.haiku.com网页就是一种电子传媒系统,具有可让人自由撰写英语俳句的电子墙,俳句爱好者可以提交自己创作的俳句作品“上墙”并且进行交流。众所周知,美国印象派诗人庞德名诗《在地铁车站》深受中国诗词与日本俳句的影响。法国著名文论家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1970年)以自己访日的观感写成,将俳句视为一种比较文化符号,认为日本的符号系统与法国的符号系统截然不同。俳句精确、纯净、亲近、易懂,反西方式的描写,赏心悦目,性质奇异,唤醒欲望,让感觉留痕,擅长于符号叠加、语言瞬间的休止,以无声的断裂建立起禅悟与俳句简洁、空灵的形式关系,“以文笔之简洁而臻于完美境界,以文字之素朴而达于深邃意境”。[4]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作家马悦然《俳句一百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是他为数不多、直接用中文写作的诗集。以“夹杂了四川方言和现代汉语”的酒后戏言,记录了他在中国游历的感悟。在他看来,俳句“最适合捕捉举杯陶然时偶然涌出来的妙句”。[5]当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注意到日本俳句更符合东方的光滑空间、多孔空间的特征,而不是西方条纹空间的特征,其原则上要求特定的标示——表示大自然四季征候的“季语”。
但是,俳句毕竟是东方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的结晶,因此,在学理上需要从东方理论话语对此进行了解与阐发。作为世界诗坛中最短小精悍的诗体,俳句具有两大艺术原则:其一是17音,3行,5-7-5句调;其二是要有季题(季语)。俳句的审美旨趣在于禅悟与留白。借用德勒兹论东方美学的观点,日本俳句具有骨架空间与呼吸空间,它的艺术形式原则与留白是其骨架,禅悟审美则是其呼吸空间,体现出生命的律动。最短小精悍的诗歌形式中蕴涵丰赡、秘响旁通、伏采潜发。吕元明教授《日本文学史》曾经论述日本十大古典美学范畴:真言、哀怜、物哀(怜)、艳(情)、寂(空寂)、幽玄、余情、有心、意气、可笑。尽管这些范畴的划分与界说未必完善,但是,却难能可贵地赋予了我们一种平台与思路,由此可以探索俳句之堂奥。例如日本审美范畴“幽玄”、“寂”(空寂)与俳句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幽玄——源出于中国道家的老、庄精神,重视冷寂、神秘、深奥、纯正的艺术美,包括高雅美、深奥美、悠长美三种境界。寂(空寂)——寂是以闲寂、澹泊为基调的艺术论,融合了禅宗意趣。主要流行于室町时代(1392—1600年)和江户时期(1600—1868年)。室町时代乃日本禅宗文化时代,“寂”在日本俳圣松尾芭蕉(1644—1694年)“闲寂风雅”的诗歌风格中得到最典型的体现,可视之为芭蕉最基本的文艺审美观。此外,在高校东方文学教学中,适当引介日本古典美学范畴与俳句知识能够消除异质文化和古典文学的隔膜,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理论意识与文学素质。
2.印度味论诗学与文艺作品的理论阐释
中国学界的外国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大多通过译文的媒介进行,尤其是东方文学与文论的研究,因国家、地区、语种较欧美更为复杂多样而凸显第二手语言媒介的性质。在目前这种语境中,东方研究领域从第一手语言入手开展文论与文学研究的一些成果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在东方文论的理论话语维度中,有一批研究成果作出了较好的但仍然可能是筚路蓝缕的工作,如吕元明的《日本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黄宝生的《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叶渭渠的《日本文学思潮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倪培耕的《印度味论诗学》(漓江出版社,1997年);以及曹顺庆借助国内东方研究领域学者力量主编的《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等。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学术资源仍然显得非常匮乏且稍显陈旧,与建构中国学术界“东方学”的伟大使命的要求,仍然有较大的距离。
印度味论诗学在世界文论中具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源远流长的印度诗学有三千年的发展史,它与西方诗学、中国诗学一道构成了世界文化中三大成熟的诗学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印度文论也开始进入欧美文论典籍,如雷奇(V.B.Leitch)总主编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精选从古希腊圣哲至今一系列重要的文艺思想家的代表性文论,2010年版甚至收入印度学者和中国美学家李泽厚的文论[6],从多个侧面体现了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当代理论形态。
印度古典诗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其核心精髓是味论。婆罗多牟尼的《舞论》在印度有如亚里士多德《诗学》在西方文艺思想的地位。以印度味论诗学对印度文艺作品进行理论阐释,是一种耐人寻味且富于学术价值的文学批评实践。印度古典味论诗学的分类(范畴)源于印度舞台艺术的理论总结,它将文艺的感情因素分为多种类型的“味”(Rasa),同时与“情”(Bhava)紧密相关。重要的(情)味包括:八“味”——艳情味、滑稽味、悲悯味、暴戾味、英勇味、恐怖味、厌恶味和奇异味(若加上平静味和慈爱味则为十味);与八味相应的八“常情”(基本感情):爱、笑、悲、怒、勇、惧、厌和惊;以及八“真情”和33种“不定情”。[7]这些古典味论诗学的类型和观念构成了印度民族特殊的审美心理定式,是从东方文化语境理解与阐发东方文学内涵与特征的重要理论话语。
印度味论诗学与《罗摩衍那》——在印度味论诗学的视域中,著名史诗《罗摩衍那》是以悲悯情味为基调的作品,兼具艳情味与英勇味。“悲悯”味是由困苦、灾难、杀戮、监禁以及与所爱之人分离造成的。艳情味(因常情“欢爱”而生,以男女为因,以最好的青春(优美的少女)为本,“欢爱与相思”(会合与分离)是其两大基础)。贯串《罗摩衍那》始终的正是这种悲悯味兼艳情味:蚁蛭仙人以同情被射杀的麻鹬而揭开史诗的序幕;罗摩被放逐森林,十车王忧愤而死,悉多被劫,在魔王的淫威下惨遭折磨,都充满凄楚感伤的情调;罗摩执著地寻找悉多,四处奔走,不断地向山川草木、飞禽走兽打听爱妻的下落,使“悲悯”情味达到了高潮。英勇味则集中反映在达磨对非达磨斗争中。
印度味论诗学与迦梨陀娑——迦梨陀娑(Kǎlidāsɑ,约生活于4至5世纪)的代表作抒情长诗《云使》(印度小神仙药叉因怠忽职守被主人大财神俱毗罗贬谪到南方山中,远离家乡与爱妻,独居一年,倍受相思之情的煎熬,托雨云捎去他对妻子的思念)和诗剧《沙恭达罗》(林中相会、结下姻缘、触怒大仙、中下咒言、国王失忆、夫妻离散、戒指重现、一家团圆)以缠绵悱恻的相思和爱情为中心,优雅地表达了印度古典文论中的“艳情味”,堪为东方古典美的标本,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印度文化与文学在世界文明中自成体系,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借助印度味论诗学和《薄伽梵歌》的理论话语,尝试对当代印度宝莱坞电影《阿育王》进行论析。电影《阿育王》宛如一扇窗口,凝聚了印度社会历史,积淀了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只要你观赏过该影片,就可以感到,若以味论诗学加以观照,阿育王形象可谓八“味”纷呈,纠结着艳情味、滑稽味、悲悯味、暴戾味、英勇味、恐怖味、厌恶味和奇异味。其中反复渲染的是艳情味,阿育王与公主荡气回肠的情节较为成功,但通过宝莱坞惯常的“载歌载舞”形式反复表达,几乎让中国观众感到冗长难忍。电影最终渲染极具暴戾味、英勇味的楞伽大战,以阿育王皈依佛教的悲悯味收束,让其回归达磨(正法),精神升华。
二、交叉文化视野:“东方学”的理论纠结及其语境转化
交叉文化视野的特征是:重视异质文化之间互为参照的学术视野,旨在克服文化偏至的障碍。由此,有助于破除西方“东方学”理论概念存在的“规训”与“学科”的纠结,反思“东方学”如何从西方后殖民批评语境转换到中国学术语境的一系列问题。
印度文艺理论话语的化身说似乎也可以用来阐释阿育王的形象,而且与西方历史哲学的循环观及西方文论的原型批评模式在学理上有文心相通之境,能够丰富当代文艺理论形态。印度《本生经》与希腊伊索寓言并称的古代世界寓言文学的宝典,叙述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经过的无数次轮回转生——国王、王子、婆罗门、商人、妇人、大象、猴子、鹿等等,每次转生皆成为行善立德的故事,寓有化身说的叙事学蕴涵。印度三大主神之一的毗湿奴(Vishnu),多次化身降凡显圣,十化身中包括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摩诃婆罗多》中阿周那王子的御者和军师“黑天”大神,甚至佛陀释迦牟尼,那么,同理,阿育王似乎也应该可以视为毗湿奴的化身。另外一个依据是欧美文论中的原型论的学理性:以加拿大国际学者诺斯罗普·弗莱为代表的“原型批评”理论模式同样基于“循环论”,其逻辑起点是将繁复多姿的文学艺术视为神话的“置换变形”(displacement),而“原型”是文学艺术中反复出现并且引发文化语义联想的要素,因此,后世文艺作品的主人公不过是神的不同面具而已。以此观照电影《阿育王》,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场景和题旨重现了印度两大史诗的原型,如美丽善良的戴维舍身挡住阿育王射杀小鸟的情境,不禁令人联想《罗摩衍那》蚁蛭仙人以同情被射杀的麻鹬而揭开史诗序幕的典故。《阿育王》结局宏大而惨烈的战场,犹如《摩诃婆罗多》之末的俱卢大战。坎贝尔《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1949)作为西方神话学的经典,揭示了原型英雄的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文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艺术及流行文化等不同蕴涵。从跨语境诗学维度思考,西方原型批评理论与印度文学、叙事学的化身说(如佛本生故事,文学形象毗湿奴——罗摩——黑天——阿育王……),都从不同侧面支持这种以历史哲学的循环观为特征的神话—诗性思维模式,是在很多方面可以交叠互补的文艺思想资源。
以交叉文化视野审视赛义德的“东方学”,可以关注更多的理论话语及其纠结,进而丰富问题框架。赛义德东方学的影响源主要是福柯的权力话语与新历史主义,以及葛兰西文化霸权论,具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美学的意蕴。其核心题旨是一种悖论式的理论纠结:东方不是东方!在福柯哲学的意义上,东方学既是一门“学科”,同时也是一种“规训”(Surveiller/Discipline)。需要指出的是,域外“东方学”的学术资源不限于赛义德,且确实有一些侧重从学科的维度力图客观科学地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与成果。“赛义德并不是第一个论述东方主义的学者,其对东方主义的阐述,也非最好。在赛义德之前,提巴威(A.L.Tibawi)、阿拉塔斯(S.H.Alatas)、阿卜杜勒-马利克(Anouar Abdel Malek)、贾伊特(Hichem Djait)、阿卜都拉·拉鲁伊(Abdullah Laroui)、阿萨德(Talal Asad)、潘尼迦(K.M.Panikkar)、撒帕尔(Ramila Thapar)等学者对东方主义有不同的论述”。[8]但从影响力来说,赛义德“东方学”仍然是我们讨论中国“东方学”问题的最重要的参照。易言之,西方学术语境中的“东方学”理论概念存在着“规训”与“学科”的纠结,凸显的是福柯式的“规训”和赛义德揭示的地理想象空间!我们需要质疑:中国是否有性质类同的“西方学”?答案是否定的。而一旦我们把目光从后殖民批评语境的赛义德“东方学”转向中国语境的东方学,突破西方式的“规训”与“学科”的纠结,回归学术探索之途,则显然立场与策略都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关于西方后殖民批评语境中“东方学”的理论纠结和语境转化的反思启迪我们,中国本身就属于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学”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其核心问题不是赛义德—福柯—葛兰西揭示的文化霸权的“规训”,而是一种正面的、建设性的“学科”思考与机构性实践。长期以来,中国的东方文史哲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东方文学人才培养、教材编写、学术活动,都得到了国家、学会、科研院所和个人各方面的支持与努力。
三、跨文化视野:东方文学史论的“轨迹”与定位
跨文化视野(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的特征是:寻求一种新型的、包容差异的宏阔视界,倡导异质文化与理论话语的际遇与生成新质的空间。在中国东方学视野的东方文学研究的题旨上,跨文化的学术视野,是我们探讨重构中国东方学新形态的可能性的逻辑起点,包括纵向的东方文学史论“轨迹”理论的梳理,横向地探讨当代全球化与数字化的语境与中国东方学的定位与取向问题。
以跨文化视野审视印度文化与文学的“神阶—魔阶”说,可以触发新的思考。此说据称源于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著名插话《薄伽梵歌》:“神阶”意味着践行达磨的正面形象:自我克制、怜悯众生、正直真诚、勇敢无畏、纯洁坚韧、超然物外、信守诺言;属于“魔阶”的是违逆达磨的反面角色,虚伪、自负、妄言、嗔怒、无知、骄矜。按照西方原型批评学理,“神阶—魔阶”说反映了神话原型思维方式常见的二元世界的对峙——天神vs阿修罗,正法(达磨)vs非法(达磨),正确vs谬误,光明vs黑暗……[9]但是,它也呈现出东方智慧,打破了较为传统的静态、封闭、非此即彼的理论窠臼,提示了人物性格与形象的阶梯式或色谱式的复杂理论形态。我们可以依据现代学术意识,借助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多元符号论(Semiotics)对索绪尔语言二元符号学(Semiology)的突破案例,将其改造为一种“神阶—人阶—魔阶……”三元动态的文艺批评模式,这样不仅能够更贴切地阐释阿育王复杂多变的电影形象乃至众多文学典型形象,而且对包容差异的跨语境的世界诗学而言,具有积极的建构作用。
在跨文化视野的意义上,东方文学史论的“轨迹”伴随着世界历史的文化圈形成,以及各文明经济实力的博弈。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枢轴”论较好地描述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从原生态到文化哲学和认识论“大跃迁”的形态,各大文明都出现标志性的“精神导师”并且开创了不同的文化与文学传统;关于中古东方文化与文学的归纳比较困难,国内东方文学史普遍采用特殊形态的“文化圈”理论来描绘东方三大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以波斯-阿拉伯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文化圈”的理论话语源于德国文化传播学派学者格雷布纳《大洋洲的文化圈与文化层》(1905年)。国内侯传文教授对中古东方三大文化圈的研究用功甚勤,论述颇为精辟。他曾以“东方文化三原色”为题分别从三个方面切入:1.文化人/知识分子:士人/仙人/先知;2.人生目的和生活方式:入世文化/出世文化/来世文化;3.文化心理:务实、想象和理想三种基本类型。在其论析中,三大文化圈作为色彩学原理的三原色,隐喻中古东方文化与文学各具特色且交相辉映,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0]但近现代东西方文明与文化出现逆转性的势能落差,在西风东渐形态中,除了后殖民语境中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之外,似乎仍然匮乏有效的理论话语。
在此,我们要满怀敬意地提及中国东方学标志性的学者季羡林先生,同时我们也要反思性地从当代全球化与数字化视野提出一些商榷性的观点。从东方文学史论的维度可以归纳为:前现代世界文明的宏观分野是东方与西方两大系统,两者发展不平衡。古代东方文明的多元性、早熟性和辉煌成就,中古东方文明的三大文化圈形成,共同构成了东方文明的黄金时代。东方文明漫长而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使其达到很高程度,形成悠久的传统和厚实的文化积淀(季羡林先生形容是“三十年河东!”)。近现代,西方文艺复兴以高扬人文主义精神和推进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为两翼,西方文明迅猛发展,表现为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扩张型的商业文明与耗弃型的工业技术文明的融合,逐渐取代东方而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轴心(季羡林先生形容是“三十年河西!”而新世纪的未来发展又或回到“三十年河东!”)。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之际,季羡林先生从宏观视野论及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东西方文明的这种动态关系,但是,这种东西方文明与文学的二元论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是否仍然是今天最有效、最有意义的中国东方学的理论话语?中国东方学的定位与取向的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前述三大文化圈概念、东西方文化圈的二元论范式,尽管简明扼要且具有一定的理论阐释力,但毕竟囿于特定的历史时段论与文化中心论;因此亟待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新语境中进行新的反思与理论阐释。以东方文学史论为例,东方学的“轨迹”和未来发展定位大致可以概括为这么一条脉络:古代原生态—中古文化圈—近现代西方强势话语与解构性的“东方学”—建构当代跨语境的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中国东方学。[11]
今天看来,文化传播学派的文化圈的概念显然是传统“帝国主义”时代辖域化的产物,属于古老的东方帝国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强调的是区域性的帝国版图与权力中心(主权)。而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所描述的当代“帝国”以经济全球化与文化传媒数字化为标志,与穆尔教授“万花筒式的后现代景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全球互联、多元对话的现实与思想观念,正在地理空间意义上和东方文学史论意义上冲击传统的文化圈和文化层概念,在思维方式上突破僵硬的文化等级制和中心主义模式。在这种“无中心、无疆界”的“帝国全球的彩虹”中,传统地理意义上文化圈和文化层概念正在发生转型和蜕变,代之以一种千高原式的全球化平台。“帝国全球的彩虹”是全球化与多元化交汇的当代性的一个隐喻性标志,它启示我们应根据世界文明与历史的发展而调适中国东方学的视野,在新语境中思考与践行不同理论资源的合理化交流、过滤、采借与生成。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中,内文化、交叉文化和跨文化这三重视野提示我们: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对东方理论话语与东方文学的关联性研究是重要的学术空间,充盈着新的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应当倡导跨语境诗学研究,不仅重视东西方之间文艺思想互为参照,而且也关注东方文化不同语境中理论话语的互相生成。
第二节 东方主义范式的转换与当代中国东方学的建构
在由来已久的“东方主义”问题框架中,以赛义德为中轴,可以历时性地梳理出三种语境中的主要范式:其一是传统东方学术语境中的“东方主义”二元论范式,其理论与实践为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奠定了基础;其二是现代西方学术语境中赛义德借助福柯、葛兰西理论而提出的后殖民批评范式,但其东方学策略体现了“规训”与“学科”的理论纠结;其三是当代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中以哈特和奈格里“帝国研究”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范式。以当代中国学术立场对东方主义的主要范式进行学术史梳理,筛选与扬弃其理论资源,对具有中国理论特色的“东方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意义。
一、传统东方语境:“东方主义”二元论范式
在传统东方语境中,“东方主义”的二元论范式具有代表性意义。英国学者萨达尔(Ziauddin Sardar)《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99年)和美国学者克拉克(J.J.Clarke)《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1997年)两部著作具有典型性。前者分章从东方主义的概念、简短的历史、理论和批评、当代实践和展望后现代诸维度展开题旨;后者则主要由“东方及东方主义介绍”、“制造‘东方’”和“20世纪的东方主义”三部分构成。
萨达尔以及克拉克所梳理的“东方主义”范式体现出如下特征:一是认为东方世界是西方思想史的镜像和重要参照系。二是以大量的文学艺术典型事例鲜活地展示了西方以东方为参照系而建构了现代性。三是通过一些代表性的例证较为清晰地梳理了赛义德之前的(反)东方主义范式。提巴威(A.L.Tibawi)的《说英语的东方主义者》(English-Speaking Orientalists,1964年)、阿卜杜勒-马利克(A.Abedl-Malek)的著名论文《危机关头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in Crisis”,1963年)和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懒惰的原住民神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1977年)皆属于经典研究成果。如果说萨达尔《东方主义》侧重于描述、反思与批判西方对东方学学科“知识与权力危险的合谋”,那么,克拉克《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则反过来强调“来自东方的启蒙——西方与亚洲思想的邂逅”[12],进而关注与探讨跨文化交流的建设性问题。这些问题框架,丰富和拓展了赛义德范式的关联域,但是在学理性维度,这些东方主义话语显然都是以东西方二元论为基础的,既有赛义德式的自我与他者之分,也有伽达默尔双向交流的阐释学思考。
二、现代西方语境:赛义德后殖民批评范式与理论纠结
从东方语境转换到西方语境,在学科背景、学术立场与理论策略上,爱德华·赛义德与前述传统东方语境中诸家所处的情境不太一样。赛义德因其里程碑式的《东方主义》而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理论范式的代表人物。在这部引发广泛反响与争议的著作问世之前,对东方主义的讨论与批判主要囿于“伊斯兰研究、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范围……提巴威所从事的是相对冷门的伊斯兰研究,而阿拉塔斯住在新加坡,所从事的是从第三世界的观点进行研究的社会学,贾伊特以阿拉伯文写作,况且,他住在突尼斯(虽然他的作品首先被译成法文,随后又被译为英文),严格来讲,霍奇森是一个世界历史学家,而丹尼尔和萨瑟恩主要从事欧洲史研究。”[13]而赛义德则是文学和文化批评家、社会活动家。作为享誉国际的学者,赛义德在西方宗主国高等院校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同时自身有具有康拉德式的双重语言文化身份,因此视野与思想创造空间更为开阔,其“东方主义”话语与理论策略更为复杂深刻,所具有的文学、美学和哲学的内涵与特征也更为丰赡,同时,其理论范式也更加纠结。
在翻译层面,赛义德著作标题“Orientalism”一词的中译也构成一个问题。该词字面上是“东方主义”,但赛义德是在三种交叠的含义(一门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上使用它的,因此,在没有中文对应词的情况下,王宇根中译本以“东方学”译之。这就造成了在中文语境(包括本文)中该词“东方主义”与“东方学”的混用。如果我们在“权力话语”和“学科”的含义上使用“Orientalism”一词,那么,一种福柯式的理论纠结就出现了:它既是“规训”,又是“学科”。耐人寻味的是,赛义德在其著作中描述东方学是西方“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14]时,特别提到福柯的名著《知识考古学》与《规训与惩罚》。福柯《规训与惩罚》的法文书名是“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但是福柯本人建议英译本书名改为“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这是因为discipline是全书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福柯创用的一个新术语”,既指名词“学科”,又指动词“规训”,“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15]而在西方语境中,赛义德揭示的“Orientalism”是一种借助“知识型”以规训东方学的权力话语与理论范式。当我们把问题框架转移到当代全球化“帝国”语境并且进行中国东方学的理论与学科建设时,必须反思东方学问题上由来已久的二元论模式,尝试转化这种理论纠结。
三、当代“后东方主义”语境:反思中国东方学学科建设
时至今日,全球化与数字化世界史进程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东方主义(东方学)”的学术语境,反思进入当代之后它所呈现的新形态,进而尝试对中国特色东方学的建构问题加以反思。克拉克认为,我们已经处于“后东方主义时代”(post-orientalist epoch),西方将在没有过去的偏见和歪曲的情况下走进东方,“东方主义这个现代社会中奇异的、充满异邦情调、即将消失的副产品可能会如预期般从历史中慢慢淡出”。[16]针对传统东方学的语境转换与后殖民批评东方学的理论纠结,我们需要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张力中反思和推进当代中国东方学学科的建设。(www.zuozong.com)
早在18世纪,西方的东方研究就已经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在当时西方的中心——欧洲,相应地,人们在具有悠久历史的西方大学中设置了东方学系以及汉学系,使研究对象和领域学科化。但由于东西方文明在近现代世界文明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有明显差异,因此,作为学科的东方研究,无论是在欧美大学还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长期以来都隐匿着不同程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优越论。例如,在中国大学的人文科学中,尤其在本科教育中,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居于外国文学的核心地位,往往是必修的主干课程,而东方文学(亚非文学)多为选修性的辅助课程。
在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化多元化框架内不同文明的碰撞、交融和互动的重要性豁显,西方世界对东方语言文化的兴趣和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和拓展,在学科意义上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即使在当前欧美学术界……有些教席则规定必须由东方血统的学者出任,有的学校为了标榜自己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宽阔胸襟,甚至另增加一些新的东方研究职位,并且专门聘用来自东方国家的学者任教。总之,东方学在欧美正处于一个更新换代的转折时期,一批有着东方血统,并在西方受过系统教育的新一代学者将登上讲坛,给传统的东方学增添新的活力。”[17]在欧洲汉学界,既有普实克、马悦然、高力克、米列娜、伊德马、佛克马、杜德桥、顾彬、魏安娜、罗德弼、李夏德这样一批兼通东西方文化的国际知名的西方学者,又有老一辈具有东方血统的著名学者如夏志清、刘若愚、叶维廉等,还有新一代具有东方血统的中青年学者在不断地成长、成熟。
中国自20世纪初,尤其是“五四”以来,对东方文学和文化的译介与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很多中国著名作家和学者都与东方文学/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鲁迅与日本文学,冰心译介泰戈尔,季羡林、金克木与印度文化及文学研究,等等。纵览20世纪,中国的东方研究留下了一条曲折起伏的历史轨迹:五四和新时期呈现出双高峰的态势,从散漫的自发形态逐步走向系统的学科自觉形态。从文化语境的角度而言,东方人用东方话语研究东方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长期以来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普通高校中的中国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群体也不断壮大,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低谷期以后,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的译介与研究在新时期呈现出健康繁荣的发展态势,日益在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中显示出其重要性,不仅在大学本科的主干课程外国文学史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成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与上述的学科发展状况相应,当前国内的东方研究领域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1)自新时期以来,国内以“东方文学史”“外国文学·亚非部分”“世界文学史(含亚非文学)”冠名的著作、高校教材不断涌现,各具特色,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东方文学总体认识的不断深化。(2)东方文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相关的东方美学、诗学及文化研究的论文、著作大量问世,新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3)学术机构、社团与刊物健康发展,使东方文学研究成为有序活动。随着中国“东方学”数代人经验的积累,尤其是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进程中跨语境理论意识的日益提升,这次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东方学’视野下的东方文学研究”(天津外国语大学,2014年)举行,将中国东方学问题提上议程,群贤毕至,集思广益,可谓正当其时。目前我们亟待在学科观念上思考与实践下列范式转型:
1.从二元论思维转向多元化理念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东西方之间的二元论和补充论这一主导的神话由于各种原因正在失去效力,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术语已经失去了其过去一贯的含义。无论是传统东方语境和立场的东方学,还是西方语境的赛义德式后殖民批评范式,都是基于东方/西方等二元论模式的理论话语。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看来,二元论思维已经落后于自然,遵循的是乔木逻辑,充盈着中心主义、等级制的弊端。无论多么“辩证”,二元论都是最经典、最熟练、最古老,同时也是最软弱的思维方式。而多元、开放、流变的块茎模式,才是符合自然之道且充满着无限可能性。[18]克拉克借助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关于文化全球化的观点,也强调摈弃扭曲的“西方与东方”二元模式,通过繁复多样、互相交叠的话语实践,“塑造新的、非欧洲中心论的世界互相依存的模式”。[19]
2.从批判性转向建设性
在当代“后东方主义”语境中,从批判性转向建设性是反思中国东方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认识自我往往需要他者作为参照系,近代以来在世界文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理论话语和学术范式,如与感悟性的中国文论或者艺术型的日本文化及美学比较,西方文化的浮士德式的永不满足的有为哲学,西方知识分子坚持正义的公共良心,西方文学与文论强烈的批判性,西方思想文化善于思辨、不断创新概念与体系的理论努力,在全世界不同文化构成中都是极为突出的。中国特色东方学学科反思与建设,即使是在当代理论话语众声喧哗的语境中也无法脱离对西方思想资源的参照与扬弃。
在“后东方学”学术范式转型视域,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的“症候”,汲取西方思想文化学术的“精魂”,研究西方学术思潮的历史脉络和理论旅行,以及它们进入中国本土语境后的文化过滤与文化移植,力求弄清其思想文化的“语境”,追问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仅仅是西方问题还是人类共同问题?是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问题?是现代性文论还是后现代文论问题?等等。只有真正弄清域外学术理论话语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中国东方学亟待鼎新革故的症结,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努力建构“守正创新”、“正大气象”[20]的中国东方学学科。
西方文学与文论面对的问题框架,脱离不了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与扩张的阴暗面的反思与批判性揭露,这是其思想文化的“精魂”。但是一些重要的西方理论话语进入中国语境后,脱离了原来的社会文化背景,可能会“水土不服”,亟待学术范式转型,理论焦点需要从批判性转向建设性。如“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原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教授葛林布莱特在西澳大学作《迈向文化诗学》(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1986年)演讲,后以此取代先前他们所热衷的“新历史主义”,其提倡的文化诗学主张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通过文学本文与其历史语境关系的研究,“使文学本文重新焕发光彩”。[21]葛林布莱特的有关理论提出不久即被介绍到中国。进入21世纪,“文化诗学”的问题再度引起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童庆炳、蒋述卓、李春青等学者过滤福柯、格林布拉特等人的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话语,倡导中国式的“文化诗学”,阐释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如童庆炳先生在《走向“文化诗学”》演讲中指出:西方文化批评一个特点就是反诗意,旨在通过这种批评对资本主义罪恶进行揭露。中国“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第一,“文化诗学”具有一种现实性的品格和批判精神,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这二者之间的一种张力,既要历史理性,也要人文关怀。第二,文化诗学要求两种阅读,一种叫做品质阅读,主要是衡量作品艺术性的高低,一种叫做价值阅读,主要是揭示作品所隐含的文化的价值。第三,文化诗学重视通过文本细读,比如说语言,来寻找作品的意义。[22]同理,作为西方学术话语的“东方主义”(东方学),在经历传统东方学术语境中的“东方主义”二元论范式和现代西方学术语境中赛义德后殖民批评范式(赛义德富于策略性地体现出其学术关注)之后,需要在当代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中(以哈特和奈格里新自由主义的“帝国研究”为标志)进行中国化的范式转型。践行这项任重道远的任务,需要从西方式的批判性转向中国式的建设性。
3.从散在性到规范化
以赛义德《东方学》为中轴,一方面可以历时性地梳理出前述三种语境中的主要范式(传统东方学术语境中的“东方主义”二元论范式、现代西方学术语境中赛义德后殖民批评范式和当代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中的多元论范式),另一方面可以共时性地思辨中国特色的“东方学”正面建设的问题。这对于中国东方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者而言,是一个开放、多元、动态的问题丛,可以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中国“东方学”学科建设时,从散在性转向规范化是一个重要的取向和特征。一种富于现代意识的“科学”东方学的学科建设,应该包括机构性实践(高校与科研院所体系、学位培养、大学教材、研究专著,以及学会与刊物等)、知识型(特定研究对象与领域、理论方法等)、专业人才(语言、翻译、教学与科研人才等)等要素。而目前看来,在中国东方学界,这些要素仍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散在性,亟待努力不断地进行合理化整合与规范化。譬如,虽然我们已经拥有较为完善的机构性实践,包括专门从事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机构、相关硕博学位的培养、形形色色的东方文学(史)教材与著作、建立了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并且颇为健康活跃,但是文史哲领域和学术学会之间会通不良,匮缺专门的期刊(仅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有非正式出版的《东方文学通讯》);虽然也形成了大致的知识型,具有特定研究对象与领域,但是似乎匮缺系统而特定的理论方法,一些传统的理论话语如日本的十大美学范畴、印度味论诗学话语、中国文论亟待参照西方文艺美学(如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维度)进一步梳理、整合、比较、激活、会通和予以创造性的更新;虽然东方文学专业似乎人才济济,但是,外语专业背景与中文院系背景人才之间分别存在着“短板”的缺憾仍然比较明显,前者长于用东方不同语种进行研究,后者长于综合分析,真正能够打通这两种背景的人才可谓凤毛麟角。如果说中国东方学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那么,其积极建设与逐步完善无疑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中,异质思想文化与文学的并存互补、各得其所,美人之美、各美其美,才能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要。世界文明的动态平衡发展规律,对任何文化和文学都提供了挑战与机遇。
注解:
[1] 麦永雄,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2] Zong-qi Cai, Configurat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 Thre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 3.
[3] http://olddoc.tmu.edu.tw/chiaungo/essay/wha-2011.htm.
[4]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3—113页。
[5] http://www.hangzhou.com.cn/20050101/ca690908.htm.
[6] V.B.Leitch(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属于著名的欧美出版界“诺顿系列”,以厚重、权威、前沿为特征,收录了从古希腊开始到21世纪初148位作者的185篇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著作节选,2010年修订版增加了近期的选篇和阿拉伯、日本、印度、中国的几篇文论片段,作为非欧美文论的代表,中国的选了李泽厚《美学四讲》中的部分内容。
[7] 参阅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倪培耕:《印度味论诗学》,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8] 〔英〕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马雪峰、苏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9] 笔者参阅了张宝胜译《薄伽梵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求证此说。虽未见其词,但可得其意。如在第十六章“神资与阿修罗资质有别瑜伽”中,神资趋向解脱,阿修罗资质趋向束缚。《薄伽梵歌》既有二元划分模式,但也有可能更为重要的复杂多元的思想。如继承印度数论中的“原质”(自性)思想,提出“三德”(萨埵——纯洁、光明、幸福、智慧;罗阇——贪欲、迷恋;答摩——愚昧、嬉忽、懒惰。三者纠结,或趋于上升,或趋于下层)动态关系。既讲究“三德”,又倡导超越三德的梵我一如的解脱。此外,数论的“五大、我慢、觉、十根、五根境”(149页)等也是《薄伽梵歌》的正文内容。
[10] 侯传文:《东方文化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以下。
[11] 王岳川:《“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症候》,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论及在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单一话语”正在让位于“多元文论对话”等症候,强调中国新世纪文论创新要强调“守正创新”之路,其基本美学特征是“正大气象”。这里借用其学术话语。
[12] 〔美〕J.J.克拉克:《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于闽梅、曾祥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3] 〔英〕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马雪峰、苏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14] 〔美〕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
[15]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译后记”,第375页。
[16] 〔美〕J.J.克拉克:《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于闽梅、曾祥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4—309页。
[17] 王宁:《欧洲人眼中的中国》,载《东方丛刊》,1998年第4辑。
[18]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 5.
[19] 〔美〕J.J. 克拉克:《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于闽梅、曾祥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3页。
[20] 参见王岳川:《“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症候》,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
[21] 刘洪一:《文化诗学的思想指向》,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28日。
[22] 童庆炳:《走向“文化诗学”》,http://tieba.baidu.com/f? ?kz=9774102,下载于2004年11月7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