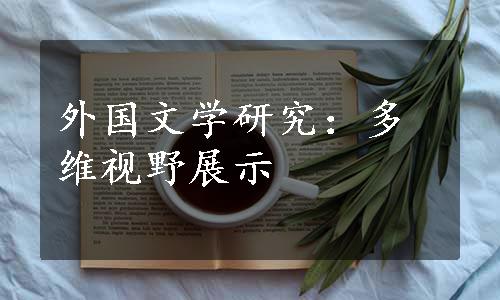
谢天振[1]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伴随着对外国文学的译介而来的,且表现出明显的比较文学意味,尽管研究者或评说者主观上当时并无此自觉。远的可追溯到林纾:林纾早期的译本大多都有他写的序言,在序言里林纾都会站在一个中国译者的立场上有意无意地把所译作品与中国文学中的作品进行比较,譬如把狄更斯的《老古玩店》(林译《孝女耐儿传》)与中国的《红楼梦》进行比较:“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着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妪,牵缀以小人,收末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迭更斯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狯驵酷,至于人意所未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已,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2]他还把《水浒》与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林译《块肉余生述》)进行比较,认为:“此书(指《块肉余生述》,引者按)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而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着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事之来源。……施耐庵著《水浒》,从史进入手,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至于后来,则如一丘之貉,不复分疏其人,意索才尽,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3]
近的可以当代翻译家戈宝权为例。作为翻译家兼外国文学研究家,戈宝权的外国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某一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或是某一个外国作家与中国的渊源关系展开,这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他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写的关于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俄苏作家与中国的关系的系列文章里。这些文章前几年分别以《中外文学姻缘》名结集出版,很受读者欢迎。不过这已经是后话,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1950—1960年代,因受苏联文艺界庸俗社会学批评的影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多热衷于探究作品的主题、作家生平与作品的关系等问题,对戈宝权这样的从译介角度研究外国文学的著述并不是很重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译介角度研究外国文学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研究者不多,影响也不大。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重新崛起并繁荣发展,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研究才重新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并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越来越受人重视的研究领域,也即译介学研究领域。
“译介学”作为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专门术语,由卢康华、孙景尧两位教授率先在他们于1984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导论》一书里提出,孙景尧并在乐黛云教授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1988年)中设专节对其进行分析。之后,谢天振于1994年推出其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又在陈惇、孙景尧和他共同主编的教材《比较文学》(1997年)中,以两万字的篇幅,推出“译介学”专章,详细阐释了译介学的基本理念、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接着,他又先后于1999年和2003年推出两本专著《译介学》和《翻译研究新视野》,于2007年出版一本教材《译介学导论》。在这三本书以及先后发表的数十篇论文里,他对译介学理论作了更加深入的阐述,完成了对译介学理论的基本建构。与此同时,国内同类比较文学教材,如陈惇、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1988年),张铁夫的《新编比较文学教程》(1997年),杨乃乔的《比较文学概论》(2002年),曹顺庆的《比较文学论》(2002年)和《比较文学教程》(2006年)等,也都开始设立“译介学”专节或专章,从而进一步奠定了译介学研究在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极大地推动了译介学研究的深入广泛的展开,并由此对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等领域产生影响,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具体对外国文学研究而言,人们开始意识到,译介学研究揭示出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较少关注,甚至长期被忽视的一面。
首先,译介学研究把我们的视角引向了翻译对中外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揭开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新的层面。
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外文学关系存在一个定式化的认识,先假定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影响下发生、发展起来的,然后努力地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创作手法等方面去寻找其中的相似之处,以证明这种影响的存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国文学是不可能直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影响的,它只能通过翻译才有可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影响。然而由于我们历来的外国文学研究对翻译的作用大多缺乏足够的认识,于是外国文学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具体途径、方式方法是什么?为何是这些国家的这些作家、作品,而不是那些国家的那些作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影响?又为何在某一特定时期是某一个或几个外国的作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特别大,而到了另一个特定时期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或几个外国作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影响?对这些问题要么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要么隔靴搔痒、言不及义。是译介学研究者们借鉴当代国外翻译理论中的多元系统论的理论视角,不仅较好地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还揭示出了制约、影响中外文学关系的诸多深层因素。
在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看来,每个社会都是由各种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组成的一个开放的多元系统。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4]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具体到承担着向国人译介外国文学的翻译文学,它在三种条件下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里有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第一种情形是,一种多元系统尚未定型,也即该译入语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幼嫩”状态,还有待确立;第二种情形是,译入语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尚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种情形是,译入语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多元系统论对翻译文学地位变化的这种阐述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实际也为我们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并对中外文学关系史上的一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圆满的解释。
参照这三种情形去审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史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不少契合之处。譬如中国清末民初时的文学翻译就与上述第一种情况极相仿佛:当时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连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
至于借用多元系统论的视角去审视新中国成立以后60年的外国文学译介,那就更能说明问题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17年,由于新生的共和国尚未发展起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新文学,文学生态呈现出一种近乎真空的状态,所以只能大量译介苏联的文学作品,包括一些二、三流的苏联文学作品。据统计,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翻译出版的俄苏文学作品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总数的65.8%强,总印数82005000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数的74.4%强。[5]然而译介过来的苏联文学作品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掩盖社会矛盾、粉饰太平的虚假之作如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等,一些塑造所谓的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作品也纷纷译介进来,对新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也从一个层面上解释了新中国最初17年间文学中的“假大空”、“高大全”作品的产生根源。
再如“文革”十年期间,由于“文革”中极左思潮的泛滥,我们的文学几乎一片空白,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本反映极左路线的所谓小说尚能公开出版并供读者借阅。这正如上述第二种情形,由于特定历史、政治条件制约,原本资源非常丰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周边国家(东南亚国家日本、越南、朝鲜等)的文学资源的中国文学,此时却处于“弱势”、“边缘”地位。于是在“文革”后期,具体地说,是进入1970年代以后,翻译文学又一次扮演了填补空白的角色:当时公开重版、重印了“文革”前就已经翻译出版过的苏联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另外,还把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连同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也一并重新公开出版发行。与此同时,当时还通过另一个所谓“内部发行”的渠道,翻译出版了一批具有较强文学性和较高艺术性的当代苏联以及当代西方的小说,如艾特马托玛夫的《白轮船》、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部曲、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约瑟夫·赫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这些作品尽管是在“供批判用”的名义下出版的,但对于具有较高文学鉴赏力的读者来说,不啻是文化荒芜的“文革”年代里的一顿丰美的文化盛宴。及至“文革”结束,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又一次出现了“真空”时,创作思想也发生重大转折,于是一边大批重印“文革”前已经翻译出版过的外国古典名著,诸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印数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册;另一边同时开始组织翻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视作禁区的西方现代派作品,从而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这第四次翻译高潮的出现正好印证了上述埃氏多元系统理论所说的第三种情形,即当一种文学处于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时,它会对其他国家文学中的形式有一种迫切的需求。“文革”结束后,我们大量译介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正是迎合了国内小说创作界欲摹仿、借鉴国外同行的意识流等现代创作手法的这一需求。
其次,译介学的研究视角让我们发现了外国文学经典化与翻译之间的关系。
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尤其是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一方面固然与作品本身的创作成就与特点有关,但另一方面,还与翻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一部作品若能被许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翻译家所翻译,历经不同的时代仍然不断地被翻译,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荷马史诗,正是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翻译家的不断翻译,被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所阅读,才逐渐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经典。然而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即使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数量繁多,浩如烟海,翻译家们是如何选择并找到他们需要翻译的作品的呢?译介学研究揭示出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般而言,翻译活动通常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第一个因素即意识形态我们并不陌生,新中国成立后最初17年正是由于新生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我们的翻译选材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文学一边倒。于是,在这“十七年”间,我们不仅翻译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还翻译了大量的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据统计,仅东德之外的东欧七国的古典(19世纪前)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有80多种单行本,共涉及100多个作家的300多个篇目,同时还有多种以国别形式编译的现代中短篇小说集问世。尤其是1950年至1959年间,东欧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被译成了汉语,掀起了东欧文学翻译的一个高潮。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我们与这些国家具有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同时在国际冷战格局中中国与他们同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样的选择也就造就了一批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读者心目中的世界文学的经典。譬如匈牙利裴多菲诗人的“自由与爱情”等诗作,捷克作家与文艺评论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等,前者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句为几代中国读者所传诵;后者的“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以及该书最后一句话“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等语句,同样对几代新中国读者产生深刻影响,两人也因此成为新中国几代读者心目中的经典作家。
“三因素”中的第二个因素即“诗学”(Poetics)不是指的作诗法,而是指的文学观念。或更确切地说,是指的在某一特定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譬如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30年,受苏联影响,我们在文学创作领域标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样的文学观念也就直接影响到我们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凡是不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外国文学作品,就被贴上“腐朽的,没落的,反动的,颓废的”等等标签,原则上不予译介;只有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外国文学作品才能进入我们的译介视野。这样,譬如我们在译介美国文学时,我们译介者的眼中就只有辛克莱,只有德莱赛,只有马克·吐温等等这样一些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至于像福克纳,尽管他于1949年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赢得了世界性的文学声誉,我们仍然不会予以译介。从两位著名的英美文学研究者当时发表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发现这种文学观念主导下的译介立场。朱虹在为纪念英国作家萨克雷逝世100周年撰文时说:“比起过去英国历史的任何时代,19世纪对于我们来说恐怕最为熟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一批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多亏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广泛的栩栩如生的形象描绘和深刻的揭露,我们得以对这一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有比较生动具体的认识。”[6]对现实主义的推崇跃然纸上。而袁可嘉在总结新中国建国10年来欧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的文章中说得更为直白:“中国人民坦率地表示不喜欢统治美国的政治,但对于优秀的美国文学作品却有着同样坦率的爱好。马克·吐温轻松幽默的笔触和西奥多·德莱赛沉重的悲剧气氛同样吸引中国读者的兴趣:《王子与贫儿》、《夏娃日记》、《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美国的悲剧》、《天才》、《嘉莉妹妹》并排地列在书架上。”[7]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他们心目中的英美文学经典作家只能是德莱赛、马克·吐温、狄更斯、萨克雷,而不可能是西方现代派作家诗人福克纳、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等人。而笛福、斯威夫特、高尔斯华绥和莎士比亚等作家因为在苏联也被列入现实主义传统作家的缘故,他们的作品在新中国建国以后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大量的译介。
第三个因素“赞助人”(Patronage)也是促成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重要因素。所谓的“赞助人”并不限于某个资助翻译出版的具体的个人,还包括赞助、支持翻译出版的党政领导部门、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文艺组织等。新中国成立后,宣传部、团中央、各地的出版社等,都扮演了赞助人的角色,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经典化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的《牛虻》了。奥氏的长篇小说尽管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有了多个译本,但当时的影响终究有限。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团中央向全国青年学生发出向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学习的口号以后,小说才真正风靡全国,总印数突破百万,保尔成为中国亿万青年心目中的学习偶像和英雄,小说也俨然成为当代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作。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小说主人公保尔最喜欢的一部小说是《牛虻》,于是爱屋及乌,中国读者也连带喜欢上了《牛虻》,从而使伏尼契这位在英国本土默默无闻的女作家以及她的在英国本土同样名不见经传的小说《牛虻》成为了中国读者心目中的经典。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读者,可以不知道卡夫卡,可以没听说过乔伊斯,甚至可以没读过莎士比亚,但他(她)一定知道伏尼契和她的《牛虻》,他(她)一定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不定他(她)还能完整地背诵保尔关于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的名言呢。至于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译介视野已经大大拓展,艺术成就得到学术界高度肯定的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如《彼得堡》、《我们》、《银鸽》、《时代的喧嚣》等一本本都已翻译进来,笼罩着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名著《日瓦戈医生》也已经翻译进来,它们的印数却平均都只有万余册而已,而借着“红色经典”之名重新推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尽管同时有十几个译本,每一本的印刷数却动辄都在两三万册以上。这背后的原因就不仅仅是靠“三因素”说就能解释的了,而需要运用译介学的理论对之进行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探讨才能说得清。(www.zuozong.com)
最后,译介学研究让我们洞察到了外国文学译介与构建世界文学地图之间的内在关系。
众所周知,每一个民族都有一幅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文学地图。然而这幅世界文学地图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它是否存在一些缺失?又为何会存在这些缺失?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显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而译介学研究则把我们引向对这些问题的审视与考察。
一般而言,每个民族心目中的那幅世界文学地图通常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民族或国家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实际翻译出版的以及在报章杂志和教科书等各种渠道介绍的外国作家作品,这些译作连同报章杂志和教科书上的介绍构成了读者心目中一幅比较具体且形象的世界文学地图;另一个方面则是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学者自己编撰的世界文学史以及他们翻译出版的国外学者编写的相应的世界文学史著述。实际翻译出版的以及在报章杂志和教科书等各种渠道介绍的外国作家作品,正如以上所述,因受到译入语国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操控,所构建的世界文学地图注定是不完整的,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它还会呈现出残缺甚至极度扭曲的形态,如在20世纪我国的文革时期。那么由译入语国的学者们自己编撰的世界文学史类的著述情况是否会好一些呢?从理论上说,答案似乎应该是肯定的,然而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时间里的一些特殊情况,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尚未形成一支比较成熟、齐整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我们在世界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的编撰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得依靠译介进来的世界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类的著述,这样呈现在我国读者面前的那幅世界文学地图就不可避免地打上外来影响的深深的烙印。译介学研究也从这个方面让我们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构建我们自己的世界文学史地图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及其背后影响这幅世界文学地图构建的诸多深层因素。
以新中国成立初期译介的俄苏文学史为例,自1950年至1962年期间新中国直接翻译自苏联出版的俄苏文学史类的著述就达11部之多。由于苏联文学界强调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标榜优秀文学作品的特点就是反映了人民性和阶级性,不符合这种标准的文学作品就不足为训,所以他们编写的俄苏文学史著述也就通篇贯穿着这样的观点和立场。具体如文学史的分期,在缪灵珠翻译的《俄国文学史》(1956年翻译出版)中,原作者高尔基为该书各章节所拟的就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俄国文学”、“十二月党人与普希金”、“平民知识分子作家”、“农民运动与文学”、“农奴解放后的文学”等这样一些标题。不难发现,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与特征在这里是得不到体现的。由于忽视甚至无视作家作品的文学性及其文学价值,这些文学史著述在作家作品的选择上多数唯革命导师领袖关于文学的片言只语马首是瞻,以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作家作品是否入选文学史的标准和依据,于是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高度肯定的作家如高尔基就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譬如在水夫翻译、季莫菲耶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1957年翻译出版)中,其上卷总共364页,而关于高尔基的章节就要占去全书的二分之一篇幅。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高尔基同时代的、具有很高艺术成就的著名诗人叶赛宁篇幅上仅占可怜的三页姑且不论,还要被冠上“不能抵抗敌对思想的影响”、“背叛了自己,背叛了自己的才智,背叛了自己对祖国的爱”等诸多恶谥。至于活跃在19世纪末到十月革命前将近30年时间里的俄国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等一大批文学流派及其创作——被誉为代表俄罗斯文学的另一高峰即“白银时代”,在这些文学史著述里仅只有寥寥数语,基本被抹煞。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更不用说“文革”十年间,呈现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那幅俄苏文学地图是何等的残缺不全。
同样的情况其实也见诸当时国内英美文学史类著述的译介。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结束,我们不光在俄苏文学地图的构建方面,在英美文学乃至其他国家民族文学地图的构建方面也同样受到翻译过来的苏联同类著述的深刻影响。一个典型的案例即是1959年我们翻译出版的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撰写的《英国文学史纲》。自从该书出版之后,该书立即成了我国英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界、外国文学翻译与出版领域的权威导向性著作,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我国同类文学史著作的编写方针,同时还直接影响了我们在翻译英美作家作品时的选择取向。
阿氏的“史纲”贯彻的完全是苏联文艺界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唯政治论、无视文学特点的做法,把在英国文学史上没什么地位的宪章派文学抬得很高,而把劳伦斯、乔伊斯、福斯特等20世纪英国文学重要小说家及其作品贬得一钱不值,还把他们贴上“颓废文学”代表、“反动文学领袖”这样的标签。受此影响,我国学者于20世纪60年代编写的《欧洲文学史》也跟着强调要“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上的欧洲文学现象”[8],并把宪章派文学也搬进了该书。而因为阿氏的“史纲”高度评价拜伦及其诗作,于是拜伦的诗作在新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翻译出版:在1949年前拜伦的诗歌只有零星的几首得到译介,其代表作《唐璜》也仅有一个节译本,但在新中国成立后,拜伦诗作包括长诗和抒情诗几乎都得到了译介,拜伦的诗作毋庸置疑地成为新中国读者心目中的英国文学经典。翻译与世界文学地图的构建关系由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译介学视角考察和分析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所揭示的并不仅仅限于上述这几个方面,包括外国文学期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包括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外国文学界乃至国内文化界的一些热点问题,譬如关于名著重译的问题,譬如围绕现代派文学的争议问题,譬如翻译与市场的消费问题,等等,都让我们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外国文学的翻译、教学与研究有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展开。
注解:
[1] 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2] 林纾:《孝女耐儿传》序,载《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页。
[3] 林纾:《块肉余生述·序》,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
[4] 〔以色列〕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载《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0页。
[5]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载《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6] 朱虹:《论萨克雷的创作》,载《文学评论》,1963年第5期。
[7] 袁可嘉:《欧美文学在中国》,载《世界文学》,1959年第9期。
[8] 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7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