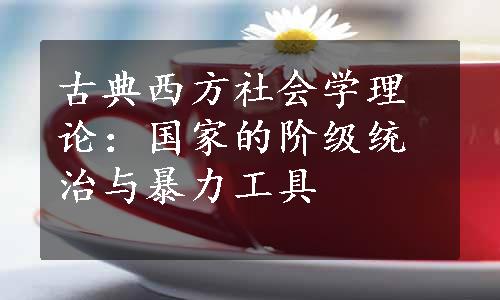
马克思在阶级、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对国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
一、国家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象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国家是在阶级社会才产生的,随着阶级的消失也会消失。在由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方,就产生了国家。国家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监狱这些政治上层建筑隶属于国家政权,是国家暴力统治的工具。国家政权代表的是哪个阶级掌握政权,这属于国体层面的问题。这些阶级怎样掌握政权,则属于政体方面的问题。
马克思在分析1848年二月革命的后果和六月革命的原因时指出:“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个共和国使一切有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一起进入了政权的圈子。……二月共和国打落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冠,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显露出来。”[114]在这里,马克思深刻阐明了国家政权的阶级性。他指出: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权里,虽然二月革命是工人和资产阶级一起完成的,但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实现自己的利益,“工人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旁边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在其他资产阶级旁边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制约的。如果没有一场击退英国这个世界市场暴君的欧洲革命战争,法国又怎么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呢?”[115]法国、英国的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由此决定的国家权力面前,工人阶级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
二、无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条件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阐述了无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条件。李惠斌认为:“《法兰西内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可以把他的这篇著作与他的其他著作加以对比的话,那么,这篇著作的重要性,它对于后人的影响,可能仅次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提出来的民主政治理论,对于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论是列宁,还是后来的毛泽东,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深受这篇著作的影响。”[116]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结构决定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理论,明确指出: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是劳动者经济上的解放——经济上获得个人权利。“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117]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打碎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建立各级基层生产者的自治政府,中央政府履职的领域为数不多,但很重要,实现了“廉价政府”的宗旨,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发现了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特别论述了“廉价政府”及其地位。他指出:“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真正赘瘤和不可缺少的外衣的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的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118]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失败的意义做了如下深刻的揭示:“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119]马克思借鉴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关于打碎国家权力以实行民主制度——使最大多数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思想。托克维尔将美国乡镇所实行的直接民主的方法描述为以一种“巧妙的方法”打碎了权力。这里的“打碎”权力指的是“分权”,即使大多数人参与权力的运行——每年一次在他们内部选举出他们自己的“行政委员”,承担繁多的行政事务;参与决定他们自己的重大决策。“当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讲,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是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时,他所要表达的就是托克维尔和美国乡镇中公民参与意义上的‘打碎权力’。”[120]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消亡”实际上指的是现代民主制度——政治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由于民主制度的实施,已经不是一个整体了。
总体而言,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作为唯物史观,不是像此前的唯心史观那样: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始终站在现实的基础上,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解释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阶级斗争、国家。唯物史观既是一种社会学理论——包含了很多可以和社会学理论范式对接的概念、观点,又是一种关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马克思之前的历史哲学家们用思辨的方法研究历史,没有形成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将社会历史理论立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是使马克思成为古典社会学理论家的根本原因之一。马克思对阶级斗争及其在阶级社会中作用的揭示,使其成为社会学传统中社会冲突研究范式的领军人物;对资本主义社会无情、尖锐的批判,使马克思成为社会批判研究范式当之无愧的先驱。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中,马克思对社会批判范式的作用高于对社会冲突范式的作用:马克思首先是一位社会批判大师,他的理论最具特色之处在于他对现实社会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性及行动倾向——改造世界高于解释世界。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目标“在于唤起群众的集体行动,引发社会变迁”。[121]这也是使马克思成为古典社会学理论家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与病态进行了诊断,认为症结在于私有财产制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如果废除私有财产制,实行全盘性的计划经济,则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与病态都可以消除。于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客观可能性及主观可欲性之外,又提出了行动的方案。不论是整个思想体系或个别的理论及概念,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都同时“包含上述三个要素——事实的分析(尤其是矛盾、紧张的事实)、价值或道德的标准,以及行动倾向。”[122]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马克思的著作已经孕育了一系列的知识传统,其中有一些在当代有关社会科学的争论中占据着中心位置。”[123]柯林斯认为:“马克思对于社会学的贡献在于,他开启了对经济阶级和经济冲突的分析,并将其置于社会运行理论的核心地位。”[124]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开启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传统。
毫无疑义,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方面。“马克思学说对后世的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深远,此种影响很难再加以描绘。”[125]英国学者戈兰·瑟伯恩[126]在他的《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表达了三重意思——对马克思的敬意,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分析方法的敬意,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公开性的祝贺。他认为,马克思倡导人类解放思想、理性地审视世界,致力于将人类从剥削与压迫中解放出来;通过历史来了解当代,特别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及权利的经济与政治实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应该成为宽泛的指引,指引后来者带着深入研究的动机去实践。马克思辩证法的公开性,“即他对社会生活中矛盾、悖论及冲突的敏感与理解”。戈兰·瑟伯恩还预言:“同人类从孔子和柏拉图至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本人将注定名垂千古。”[127]谢立中认为,马克思“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实践提供了一套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话语,以至于马克思同时代或之后绝大多数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家(涂尔干、韦伯、滕尼斯、齐美尔、帕森斯、达伦多夫、吉登斯等)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得不与马克思进行‘对话’,通过与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争论来证明自己的立场,确立自己的合理性,发挥自己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不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就无法真正透彻地去理解孔德、涂尔干、韦伯、滕尼斯、齐美尔这些‘正宗’的经典社会学理论家们的思想。这正是当代西方学者们在编写社会学理论著作时,都不约而同地将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列为一章的基本原因。”[128]
思考题:
1.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贡献是什么?
2.马克思如何看待社会发展的动力?
3.简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4.简述马克思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学发展的影响。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2]〔英〕戈兰·瑟伯恩著,孟建华译:《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3]〔法〕亨利·列斐伏尔著,谢永康、毛林林译:《马克思的社会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4]〔法〕亨利·列斐伏尔著,谢永康、毛林林译:《马克思的社会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5]周晓虹著:《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6]常向群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7]〔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8]在当时的德国,律师不是一个独立的职业,是地方官僚政府的一部分。
[9]〔德〕伊林·费彻尔著,黄文前译:《马克思:思想传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10]青年黑格尔派是黑格尔逝世之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德国思想界出现的一个哲学—政治团体,以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为核心概念,提倡一种纯意识形态的自由。青年黑格尔派的多数成员以精英人物自居,满足于在思想的王国里高谈阔论。马克思则密切关注现实和普通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是他能最终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立场的动力。
[11]由于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鲍威尔过从甚密(鲍威尔是马克思的导师),鲍威尔的左倾和反宗教观点令他被视为国家的危险分子、被解除了波恩大学的教职,这也影响到了马克思的命运。第一,马克思毕业后进入大学任教的机会归零了,第二,他只能从柏林大学转往一所较小的大学——耶拿大学(有人称其为柏林“劳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2]1841年,《莱茵报》在科隆创办,创办人多为基督教和犹太教人士。
[13]1843年3月,《莱茵报》因其越来越浓郁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为普鲁士当局所不容,被查封。这使马克思认识到,资产阶级并不是为自由而战的身躯,而是一副行业自由的骷髅。为此,他决定退出《莱茵报》。
[14]〔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八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4页。
[15]《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在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1927年才正式面世。该手稿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的第三篇第三章即国家部分的批判分析。
[16]〔德〕伊林·费彻尔著,黄文前译:《马克思:思想传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17]《德法年鉴》的停刊,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在德国的秘密传播遇到了困难,另一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和卢格这两位编辑在观点上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
[18]〔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八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5页。
[19]〔德〕伊林·费彻尔著,黄文前译:《马克思:思想传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20]在马克思本人原著中,此篇论著的标题为“关于费尔巴哈”。1888年,恩格斯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附录以“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为标题发表出来。现在通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篇名是前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发表该论著时所定的。
[21]他们先是到了曼彻斯特,这个城市为他们提供了认识英国工业发展和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良好条件。随后,两人又去了伦敦。在伦敦,马克思与“正义者同盟”和宪章运动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
[22]侯惠勤主编:《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磨砺——马克思主义著作精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23]梁赞诺夫(1870—1938),早年投身革命,多次被捕、被流放,两次流亡国外(德国和奥地利)。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寻找、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支持下,梁赞诺夫筹建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任第一任院长(1921—1931)。1924年起,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直接隶属于苏共中央。1931年,与1924年成立的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956年改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我国学术界简称其为“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梁赞诺夫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培养了一批马克思字迹辨认专家,启动了MEGA1(1927—1935)的编辑工作,为MEGA1的编辑、出版奠定了基础。现在,总部设在德国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的编辑委员会正在从事浩繁的《新MEGA: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共114卷,含马克思的手稿:摘录笔记,创作手稿,誊清稿,发表稿)的编辑工作。这是马克思研究的重要一手文献。由于梁赞诺夫的努力,马克思研究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24]《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针对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而写成的一部论战性著作,以法文写成于1847年上半年,并于同年7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
[25]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描绘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轮廓,但对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确切的规定和准确的表达。《哲学的贫困》第一次使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和核心观点实现了思想上的完全成熟和术语上的准确表达。在此基础上,它科学地概括了阶级斗争理论。至此,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形成并进入到运用、检验和发展时期。
[26]《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中文译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按照马克思的最初计划,他将以一系列论文来阐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新莱茵报》的停刊,使这组论文只发表了前五篇。此后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过几次。1891年,恩格斯考虑到对工人宣传的需要,对该书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力求将这个版本中的观点在一切重要点上与马克思后期的观点统一起来。
[27]《共产党宣言》最初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受委托起草的一个纲领。当时,共产主义在欧洲已经形成一种势力,针对这种势力,神圣同盟制造了种种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试图扑灭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伟大纲领性文献,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了工人运动的崭新旗帜。
[28]侯惠勤主编:《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磨砺——马克思主义著作精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29]1848年2月,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为反抗资产阶级采取的一系列敌视工人阶级的措施,巴黎工人于1848年6月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但起义很快遭到残酷镇压。随后,在资产阶级内部各个派别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路易·波拿巴掌握了政权。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也相继失败,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转入低潮。从大的历史脉络上看,这次运动是1789年以后60年间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的法国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和妄图复辟的封建贵族之间、资产阶级共和派和立宪派之间,围绕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问题,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斗争。在此期间,除了两次封建王朝复辟外,资产阶级专政的政体经历了两次君主立宪制、两次帝制、三次共和制,直到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和巩固,法国才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法国历史上的君主政体一去不复返了。
[30]《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的战斗机关报,马克思任主编。《新莱茵报》编辑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勇敢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
[31]转引自〔德〕伊林·费彻尔著,黄文前译:《马克思:思想传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页。
[32]在伦敦期间,马克思曾经受聘为《纽约论坛》的国外记者,后来又在一个自由派主编的手下工作过。
[33]〔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八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6页。
[34]《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是《新莱茵报》的续刊。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该杂志于1850年3月—11月共出了六期。
[35]孙承叔著:《真正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36]〔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八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6页。
[37]《资本论》的出版,巩固了马克思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他实际上成为了第一国际的领袖人物。为避免第一国际在各种力量的斗争中解体,马克思决定把第一国际总部迁往美国。1876年,第一国际在美国费城解散。
[38]参加攻占巴士底狱起义的市民通过选举产生了一个革命的巴黎市政府——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要求废除封建特权,废除官职世袭和买卖制度,改行选举制;重建司法制度,审判官、司法官员由世袭制改为任命制或选举制。1789年8月26日,巴黎公社通过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39]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缘起是第三等级和贫民阶层反对封建王权的斗争。以教士、公证人、律师、行业会员为主组成的“三级会议”代表一千多人向国王提出陈情书,要求限制专制王权、颁布国王宪法、废除农村的领主特权。王室的反应使得巴黎市民感到改革进程有被扼杀的危险,于是于7月14日发动了武装起义。暴力活动席卷了巴黎的大街小巷。这一天,是历史上著名的反对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法国大革命的开端,后来被确定为法国的国庆日。
[40]李惠斌著:《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
[41]李惠斌著:《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42]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斯宾塞也葬在那里。
[43]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44]〔德〕伊林·费彻尔著,黄文前译:《马克思:思想传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45]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关于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宏观社会学、社会冲突等。
[46]〔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八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1页。
[47]〔法〕菲利普·卡班,让—弗朗索瓦·多尔蒂耶主编,吴绍宜主译,夏其敏参译:《法国视角下的社会学史与社会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48]黄瑞祺著:《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51]马克思著:《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www.zuozong.com)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67]马克思著:《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7页。
[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6-857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页。
[71]孙承叔著:《真正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1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1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页。
[7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
[7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1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1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2页。
[8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页。
[83]石向实、朱晓鹏等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1页。
[84]孙承叔著:《真正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8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0页。
[9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页。
[9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9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94]〔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八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7页。
[95]〔法〕菲利普·卡班,让—弗朗索瓦·多尔蒂耶主编,吴绍宜主译,夏其敏参译:《法国视角下的社会学史与社会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96]〔法〕菲利普·卡班,让—弗朗索瓦·多尔蒂耶主编,吴绍宜主译,夏其敏参译:《法国视角下的社会学史与社会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97]〔法〕菲利普·卡班,让—弗朗索瓦·多尔蒂耶主编,吴绍宜主译,夏其敏参译:《法国视角下的社会学史与社会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98]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5页。
[99]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22—24日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
[100]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
[101]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102]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103]黄瑞祺著:《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105]马克思著:《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1页。
[10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
[10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1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0页。
[1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112]〔法〕菲利普·卡班,让—弗朗索瓦·多尔蒂耶主编,吴绍宜主译,夏其敏参译:《法国视角下的社会学史与社会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114]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页。
[115]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116]李惠斌著:《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117]转引自李惠斌著:《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118]李惠斌著:《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页。
[119]转引自李惠斌著:《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1页。
[120]李惠斌著:《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121]黄瑞祺著:《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22]黄瑞祺著:《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123]转引自周晓虹著:《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124]〔美〕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第八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2页。
[125]黄瑞祺著:《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4页。
[126]戈兰·瑟伯恩,1941年出生于瑞士卡尔马,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剑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出版《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世界上的不平等》《性与权力:20世纪的家庭》等多部著作。
[127]〔英〕戈兰·瑟伯恩著,孟建华译:《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28]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