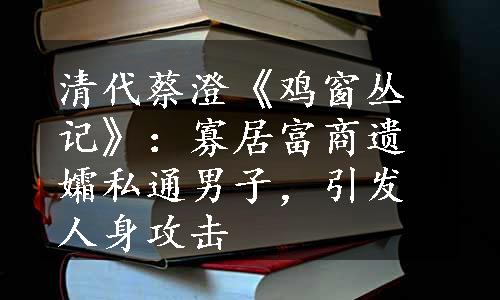
攻击与喋血
清代蔡澄的《鸡窗丛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河间富商的遗孀魏氏,寡居期间喜欢与男子私通,并且频频换人。她的小叔子长得相貌俊秀,魏氏屡加挑逗,但小叔子不为所动。一次魏氏竟然强迫他同床行事,不料这位仁兄畏怯不前,魏氏大怒,一口咬掉了小叔子的“那活儿”。事情闹进官府,照理该判魏氏有罪,但有个刀笔吏受了魏氏的贿赂,在他写的状词中只有八个字:“不节不咬,不咬不节”。官府看了,便认为魏氏无罪,那个小叔子反而被捕入狱。小叔子出狱之后,通过河间老乡的举荐,去京城做了太监。这个故事说明太监本身是暴力的产物,是暴力的牺牲品。因此,他们的行为与正常人比较起来往往会多一些暴力的成分。
《新唐书·宦者传》:“杨思勖本姓苏,以养于内宫杨氏,被阉,入内侍省。思勖勇谋有膂力,残忍好杀。玄宗作临淄王诛灭韦后时建功,累迁右监门卫将军。开元之初,讨安南梅玄成叛变尽诛党羽,积尸成‘京观’而还。十二年,玉溪覃行璋作乱,生擒之,斩首三万级,加辅国将军号。十四年,讨邕州贼,生擒大海斩首二万,积尸为‘京观。’十六年,泷州陈行范称帝作乱陷四十余城,思勖十余人进讨。追至苗区深州之云际、盘辽二洞杀之。斩首六万级,获马口金无算。思勖刚决残暴,所得俘囚,多生剥其面,或剺发际,掣去头皮,将士以下望风慑惮,不敢仰视。而内给事(指太监)牛仙童使幽州,受张守珪厚赂,玄宗怒,命思勖杀之。傅架之日,手探其心,截去手足,割肉生吃其尸,其残酷如此。开元二十八年卒,高寿八十余。”这是唐代太监阴暗、冷酷的一个典型。在他们的心目中,人的价值远逊于权力的分量。同时,作为受过巨大心理摧残的个体,他们对社会给予自己的不公平待遇和歧视怀着极大的不满。当他们掌握一定的权力以后,往往会使出最为残酷的手段来求得心理平衡,发泄积蓄在心理上的不满情绪。
在中国历史上,严刑与酷吏屡有记载。在这种封闭的农耕经济环境中,竟然造就出如此花样繁多的对人的摧残方式,不能不让人吃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太监既不是始作俑者,也非登峰造极者。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些记载:
《戴就传》:“……收就于钱塘县狱。幽囚考掠,五毒参至。又烧斧,使就挟于肘腋。每上彭考,因止饭食不肯下,肉焦毁坠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穷竭酷惨,无复余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马矢董之,一夜二日,皆谓已死,登船视之,就方张眼大骂曰,‘何不盖火,而使灭绝!’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坠落。”
《旧唐书·刑法志》:“时周兴、来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狱。俊臣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瓮,以火环烧炙之,兼绝其粮饷。其所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
《宋史·宦者石得一传》:“元祐初,领成州团练使……恣其残刻,纵遣逻者,所在棋布,张阱设网,以无为有,以虚为实。朝廷大吏及富家小人飞语朝上,暮入狴犴,上下惴恐,不能自保。”
《刑法志》:“刘元吉之系,左军巡卒,系缚榜治,谓之‘鼠弹筝’,极其惨毒。帝令以其法缚狱卒,宛转号叫,求速死。及解缚,两手良久不能动。帝谓宰相曰:‘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理宗初即位……天下之狱,不胜其酷,而又擅置狱具,非法残民。或断薪为杖,掊击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脑箍’;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夹辫两股,令狱卒跪跃于上,谓之‘超棍’,深深骨髓,几于殒命。”
《明史·刑法志》:“田尔耕、许显纯在熹宗时为魏忠贤义子,拷杨涟、左光斗辈,坐赃比较,立限严督之。两日为一限,输金不中程者,受全刑。全刑者,曰械、曰镣、曰棍、曰拶、曰夹棍。五毒备具,呼謈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明日,涟死,光斗等次第皆锁头拉死。每一人死,停数日,苇席裹尸出牢户,虫蛆腐体。”
关于这类记载,几乎件件触目惊心。以大镬煮人,为瓮以醢人,凿颠抽胁,剖心肝,剥皮,钻去髌骨,漆头颅为溺器,制人皮为马鞍,火以焚身,马车以裂体;以一人之身体,先断其舌,再刻其面,而窒之以墨,再截其鼻,再割其耳,再斩左右趾,然后笞杀之,枭其首,俎其骨肉。这些行为极其残酷,都是一些灭绝人性的行为,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使人性及良知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即使非太监所为,也是为一般有廉耻心、同情心以及正义感的人所不能为之的。这些酷刑的产生,在法理上有一定的依据,再加上社会上一批心理变态的酷吏(当然包括太监)推波助澜,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
在法律的前提下由酷吏对罪人进行的人身攻击,是不能得到原谅的。但在为了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利益而展开的各种战争,在战争的前提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攻击,就更不能原谅了。在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三个部落的领袖人物黄帝、炎帝、蚩尤之间就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战争。《庄子·盗跖篇》: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其鏖战之剧烈程度可见一斑。据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也发现了战争的痕迹。如宝鸡北首岭的一座墓里埋着一名无头的成年男子,双膝之间随葬有成束的骨镞,在头颅的位置上放了一件带符号的双耳尖底陶器,用来代替失去的人头。在山东绛县墓葬中有头部中箭,石镞射人鼻骨的遗骸发现。在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中,有八座墓葬中所埋的死者都遭过乱箭的射击,中箭的部位主要是在胸部和腹部,这显然是氏族间争斗或仇杀中被处死的俘虏。
不论是法理上的依据,或是考古中的发现,还是中国历朝历代更替的史实,都说明太监群体之所以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与正常的统治运作秩序南辕北辙,并且往往采用一些异乎寻常的手法来开展人与人之间的攻击。除了他们的生理基础以外,还有着相当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氛围。
从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看,像唐代的杨思勖那样,亲手施行暴虐的太监还不是很多的。绝大多数的太监都是靠搬弄是非,捏造事端,借他人之手加害于人。他们的手段之高明、残酷,往往使洞悉他们阴谋的人主自叹不如。在唐代天宝以后的九个皇帝之中,有7个皇帝是由太监拥立的,更有几个皇帝是直接或间接被太监弑逆谋害的。东汉的太监敢杀大臣,而唐代的太监弑主杀君,几成家常便饭。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开成四年四月乙亥,上(指唐文宗)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何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王)、汉献(帝)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不如远甚。’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此不复视朝。”这段记载颇值玩味。(www.zuozong.com)
摩尔根在谈到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时分析道:“当人类文化处于蒙昧社会的低级水平时,人们在规定范围内实行共夫共妻,这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主要原则。这种规定集体同居的权利和特权(jura conjugialia)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体制,终于成为社会结构的组织原则。这些权利与特权必然根深蒂固,其稳定程度乃至于人类要经历若干次变动,以造成不知不觉的改革才能慢慢地从中解脱出来。”(《古代社会》第47、48页),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原始蒙昧的社会基因仍然残留在封建集权主义的社会之中,太监作为皇帝的家臣及奴仆,在正确处理与主人的关系的时候,也并非是尽如主人之意的。因为他们残缺的肢体,扭曲的灵魂都无时不在地想达到一个人主的境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会攻击一切。
当了解到太监的这种攻击冲动来自于社会和原始的本能以后,我们就不难了解它的极端危险性了。用康罗·洛伦兹的话来说:“完全相互依赖的小团体可能互相发泄怒气,因此防止了他们与陌生人或圈外人的争吵。但是明显的,当团体的分子愈是彼此了解,彼此相爱,则受压抑的攻击性也愈显得危险。”(《攻击与人性》,第62、63页)。太监与人主之间的关系即是如此。个人肉体的攻击显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不会太大的,但太监对帝王的攻击,却会影响整个正常的统治秩序,它给社会带来的破坏程度是无法用痛疼来衡量的。就拿唐代来说,从玄宗时期的高力士用权,到肃宗、代宗、德宗三个时期的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莫不是位极人臣,功高震主。当时宰相不过三品官,而太监则任典兵监军,官拜骠骑大将军,位在一品之上。因此,“弑君立君,出于中尉;生杀予夺,决于北司。”唐代亡于太监之手,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世人啼笑皆非的历史悲剧。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的价值哲学,曾把世界理想地分为外在的事物与人类心灵内在法则两大类,并认为人类恐惧并导致相互攻击的原因,既有对深不可测的高价值所引发的一种情绪上的冲动,也有其他无意识因素的参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封建帝王扮演的是父亲角色,带着专横与不公正的特征,而作为太监个体来说,无论是被迫去势还是自愿受宫的人,其实施的过程,一般都是由父亲亲自动手的,至少也是有父亲在一旁。在这个过程中,太监做人的尊严被完全剥夺了,肉体上的痛苦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他们的心里。从理论上讲,就是“从原始父亲,经过兄弟宗族,发展到成熟文明所特有的机构化权力制度,统治变得越来越非人化、客观化和普遍化,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合理、有效和多产”(《爱欲与文明》,第63页)。而这种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越来越合理和规范的各种社会制度及伦理道德,对太监个体来说,又无疑造成了新的压抑,这种新的压抑的后果,就是引发更为激烈的攻击性行为的发生。
在太监文化发展史上,以凶残著称的当数明代的魏忠贤。这一时期,特务机构的建立并完善,也为太监们充分发挥他们的“凶残”才智提供了舞台。《明史·魏忠贤传》:“当是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戚臣李承恩者,宁安大长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赐器。忠贤诬以盗乘舆服御物,论死。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武弁蒋应阳为廷弼讼冤,立诛死。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惸舌,所杀不可数,道路以目。”
当时的太监特务横行,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境地。在《明史·刑法志》、《幸存录》还记载一个近似天方夜谭的故事:一天晚上,有四五个人在喝酒,喝着喝着一个人就有了醉意,讲起了醉话,并开始大骂魏忠贤,众人皆劝他少说两句,借着酒劲,这位仁兄又吼了一声:“怕什么,剥不了我的皮。”话音未落,太监特务便破门而入,当即将此人押送魏忠贤处。魏大人冷笑一声,当堂令太监们将这位骂者活活剥了皮。剥皮的方法是先将人的手足用巨钉钉在门板上,然后取沥青浇遍全身,再用铁锤敲打,一会儿整张皮就脱落了,“其皮壳俨若一人”。这些太监干起这种惨无人道的勾当来,谈笑自若,确实令人发指。
考察一下魏忠贤的历史,这位太监的行为不是偶然的。他从小不务正业,不读书不识字,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无赖。为了雪耻求荣,自己动手阉割了生殖器。为了出人头地,他不择手段地巴结当时熹宗的乳母,并与这位乳母结成了“对食”伴儿。当年引荐魏忠贤入宫的太监魏朝,不仅失去了他的“菜户”客氏,而且被逐出宫廷,放到凤阳去看守皇陵。魏忠贤仍不肯放过这位“情敌”,派人跟到凤阳,害死了这位曾经有恩于他的人。熹宗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却是一个好木匠,他对于治理国家毫不感兴趣,只对他自己创造的各种精巧的亭台楼阁感到欣慰。于是,不识字的魏忠贤在他的“性伙伴”的支持下,竟然当上了秉笔太监,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无法判断阉割对于魏忠贤这类市井无赖会造成多大的心理损害。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正是由于这种阉割情结的出现,引发了这类人物人性中的恶的一面,从而给社会造成了如此之大的损失。
像魏忠贤这类大腕级的人物,在历史上还是为数不多的。比较多的是居于中下级的小太监,他们的行为也许被“大腕”的“光辉”所掩盖,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生态度则是构成这种文化现象的主体,而这种主体往往会被研究者所忽视。
日本学者三田村太助在其所著《宦》一书中,对太监,特别是对普通太监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具体的描绘:太监穿一种叫“袍子”的灰色长上衣,外加暗藏青的短上衣叫“褂子”,穿黑色裤子,戴宦官帽,走路时,略微前倾,迈着小步子,颇具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太监给人一种难言的讨厌感觉。面貌清秀的太监给人以女扮男装的错觉,年纪大了以后,又像假扮的男装老妇女。太监被阉割以后,自己原来的声音就丧失了,特别是从小去势的,其声音就与妇人一模一样。长大以后去势的,声音变得非常尖锐刺耳。年轻时去势的太监,短时间内会长得很胖但肌肉柔软,松松垮垮,更谈不上有力气。大多数太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瘦,到了三十岁以后,脸上会出现许多皱纹,四十岁的太监看起来就像六十岁的老人。这种身体变化也带来了个性的反常,他们有时会因为一点点小事而发怒,但发完脾气以后又会变得若无其事。他们并非十分残忍,一般对比他们强的人或弱的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敌意。他们尾随比他们强的人,并嘲笑比自己弱小的人。幼年时去势的太监,由于当时的年幼无知,长大后,想起自己的性无能或曾受人使唤之苦,大多痛恨自己的父亲,但能孝顺自己的母亲。他们具有强烈的团结心,有排外心理,对太监以外的人都抱有敌对的态度。太监们的团结意识和对付外界的强烈抵抗能力,是与宫廷的特殊环境和皇帝的威严分不开的。太监一旦离开宫廷,离开了他们所依附的帝王,便和一般人一样懦弱了,有时表现得更有过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太监是非男非女,非大人非小孩,非恶人非善人的奇怪的人,他们之所以能与帝王建立起这种特殊的关系,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生理构造。
日本学者的分析更多地集中在太监个体的表层形态上,且年代的跨度只限于晚清时期。因为这一时期有许多可以实证和引述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一种比较科学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但是,从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来看,清朝已经不是封建帝制最为强大的时代了。依附于它的各种意识形态及文化现象,似乎已经不能完全成为我们所需要的典型。
康罗·洛伦兹这样写道:“就人类想法来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友情是代表最受人珍惜的价值中的一个,不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将使我们觉得它是残忍的,而有冷颤之感。然而,无名群体的这些简单而且看来似乎是无害的机能,可能转变为残忍的甚至可怕的东西。人类社会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些机能。由于组织得相当好的个体间的关系及被冠上名氏称号后,这些机能就被隐藏起来。但是偶然间,它们会像火山爆发的威力那般地喷泄出来,完全地驾驭人类,而使得这些行为不再被称为是人性的。”(《攻击与人性》,第154、155页)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攻击及残害,是人类劣根性的表现,是人类兽性尚未完全泯灭的标志。这种攻击与喋血,并非始于太监,只是太监的这种行为比较特别罢了。
(1994年7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