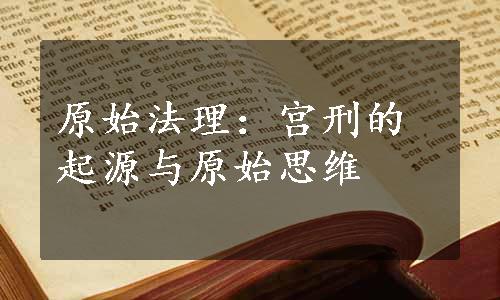
原始法理与思维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宫刑”,也许就不会有太监。当然,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也就不会产生“太监文化”这朵“恶之花”。研究“宫刑”这种刑律的起源,以及与此相关的原始思维,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种文化产生的必然性有很大的帮助。
英语中的太监(阉人)名为“Eunuch”,词源是希腊文,意思为“床的守护者”。中国的太监又称宦官,从“宦”字的构成来看,它是“宀”下面加一“臣”字,意为“家臣”。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星宿中有四颗是属于“太监”的。无论从星象的排列还是从造字的意味来看,太监从属于帝王,天经地义。那么,这些“床的守护者”的来源是什么呢?这里又要提到我国古代的“五刑”,我们所研究的是“宫刑”。
《尚书·吕刑》中有“爰始淫,为劓、刖、标(即宫)、黠”。又有“舜典五刑,有宫”的记载。据史料记载,“五刑”的主要对象,是以蚩尤为代表的所谓叛逆不训的“乱民”。《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云笈七谶》卷一百《轩辕本纪》:“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化为枫木之林。”
《皇览·冢墓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族。肩髀(大腿)冢,在山阳钜野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
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刑法实施的对象是统治者的对立面,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所遵循的共同原则;二是有关枫木的含义。
《梦溪笔谈》:“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虽然以蚩尤失败而告终,但民间的同情却在蚩尤一方。其原因就是蚩尤代表统治者的对立面。这些记载中多次提及“枫木”。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有关太阳的神话中,常提到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木有许多相近但又有所不同的名称,如扶桑、扶木、若木、若华等。
《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佚书《玄中记》:“蓬莱之东,岱岳之间,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岭常有天鸡,为巢栖于上。每夜半时则天鸡鸣,而日中阳鸟则应之。阳鸟鸣,则天下之鸡皆鸣。”《神异经》:“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则鸣。”
“扶桑”被研究者普遍认为表现了中国古代先民们的宇宙观念。后来此词又作为特定地域的代名词,而存在于若干典籍之中。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东方的扶桑木、中央的建木和西方的若木为三点,古人构造了一种以神话形式出现的宇宙观念。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但是这种非理性语义层面的存在,正是原始神话的特色之所在。对于研究者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在这种非理性语义层面之下的深层结构之中,确实还存在着某些合乎理性的方面。”(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22页)这里所指的由图腾类树木构成原始的宇宙观念以及其他的文化观念,是明白无误的。
再让我们回到“枫木”上来。
《尔雅翼》卷十一:“(枫)树老有瘿瘤,忽遇暴风骤雨,瘿上耸出一枝,一夜暗出三五尺,形如人鬼。口眼备,南中谓之枫人,变谓之灵枫。越人以汁取为神事之。”《述异记》卷下:“南中有枫子鬼。枫木之老者,为人形,亦呼为灵枫。”《南方草木状》卷中:“枫人。五岭之间多枫木,岁久则生瘿瘤。一夕遇暴雷骤雨,其树赘暗长三五尺,谓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有通神之验,取之不以法,则能化去。”
其实,枫木的本质与扶桑一样,体现着一种与宇宙观和生殖文化有关的观念。只是枫木作为与“罪恶”、“死亡”有关的图腾意义,与桑林的内涵有着本质的区别罢了。扶桑木作为古代华夏民族的太阳神和始祖神,它体现的仅仅是存在于观念之中的图腾,而具体的形象,则由当时遍植于黄土高原的桑树所替代。这种桑树即成为受到普遍崇拜的生命之树。
《淮南子》高诱注:“桑林者,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这是生命的象征。《拾遗记》卷一:“昔黄帝除蚩尤及四方群凶,并诸妖魅,填川满谷,积血成渊,聚骨如岳。数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垩之山。望之峨峨,如霜雪矣。”而枫木则生于此地。既是死亡的象征,也是不屈生命力的象征。
汉字“生”在甲骨文中是这样的:
与“生”同义的“姓”字,其字形则取像于女子跪拜在树林之下:
《说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这种标志着血缘生命的图腾,既表示血缘的划分和部落的认同,也意味着在我国明显地存在着一个祭木的风俗。对于这种具有崇拜意味的社木选择,除了有统治者的标准以外,如前面引述过的《墨子·明鬼》:“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社。”在民间的祭祀中,大众的价值取向则不一定与统治者相同,只是这种民众的价值观念不被正史所认同罢了。
其实,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树木成为崇拜物也不是偶然的。“大森林曾是人类生命的摇篮,茂密的丛林除了给人以生活的养育之外,也给人以生命的启示,森林葱郁的生命力使人类羡慕不已。于是从交感巫术出发,他们试图从崇拜和模拟树林的生命力出发,来增强和扩大自身的生命力。于是那神树就成了一种生殖能力的化身,对神树的供奉也就成为生命的崇拜与祭祀。”(《中国生殖文化论》,傅道彬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在这里我们所要研究的是“桑木”和“枫木”所蕴含的不同文化意义,以及形成这些文化意义的不同历史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原始的枫木崇拜是如何发展为“椓刑”,即“宫刑”。
摩尔根指出:“如果我们沿着几种进步的路径上溯到人类的原始时代,又如果我们一方面将各种发明和发现,另一方面将各种制度,按照其出现的顺序向上逆推,我们就会看出,发明和发现总是一个累进发展的过程,而各种制度则是不断扩展的过程。前一类具有一种或多或少直接连贯的关系。后一类则是从为数不多的原始思想幼苗中发展出来的。近代的种种制度实生根于野蛮阶段,而推其萌芽之始,则又在更早的蒙昧阶段。它们一脉相承,贯通各代,既有其逻辑上的前因后果,亦有其血统上的来龙去脉。”(《古代社会》,第4页)
从法律制度的形成上溯到古代神话传说中特有的内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这些故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的标准,以便说明这类崇拜的性质。此外,由于它们显示出崇拜的真正起源已经迷失在远古的朦胧之中,从而间接地证明了这种崇拜的年代之久远。”(《金枝》,弗雷泽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原始人类向树木乞求生命的过程,是一个由自我的生命意志向外扩张的过程。同时也包含了对人的生命以及“集体意志”事物的否定过程。从原始森林中走出来的原始人类,树木既为他们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物质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秩序。于是,在对“神木”崇拜的同时,也自然会产生出对一些与“神木”特有的文化意义相反的否定性崇拜。这与他们在生活中的砍伐树木,发展生产,拓宽生存空间,向大自然摄取更多的“能量流”的行为是一致的。(www.zuozong.com)
既然树木象征着生生不息的生命,既然否定这种生命力象征的最原始的办法就是彻底砍伐,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宫刑”的产生就非常容易了。
从古代的五刑(大辟,即死刑;宫,即破坏生殖器;刖,即断人足;劓,即割鼻子;墨(黥),即在脸上刺字)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用刑方式实际上就是以砍伐树木来比照的。
在我国历史上,到了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了徒刑。至汉代逐渐废除了宫刑,并以笞刑和徒刑来取代墨、劓、刖等肉刑。南北朝时期正式出现流刑,到隋朝时基本上就形成了《唐律》中规定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的内容。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对罪犯的认知和比照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理的形成固然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但法理所体现出来的原始逻辑关系,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列维·布留尔指出:“在大多数原始人的观念中,天空就像是扣在陆地或海洋平面上的一只钟。因而,世界止于地平线的一周。在这里,与其说空间是被想象到的,还不如说是被感觉到的。空间的各个方向都包含着属性,如我们见到的那样,它的每个区域都与通常在它里面的一切东西互渗。原始人关于时间(主要是具有量的性质)的观念一直是混乱的。差不多所有的原始语言表现时间关系的手段都非常贫乏,但表现空间关系的手段却又十分丰富。将来的事件,假如它被认为可信,假如它引起强烈的情感,常常被感觉成现在的事件。”(《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25、426页)
从树神崇拜发展到原始法理的形成,互渗律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原始思维中,从树的枝干到人的器官几乎是同一类的东西。因为作为不同的生命形式,这种对观念的肯定和否定,是通过人类具体操作来完成的。宫刑在古代是“罪死刑一等”。阉割去势的男人,其罪行是仅次于死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刑又是“赦死”之刑。
香港有一位叫陈存仁的医师,在一篇《男性酷刑太监考》中记述过两个关于太监溯源的字形:一个是日本学者白川静所藏的甲骨文中的太监字形(见下图)。
另一个是《殷墟书契》中的断片字(a),以及《甲骨学文字篇》中的另外两个字(b)、(c)(见下图)。
日本学者认为该字形的左半边表示人的阳物,右半边表示用刀切断,合并后二字即为太监。这个理解有些牵强。(《传记文学》(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1991年元月,第五十八卷第一期,第126页)
在甲骨文中, 之形也可代表人的鼻子。而用
之形也可代表人的鼻子。而用 来表示一些特指的意思,并无切割之意,罗振玉的《殷墟书契》中所载的字形与上图(a)相同。而王国维的弟子朱芳圃所著的《甲骨学文字编》中所载的字形,即上图(b)、(c)才是阉人的象形体。有文献可考的资料中发现,在殷代,当时十分流行将战争中的俘虏“去势”后进行祭祀,也就是我们前面引述过的“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尚书·吕刑》)。
来表示一些特指的意思,并无切割之意,罗振玉的《殷墟书契》中所载的字形与上图(a)相同。而王国维的弟子朱芳圃所著的《甲骨学文字编》中所载的字形,即上图(b)、(c)才是阉人的象形体。有文献可考的资料中发现,在殷代,当时十分流行将战争中的俘虏“去势”后进行祭祀,也就是我们前面引述过的“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尚书·吕刑》)。
除了对待战败的俘虏以外,这种刑法的对象还有哪些呢?
《尚书·传》:“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尚书·吕刑正义》:“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
这是对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的严厉惩罚。
宫刑又称“椓”刑。《诗经·大雅·召曼》有“昏椓靡共”的诗句,郑玄注:“昏、椓,皆奄人也。”孔颖达疏:“此椓毁其阴,即割势是也。”这“势”与“阴”是相同的。《正字通》:“男子势曰阴”。此外,《史记·吕不韦传》中有“私求大阴人缪 为舍人”的说法。到了后来,这种仅次于死刑的刑罚就不单单用在“男女不以义交”的意义上,犯别的罪的人也可以处以宫刑。
为舍人”的说法。到了后来,这种仅次于死刑的刑罚就不单单用在“男女不以义交”的意义上,犯别的罪的人也可以处以宫刑。
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一文中写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7页)
有人从褚人获的《坚瓠续集》卷四中的“妇人幽闭”条目中得到启发。此条引明朝王兆云《碣石剩谈》:“妇人椓窍,椓字出《吕刑》,似与《舜典》‘宫刑’相同,男子去势,妇人幽闭是也。昔遇刑部员外许公,因言宫刑。许曰,‘五刑除大辟外,其四皆侵损其身,而身犹得以自便,亲属相聚也。况妇人课罪,每轻宥于男子,若以幽闭禁其终身,则反苦毒于男子矣。椓窍之法,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只能便溺,而人道永废也。是幽闭之说也。”这里也许是指运用外力使妇女的子宫脱垂而丧失其生殖功能。
以上的引述都表明,即使是在逻辑思维与科学技术都很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在互渗律的作用下,其法理的出现,也有一定的自然依据。
鲁迅先生指出:“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病后杂谈》,第137页)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
“法律的原则常常是隐含的,具有弹性的,并且是不断改变的。通过考察一个社会如何解决权利冲突或破坏规则的案例和特例,我们已经可以逐渐地了解一个社会的法律程序和原则。通过对这些案例判决的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出该社会的法律原则。”(《文化·社会·个人》R·M·基辛著,第383页)从树神崇拜引发对公众“利益”逆向行为的否定,用简单的模仿行为来操作否定的观念,到大面积地在敌对势力(俘虏)中来扩展这种有效的行为,然后再上升到法理的高度将这种行为系统化,这样的发展线索,体现了传统文化中人性结构的植物性生存状态。即使用严酷的手段使可能违背统治者利益的人们彻底丧失肉体冲动,通过这种“杀一儆百”的做法,将更多的人变成无知无欲、顺应环境和社会既定安排的“植物人”。就如孔子所说的:“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抱忠义,而不觉所以然也。……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论语·卫灵公》)
用简单的手法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如此复杂和具有破坏力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圣人推崇的所谓“简易之教”,也是名符其实的“害人之教”。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