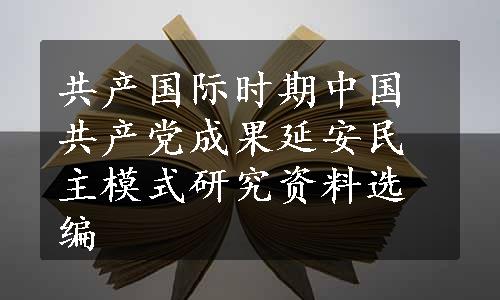
共产国际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
(1919~1943)
托尼·赛奇(Tony Saich)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改变了中国20世纪主要时期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1920年建立到1949年取得政权,国共斗争占据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一段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以来披露出大量的新文献,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过程的关键成分。新文献表明了中共如何解释由它扮演主角的革命,其政策怎样随环境变化而变化,而政策又怎样与党员和政府发生联系,以及中共怎样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复杂而重要的关系。对中共党员来说,这些信息不总是相同的,也不是对等的。一名党员对某一事件及其特殊解释知道多少,要看他在党内的地位。
当然,20世纪中国革命的细节是独特的,但是它的许多一般特征与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首先,传统帝制以及满清统治者不能为它的公民,尤其不能为城市精英和知识分子“提供福利”。人民觉醒了,帝国失去了选择余地,这是不满的知识分子开始挑战国家权力的前提。其次,地方精英的政权基础遭到破坏,丧失了压制反叛者的能力,使共产主义运动盛行起来。在这些地区,共产党人能够建立地方的军事优势。第三,对革命者来说,组织和组织理念是重要的,可以提供运动的方向和目的,使革命者获得理论,并使他们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引导其他社会力量,克服当地居民的阻力和冷漠。
本文将论述三个问题。首先讨论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中的一般问题。其次详述中共的发展以及它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我将追溯中共从一个密谋的小团体到武装夺取政权的发展。最后,对研究中共的一些关键的社会经济政治资料做出评估。
共产国际与中共:一般观察
在50年代,西方国家从中共受莫斯科监护的假定出发,试图发现革命初期共产国际影响中共的资料。这类资料不难找到。[2]一些西方学者把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的瓦解视为苏联政策的失败或斯大林本人的失败。[3]有趣的是,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的最新结论。[4]苏联学者同样有权利宣称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许多历史文献都提供了这样的结论。[5]1927年中国革命的大失败是苏俄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关键因素。托洛茨基本人深入分析了中共因屈从斯大林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而遭到的失败,这一分析影响了以后西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著述。[6]然而,托洛茨基对统一战线失败的分析,以及他告诫中共应与资产阶级绝交而去依靠工人阶级,同样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十分弱小,几乎没有形成。[7]
在西方学术界,施瓦兹(Schwartz)和施拉姆(Schram)是一个例外,他们反对把一场革命归之于苏联的观点。施瓦兹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曾受到布尔什维克理论的影响,但是他认识到了传统因素的作用和毛泽东的“创新”,以及1927年以后毛泽东的支持者日益壮大的事实。[8]中国共产主义中的本土因素后来成为挽救失败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在60年代初中苏分裂已明朗化之后。一些学者,如施拉姆,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强调许多事件的发生是因为无视共产国际的影响而不是由于这种影响。[9]
80年代和90年代披露的资料表明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持续不断的,中国对世界革命所持的立场不同于莫斯科基于苏联地理政治利益形成的看法。共产国际在中共的建党和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各个时期,它的权威并不总是被接受,即使接受了,也未必是决定性的。不过,直到1938年之前,共产国际的声音还是不能被忽略的,当时共产国际可以明确地表达意见,并通过通讯网把意见下达给中共领导。这些意见具有相当大的决定作用。共产国际制定中国政策的合法性成为王明的亲苏集团和毛泽东领导的更接近革命本土根源的集团之间斗争的关键。
最新一代的学者,历史学家德里克(Dirlik)认为,共产国际对锻造初生时期的党具有决定意义。[10]他的著作表明,共产国际的作用在于引入列宁主义,使中共得以排除原先更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11]相比之下,万德凡(Van de Ven)则强调共产主义运动的本土根源。他认为,不仅地方观念强烈地影响了中共头10年的历史,而且还出现了地域性的集团,如在四川,这些集团的存在与共产国际无关,他们甚至没有接触过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他表示,中共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艰苦过程才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变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12]叶文清(Yeh Wen-Hsin)也强调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本土性。她研究了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重要来源的杭州激进主义者,认为旧世界的黑暗而非新世界的启示引导这批人走上革命道路。但是,她不同意万德凡关于中共于20年代进化成为列宁主义政党的观点。按照她的见解,根本不存在进化问题,中共成为一支整体力量是以排除大多数早期党员为代价的。例如,施存统,叶文清著作的主要人物,因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而退党。20年代末,中共的基础是新党员,而老党员也因其经历而激进化了。[13]
正如上述,对于共产国际来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地区,因而中国政策成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冲突的焦点。直到30年代中期,中共还向共产国际派出常驻使团,而共产国际则试图通过其上海的远东局来协调自己的活动。[14]通过这些机构和代表,共产国际得以把自己的意志和政策贯彻到中国。
共产国际的机构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声望,但是必须找到中共党员才能传递命令,贯彻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总是远离他们试图影响和解释的现实。共产国际代表,从马林、鲍罗廷、罗易到弗拉基米洛夫,在把共产国际的政策运用于中国时,都失败了。[15]他们经常发现,共产国际根据意识形态确定的政策太简单,无法处理中国革命的复杂现实。共产国际的驻华机构因与莫斯科通讯困难而享有短期的决策自由,但是没有长期决策的自由。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偏好严重限制了根据本地情况调整政策的余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心在收到边缘地区送来的充满各种细节的过量信息时,试图按照基于流动的阶级阵容的简单公式编排信息和下达政策指令。有一个很好的案例。马林试图把列宁对殖民地国家革命下达的指示变成适合于中国的战略。这样一来,他不仅要为适应指示和意识形态的框架而解释现实,而且要推动中共与国民党的联合。在个别情况下,国际代表试图根据现实情况修正他们的任务,这又与共产国际的领导发生了冲突,后者把这种修正解释为“意识形态的背离”。
对共产国际代表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处在异国他乡,还因为他们必须通过他国的观点和经验解释现实。这些代表不会讲汉语,以前也没有在中国的工作经验。因此,他们依靠中国领袖向他们提供当地情况的信息。马林通过廖仲恺了解国民党的信息,以及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成员,国共合作的坚定支持者,这就使马林对国共合作采取了积极态度,从而低估了国民党中反对国共合作的力量。
而且,为了使这一决定能够被人理解,共产国际代表必须找到本地的“传递者”在中共内部宣传他们的观点。在一些场合,这是有效的,另一些场合则不然。例如,30年代初,米夫可以通过王明和博古批判李立三的政策,把革命活动重点保持在城市地区。相比之下,马林在试图促进国共合作时却常常失败。甚至在中共三大会议上支持马林国共合作立场的陈独秀,最初也拒绝过马林的建议。事实上,只是因为马林诉诸了共产国际的纪律,他才迫使陈独秀和中共其他重要领导人站在他一边,尽管还有其他原因。
共产国际代表在组织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成功地把他们的思想塞进了中国党员的头脑中,因为中共党员需要强大的组织,党内争论需要意识形态发挥作用。
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对于早期的中共领袖具有吸引力。[16]儒家官僚政治在1911年革命中的崩溃遗留下了中共领导人所感受到的组织真空,这可以用布尔什维克式的现代政党来填补。这种政党提供了一种可以超越领袖个人权威的制度形式,[17]以及有助于决策和执行的合理的层级结构。
20年代产生的许多中共领袖都痴迷于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他们感到这种组织形式可以挑战强调服从有力的个人领袖的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18]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把过去的传统体制简化为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即“皇权”。但是,以前的中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抽象的”制度所起的作用,而相对复杂的官僚体制也得到了发展。中共领袖在研究适当的组织形式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理论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胜过个人,但是从一开始,这种组织就与列宁密不可分。后来,最高领袖统治组织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变得明显起来。
此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似乎提供了不同于单个军阀或国民党统治的另一种选择。国民党组织于20年代初期的重建,是与列宁主义组织的领袖崇拜相联系的。孙中山是最高领袖,这个位置后来被蒋介石接受下来。至于中共,领袖支配组织体制的形成经历了较长时间,直到40年代毛泽东在中国西北陕甘宁根据地掌握最高权力时,才完成。[19]
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共党员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观念。首先,党的报刊翻译了主要著作,促进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
其次,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如维金斯基和马林经历过这样的党组织,曾用许多时间来宣传他们的观点。实际上,马林目睹了中共早期缺乏纪律的现象,他颇感惊奇。他提供了基于党组织的作用和思想,以及把宣传当作政治武器的信息。[20]而且,他强调中共的斗争与世界反帝斗争相连,是后者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照马林和后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说法,民族政党的利益应当从属于共产国际。
第三,20年代逐渐回来一批有影响的人物,像蔡和森,他曾在欧洲学习,熟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组织和现代工人运动。随着20年代的进步,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因中共骨干分子去苏俄访问或受训而得到加强。第一批中国学生于1921年春赴苏俄,20年代和30年代约有1000人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21]从苏俄回来的学生分为不同的团体,他们通过培训完全接受了党的组织和纪律的观念。他们当中有些人对中共以后的发展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如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22]
共产国际还影响了中共话语的形成和党内斗争的形式。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免除陈独秀的领袖职务一事,加强了共产国际已有的影响,以及把意识形态作为党内斗争武器的观念。陈独秀的免职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具有潜在损害性的事件。在许多人看来,陈独秀是进步的象征。这种看法不仅来自五四运动(1915~1919),也来自更早的反对帝制的斗争。许多早期领导人都因为与陈独秀的个人关系或忠实于他而入党。按照中国传统,攻击受尊重的长者是一个大问题。
陈独秀的免职是合法的,这不仅体现在对他的“错误”的批判上,而且因为援引的意识形态符号也维护这种攻击。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路线,产生了合法的政策,而理解这一“路线”则是进行领导的必要条件。其结果是加强了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控制,人们认为共产国际比一个国家的党具有“更高的智慧”,它能够洞察革命进程。同时党内争论受制于意识形态符号的操作,关于政策分歧的真实争论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可行性了。正如中共六届二中全会(1929年6月)决议所说,决没有什么党内和平。[23]错误倾向必须予以斗争。所有经常性的政策争论都被上升为路线斗争。因此,八七紧急会议(1927年)宣告了意识形态的正确,这是实施控制,进行领导和加强党内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因此,许多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内部争论被引入中国党。反对党的政策的人被贴上了标签,如“托派”,“无政府主义者”,“右倾分子”,“左”倾分子等。一旦贴上这样的标签,党中央便可以更容易地对付反对意见。“正确路线”也是党中央自己的推论。党中央很难在自己领导中认识错误,而政策失败则必须寻找一个“替罪羊”承担破坏党的正确路线的罪名。
选择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从一开始便具有掌握意识形态真理的倾向,而真理则源自党的组织形式。但是,在早期阶段这一倾向并不那么明显。中共成立之前,中国没有认真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选择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形式必然排除理论分析。因此,“在他们(党的创始人)看来,从组织上定义分析取代了理论分析”。[24]因此,人们假定来自苏俄的人或他们的代表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这一问题及其相关的政策需要。
值得我们注意的最后一个一般问题是,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取得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往的分析认为,毛泽东取得中共最高权力没有经过共产国际,[25]但是新发现的资料表明,共产国际至少愿意默认毛泽东的崛起以及他对党内敌手张国焘和王明(莫斯科自己的学生)的胜利。[26]在与张国焘、王明的斗争中,共产国际的言行有利于毛泽东而不是他的对手。共产国际是否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见,无关紧要。而且在许多场合,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不要模仿苏联经验,而应当制定自己的政策,共产国际七大(1935年)接受了各国党应拥有更多自由的意见。共产国际对最后形成的政策是否予以批准是一个不同的问题。1938年9月,共产国际通知中共,它批准了中共一年来的统一战线政策,当时毛泽东曾与王明竞争领导权,而现在中共已被毛泽东所掌握。当时,负责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宣布毛泽东应当比王明(人们认为此人是莫斯科最亲密的盟友)更有资格担任党的领袖。[27]因此,共产国际不反对毛泽东,毛泽东也未必反对共产国际。[28]
各个时期
(一)1920~1927:从知识分子团体到有组织的政党
中共早年是从一些不同的知识分子小团体发展成为更严格地组织起来的列宁主义政党的。这个过程充满了争论,最后第一批党员中的许多人离开了党,取代他们的人经历了20年代的城市斗争。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证实了这些冲突。然而,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通过对国民党的内部力量进行阶级分析,越来越不顾一切地要继续维护这种合作。
中共是五四反帝示威(1919年)中的知识分子动乱的直接产物。[29]在此之前,中共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帝制的崩溃和随后发生的社会政治真空。表面无害的武昌起义导致了清朝政府的下台,尽管发生复辟,但是帝制毕竟结束了。关注国家未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应当采取什么制度才能进入“现代世界”。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剧变和事件。由于王朝的垮台没有明确的继承人,局势的逻辑要求建立共和国。最初尝试是建立一个可预期的有效的议会共和国,但是在袁世凯统治下没有成功。同时,中央权威分崩离析,军阀主义兴起。[30]徒有其名的北京政府继续进行统治,试图取得外国政府的尊重,但是受到了许多变幻莫测的有实力的政治派别的影响。五四运动时,北京政局受段祺瑞和皖系的统治。段祺瑞及其支持者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植,这个事实在以反日著称的五四爱国运动时期破坏了段祺瑞的信誉。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是抗议凡尔赛和约把德国侵占的山东转交日本。群情激愤引发了1919年5月4日3000名抗议者走上北京街头。抗议起初是和平的,后以32名抗议者被捕而告终。后来披露出凡尔赛和约部分地依据北京政府与日本的一项协议,从而增加了段祺瑞的困境。而段祺瑞势力的发展也使他的敌人,奉系和直系联合起来向他进攻,把他驱逐出京。随后,北京政权由这两个政治派别分享。
同一时期,苏俄对中国产生了兴趣。[31]但是从1918年夏到1920年初,西伯利亚是反对中央的主战场,阻碍了苏俄与中国的接触。实际上,早在1920年初,俄国就向中国派出了首名代表进行调查和建立联系。1919年卡拉克罕声明(Karakhan Declaration)宣布放弃前沙皇在中国的特权,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国很容易做出这种宽宏大量的姿态,因为当时俄国远东的情势不允许俄国人表示任何承诺。但是,宣传好处是明显的,苏俄与仍然试图肢解中国的旧帝国主义列强划清了界限。
苏俄的姿态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知识上的吸引力,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希望更深入地理解十月革命。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布尔什维克革命证明了急剧改变不发达状况的可能性。这种向往苏俄的基本倾向,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发生兴趣,产生了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革命政党以便引导和控制将来活动的想法。
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8月)上制定了有关中国的政策框架,讨论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斗争怎样才能与世界革命战略结合起来的问题。列宁认识到了东方民族运动的意义,但不愿接受罗易观点。罗易希望把推翻资本主义的使命从“先进的”西方转移到“落后的”东方。[32]列宁认为,推翻帝国主义的运动是更广泛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民族斗争只有摧毁殖民制度才能取胜,因而是更广泛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为了推动这一运动,列宁认为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必须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暂时的联盟,同时保持自己的特征和独立性。显然,共产国际代表必须把这一战略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
1920年4月,维金斯基率团访问中国,送行的有布尔什维克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支部领导人V.D.Vilensky-Sibiryakov。这次行动经过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同意。除了熟悉人事和建立联系之外,代表团的任务是研究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可能性。维金斯基一行发现上海十分适宜培育布尔什维克的组织。[33]按照德里克的看法,此行恰逢其时,中国的激进运动已经达到了一个危机点,原先的思想和组织准备进入了死胡同。[34]维金斯基代表团与激进知识分子,北京的李大钊和上海的陈独秀建立了联系。他俩在讨论中已经涌现了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念头。[35]后来,1920年7月5日~7日北京召开了苏联共产主义者的中国工作会议,由Vilensky-Sibiryakov主持。会议研究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36]
有人已经指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不仅出乎意料,而且也不是因为维金斯基的召唤,而来自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社会所做的研究。后来中共的许多领导人都在“新民学会”、“觉悟社”、“互助社”等社团学习过。[37]这些社团是伴随清王朝的灭亡出现的社会激进化的产物,有些早期成员属于五四运动时期最激进的思想家。至于五四运动之前的社会主义,公正地说,这时和在这之后,已经普及了,成为知识分子中的时髦话题。[38]
五四运动体现了上个世纪对中国发达的传统文化的批判达到顶点。马克思主义不是运动中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思潮,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思潮。但是,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赞成这一思潮。最著名的人有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还有其他一些人,如李达,他在促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39]这些人在中国青年中特别是在大学生中享有的声望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在这里更早地赢得本应在其他场合赢得的听众。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许多知识分子最初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似乎对马克思主义及随后列宁主义变体的国际主义教条是一个讽刺,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民族救亡的可能。这一点对于理解随后的发展以及马列主义在中国所采取的极端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运动的重要刊物是《新青年》,它后来成为中共的机关报。[40]《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陈独秀任主编,正式撰稿人不仅有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如陈独秀本人和李大钊,也包括自由主义者胡适。所有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批判儒家的原则,代之以能使中国跻身于现代世界的政治社会实践。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是政治权力问题。对十月革命所持的立场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胡适和自由主义者拒绝把十月革命的价值观用于中国,而陈独秀和李大钊则同情十月革命,希望更多地了解十月革命的情况。正如迈斯纳(Meisner)所说,根本的区别在于中国问题应当通过政治革命还是缓慢的改良来解决。[41]
对于劳动问题不断增长的兴趣也有助于人们同情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期,城市无产阶级有了更多的政治觉悟,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虽然工人人数仍然不多,但是正在急剧增长,这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中国迟缓的现代化正在推进,因为战争使许多洋货的进口中止了。许多激进学生,如张国焘、罗章龙,对工人运动及其未来的发展产生了兴趣。两人开始在北京的铁路工人中从事组织工作,并成为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五四时期上海劳工的力量给中共领袖和工运活动家李立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吉斯诺(Chesneaux)和许多作家曾用适合中共口味的述语解释工人运动的发展,认为工人运动服从于中共的领导。[42]但是,上海的工人运动并不是从共产党人组织者到达后才开始的,中共必须经过斗争才能适应这个现实。正如佩利(Perry)所指出的,上海劳工继承了“集体行动的传统,并不总是轻易地适应外部组织者的计划”。[43]她的详尽研究表明工人对国共两党的建议和政策的反应随两党及其各自的政权而有所不同。
五四运动时期各城市中心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共产党组织的先驱。上海小组是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大约成立于1920年8月,[44]它是松散的,在第二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前承担着临时中央的职责。在上海小组的帮助下,建立了武汉小组(1920年9月)、济南小组(1920年11月~12月)和广州小组(1921年1月)。此外,北京(1920年10月)、长沙(1920年底至1921年初)、天津(1921年5月前)、香港(1921年5月前)和重庆(1920年3月)的小组也自称为共产主义者。[45]他们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他们遵照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甚至不意味着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共产主义的。例如,广州小组在陈独秀到达之前的9名成员中有7名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只有两名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Rosta通讯社的成员,即斯托亚洛夫斯基(Stoyanovich)和佩林(Perlin)。1921年1月,陈独秀到达广州,他的首要任务是改组小组,消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北京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这里的共产主义小组也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早期的共产党员李大钊和张国焘对此非常苦恼。[46]
虽然各地的组织结构和名称各不相同,但是一大召开时,各种共产党的组织在功能上分为三个层次。党的核心是处于非法状态的共产主义小组;然后是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是党的后备军;最后是可以公开露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们试图面对最广泛的听众。[47]
在中共一大之前,各小组的工作随地域的不同而不同,而工作强度也是如此。但是一般来说,为了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新生的小组投身于工运和宣传。例如,为了便于工作,上海小组分成了两个部门,劳动部和宣传部。而党的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协调的,1921年上半年,上海的工作甚至无法进行下去了。因为缺乏经费和人手,无法贯彻超额的工作量,而且新生的党怎样行动,也众说不一。这种情况构成了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的背景。出席大会的有13名代表,代表着53名党员。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的代表Nikolsky也出席了大会。
尽管共产国际出台了政策,还派出了代表,一大仍然采用了宗派性的亲无产阶级的路线,并激烈地反对与资产阶级进行任何合作。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感到,无产阶级太弱小,党应当集中于教育,研究其他办法,如遭到拒绝的社会民主主义。大会通过的“纲领”号召“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纲领”和“决议”在反对与其他政党、团体或“黄色知识分子阶层”联合问题上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48]工人运动被确定为党的工作中心,其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
党本身采取以本地代表会议为基础的秘密的等级结构。最高权力被授予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机构必须建立,而更分散的组织则拒绝这么做。它还有权监督和指导财政、出版和任何地方组织的政策。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选择了中央领导班子。这时党员很少,大会还是决定建立临时中央执行局负责各支部的联络等事项。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被选为执行局成员,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49]由于陈独秀缺席,周佛海成为他的代表。
中共一大的调门很高,工作进展却不大,仍然意见不一,经费困难,而新当选的总书记陈独秀直到8月中旬或9月才回到上海。但是,1921年11月,通过了一项工作计划,传达到了各地。[50]该计划试图使党的结构正规化,要求五个主要地区分别建立30人左右的区执行委员会。“正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应按党章的要求建立起来。计划强调了工运工作,要求各区至少应有一个受其控制的工会。重点是组织铁路工人,目标是建立全国铁路工会。
强调工人阶级和敌视资产阶级的独断立场与共产国际正在考虑的政策路线背道而驰,随后共产国际迫使中共与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进行合作。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试图说服中共。
中共承受的与其他阶级力量进行合作的压力,因马林的到来而增加了。一般来说,马林对中共的评价是悲观的,对以华南为基地的国民党却做出了积极的反应。[51]因此,马林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联合。无产阶级加入资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障碍是通过这样的断言排除的: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四种力量的结合,即知识分子阶层、海外爱国者、士兵和工人。
最初,这个观点完全被中共领导人所拒绝。陈独秀于1922年4月6日致信维金斯基表明了这一点。[52]但是,到1922年6月,中共的立场便明显改变了。这大概是马林和青年国际代表达林的影响开始起作用了。[53]中共开始宣传国民党是“革命的”,中共二大(1922年7月16-23日)决定通过暂时的联盟参加民主革命。[54]有一点非常重要,决议说“全国所有的革命政党”,不仅仅指国民党。但是,由于“民主因素”不体现无产阶级利益,中共决定促进独立的阶级运动。工运仍被视为中共的主要工作。二大文件要求工会代表全体工人,不管信仰什么,应教育他们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党被视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体现,而无产阶级的目的则被理解为推翻资本主义。大会还要求加强组织,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被奉为最有权力的机构,有权实施党的决定。现实情况相差很大,一些党员组成派别仍然是因为战略和策略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
大会赞成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外部合作,而不是马林所建议的“内部联合”。当马林(去莫斯科述职后)回到中国时,他发现他的政策受到多数人的反对。5人中央执委中有4人属于张国焘的“小集团”。“小集团”以劳动书记处为基础,反对与国民党进行合作。[55]
马林为了使大家接受他的主张召集了杭州会议(1922年8月28-30日),而第一次杭州会议是由中共召开的。为了克服多数人的异议,马林可以引述“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南代表的指示”。[56]这个文件是由拉狄克根据马林的叙述起草的,得到了后者的认可。共产国际的强制性纪律有助于使中共摆脱理想主义和排外主义,把资产阶级包括在一个临时联盟中。此外,马林用这个文件说服中共党员接受他的意见,加入国民党实行“内部联合”。会议要求个人加入国民党,同时保留中共党籍。中共可以在国民党内部指导工作,领导工运。马林所关心的是,中共拥有必要的生存自由,《向导周报》能够自由地批评国民党,使其能够采取更强的反帝行动。中共三大终于通过了马林所建议国共合作的路线,但是并没有消除党内的反对意见。[57]这个问题留给了鲍罗廷,他来中国是为了取代马林执行政策。
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时(1923年6月12~20日),党的状态很糟。[58]不仅党内因国共合作问题而闹对立,[59]而且1923年2月的广州铁路工人罢工遭到野蛮镇压,这一事件击碎了党对工人运动所怀的极高期望。[60]铁路工会,最好的共产党组织的毁灭,随后,工运遭到普遍打击,许多党员认识到单独的无产阶级力量太弱。陈独秀在三大上的工作报告反映了党内的沮丧,正如马林向共产国际所报告的那样。[61]
中央执委的人数增加到了9人,但是在第一次会议上只选出了一个5人的中央局代表中执委行使权力。中央局每周开一次会,而中执委每4个月开一次会。因此,实权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里。中执委还选出一位主席主持两个机关,处理党的日常事务和文件的秘书处和党的会计处。[62]
尽管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但是很快这个决议就不能顺利执行了,实际上它几乎根本无法执行。党的中央局决定回上海,因为它感到和孙中山在一起什么事也干不了。此外,中央局想在北方发展新的组织以便激烈地改变国民党内的主流意见,如果不行,便成立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政党。这与马林的想法背道而驰,尽管他也在设想一个没有孙中山作领袖的国民党。
对孙中山失望是因为孙中山执迷于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并反对改组国民党。同时也因为中共党员认为孙中山对北京局势漠不关心。1923年6月,由于曹锟的诡计,黎元洪失去民国总统一职。中共认为,这一权力真空为孙中山提供了一个去上海召集国民议会,从而成为民族运动领袖的绝好机会。但是孙中山拒绝这一建议,宣称不可能召开国民议会,并说当商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便会集结在他周围。
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一直存在着猜疑,而广东则是一个例外。鲍罗廷来广东后便致力发展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他承诺苏联将给予更大的财政支持,1924年1月最终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鲍罗廷遵照共产国际1923年1月和5月关于中国问题决议的一般框架行事。共产国际认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支持者。通过反对这些敌人,中共可以加强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力量,并在国民运动中更广泛地控制农运和工运。用斯大林的比喻来说,国民党右派将像挤柠檬那样被挤掉。大家公认,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早晚会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无产阶级的代表将停止暂时的合作,并夺取领导权。当这一刻来临时再做决定是非常困难的,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一下子就把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搞掉了。
起初,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党人小团体来说是非常成功的。1924年1月到1926年5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迅速增长。1925年1月,中共党员人数不到1000人,至1927年4月,便几乎达到了58000人。共产党人在城市地区影响的扩大来自民族主义的五卅运动(1925年)。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庇护有助于中共发展对农民的影响。彭湃建立的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63]
中共的成功是它失败的主要原因。一些国民党领导人将中共的成功视为对他们的革命领导权的真正威胁。农村不断发展的革命运动使这些国民党领导人不安,他们不愿意彻底打破传统的权力结构。事实上,中共被两个冲突的目标所困扰。一方面,它试图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来推动民族革命,另一方面,它又要推进社会革命,把这一革命指向国民党内的强大势力。当中共试图通过改造国民党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时,国民党内反对中共党员的力量便加强了。这场与中共的斗争以及对国共合作的重估,同时伴随着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矛盾的扩大,军权集中到了国民党内正在崛起的右派领袖蒋介石手中。
连续几次会议的文献证明,中共内部在国共合作的政策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但是,对合作所持的立场取决于中共党员工作的特殊环境。这种环境看来如此不同,陈独秀、维金斯基和党中央在上海工人中间从事着非法活动,而鲍罗廷和他周围共产党人则在广东国民党的保护下公开活动,并从事农民运动。1930年鲍罗廷在莫斯科就针对对他的反革命行为的指控做自我辩护时谈到了这一冲突。他说,“中国革命有两条路线”,一条在上海,一条在广东。[64]两个对立中心之间的摩擦在党受到国民党内敌人的威胁时瓦解了党的统一行动。陈独秀多次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并建立一个开放的国共联盟,而广州的党组织则要求接管国民党的领导权。使局势更为复杂的是,共产国际重申中共应坚持留在国民党内,同时加强自己在群众运动中的独立性。
苏俄愿意提供支持,以增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并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列宁主义政党。鲍罗廷被派去监督这项工作。与马林不同,他不仅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还受到苏联政府的委托,并代表俄共(布)。[65]鲍罗廷于1923年10月初到达广东后立即开展工作。第一项任务是改造国民党,经过努力,他赢得了孙中山的支持。鲍罗廷担任了孙中山于10月底成立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他提出了一份改造党的计划,开始筹备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是鲍罗廷提供了国民党章程草案。[66]
1924年下半年,北京政局的变化似乎为国民运动尤其是为孙中山发挥全国影响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1924年10月,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违抗命令,不再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反而与后者结成联盟,共同夺取了北京政权。其结果是吴佩孚和华北直系的倒台。孙中山应邀来首都参加讨论中国统一问题。孙中山打算建立一个包括群众组织代表、商团代表、反对吴佩孚的军队代表在内的国民议会。这正是1923年6月中共试图说服孙中山却没有被接受的建议。但是,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取代曹锟取得政权。他没有召开国民议会,却召集了“全国善后会议”。孙中山表示反对,因为该机构排除了群众组织而有利于军队。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开始,从而导致段祺瑞和国民党关系的断绝。
孙中山的北京之行在中共内部引起了分歧。陈独秀和反对此行的党中央认为孙中山应当留在广州巩固革命的成果。鲍罗廷和广州的共产党人认为孙中山应赴京扩大国民运动的影响。鲍罗廷的意见占了上风,中共开始公开地支持召开国民议会。
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1925年1月11~12日),尽管气氛很紧张,但是比三大乐观得多,代表们似乎预见到革命浪潮正在兴起。[67]尤其是,大会试图阐明中共与全国革命运动的关系,更明确地规定工运和农运政策,调整党的组织结构。
大会回顾了迄今为止的全国革命运动,试图正确地概括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68]许多党员发现既要在国民运动中发展国民党力量,又不能忽略中共自己的任务,两者很难取得平衡。这种紧张一直持续到1927年两党分裂。大会决议反映了陈独秀对中共卷入国民党的担心。“左”倾错误是继续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加入国民党和参加国民革命,担心中共成为一个“黄色政党”,而“右倾”错误却被定义为更具危险性。党员中有一倾向,认为集中力量搞国民运动和做国民党的工作意味着无视中共自己的任务。大会批判了这种倾向,将其视为一种劳资妥协的政策主张。
与1924年5月初的中共将国民党分为左派和右派的做法不同,现在大会发现了中间派。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和激进知识分子,右派的成分是军队、官僚,政客和资本家,中间派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革命力量。大会认为这个中间派很重要,虽然他们的数量不多,但是占据了国民党的领导位置。中共的任务是扩大国民党左派。但是这不能以忽略反帝和工农的经济斗争为代价。
大会决定把中共的力量仍然放在工人运动方面,认为这一运动正在进入一个可能获得发展机会的新阶段。决议把工人运动视为国民革命的支柱,却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工人运动的独立。[69]实际上这是批判广州的共产党人听任工人运动失去其独立性,大会说1924年5月的中执委扩大会议已经纠正了这一问题。
建立一个强大的劳工组织将确保中共在国民运动中起支配作用,正如中共自我定义为“工人阶级的领袖”。因此,中共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工会,加强阶级宣传。大会强调发挥车间党支部的作用,确保执行党的政策,并指导工会和工厂各小组的工作。今后所有工厂,只要有三名以上党员,就应建立党支部。
在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地区发展农民运动是中共三大迄今做出的最广泛的农民问题决议。[70]但是,大会没有制定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决议承认中国革命的农民特点,认为农民参加革命对于革命成功至关重要。决议表示支持国民党在南方的政策,同时又批评国民党把农民用于自己的目的。大会宣称国民党在其需要农民支持的地区组织农民协会,却不要求地主对农民做出让步,也不对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利提供足够的保护。决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明统战工作模棱两可的很好的案例。决议要求利用国民党的组织,接着又责备国民党,然后要求采取独立的行动。一些同志无疑会对他们如何适当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感到困惑。决议还批评了广州共产党人的政策,宣称他们对国民党角色的强调使农民怀疑自己的力量,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地位。这使农民对中共感到失望。
中共继续采取严格的组织体制,认为这是关系到党的“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党的领导人希望改善党组织将使党避免成为仅仅是“宣传小团体”的集合。尤其是,“组织决议”强调党支部作为党组织基本单位的作用。[71]为了吸收更多的工农分子入党,入党手续将放宽。以后,入党不必再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只要有“阶级觉悟”就可以直接入党。地方一级的党组织将得到扩大,5名党员必须成立一个小组的规定变成了3名党员就可以成立一个支部。对支部作用的强调标志着把地区为基础的党变成以职业为基础的党。为了控制党在其他组织如国民党中的活动,大会决定建立党团。
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改变了党的组织,它希望这些决定有助于党应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尽管北京会谈失败了,孙中山也逝世了(1925年3月12日),局势的变化比原来预期的更为激烈。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一场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众斗争,它为中共提供了迅速发展的机会,尤其在上海。但是,这场运动也使中共感到为难,它试图抓住新的形势,掌握住党员队伍。从1925年到1927年4月的这一时期标志着中共影响工人运动的高潮,也是上海受中共影响的各个组织发展的高潮。1922年10月成立的上海大学使中共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统一战线的保护下,一些重要人物,如邓中夏、瞿秋白,为工人运动输送了干部。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还在动员妇女组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2]
五卅运动源于上海1925年2月的一次反对日资纺织厂的罢工。[73]在经过几个月的熬煎后,5月15日厂方保安杀死了一位罢工者并打伤若干人,引发了动乱。5月28日一些人受伤或被捕,中共与其他组织号召5月30日举行联合示威。公共租借区的警察向示威者开火,打死10人,打伤和逮捕了许多人。中共为了控制运动,建立了上海总工会。上海总工会成立于6月1日,李立三任主席。上海运动一直持续到7月便开始降温,到9月中旬,总工会被强制关闭,中共领导人转入地下。这场运动还波及到其他城市,引起了1925年6月到1926年10月的省港大罢工。共产党人的影响由此而大增,中共党员数量从中共三大时的994人发展到1925年10月的3000人左右。
中共的反应是努力扩大自己的作用,使自己从“小团体”变成一个“集中的群众性政党”。1925年10月中执委会议决定进一步放宽入党手续。承认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必备条件,任何工厂工人都被认为是当然的党员。尽管与国民党的合作仍然坚持着,但是中共宣称国民党现在只有左派和右派,而右派越来越倾向于反革命。这次会议还在一定程度上提到了农民问题。[74]告农民书说,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土地国有。关于农民最低要求的8条纲领制定出来了。这个纲领根据的是南方的经验,发展了陈独秀早在1922年11月提出的主张。它要求承认农民协会,在农村经选举建立自治机构,由农会和自治机构规定最高地租和最低粮价,向农民提供无息贷款,向富农发行特别债券,成立农民自卫军。为了承认农民的作用,以前的工农委员会分成了工人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两家。[75]会议尽管强调了农民,但是仍然把工人阶级看作主要的革命力量。告农民书说,农民只有与工人阶级站在一起才能达到目的。
中共的成功和更具进攻性的组织和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内各派的担心,右派开始赢得对运动的控制,冲突在所难免。
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使冲突暴露出来。蒋介石下令戒严,他宣称共产党领导的中山舰正在策划对他的绑架。无论这件事真实与否,它为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剪除共产党人的机会。他软禁了约50名苏联顾问。鲍罗廷可以就释放他们进行谈判,但是蒋介石的要价很高。其中包括禁止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提供国民党内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单,放弃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独立组织。而且,中共党员不能再在国民党组织中担任领导人。最后这一条意味着共产党员谭平山必须把权力极大的组织部长一职交给蒋介石。鲍罗廷还要被迫支持北伐,而以前他曾反对北伐,以换取蒋介石对抑制国民党右派的承诺。[76]当然,蒋介石仍然要依靠苏联的军队和援助才能进行北伐,他宣布他最初的行动不是反对与苏俄的联盟。北伐于1926年正式开始,而一些军队向北开进的时间则要早一些。
这些事件加剧了共产党人的混乱。在公开场合,他们接受国民党中执委5月通过的规则,[77]但是私下却对这个倾向不满。显然广州地区的党提议立即反击蒋介石,接管国民党,而陈独秀却建议退出国民党。6月,他提出了一项折衷的建议,即继续实行国共合作,但这是外部合作,不是内部合作。但是,这一选择被共产国际制止了。
甚至1927年4月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之后,共产国际仍然拒绝中共退出与国民党的合作及相关政策。共产国际的政策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1926年12月)《关于中国问题的议题》规定的。它要求中共继续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夺取民族革命的胜利。[78]不允许国民党右派把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同时,《议题》要求中共控制社会革命。农村革命被定义为革命斗争的中心问题,共产党人在农村地区应通过农民协会取得“实权”。[79]按照《议题》的观点,担心农村阶级斗争将削弱反帝统一战线是没有道理的。在身处莫斯科的那些人看来,这一方式是可行的,但是中共却无法根据这些矛盾的要求行动。中共疏远了激进的农民领袖,试图制止“过火”,但同时又引起了国民党左派的敌意和怀疑。
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五大(1927年4月27日~5月9日)讨论了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的问题。[80]大会没有安排与国民党决裂的议题,而是讨论如何在没有令人苦恼的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推进农民运动。蒋介石的“背叛”是首要问题,这一事件被大会视为革命的预兆。陈独秀冗长而饶有兴趣地回顾四大以来党的工作,他说蒋介石的背叛把中国革命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81]按照他的观点,资产阶级现在离开了革命阵营,减少了革命阵营的数量,却提高了它的质量。四个阶级的联盟已变成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因此,今后的任务是加强这三个阶级和中共在军队中的工作。仍然留在革命阵营的少数资产阶级如果表现出“反革命倾向”,那就驱逐他们。
未来党的政策是在国民党区域中努力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虽然大会承认这个目标还很远。陈独秀认为,党应讨论夺取政权的准备工作,他认为中共不再是一个反对党了,而变成了一个真正开始领导革命的政党。
尽管发表了如此豪言壮语,中共仍然必须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来发挥作用。这就意味着农民政策仍然被错误地抛弃在一边,没收一切土地的观点也被拒绝。陈独秀评论说,过去农民运动的政策“太右倾”,而现在的错误是采取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的激进政策。
重新定义革命力量和温和的土地政策无助于中共摆脱困境。尽管限制了农民运动,但是仍然发生“过火”问题。中共完成了得罪所有人的工作,武汉的国民党政府指责共产党太过分,农民领袖指责中共不支持他们的激进行动,把他们交给军阀武装和国民党军队蹂躏。镇压共产党的活动仍在继续,1927年夏天的事件似乎嘲弄了中共领导人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决策。共产党人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国民革命的将军和政治家们一拨又一拨地“背叛革命”。
与国民党左派决裂的可能性由于莫斯科的来信而进一步减弱。斯大林由于要同托洛茨基做斗争,不可能承认与国民党继续合作的荒谬。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还从积极的方面解释了与蒋介石的决裂。它重申必须把农村的革命置于中心地位,但是只能以与国民党继续合作为条件。[82]
中共妥协政策的最高点是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两党关系的议决案。议决案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政府任职的共产党人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工作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在政府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将放弃他们的职务。而且,群众组织应交给国民党当局领导和控制。[83]后来,中共吞吞吐吐地表示要搞“外部合作”,而不是“内部合作”,而这是陈独秀以前多次提议过的。
顺从的姿态不能解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冲突。汪精卫怀疑共产党人于6月初已经动员起来了,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向他透露了斯大林一封电报的内容。电报要求共产党人改组左派,驱逐“反动的领导人”,准备切实地建立革命军队,尽管这一军队仍然服从国民党的领导。[84]
直到7月中旬,充满不安的休战还有继续,而局势则在急剧发展。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陈独秀辞去了总书记职务。[85]7月12日选出新的五人政治局临时常委会,第二天,它就发布了公开批评武汉政府的声明。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政治事务委员会声明停止合作;8月1日,中共南昌起义爆发;[86]8月5日,汪精卫开始大规模清除共产党人。国共合作以悲剧告终,这说明中共必须找到新的战略。
20年代早期,中共从事工运和摆脱封闭状态的能力受制于经费短缺和人手不足。在上海,外国人的出现甚至使工作更为难做。此外,中共的组织者必须在上海与其他已成立的工人组织进行竞争,共产党人的活动经常受到青红帮、甚至基督教青年会的破坏。而在广州,国民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掌握了更多的群众,具有更大的影响。1924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的总结说工人组织为“零”。
五卅运动和北伐为中共提供了打破封闭的机会。但是,问题还存在。中共缺乏基层组织人才,难以获得广泛的群众支持。许多新党员,由于入党手续的松懈,不能理解中共的原则。由于缺乏基层的劳动力,中共只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努力控制民族主义的运动。因此,中共在五卅运动开始时成立的上海总工会到1925年9月中旬就必须关闭。其部分原因在于缺少革命动力,也因为上海的其他组织对它的攻击。其实,陈独秀后来用粉饰的语气承认,上海运动实际上是由上海商会组织的,共产党人的影响微不足道。这种机会主义表现为试图接管既定组织的领导权,而不是建立坚强的基层支持。
这种战略的最初成功蒙蔽了中共领导人,特别是上海的领导人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共领导的受到反帝民族革命支持的革命似乎是可能的。因此,1926年5月,陈独秀感慨地宣称中共领导了125万工人。这一数字来自各组织的人数调查,他们的代表出席了第三届劳工大会。但是,中共没有创造出巨人,只创造了一个泥足的菩萨。当运动低潮来临时,上海工运工作中熟悉的问题重新浮现了:行会传统和青洪帮的影响依然存在。[87]
在20年代,中共没有在中国城市中建立起必要的支持基础,在南方农村也没有建立起坚强的支持。在这一时期,中共缺乏一贯的农村地区政策,原来实行激进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一刀切政策,而一旦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便采取了退让政策。但是,毛泽东仍然对农民政权印象深刻,他后来把农村组织与军队联系起来了。[88]与中共中央不同,毛泽东认为农民运动的“过火”对于克服战胜反革命势力和地主政权是必要的。他对整个革命战略提出了批评。他没有明确地宣称无产阶级领导权,他的报告集中论述贫农的角色和力量。
农民运动主要流行于鄂南、湖南、广东和江西。当北伐从国民党南方大本营出发时,大块农村地区受到国共两党的联合控制。在这里,农民协会建立起来了,它们通常在受过专门培训的农民组织者的领导之下。中共的支持者经营着许多农民协会,中共领导人把这一点视为控制农民运动的渠道。但是,像在中国城市一样,中共在农村地区也缺乏足够的地方干部。1926年7月的一份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报告提出了这个问题。大约80万农民参加了60个县的农民协会,但是只有600名党员在20个县工作。[89]因此,党与许多地方社区的联系是薄弱的。中共采取了与中国城市工人阶级相同的自上而下的人数调查办法,以便控制农民。因此,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谈到农村约有1000万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看来,他是把这种计算方式作为中共控制农民数量的依据。
但是,共产党人的出现是以国民党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一旦受到国民党的进攻,中共党员除了撤退到更边远的农村别无它法。中共由于历史短暂规模弱小不大可能建立足够的支持基础。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也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缺少数量和财政资源,也因为这么做必然加快与国民党特别是与国民党强大的右派势力发生冲突的步伐。
“第一次革命”的失败不是由僵硬地执行错误的共产国际政策直接引起的,也不是因为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或“机会主义”。造成失败的更直接的原因是中共没有能够在中国城市和农村获得真正的支持,没有建立起保卫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总是落后于中国的事变,常常把这些事变解释为下一次革命浪潮的预兆,认为这些预兆将会把历史引向正确的方向。当这些浪潮来临时,中共却不能引导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二)1927~1937:从城市革命到建立农村根据地
这一时期以两种不同倾向为标志。一种是不断尝试以城市为基础的革命的失败。在这些努力中,共产国际可以紧紧掌握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另一种是根据地的中共领导人不断增强的自主性,这些根据地建立于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位于华中和华南的一些地区。共产国际对党中央的控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使党组织任命赞成自己政策的领导人,另一方面,它必须摆脱每一次政策失败引起的谴责。[90]因此,来自共产国际的大量信件便责备中共领导人本人没有正确地执行甚至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根据地的生活提供了共产国际议程之外的学习经历。毛泽东从这些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形成了他和长征后到达西北的其他幸存者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下台后,最初的农民政策是激进化的。1927年7月,中共宣布革命进入了另一个新阶段,尽管各种迹象都显示相反的情况,它仍然说,革命正在进入高潮。[91]这种无视现实,认为革命趋势正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的观点在20年代最后几年不断得到重复。
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使共产国际紧紧控制了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这次会议评估了过去的政策,制定了新的战略,选出了党的新领导人。[92]会议标志着从国共合作战略到国共冲突战略的转变。前任中共领导人因其错误而受到谴责。这一点可以从会后发给党员的“通告信”和罗明纳兹对八七会议本身的评论中清楚地看出。[93]通告信说,机会主义错误在于对国民党和群众运动的态度,尤其没有充分支持乡村革命。它几乎没有提到今后的战略,强调了中共的唯一领导权,但是仍然要求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值得指出的是,继续合作的要求不仅来自斯大林要表明自己与托洛茨基的斗争绝对正确,而且也是由于中国的局势。国民党的重要成员还在支持中共,他们可能与共产主义事业站在一起。在国民党的中央领导中有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和邓演达,军队中有贺龙和叶挺。许多基层的国民党支部和军队也喜欢共产党人。[94]罗明纳兹在会议上的发言明显包括了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加以谴责的意图。按照他的说法,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建议无关,而在于中共没有把共产国际的指示贯彻到群众中去。[95]
关于组织问题,党准备转入地下,要求党员“铸造强大的、秘密的”组织。会议还强调了保存党在工会中的组织。会议在召开代表大会之前选出了9人临时政治局,接着产生了瞿秋白、李立三和苏兆征三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96]
会议制定了新的起义战略,试图发动军队兵变和农民起义,但不成功,反而进一步消耗了共产党人的力量。但是,失败没有打击中共的盲动(尤其是瞿秋白的盲动)。1927年11月出台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政策激进化了。对地主,无论大小,都不能手软,工人应该夺取工厂权力。这个决议导致了1927年12月广州公社起义的大失败。
广州公社的失败是紧接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发生的,这清楚地表明改变策略是必要的。瞿秋白领导的党中央不可能继续它的“盲动主义”了。中共失去了与上海、武昌和广州等中心城市工人阶级的联系。甚至在农民已经动员起来的地方,起义政策还试图恢复中共对无产阶级的领导,以便夺取大城市。这一办法的失败表明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还导致了共产国际对中共贯彻实际政策的影响急剧削弱。
代表大会需要重新评估过去和改变政策方向。因此,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开始了,为安全起见,它将在莫斯科召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97]这次大会有两个出发点。一是反抗国民党的军事政策是必要的,二是瞿秋白领导的不计后果的“盲动主义”不再显示任何真正的成功。毫不奇怪,共产国际的影响仍然起支配作用。“政治决议”把革命描绘成两个浪潮之间的低谷。[98]第一个浪潮由于“不断失败”而衰退了,新的浪潮还没有来临。这个观念既有利于攻击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又能支持未来的起义。[99]判断这些浪潮是困难的,而新的中共领导人则应在新高潮来临时抓住高亢活动的征兆。
运动发展浪潮性的概念不是六大的创新,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提出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判以前运动特别是广州公社的“过火”,同时坚持认为革命的进一步高涨是可能的。但是,这种高潮可能没有规律,因此,党必须当心不要让运动失去控制。确保协调的政策取代了建立群众组织。[100]
六大的主要贡献是把苏维埃作为武装起义推翻旧政治体制后建立的政府体制。大会把苏维埃当作全国的政府形式,而实际上,它意味着苏维埃将只统治农村地区。大会中保留了中共夺取大城市的意图,而社会现实则使大会更强调农民的革命作用。[101]党将与尽可能多的农民结成统一战线,其中包括中农。富农将受到压制,贫农将负责农民协会。大会强调农民游击战的重要性。它希望这将有助于稳步地扩大农村改革和工农革命军。但是,大会明确地说农民只能处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102]
六大建立了新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委员会由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央监察委员会由3名委员2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政治局成员来自7名中委:苏兆征(22票)、项英(22票)、向忠发(21票)、周恩来(21票)、瞿秋白(16票)、蔡和森(16票)和张国焘(10票)。在7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一名是李立三。政治局常委包括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瞿秋白、项英和蔡和森,候补政治局常委有李立三,徐锡根和杨殷。向忠发被选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大会提出党的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但是七大直到1945年才召开。
表面上看,六大似乎产生了一个适当的长期纲领。实际上,它给中共出了难题。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而中共却把夺取城市地区的无产阶级基地当作了至高无上的任务。而实现这些目标的机会,由于六大之后不久中国和苏联两国局势的急剧转变,变得更加困难了。
中国的局势正在朝着对中共多少有利的方向发展。在城市地区,中共正在缓慢地从国民党对它的镇压下以及它的几次起义失败中恢复过来,而在农村地区,自1928年以来,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正在稳步扩大,开始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动力。但是,各个苏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产生了不同的政策,这些苏区为了生存不得不同当地的社会团体实行妥协。
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的派别斗争更直接地影响了中共新的领导班子。虽然中共六大会议上流传着各种说法,但是布哈林仍然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指导大会。实际上,六大“政治决议”是以他在大会上所做的9个小时的讲话为基础的,新政治局把他的这些指示合并起来了。1928年底,布哈林成为斯大林攻击的主要对象,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
这就促使中共采取越来越“左”的政策,当这个政策达到顶峰时,又被共产国际反过来指责为立三路线。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共中央,声称新的革命高潮的征兆在中国已清晰可见,“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特别危险。[103]政治局接到信后很快起草了一份正式决议,阐述党怎样才能把国际路线贯彻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104]实际上,到1930年4月的这个时期是中共政策转变的独特阶段。
莫斯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继续影响着上海的党中央。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给中共中央来信,这一次是宣布“革命高潮的开始”。[105]中共应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新的革命高潮。共产国际再次推行自己的观点,即“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是党内最危险的倾向。政治局响应了这封信,于1929年12月20日和1930年1月11日做出决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立场,宣布更激烈地批判“右倾机会主义”。[106]
在“右倾机会主义”受攻击的第一批受害人中有1929年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刊登了开除他和其他许多人党籍的决定。陈独秀被指责为具有“托派”和“取消主义”倾向。然而,1927年7月以前陈独秀主政时,与托洛茨基没有特殊关系。他坚持对国民党妥协的立场,这一点,斯大林是认可的,而托洛茨基则持反对立场。当国民党左派也把矛头对准共产党以后,陈独秀对革命的分析开始接近托洛茨基的立场。他的转变,因他在党内的威望,而使党产生了危机,大清洗开始了。被开除的托派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叫“左翼反对派”。尽管如此,这个组织仍是一个小小的宗派,其影响十分有限。托派年谱的编纂者本顿(Gregor Benton)认为他们是中国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激进民主主义的不同政见者。但是,托派在党内和中国工人阶级中并没有什么持续的影响。除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托派内部还充满了个人意气。“中国反对派”不仅是国民党的敌人,也是中共的敌人,实际上,他们在中共方面的处境比他们在国民党方面的处境还要糟糕。[107]
不幸的是,被共产国际当作已经出现的革命高潮并不存在,至少在城市地区。共产国际坚持政治罢工和准备武装起义,这一主张,没有把无产阶级团结到共产主义事业上,反而疏远了他们。中共领导决定把农村正在兴起的苏维埃运动当作恢复自己在城市影响的工具。这个政策是在李立三领导下制定的,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做出决议,把目前阶段当作为一个革命高潮,主张夺取武汉,进而接管一省或数省的政权。[108]决议努力贯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意图,但是几个月后的失败却引来了苏联的严厉批判。
该决议曾上报共产国际批准,但是共产国际推迟了正式答复,部分原因是李立三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109]后来,共产国际批判了该决议关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相互依赖的观点。6月11日的决议认为,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最薄弱的环节,中国革命可以在世界革命和最后阶级战争爆发之前首先发生。这种观点可以在共产国际的下述说法中找到支持,即世界帝国主义的稳定性很快就会动摇,虽然这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如此,共产国际仍不愿意让李三立谈论世界革命。决议还暗示需要苏联的帮助,不久李立三便公开提出了这一要求。共产国际对此置之不理。争取苏联支持中国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要求后来被指责为“半托洛茨基”的错误。关于成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快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预言后来也被当作李立三托洛茨基倾向的证据。但是,这个预言是符合当时共产国际分析的。
7月16日,党中央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要求批准6月11日决议提出的战略。两天后,中共全国组织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宣布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并说中共是一个准备夺取政权的党。而且会议还要求中央和地方建立行动委员会。“红色区域”应当建立工农革命委员会,它将是唯一的领导机构。
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终于在一封信中对中共中央做出了答复。这封信引出了不同的解释。[110]它无论在一般政策上还是在实际战略上,都与李立三的观点没有根本分歧。但是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李立三运作的不满,指责他不能圆满执行年初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不像李立三那样愚勇地宣称世界革命即将来临,但也不敢排除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信件没有反对夺取武汉以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主张,但它似乎反对李立三“直接的全国范围的革命”理念。
李立三和党中央什么时候才知道共产国际的观点,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信件要花一两个月才能送到,而全部文件可能不会在9月初之前送到。但是,中共领导人已经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海远东局的电报于7月底知道了共产国际的意图。[111]
李立三知道多少,他什么时候明确地拒绝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这些都无法确定。8月6日,李立三主持中央行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号召全党动员进行直接革命。这时,共产国际才有了更明确的意见,认为李立三走得太远了。瞿秋白和周恩来被派往中国缓解李立三的过火,但是没有批判他的整个政策。从共同责任中摘清共产国际,无疑是很困难的。
共产国际原来所以忍住没有批判李立三,是因为战略还处在执行的过程中,一旦这个战略遭到失败,便引来了苛刻的谴责。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之间,李立三最强大的反对派是王明和“回国学生”团体。他们受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支持。[112]但是,反对派没有涉及现行和以后的政策,也没有对“左”倾路线提出不同意见。王明于6月11日决议之后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与李立三只有一点不同,即中国革命不必把世界革命作为自己的前提也能立即发生。[113]
当米夫和他在共产国际中的支持者对三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不满时,共产国际也开始采取了强硬的立场。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党员们发出一封信,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114]它给李立三戴上了“反共产国际”和“半托洛茨基”的帽子。米夫于1930年12月亲自来华提议尽快召集四中全会。1月7日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及其被保护者王明支配了这次会议。
在米夫指导下形成的四中全会决议对李立三进行了严厉的谴责。[115]李立三被指责为背叛了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造成了党的巨大损失。“‘立三路线’完全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互相矛盾,不过是‘左’倾的掩盖之下的机会主义和对于实际上真正革命地去组织群众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背叛国际路线有一点是真实的,共产国际自己抛弃了使用红军夺取城市的观点。
对于中国的新领导人来说,共产国际没有转向苏区,而是转向了王明和“归国学生”。政治局的根本变化是王明。四中全会前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成为政治局的正式委员。向忠发仍任总书记,实权则掌握在王明手里。[116]四中全会后几个月,“归国学生”的力量因提拔博古和张闻天而增强了。被新领导班子排挤的团体以工人活动家何孟雄和罗章龙为首。他们认为四中全会的政策正在损害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工人运动。他们成立了一个反对派组织,要求召开紧急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召回米夫。在无法解释的环境中,这个团体被出卖了,遭到英国警察的逮捕,后被移交给国民党处决了。[117]王明否认与出卖有牵连,但这对他是方便多了,等于把这个与工人有最密切关系的团体赶出了中共。
立三战略的失败不幸损害了中共在城市地区的力量,许多共产党要人遭到围捕,地下支部几乎全暴露了。这些年中共在上海的经历就像一部充满密探、中国的和外国的警察、秘密住址、以及与帮会打交道的惊险故事。但这是现实,中共党员经常遭到失败。自共产党人领导的上海起义把权力交给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又把枪口指向共产党人之后,此后一个时期的中共党史便是一部不断遭受镇压的历史。1927年4月中共在上海的党员约8000人,1934年下降到仅仅300人。[118]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损害也大致相当。1930年共产党人主持的组织有2000工人,1932年下降到500人,1934年则就变了一小撮儿。[119]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转向了国民党,对中共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顾顺章的情报使汉口、南京、天津、北京和上海的中共组织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是所谓“白色恐怖”。虽然周恩来暴露后逃离了上海,但是其他人却没有这样幸运。向忠发[120]于6月被捕,约40名其他中共高级干部连同800名基层党员也被捕了。[121]严厉的打击还导致了劳伦斯的被捕,他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国际联络部的主任。他公开的职务是泛太平洋工会总书记。劳伦斯和他的夫人被上海市警察局逮捕,严重地打击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尽管没有使工作完全中断。[122]
但是,正如施特拉马罕(Stranahan)所说,遭受严重挫折的中共仍然能够很好地在上海发挥作用。[123]日本的进攻和国民党的镇压给中共造成了存在的机会,使它扩大了十分有限的支持,中共开始渗透到各类组织中去,并建立起网络。这些组织包括“红色大众同盟”,以及中国救亡协会、自卫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等组织。上海党通过对这些组织的渗透,首次集中了力量,使自己的目标能够适应上海的政治社会环境。尽管力所不及,这些工作仍然使党获得了经验,并建立了有益的联系。1935年北京反日示威后,全国救亡运动发展起来。这意味着1937年国共统一战线恢复时上海仍然残存着可以派刘晓前去经营的组织。
这些情况增加了业已建立的根据地党组织的相对重要性。上海的党中央只剩下了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传递到苏区的联络职能。[124]实际上,1931年初,共产国际便指示中共中央研究一下迁往苏区的问题。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苏区,给上海留下了一个缺乏有效领导的党组织。还需要研究的是,留守上海的机构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
党中央越来越埋头于苏区的工作,不断向那里派送重要干部。1933年初,博古和党中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125]党中央开始迁往苏区的情况表明,合法领导革命运动的中心领导已转向苏区。但是,这个过程必然会产生冲突和摩擦。这并不是说,当党中央开始向江西苏区转移时,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便成为掌管中央的“归国学生”的直接的有意识的打击目标。
尽管城市地区受到镇压,但是1931年时中共的处境已大大好转。1927年的某一时刻,中共党员数量低于10000人。到1930年底,党员人数增长了10倍,而主要成份已从来自城市变成了来自农村苏区。对中共来说,这一发展趋势有赖于苏区根据地和红军的稳步扩大。除了毛泽东的江西苏区外,[126]重要的根据地还有贺龙的湘鄂西和徐向前的鄂豫皖。[127]由于蒋介石与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冲突,苏区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30年11月,蒋介石取得了胜利,而在10月时,他就对苏区发动了试图消灭共产党人的第一次“围剿”。虽然中共没有夺取一座大城市以及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红军的军事实力却得到了普遍的发展。
1931年11月,第一届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上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可以在全国统一调遣各分散力量的军事机构。毛泽东失去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他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苏维埃政府主席。[128]项英和张国焘被任命为他的副手。朱德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由彭德怀和王稼祥担任。大会制定了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的职能是行使“工农民主专政”。但是,苏维埃只是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伪装的一党专政。在边远农村,没有产业工人,无产阶级几乎全由农村手艺人、手工业者和农业劳动者构成。尽管如此,宪法还是宣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群众走向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应当在苏维埃中拥有更多的代表。[129]
大会通过的最重要的法律是《土地法》。[130]它缓和了以前的政策,但是其中急剧转向农民的倾向却疏远了许多人。这部法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证明了在特定环境中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怎样破坏了对中共的支持。中共刚到达江西时制定了间离中农和富农等团体的激进政策,这些人对中共生存极为重要。中共决定重新分配土地对于确保农民支持反对国民党的斗争至关重要,但是以严格的阶级定义为基础的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引起了不可预期的经济社会问题,这就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因此,苏维埃《土地法》比以前的政策规定了更多的自由,没有提土地国有化和集体化。它体现了向疏远的“中间阶级”寻求支持的审慎尝试。但是后来,1933年6~9月期间,许多“中农”又被重新定为“地主”,受到了严厉的对待。这正是蒋介石发动第四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政策的重新激进化开始于土地调查运动,其意图仍然是确保农民支持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共试图通过这一运动创造一个有利的革命环境,以达到政治军事目标。但是,土地所有权的不断改变引起了根据地的社会经济问题,过火行动经常发生。这就需要定期纠正,采取温和的或“纠左”的政策。因此,10月到11月期间,新“地主”又被降为“中农”。最后,1934年初,由于“富农”的进攻,政策再次激进化了。这种走马灯式的变动直到共产党军队退出根据地才中止。
1933年1月,当第四次“围剿”来到江西苏区时,博古领导的党中央残部也进入了这一地区。而鄂豫皖和湘鄂西两苏区已于1932年9月和10月分别丢失了。虽然江西苏区坚持住了,但是组织更好的第五次“围剿”又于1933年10月开始了。[131]对中共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时候,因为中共当时不仅正在从事土地调查运动,而且还在开展一场重要的党内斗争,即通常所说反对罗明路线。斗争罗明及其支持者,意在解决党的干部问题,以应对国民党的进攻。罗明自1932年3月以来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认为国民党的进攻造成了闽西的恐慌和疲惫。他责备党的领导机械地抵抗国民党,在所有地区使用同一种战术。他要求采取灵活多变的军事战术,以适应不同的情况。罗明无疑是指当地情况来说的,这就使党中央可以把他的观点解释为对整个党的政策的攻击。1933年2月,博古和党中央批判了所谓罗明路线,而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又暂时地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攻击他们的敌人。[132]在江西苏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受到了批判,受批判的还有邓小平。[133]
随着第五次“围剿”慢慢地收紧苏区,1934年1月15至18日,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正式成员和候补成员,以及各个省委的代表。从表述看,博古的政治报告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典型实例。[134]对博古来说,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他坚信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政策一贯正确。令人吃惊的是,五中全会上没有正式的军事报告,博古所说的基本任务,无非是继续反对拒绝看到大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没有遗忘,全会要求加强主要工业中心的党组织,尽全力“准备、组织、领导工人罢工”。党的整个力量将集中在“工厂和工会的罢工”上。此外,全会听取了陈云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经济斗争和工会工作的报告,对这个问题做了决议。[135]全会选举了新的政治局,吸收了毛泽东。这不同于以前人们所了解的情况。[136]
五中全会之后,紧接着召开了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党的领导有了一次鼓舞士气的机会。大会堂矗立了起来,开幕式上进行了阅兵,鸣放了礼炮。大会不遗余力地把苏维埃描绘成一个正式的全国性政权,而不是一个虚弱的地方的造反根据地。对国家地位的渴望反映在选举上,它再次补足了各人民委员部,其中包括一个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而且,大会提议所有苏区根据地将设立成省的建制。无论它们大小如何,也不管这一事实,它们只是国民党控制的大海中的一些孤岛,称省是名不符实的。大会终于谈到战争,号召红军把阵地战作为中心任务和基本战略。
这次会议没有提到中共面临的紧迫问题,即国民党“围剿”。苏区实际上是在1933年10月到达瑞金的奥托·布劳恩的军事控制之下。布劳恩最初试图从内线保卫根据地,后来他采取了“短促突击”的战术,这个办法也被用于对付国民党在“白区”的进攻。他希望把战争从苏区周围地区引开。但是,这个战术也失败了。1934年夏末,博古、周恩来和布劳恩制定了退出苏区的计划。这个计划非常机密,只逐渐地通知了其他领导人,并且限于需要知道的人。撤退的决定终于通过一篇文章公布了,标题冠冕堂皇:《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是张闻天起草的,刊登在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上。文章提出撤退和交出个别地方的苏区是为了赢得全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137]10月,中共开始了所谓的“战略转移”,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长征。留下来的党组织由项英领导,他还掌握着军务。此外,在陈毅领导下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这个办事处还负责指导留在中国南方前根据地游击队的斗争。[138]撤退开始时并不顺利。中共不知道向哪里开进。11月底的战斗使部队人员从出发时的86000人减少到了30000人左右。[139]
1935年1月红军到达贵州,有了一段休整的时间。在这紧要关头,1月15至18日在遵义召开了长征路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上升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开始。[140]会议议程是讨论当前局势和红军去向,但是后来转向了审议过去的政策,这预示着党的领导的变动。
会议上,博古和周恩来先发言,而毛泽东的讲话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批判了军事政策。在接下来的争论中,许多人都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张闻天起草了会议文件。[141]决议批评博古和布劳恩以前的错误,但是采取了妥协的方式。布劳恩固执地拒绝所有针对他的批评,而博古只愿意承认宣判的部分错误。会议通过了党的政治路线,军事失败被归咎于博古和布劳恩提出的“单纯阵地防御”的错误的军事路线。[142]
毛泽东进入五人书记处,另外4人是张闻天(总书记)、周恩来、陈云和博古。毛泽东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中共中央军事领导小组。周恩来成为主要决策者,毛泽东是他的主要助手。这就打破了布劳恩对军务的控制。毛泽东没有成为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军事委员会或政治局的主席,但是他成为党的最高的五人领袖之一,有权参与党和军队的一切决策。
长征期间,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主要挑战者是张国焘。张国焘不接受遵义会议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他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当时,他指挥着一支远比毛泽东强大的军队,这支红军有80000人,而毛泽东最多有20000人。但是张国焘被彻底打败了,[143]1937年初,在延安受到严厉批判。3月通过的一项党的决议批判了他过去的错误。当国共重新合作时,张国焘决定离开共产党人在延安的新家,于1938年4月加入了国民党。[144]
当红军还在长征途中时,共产国际影响中共的最后一项决定开始生效。这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8月)制定了一个新政策,要求联合所有力量、阶级和国家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个政策变化主要因为苏俄意识到了德国和日本日益增长的对它安全的威胁。
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把这个新政策贯彻到了中国。但是,应该指出,王明自己在思想上经历了从下层统一战线到上层统一战线的变化。[145]实际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已经促使中共中央于1933年1月建议改变在满洲地区的政策。[146]中共中央指示当地党组织如果保证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巩固,那么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合作是可能的。按照这封信的观点,这么做可以确保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莫斯科以中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名义发布的《八一宣言》(1935年)清楚地表明,中共将实行从内战到新统一战线的战略转变。[147]《宣言》声称“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责”。然后,它批评了蒋介石、阎锡山和张学良等“败类”和“卖国贼”采取不抵抗政策。如果国民党停止进攻,中共和苏维埃政府保证将与他们密切合作,保卫祖国免遭日本侵略,无论其他方面有何分歧。中共宣布愿意与所有人合作成立一个国防政府,这个政府将实行驱逐日本人的十大纲领。《八一宣言》明确表达了上层统一战线的政策。
由于长征途中与莫斯科的通讯极为困难,《宣言》什么时候传到中共中央手里,不十分清楚。当然,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名信使张浩到达陕北时,通讯便恢复了,但有迹象表明,《宣言》的有些内容,中共知道得要早一点。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的一份秘密命令反映了《八一宣言》的精神。[148]
1935年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讨论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含义。[149]会议决定以最广泛政治阵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这个阵线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和小地主的成员。党将努力争取这个联盟的领导权。新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将是以十大纲领为联合基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改名为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政策的转变反映和解姿态。政策变得温和了,富农将与其他成份享有相同的权利,不再被剥夺财产,而工商业者在苏区的投资也受到了欢迎。[150]会议还产生了一个与新路线相一致的军事决议,号召把内战与反日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反日斗争的力量。根据地将要扩大,与苏联联接起来,使两支军队能够共同反对日本。游击战的广泛运用反映了从不同于强调正规战的变化。[151]此外,入党标准也放松了,“左倾关门主义”被当作比“右倾机会主义”更大的危险。会议强调必须灵活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这也许是不点名地批评了博古、王明一伙儿。
尽管有了新的策略,中共仍然花了两年时间才接受蒋介石作为新统一战线的伙伴,而且这是蒋介石被自己的部下逮捕即通常所说的西安事变之后。中共与张学良指挥的威胁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的新家西北根据地的东北军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152]由于这一合作,中共降低了批评蒋介石的调子,并于1936年9月17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建议与蒋介石签署协议。[153]这显然是棘手的事情,决议经过精心设计。批评国民党没有停止,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没有放弃,但是决议指出,抗日呼声的高涨将迫使国民党参加这一斗争。中共提议成立民主共和国,其政府形式将比时下的苏维埃政府具有更普遍的民主,而比国民党政府具有更多的进步性。
在张学良看来,这种妥协必然与蒋介石坚持首先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立场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1936年12月,当蒋介石来西安督促根除共产党的战事时,被张学良绑架了,一周之后才被释放。值得指出的是,共产国际施加了尽可能的压力来劝说西安事件和平解决,并让释放之后的蒋介石领导全国抗日。
西安事变确实构成了内战时期与全国抗战的联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和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赫然揭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意图。随后的日本入侵和共产党的让步最终把蒋介石推入了合作。1937年8月,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军队作为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11月,留在华中的游击队更名为新四军。
(三)1937~1943:合作政治与根据地的强化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共产党军队提供了十分必要的喘息机会,[154]使他们可以公开活动,发展行政机构,最重要的是,可以从国民党那里取得财政拨款。但是,由于双方的不信任感难以去除,新的合作很快便出现了紧张。
一旦决定与国民党合作,毛泽东便开始考虑怎样在抗战中使用共产党的军队。中共准备发表一个要求国民党政权民主化的声明,而毛泽东则关心怎样保存军事实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但是,一些人担心过于消极的反应会破坏人民对中共的同情。最后,中共采纳了自卫和扩张的政策。
统一战线问题把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暗斗推到了前台,这是毛泽东掌管全党之前最后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在中国工作的毛泽东认为国民党不可能领导抗战,共产党必须保持独立性和主动性。相反,王明则更执着于统一战线政策,并且因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而受到指责。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其他7名成员,包括康生和陈云,到达延安的中共大本营。王明受到热烈的欢迎。毛泽东是第一次见到王明,故意说他是“从天上来的神仙”。[155]但是王明作为党内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也立即对毛泽东提出了挑战。王明做了以统一战线中应当采取什么立场的报告,毛泽东投了赞成票,部分地接受了这个报告,因为它显然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但是毛泽东对于怎样搞统一战线另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为了应对这些新来者引起的局面,政治局于12月9~14日召开了会议。会上,王明赢得了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树立了他的影响,虽然他的权力基础不强。王明发表重要讲话时,毛泽东保持沉默。王明12月27日的文章要求把一切工作都统一到著名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去。[156]这与毛泽东关于“独立性和主动性”的号召有明显差别。王明显然认为,他的主张是在边区之外开展党的工作的最佳途径。这种合作是长期的,在战后国家重建时期也要继续。他还号召统一战线应当扩大到两党之外,有效地动员其他抗战力量。虽然王明同意中共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但是他也坚持八路军保持自己的独立。
会议做出了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认为代表团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显然加强了王明的突出地位。事实上,组织上的变动却加强了毛泽东的地位。会议的另一个决议是尽快召集中共七大。为此成立了准备七大的25人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这反映了当时的权力关系,王明尽管有威望,但他肯定已经认识到了,他不能取代毛泽东。而且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决定取消总书记一职,以便鼓励集体领导。因此,张闻天失去了他的职务,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陈云和康生组织。[157]毛泽东保留了他担负的军委主席这一有影响的职务。
会议之后,王明在周恩来和博古的陪同下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一职。这使王明脱离了党中央,留下毛泽东同时经营党中央和军队总部。在武汉,王明开始执行与毛泽东根本不同的统一战线策略。最初,由于武汉情况复杂多变,王明的合作政策取得了成功,他利用合法活动的机会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
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冲突在1938年3月初于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达到了高峰。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共在中日战争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与12月会议的情况一样,王明发表了重要讲话,而毛泽东没有正式发言。但是毛泽东的反对立场使会议没有做出正式决议。王明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发表了,广为流传。
王明的报告指出统一战线将在“民族革命联盟”[158]的形式中巩固起来,这一形式类似于第一次统一战线,或者是一个各种党派都可以保持政治和组织独立的联邦。他强调必须“统一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统一作战”。他还强调国民党必须正式规定其他团体的合法活动。他提议建立国民大会,这样其他党派就可以协商,政府也可以认可和鼓励其他群众组织的发展。最后,王明指出,正确的军事战略应当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附之以游击战。
贬低游击战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而军事战略问题在以后几个月里,特别是在5月底徐州的沦陷危及武汉之后,具有了重要意义。还在4月份时,毛泽东就要求八路军在华北发展游击根据地,5月,他又强调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游击战,只有在十分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运动战。
这种政策冲突由于王明开始参与武汉保卫战而变得严重起来。5月14日,党中央指示新四军及其上级长江局把工作转移到农村地区,在那里建立游击队。[159]接着,1938年5月22日,党中央又指示河北、湖南和武汉的党组织在徐州沦陷后应致力于开展农村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最后,大多数学生、工人和革命者将回到家乡推动这一过程。这些指示使武汉党的工作外围化了。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王明在6月15日的公开演讲中承认武汉可能沦陷,他把马德里战役作为英勇保卫战的案例。王明主张在国民党领导下实行总动员,使日军在到达武汉之前就陷入运动战之中。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应被用于破坏敌人的供给线。
这些建议适得其反。因为国民党总是怀疑中共的群众动员,8月5日发布了限制各地群众组织活动的禁令。许多组织关闭了,中共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秘密警察的严格审查。王明通过法律手段扩大共产党人影响的努力最终失败了。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于日本之手,使王明在党内的声望又一次受到重大打击。
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中共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利用这次会议加强了他的优势。[160]这一优势因王稼祥带回莫斯科的消息而提高了。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9月指示的内容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指示批准了中共一年来在统一战线方面的政治路线,而季米特洛夫则全力支持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就戳穿了把王明当作“共产国际的人”的各种说法。实际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是在收到这一消息之后才决定召开六中全会。[161]武汉在会议期间失陷,使事情变得对毛泽东更为有利。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明确化了。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语气尖锐,因为王明这时因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而提前离会了。王明显然认为他已与毛泽东达成了妥协,他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作为政治策略家的毛泽东。
毛泽东不打算毁坏统一战线,他认为这有利于中共。因此,他在公开讲话中赞扬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162]毛泽东甚至说,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扮演着主要角色。阶级斗争不能损害全国抗战。毛泽东还建议“新民主共和国”将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为基础。这些都是王明能够衷心拥护的观点,王明甚至间接地颂扬毛泽东在中共的关键作用。
但是,随着王明的离去和武汉的陷落,毛泽东谈到另一个不同的问题。他谴责国民党不允许统一战线采取正确的组织形式,严厉地批评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163]他继续批评王明利用合法渠道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以及王明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战略。他明确表示,这是一个错误,其来源是苏维埃革命对王明的影响。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将从农村走向城市。[164]
会议决议没有严厉谴责王明的政策,也犯不着把这些不愉快的情况告诉普通党员而冒政治风险。毛泽东只要让党的高级干部知道就足够了。六中全会在沉重打击王明之后,立即改组了党的地方局体制,从而瓦解了王明的组织基础。11月9日,王明的长江局撤消了,他以前管辖的地区交给了两个新成立的局,即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和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
由于延安的党中央重新团结起来了,会议决定设立混乱时期的临时决策机构。此外,制定各级党组织在各自不同环境中怎样工作的规则也十分重要。因此,在具体组织问题上产生了三个决议。统一战线意味着中共可能脱离秘密状态,从事广泛的活动。这些活动将用于扩大党的影响,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投降主义”。关于工作规则和纪律的决议试图控制做出决策和传递信息的渠道。因此,决议禁止个人以党的名义讲话或发布个人名义的文件,除非得到中共中央或其他领导机关的授权。
决议重申中共中央是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最高机关,然后继续概括了行使实际权力的机构。当中共中央委员会休会时,由它选出的政治局领导工作。政治局至少每三个月开一次会。书记处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准备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书记处至少一周开一次会。这就把书记处摆到了强有力的地位,使它可以控制信息,并有效地控制议程。最重要的是,在各政治局会议之间,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不能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书记处可以做出新的决定,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它。只是事后书记处必须报政治局批准。[165]六中全会把毛泽东摆到控制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位置。
国共重新合作也使中国城市地区工作再次活跃起来。前面讲过,上海的党组织毁坏了,但是幸存的共产党员还在通过许多掩护组织继续活动,通过渗透其他组织从事爱国抗日工作。曾经负责“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利用这一新情况对中共以前的政策进行了全面批判。[166]他的见解当时曾遭到坚决拒绝,现在则加入了毛泽东后来对王明、博古控制的党的“左”倾的评价。
中共历史学家认为,1936年上海日资棉纺厂一定成功的罢工证明了刘少奇从阶级行动转向民族抗战的新政策是正确的。这次罢工是全国救亡协会领导的。该组织是以前成立的,曾是在组建许多不同群体的特定的救亡协会时形成的。事实上,中共在这个协会中的作用极小,但是这种方式很适合新的策略,而且协会将是中共战时重建活动的重点。[167]1936年12月的反日示威从北京开始,很快就波及上海,从而给予中共的新战略以极大的推动。[168]但是,日本人对上海的进攻意味着这种发展十分缓慢,中共很难协调自己的行动。然而,这对1945年内战爆发时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上海的中共党员人数从1937年11月的130人增长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的2000人以上。[169]
国共之间的新关系很快就黄了。因为中共开始扩大影响,与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冲突在中共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和第一次反共高潮”时(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以及1941年1月)达到了顶点。这些冲突没有结束统一战线,但是加强了毛泽东这个观点:中共不应只利用国民党这一条渠道。对毛泽东来说,统一战线比与蒋介石的联盟更重要。中共政策转向了孤立蒋介石,努力在反日同盟中扩大自己一方的力量。
这一因素再加上失去国民党的财政支持,使中共根据地的内部政策发生了变化。权力分享体制和适度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以便争取统一战线的其他力量。毛泽东告诉党的信徒们,制胜的“三个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170]在更公开的场合,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171]但是,这个文献公开声明中共要求领导革命。按照他的观点,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倾向。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责任。第一阶段是几个阶级的“革命民主专政”。在第二阶段,非无产阶级将逐渐地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进入它的社会主义阶段。虽然毛泽东说第一阶段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他对什么时候实行阶段转变讲得很含糊,他批评“左”倾分子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前就可以社会主义。然而,这篇文章确实进入了中共的政治议程。
按照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之前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观点,毛泽东勾勒了吸引非中共力量的适度的经济政策。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只要它不控制“国计民生”。在农村,提倡富农经济,只没收和分配“大地主”的土地。他把这个经济纲领描述得与孙中山思想相一致。[172]
较开放的调和的外部政策伴随着一场广泛的党内战役,战役的目的是清除现行政策的反对者,加强党的纪律,打击不同意见者,忠实于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对过去的分析和关于未来的观点。整党实际上始于1941年,直到1945年才完成。
在这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直接影响很小,如上所述,这种影响未必像许多学者以前所说,对毛泽东在党内的优势地位不利。共产国际影响的下降显然在于中共对共产国际的重要决定运用了一套解释方式。如上所说,毛泽东正是根据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对他表示默许支持的消息,才决定召开能够从政治上打败王明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对日作战不是孤立进行的,延安的中共领导不能完全忽视共产国际。在公开场合,毛泽东和中共全力支持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正如他们全力支持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样。但是,这两个事件使中共可以提出自己的有悖于苏联目标的路线。例如,中共对中立条约的评论认为,这一条约标志着苏联和平政策的又一次胜利。[173]他声称,这个条约决不会损害苏联对中国战争努力的支持。这个观点完全不同于蒋介石的立场。但是,中共利用了这个条约,把它当作提出自己观点的一个机会,称恢复鸭绿江以南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责任全在中国自己。尽管如此,中共也要被迫捍卫这样一个立场,即不再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民族主义要求。从中共的观点来看,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的入侵是一个幸运的解脱。苏联在资本主义战争中奉行的和平政策立场,一夜之间变成了苏联来领导反法西斯的斗争。
“资本主义强国”,如英国和美国,曾经“串通”鼓励日本南进之前进攻苏联,现在,必须把他们当作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日本对珍珠港的进攻把美国拉入了战争,使中共可以要求战争中的国际力量推进统一战线。中共迅速放弃了凭自己力量恢复全部领土的观点。
中共1941年12月9日的声明号召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反日反法西斯的阵线,它将包括所有反对日本的政府和人民。[174]现在,中共认为美国和英国将在打败日本和统一中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左的”倾向应当避免,所有党员都应与英美合作。
共产国际的决议(1943年5月15日)使中共摆脱了必须服从它的规定,再次肯定了对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已成为现实的东西,即中共应当继续根据自己的条件从事自己的革命。同时,这也去除了王明一伙儿可能获得的任何支持基础。共产国际的决议加上其他国内因素,促成了对毛泽东的崇拜。
中共收到这一消息之后,于5月26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做出了相关决定。[175]毫无疑问,这个决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解散的意见,它指出使本地共产党“更加民族化”将起到加强他们的作用。领导中心不再认为是必要的了,有趣的是,“决定”指出,共产国际从1935年起没有再干涉过中共事务。针对一些中国国内批评家说中共现在也到了解散时候的议论,“决定”进一步断言,没有共产国际,中共也将继续承担和加强自己的职责。
资料来源
中共1919年到1943年这一时期拥有丰富的研究资料,但是在许多领域还存在着揭秘问题。莫斯科档案的公布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目前的研究正在取得进展。
(一)档案类
莫斯科保存着中国革命的大量资料,特别是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The Russian Center for the Storing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即前中央党档案馆。
中央档案
北京温泉村的档案主要是中共的。它包括中共建党以来不同时期中共中央、下属组织和部门、革命团体和掩护组织的档案和相关文献。共有202个完整的卷宗,大约800万件。其中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共产国际的重要文献,共产国际的执委会、远东局和东方部,以及共青团国际和工会国际关于中国的决议、决定和声明。遗憾的是,控制很严,甚至连中国学者都很难接近它们,至于外国人要想阅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需要指出,中国各级行政系统都掌握着中共党史相关时期的档案。[176]
马林档案(The SneevlietArchives)
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档案有一部分是马林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和在华时期的文献。最重要的材料是马林向共产国际提供的有关中国局势、国共两党关系以及中共党内事务的报告。此外,还有马林对自己亲自参与的重大事件所做的解释。尤其有趣的是关于中共三大的解释。这些档案完全开放。涉及马林在华时期的最重要的材料由我发表了,见《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马林的角色》(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
调查局档案
台湾台北的档案由国民党掌握,1949年后从大陆送到台湾。这里包括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共地下活动的丰富文献,也有关于根据地活动的。这些档案都是国民党“围剿”红军时获得的。最后还有几套完整的报刊,里面载有关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文章,或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文献。这批档案现在完全对研究者开放。
(二)不同时代的中共报刊
以下为本文引用的这一时期中共最重要的报刊。
①《八路军军政杂志》:八路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1939年1月15日到1942年3月25日。
②《布尔塞维克》:中共中央机关的地下刊物,1927年10月24日出版,1932年7月停刊。最初是周刊,以后成为半月刊,最后是月刊。
③《党报》:中共第一份党内报纸。1923年11月30日出版,没有固定的出版商。什么时候停刊不祥,但是有一期是在1924年6月1日出版的。
④《斗争》:中央局机关的周刊,1933年2月创刊,广泛发行于各根据地。第73期于1934年9月30日出版。
⑤《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月刊,1920年11月7日创刊,第6期发行于1921年7月7日。
⑥《共产党人》:中共党内报纸,1939年10月20日创刊于延安,共出了9期,1941年8月停办。
⑦《红旗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1930年8月20日于上海创刊。从1931年3月9日起改为《红旗周报》。
⑧《红旗周报》:《红旗日报》的继续,始于1931年3月9日。1933年8月,改为半月报,1934年3月1日终于第64期。作为秘密报刊,它经常采取以伪装封面。
⑨《红色中华》: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办于瑞金。长征开始后,它实际上停办了,直到陕甘宁根据地才恢复。1937年1月29日改为《新中华报》。
⑩《解放》:初为中共中央机关的周刊,后改半月刊。1937年4月24日创刊,1944年5月停刊。总共出版了134期。
〇1《解放日报》:中共中央报纸,创办于1941年5月16日,根据地的主要报纸,垄断着新闻报道,1947年3月27日停办。
〇12《劳动者》:1920年10月3日创刊,1921年1月2日停刊。
〇13《列宁生活》:博古领导的上海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出现于1932年到1934年。
〇14《犁头》:广东农民协会机关报,1926年1月25日开办于广东省,最初每10天出一期,后来改为周报。最后一期,即第23期,出版于1927年1月7日。一般认为,它是亲中共的报纸。
〇15《先锋》:首期发行于1923年7月15日,1924年初停刊前只出了3期。
〇16《群众》:中共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公开周刊。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后来移到重庆。1946年6月开始在上海出版,1947年被国民党查封。1947年1月又在香港恢复每周的出版,直到1949年10月20日自动停刊。(www.zuozong.com)
〇17《实话》: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30年10月创刊于上海。后改为《红旗日报》。
〇18《向导周报》:1922年9月创办于上海,共出版过201期,1927年7月18日停办。
〇19《先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双周报,1922年1月15日创办,1923年8月15日停办。
〇20《新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对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有重要影响。最初叫《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现名。1920年9月起它开始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出版,中共成立后又作为中共的刊物出版。1922年7月暂停,1923年6月作为党的理论刊物恢复出版。1926年7月停刊。
〇21《新中华报》:在延安出版的中央苏维埃政府报纸,《红色中华》的继承者,创办于1937年1月29日。1939年1月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纸。共出版过230期,1941年5月15日停办。
〇2《中国农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月刊,1926年1月1日创刊。主编毛泽东。1926年12月暂时停办,但是1927年7月在汉口又恢复过一个很短的时期。
〇23《中国文化》:延安的理论月刊,1940年2月15日创刊,只经营到1941年8月20日。
(三)出版文献
中共的主要文献可以在《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和《六大以前》中找到(1952年和1981年版)。这两卷书最初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1年12月和1942年10月编辑出版的。它们是高级干部作为整风运动准备的学习材料。1980年后与党的新的历史决议相联系而进行了再版。再版时撤掉了读者可能在毛泽东著作中找到的毛泽东的文章。这些著作包含经过严格编辑的毛泽东的讲话。
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收藏,中央档案馆出版了14卷本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82~1987年)。这套选集提供了大量的没有公开过的资料。最近它才有了公开发行的版本。总共18卷(1989~1992年),时间跨度从1921年到1949年。就原版的细节等信息而言,18卷本比内部版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但是,它并没有包括所有的文件。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最重要的原始文件有3卷本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卷为1919~1928年(北京,1980年),第2卷为1929~1936年(北京,1982年),第3卷为1936~1943年(北京,1989年)。编辑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
近几年,中共开放了1949年以前的完整的毛泽东的选集,即5卷本的《毛泽东文集》(1993年,北京),从1921年到1949年。此外还有日本人Takeuchi Minoru编的20卷本《毛泽东集》(1983年,东京),以及10卷本的《毛泽东集,补卷》(1983~1986年,东京)。在英语方面,有施拉姆(Stuart Schram)和他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合作者大量承担的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著作编选本。沙佩(M.E.Sharpe)编的4卷本从1912年到1934年。这一系列的总标题是《毛泽东的权力道路,1912年到1949年的革命著作》
在英语方面,中共这一时期的最大文集是托尼·赛奇的《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兴起:文献和分析》(The Rise to Power of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Armonk,NY,1996)
本文已提到的重大事件实际上在中文文件的各种选集中都有。这些文件,主要但不是全部,是由中共党史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由党史资料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的。
(四)回忆录、传记和指南
不幸的是,大多数重要的中国事件亲历者在中国盛行写回忆录之前就去世了。但是还是有许多资源可资利用。
罗易(M.N.Roy)的《我在中国的经历》(My Experience in China,Calcutta,1945)十分有趣。而布劳恩(Otto Braun)的《中国的共产国际机构,1932~1939年》(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1932-1939,Stanford,1982)要差一点。王明的回忆录值得深入,但是应当谨慎对待他的《毛泽东的背叛》(Mao's Betrayal,Moscow,1979)。
张国焘的回忆录有大量的资料,但是也要谨慎对待。其他有趣的资料还有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北京,1986年)。这本著作对于研究中共的发展和高层政治如八七会议的情况具有特殊意义。伍修权的回忆录非常重要,它提供了党内亲苏集团怎样垮台的宝贵资料。伍修权是中共的翻译,他在30年代与共产国际代表接触密切。[177]还有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短篇回忆录,散见于专集和党史杂志之中。
在中共和共产国际的人物传记方面有胡华教授生前发起的《中共党史人物传》(西安,1980年到现在)。最初出了50卷,现在已有55卷。一般来说,这部系列传记的质量越写越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利用这部系列用得上陈玉堂的《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字号·笔名·化名》(北京,1985年)。这部词典包括有关共产主义运动主要人物的192个条目。每一个条目都提供了简历细节和别名等,以及这些别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使用过。其中最有用的就是别名索引。就较好的人物资料来说,有900页的《中国共产党人名辞典1921~1991》,它包含1万个杰出人物的简历。
在党的组织史方面,已出版了若干重要著作。有王健英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增订本,从一大到十四大)》(北京,1982年)。该参考书应结合赵生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1987年)来读。
(罗燕明译)
【注释】
[1]本文是托尼·赛奇先生为本书提供的专稿。
[2]参见Robert C.North,Moscow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Stanford,1953).
[3]见Conrad Brandt,Stalin's Failure in China(Cambridge,Mass,1958).1938年的一篇文章站在斯大林的立场上提出了这一指责,见Harold R.Isa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1961,Second Revised Edition).
[4]这些观点承认共产国际的中国路线在当时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声称1925~1927年期间犯了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些错误来自当时共产国际内的右倾倾向和总书记陈独秀“盲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5]参见R.A.Ulyanovsky(ed.),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Moscow,1979)and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and Communists in the East(Moscow,1990).
[6]参见L.Evans and R.Block(eds.),Leon Trotsky on China:Introduction by Peng Shu-tse(New York,1976).关于对中共失败的分析,参见Harold R.Isa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1961,Second Revised Edition).
[7]对这一时期工人运动最完整的分析,见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Stanford,1968).有一篇文章利用最新资料刻画了中国上海的劳动,见Elizabeth J.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1993).
[8]见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1979).
[9]施拉姆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以及在毛泽东人格上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影响,见Stuart R.Schram,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New York,1969).更新一些的观点见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Cambridge,1989).用冲突的观点分析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这方面的文章可看John W.Garver,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Oxford,1988)and“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113,March 1988,pp.29~59.
[10]中国学者Huang Xiurong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北京,1989年),第95~96页。
[11]见Arif 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Oxford,1989).关于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论述见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91).第五章研究了无政府主义在五四运动中的影响,第六章分析了2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别。
[12]见Hans 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91).
[13]见Wen-Hsin Yeh,Provincial Passages.Culture,Space,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96).
[14]大概1934年共产国际已经结束了在上海的活动。见Frederick S.Litten,“The Noulens Affair”,The China Quarterly,No.138,June 1994,p.508.
[15]关于马林的角色和他碰到的问题的研究,见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Alias Maring)(Leiden,1991)and“Interpreting China:The Case of Maring”,in Kurt Werner Radtke and Tony Saich(eds.),China's Modernisation.Westernisation and Acculturation(Stuttgart,1993),pp.59~82.对鲍罗廷在华工作的研究,首推Lydia Holubnychy未完成的著作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3~1925(New York,1979).布劳恩(Otto Braun)谈过自己在华的工作和挫折,见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1932~1939(Stanford,1982).还可参见M.N.Roy的回忆录:My Experiences in China(Calcutta,1945)and M.N.Roy's Memoirs(Bombay,1964),最后是Vladimirov在延安的挫折:The Vladimirov Diaries:Yenan,China,1942~1945(New York,1975).
[16]关于20年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介绍,除Dirlik和van de Ven外,还可看Michael Y.L.Luk,The Origins of Chinese Bolshevism.An Ideology in the Making,1920~1928(Hong Kong,1990).
[17]关于这个问题,参见Lawrence R.Sullivan,“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Doctrine,1921~1949,”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Leiden and Amsterdam,January 1990.
[18]见Sullivan,同上。Frederick C.Teiwes with Warren Sun饶有兴趣地分析了党的规范与毛泽东掌握最高权力之间的冲突:“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1937~1945”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New York,1995),pp.339~387.
[19]见David E.Apter and 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China(Cambridge,Mass.,1994).
[20]除与中共早期领导者经常接触的经历和参与各次会议的情况外,马林还公开了他在中共报刊上用孙铎的笔名发表的许多文章。他经常在《向导》发表文章。他在华发表的这些文章的英译本及其他著述,见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2,pp.737~836.
[21]这一数字也包括国民党党员。从1925年到1928年,该大学称作孙中山劳动者大学。第一批14名赴苏俄的学生来自上海外国语学校,这也是中共的一个据点。其详情见M.F.Yuriev and A.V.Pantsov,“Comintern,CPSU(B)and 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n R.Ulyanovsky(ed.),Revolutionary Democracy and Communists in the East,pp.283~333.作者估计,在1949年之前中共的118位领导人中间,约70%的人在苏俄学习过。
[22]也许还要加上康生,他接受了苏联秘密警察的培训,1975年逝世前在中国一直从事这项工作。关于康生,见仲康:《康生评传》(北京,1982年),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The Claws of the Dragon:Kang Sheng—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eople's China(New York,1992).
[23]此文献的英译本见Tony 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ocuments and Analysis(New York,1996),pp.386~400.
[24]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p.269.
[25]John E.Rue,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1927~1935(Stanford,1966).
[26]Teiwes and Sun在“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对此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27]王稼祥在1938年9月14日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这个信息。这就是说,毛泽东在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决定召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11月)。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85年)第10卷,第574~575页。还见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1987年)第145页。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总书记。
[28]毛泽东本人认为共产国际在1927年之前、1935年中期到1943年解散之间发挥着进步作用。
[29]五四运动的名称来自反对凡尔赛会议决定的示威,但是它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基础的政治文化复兴运动。关于这一事件及其知识分子和社会环境的出色分析,见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1960).关于五四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启迪作用的分析,见Vera Schwarcz,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86).
[30]关于袁世凯的研究,见Ernest P.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Ann Arbor,1977).军阀主义,见John E.Sheridan,“The Warlord Era:Politics and militarism Under the Peking Government,1916~1928,”in John King Fairbank,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Part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12,pp.284~321.
[31]关于苏联该时期的在华利益,见Allen S.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 1917~1924(New York,1954).
[32]相关资料见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New York,1977),1 and 2.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Der Zweite 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Hamburg,1921).对这次大会有关中国问题的分析,见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pp.12~22.
[33]Konstatin Shevelyov,“O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n Far Eastern Affairs,No.1,1981,p.129.
[34]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p.253.
[35]维金斯基显然没有明确指示建党,只是暗示等考察了中国局势之后再说。也许建党的想法在他到达中国之前已在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谈论过了。一种说法是,1920年初,陈独秀去南方时,与李大钊在北京到天津路上讨论了这一问题。见陈绍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综述》,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北京,1987年),上卷,第24页。
[36]Shevelyov,“O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130.
[37]关于这些社团和他们的政治化,见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pp.38~50.
[38]较早时期的情况,见Martin Bernal,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Ithaca,1976).关于20世纪初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起源、其乌托邦、革命理论、女权主义、文化和民族等主要理念的最详尽分析,Peter Zarrow,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1990).
[39]关于李大钊,见Maurice Meisner,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Cambridge,Mass.,1967).关于陈独秀,见Lee Feigon,Chen Duxiu: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Lawrenceville,1983).中共历史学家承认李达在建党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他早年的理论贡献。实际上,他主编了中共第一个正式刊物《共产党》。见Li Qiju编《共产党月刊与李达同志》,载《光明日报》1979年7月2日;《建党前后的李达同志》,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第15~31页。关于对他早期建党思想的评估,见Hans van de Ven,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Political Order,1920~1927(Harvard University: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1987),pp.62~65.关于他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见V.Burov,“Li Da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Ideas in China”,Far Eastern Affairs,No.3,1983,pp.102~113.
[40]1920年9月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报。
[41]Maurice Meisner,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42]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p.405 and passim.
[43]Perry,Shanghai on Strike,p.4.关于中国劳工待遇的细节,见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Stanford,1986)and Emily Honig,Sisters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1~1949(Stanford,1986).
[44]以前认为这个小组成立于5月,但是5月更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的日期。最近,一位中国学者认为,小组是6月成立的,因为发起党员施存统于1920年6月20日去了日本。但是,这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变化很快。很可能施存统和其他一些资料都是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共产主义团体的正式建立则是后来的事情。见Jin Liren,《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第一章,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第78~83页。
[45]关于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各组织成立的详情,见Tony Saich,“Through the Past Darkly:Some New Sources on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30,2,1986,pp.167~176。早期中共党员张太雷在一份报告中说,1921年5月1日,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武汉和香港等城市已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见《张太雷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报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史课题组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北京,1986年)第44页。显然,没有关于天津小组活动的资料。这份提交共产国际的报告提到了重庆小组的活动。需要指出,这个小组没有派代表参加一大,显然它是在脱离其他中心的情况下发展的。关于这份报告,见《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北京,1984年)第27~32页。对报告及其意义的分析,见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pp.73~75.
[46]8个创始成员中有6个是无政府主义者。
[47]关于所有这些组织的成立祥情,见Saich,“Through the Past Darkly”。
[48]See“The First Program of the CCP”and“The First Decision as to the Objects of the CCP,”in Ch'en Kung-po(Chen Gongbo),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An Essay Written in 1924 by Ch'en Kung-po(New York,1966).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Martin Wilbur.
[49]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北京,1982年)第2页。
[50]《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27~28.
[51]马林1922年7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清楚地显示这一点。见“Bericht des Genossen H.Maring fur die Executive,”V.Ravesteyn Papers,No.79,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52]这封信的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34.
[53]达林4至6月在广东帮助安排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在这一期间,他研究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行性问题。
[54]出席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代表着约195名党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和邓中夏入选中央执委,陈独秀任中央局主席,张国焘任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向警予入选候补执委,任妇女部长。Christina Kelly Gilmartin对中共的妇女政策和向警予的作用做了有趣的分析,见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Communist Politics,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95).她证明在共产党文献中树立一位妇女的声音并使之在上海党组织中有所表现,有多么困难。尽管发表了声明,党组织中仍然是由男性统治的。事实上,正是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二大上建立正式的妇女局。
[55]劳工书记处成立于1921年8月,马林起草了成立宣言。
[56]For the Text See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1,pp.328~339.
[57]后面将说到,大会之后怎样执行这一政策,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58]文献没有显示出席者的准确人数,各种回忆录又相互矛盾。较可靠的说法是30人左右,代表着420名党员。
[59]主要的对手是张国焘和蔡和森。争论之激烈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证实:决议仅以21票对16票勉强通过。
[60]1922年11月,党的中央局迁到北京,以便利用军阀吴佩孚的保护。吴佩孚被苏俄人民外交事务委员会视为“民主派”和进步力量,可被全国运动所推动。他曾支持工人运动,允许共产党进行宣传,其目的在于赢得民众支持,反对他的对手张作霖。但是,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会成立大会被军队破坏了。吴佩孚的士兵野蛮镇压了随后发生的罢工。第一手资料,可看罗章龙1923年3月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现载《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北京,1981年)第433~583页。2月,党中央决定离开北京迁回上海。在上海,3月底4月初党中央还在活动,但是决定赴广州在更宽松的环境中开展工作。
[61]陈独秀报告的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60~63.关于对国共合作的争论以及大会相关文献的分析,见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1,pp.175~186,2,pp.570~629.
[62]中央正式执委的得票如下:陈独秀(40),蔡和森(37),李大钊(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英(27),罗章龙(25)。还选出了候补执委5人。中央局的5名成员是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和罗章龙。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
[63]关于海陆丰苏维埃,见Fernando Galbiati,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Stanford,1985).
[64]“Istoricheskie korni chentusiuizma”(Historical Roots of Chen Duxiu-ism),Problemly Kitaia(Problems of China),No.3,1930,p.210,quoted in L.Holubnychy,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3~1925(New York,1979),pp.376~377.
[65]Holubnychy,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pp.254~256.
[66]《孙中山对弹劾共产党呈文之批示》,载《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1927年9月),《革命文献》1955年6月,第9卷,第2页。
[67]20名代表,代表着994名党员。维金斯基代表共产国际出席了会议。大会选出了9名成员的中央执委会,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和李维汉。5名候补执委。陈独秀被选为中执委的总书记,这一职务取代了原来的中央局委员长。
[68]《关于民主革命运动之议决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89年)第1卷,第329~341页。
[69]《对职工运动之议决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89年第1卷),第342~357页。
[70]《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同上,第386~364页。
[71]《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89年)第1卷,第379~382页。
[72]见Gilmartin,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p.134~136.这一运动也使中共在上海之外的广大地区扩大了它的妇女组织。尤其是在共产党支持下于1925年5月成立了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它有约1000名成员。
[73]详情见Richard W.Rigby,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Canberra,1980).
[74]对这次会议的分析和相关文献的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106~109 and pp.152~166.
[75]工人委员会由张国焘领导。农民委员会直到1926年11月才成立,它由毛泽东领导。此外,军事委员会也成立了,也由张国焘领导。
[76]C.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Y.How,Documents on Communism,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New York,1956),p.228.
[77]Ibid.,pp.225~27.
[78]这些“观点”见Jane Degras(ed.),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s(Oxford,1953),2,pp.336~348.
[79]毛泽东和彭湃追求的是半独立的政策。
[80]出席会议的80名代表,代表着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最重要的代表是印度人罗易。大会选出了29名正式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最高的组织形式是政治局,它有7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李维汉组成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仍担任总书记。
[81]《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共党史教学资料》第3期,第26~59页。英文摘译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228~243.
[82]See“Resolution of the Eighth ECCI Plenum on the China Question”,in Degras(ed.),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2,pp.384~390.
[83]见《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决议中最重要的内容已于1927年8月7日在一封信中转达到了全党。这封信是在下面将要讨论的八七会议上起草的,可以在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的《八七会议》(北京,1986年)第5~37页上找到。
[84]Xenia J.Eudin and Robert C.North,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1920~1927:A Documentary Survey(Stanford,1957),p.304 and Robert C.North and Xenia J.Eudin,M.N.Roy's Mission to China,p.107.
[85]按照张国焘的说法,陈独秀于1927年7月15日提交了一封辞职书。他辞职的理由据说是共产国际坚持中共发展自己的政策,同时又要中共不退出国民党,这是不可能的。Chang Kuo-t'ao(Zhang Guotao),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27(Lawrence,1971),1,pp.655 and 715.但是,这种说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完全一致。中共的中央机构已经改组了,陈独秀的领导权于1927年7月12日中止。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资料》(北京,1982年2月)第57~58页。
[86]这一天,8月1日标志着红军的创立,同时也是建军节。
[87]《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259~263页,以及Perry,Shanghai on Strike,passim.实际上4月12日镇压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行动是由各种流氓帮会执行的,其中有些帮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有联系。
[88]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Minoru Takeuchi编:《毛泽东集》(东京,1983年),第1卷,第207~249页。
[89]《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63~179页。
[90]显然,我们不能深入所有细节,只能把问题集中到李立三任领袖的案例上,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91]《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中策略》,见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的《八七会议》(北京,1986年)第84~89页。
[92]出席会议的有22名中共党员和3名苏联顾问。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召集会议。会议准备工作由瞿秋白、李维汉和张太雷共同承担。
[93]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296~313.
[94]这个判断多少不同于Conrad Brandt等人,他们把与国民党的继续合作归因于斯大林需要“隐藏掩盖他绝对正确的丑恶事实”。见Conrad Brandt,Benjamin Schwartz,and John King Fairbank,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New York,1966),p.98.
[95]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华是为了替换鲍罗廷和罗易。他参加起草了会议通过的“通告信”,于1927年底回苏。
[96]政治局委员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和任弼时。7名候补政治局委员中有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和张国焘。
[97]中共六大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建议是临时政治局主席瞿秋白、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提出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接受了这一建议。见Alexander Grigoriev and Konstatin Shevelyov,“On the 60thAnniversary of the 6th CPC Congress”,Far Eastern Affairs,No.5,1988,pp.81~82.出席六大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投票权的代表84人,他们代表着13万党员。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19~1990》(北京,1991年)第60页。这个数字是周恩来在向大会做报告时提出来的。
[98]《政治决议》,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初版于1941年延安,1952年和1981年于北京重印)上卷,第1~17页。英文摘要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341~358.
[99]陈独秀的政策被宣布为机会主义倾向。但是,瞿秋白的“左倾”被看作当时党内更大的危险。陈独秀后来被打成托派,下面还要讲到,他后来的观点确实更接近于托洛茨基,是中国托派的同情者。
[100]1928年2月的《中国问题决议》见Xenia J.Eudin and Robert Slusser(eds.),Soviet Foreign Policy,1928~1934;Documents and Materials(University Park,1967),pp.83~86.
[101]《农民问题决议》的摘要,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369~376.原文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第39~45页。
[102]实际上,党员的主要成分已逐渐变成了农民。大会期间的党员为130194名,据说其中76.6%是农民,工人只占10.9%,知识分子占7.2%,士兵占0.82%。这些数字是否可靠,是有争议的。
[10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历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北京,1982年)第2卷,第1~18页。
[104]《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关于中国党应针对目前形势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的训令的决议》,载中央党校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1978年)第2卷,第6~19页。决议日期为1929年5月15日。
[105]该信发表在1929年12月29日的《真理报》上。
[106]1929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见中央党校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523~529页;《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同上,第6卷,第1~11页。攻击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是陈独秀,他被恶意地宣布为“托派”和具有“取消主义”倾向。
[107]关于这一运动的分析,见Gregor Benton,China's Urban Revolutionaries: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otskyism,1921~1952(Atlantic highlands,NJ,1996);陈独秀给托派的信,见Gregor Benton(ed.),Chen Duxiu's Last Articles and Letters,1937~1942(Amsterdam,1995).反对者的回忆录,见Wang Fan-hsi(Wang Fanxi)Memoirs of a Chinese Revolutionar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regor Benton(New York,1991);不同的观点,见C.Cadart and Cheng Yingxiang,Memoires de Peng Shuzhi:L'Envol du Communisme en Chine(Memoirs of Peng Shuzhi:The Origins of Communism in China)(Paris,1983).
[108]《新的革命高潮与一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见《红旗》第121期,1930年7月19日,第1~4页。
[109]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代表确实在6月20日的信中做出了答复。他表示不同意决议,要求决议不要下发。这似乎激怒了李立三,使他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撤回这位代表,解散远东局。见Yang Yunruo:《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实,1919~1943》(北京,1983年),第86页。
[110]见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Cambridge,Mass.,1979),p.143:“除了责备政治局6月11日的信外,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23日的信实际上认可了中共的基本战略建议”; Hsiao Tso-liang,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1934(Seattle,1961),1,p.25:“仔细考察共产国际1930年7月23日的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的决议,将会发现超出时间限定和战术的差别”;and Robert Thornton,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28~1931(Seattle,1969),p.175:“共产国际的分析当时就戳穿了李立三理论的两可之处,李立三本来想利用这种含糊性坚持自己的立场。”
[111]1931年年初之前,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没有直接的电报往来。
[112]“归国学生”团体指从苏俄学习后回到中国的那些人。他们在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指来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28个布尔什维克”。米夫是他们的后台,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任职,并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理书记和中山大学校长,对这些学生有很大的影响。
[113]王明:《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载《布尔塞维克》,1930年6月5日。
[114]这封信通常指1930年11月16日的信,因为这是它到达中国的日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历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03~112页。
[115]《中共四中全会决议》,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第114~118页。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457~463.
[116]在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已批准了政治局成员名单。新政治局的成员有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云、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和王明。7名候补委员包括刘少奇和毛泽东。政治局常委有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
[117]罗章龙没有被捕。
[118]See Patricia Stranahan,Underground.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1927~1937(Lanham and Boulder,1998),pp.111 and 154.它出色地描述了国民党镇压时期的中共组织和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
[119]Perry,Shanghai on Strike,p.105.
[120]向忠发也叛党投了国民党。
[121]Frederic Wakeman,Jr.,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95),pp.151~156 and Stranahan,Underground,pp.116~118.
[122]在国际抗议活动之后,劳伦斯夫妇于1937年8月被释放,1939年7月离开中国。劳伦斯的真实名字叫Yakov Rudnik。远东局可能于1934年结束了工作。这一段激动人心的间谍工作,见Frederick S.Litten,“The Noulens Affair”,pp.492~512.
[123]See Stranahan,Underground,pp.147~184 On Which the Following is Based.
[124]Yang Yunruo,《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实,1919~1943》(北京,1983年)。
[125]这是公开出版物使用的日期,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所遵循。例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1987年)第91页。一些当代文献表明,党中央早在1931年初就开始迁往江西了。这只是说主要人物确实于1931年开始动迁,但是正式组织直到1933年1月才搬往江西。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在这一时期很大程度上已是没有工作效率的余部了。
[126]关于江西苏维埃的研究,见Derek Waller,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Mao and the Two National Congresses of 1931 and 1934(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73)and Trygve Lotveit,Chinese Communism 1931~1934.Experience in Civil Government(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No.16,1973).关于文献和分析,见Hsiao Tso-liang,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30~1934(Seattle,1961 and 1967),Two Volumes.
[127]鄂豫皖苏区,见Odoric Y.K.Wou,Mobilizing the Masses.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Stanford,1994),pp.98~162.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共与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互动,如工人、宗教团体、乡村精英、学生、知识分子、军人和农民。研究表明,中共怎样使自己的战略适应革命进程遇到的各种条件。
[128]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所有著述和有关1931~1934年苏维埃的分析,见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Volume IV,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1931~1934,Edited by Stuart R.Schram,Associate Editor Nancy J.Rhoades,Guest Associate Editor Stephen C.Averill(Armonk,NY,1997).
[12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见《红旗周报》第25卷,1931年12月4日,第2~7页。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552~556.
[130]《中华苏维埃土地法》,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第181~183页。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556~558.
[131]蒋介石亲自指挥,动用了100万军队。这是一场比以前更为周密的战役,逐渐地收紧了苏区。
[132]关于罗明的观点,见《对工作的一点意见》,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1982年)。关于党中央的回答,见《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第384~385页。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596~602.
[133]这不是江西苏区的第一次清洗。进攻长沙是夺取大城市计划的一部分,其役失败后,1930年夏天红军回到江西苏区。之后不久,毛泽东便与当地共产党力量发生了冲突。毛泽东利用江西苏维埃政府开始清洗江西行动委员会,该机构是1930年7月前成立的,其任务是执行李立三的起义政策。毛泽东的对手被指责为国民党秘密组织“AB团”(“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简称)的成员以及犯了“取消主义”的罪行。出于对清洗的不满,当地一支红军力量反叛了,于1930年12月初在富田村被残杀。双方都声称自己是按照意识形态的原则行事的,而实际上,这一冲突却表现为外来红军与本地共产党的冲突。在30年代和40年代,这种冲突模式在各根据地一再重复。关于富田事件的完整分析,见Stephen C.Averill,“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Armonk,NY,1995),pp.79~115.Averill指出AB团名称的来历是不确定的。虽然一般认为是指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但是它表示这个名称来自该组织的两级运作方式(“A”指省级,“B”指本地)。
[134]《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见《斗争》第47期,1934年2月16日,第1~16页。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609~622.
[135]该决议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50~70页。
[136]政治局可能有12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包括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和顾作霖。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刘少奇。五中全会成立了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其成员有博古、张闻天和周恩来三人。博古为总负责。
[137]《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见《红色中华》第239期,1934年9月29日,第1~2页。
[138]关于这支部队从留守到1937年被第二次国共合作所拯救的历史,见Gregor Benton,Mountain Fires.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 1934-1938(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92).
[139]对这段史诗般的事件所做的新闻式的描述,见Harrison E.Salisbury,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New York,1985);学术性的研究,见Benjamin Yang,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Chinese Communism on the Long March(Boulder,Colorado,1990).
[140]关于这次会议,见Thomas Kampen,“The Zunyi Conference and Further Steps in Mao's Rise to Power”,The China Quarterly,No.117,March 1989;Benjamin Yang,“The Zunyi Conference as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A Survey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106,June 1986;and the Much Earlier Jerome Ch'en,“Resolution of the Tsunyi Conference,”The China Quarterly,No.40,December 1965.参加遵义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和凯丰。7位军事领导人,布劳恩及其翻译伍修权也出席了。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可能担任会议记录。
[141]会议文件包括长决议和短决议。长决议可能是为向全党传达准备的,而短决议则是为高级干部准备的。
[142]短决议的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640~643.
[143]关于张国焘的失败,见David E.Apter and 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Cambridge,Mass.,1994),pp.39~49.
[144]关于张国焘丰富多彩但不完全可靠的自传,见Chang Kuo-t'ao,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Vol.1:1921~1927; Vol.2:1928-1938(Lawrence,Kansas,1971~1972).
[145]On This See Shum Kui-kwong,The Chinese Communists'Road to Power: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1935~1945)(Oxford,1988),pp.18~27.
[146]Shum认为这个政策来自王明的思想。见Shum Kui-kwong,The Chinese Communists'Road to Power,p.19.建议信见《中央给满洲各级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载《斗争》第18期,1933年6月15日,第1~5页,第19期,1933年7月19日,第14~16页,第20期,1933年8月5日,第14~16页。
[147]这个宣言是在8月的共产国际大会上提交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批准的,因此通常称作《八一宣言》。按照王明的说法,他起草宣言时正在从1935年6月的一场病中恢复过来。见Wang Ming,Mao's Betrayal(Moscow,1979),p.68.以前,这份宣言的来历曾引起过争论,现在很清楚,它是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的。
[148]《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561~571页。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698~705.
[149]出席人员大概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王稼祥、凯丰、邓发、李维汉、吴亮平、杨尚昆、奥托·布劳恩、郭洪涛和张浩。
[150]见张闻天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政治决议,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第734~745页。
[151]该决议,同上,第2卷,第286~289页。中共中央已于1935年11月21日就发展游击战争问题向陕甘地区做了通告。
[152]毛泽东领导他所控制的第一、三军团去了陕北,于1935年10月到达吴起镇。在这里,他与当地红军一起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当1937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时,这块地方成为陕甘宁边区。相反,张国焘和他的队伍南下成都平原,与国民党军队打了几仗之后,去了康川边。张国焘想在这里建立稳定的根据地,甚至要求人们承认这个地方是党中央。1937年2月,他在国民党手里又吃了败仗,最终他的部队迫使他北上与毛泽东和其他人汇合。
[153]决议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第779~782页。
[154]除陕甘宁边区外,还有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根据地。最近的研究揭示不仅各根据地的状况不同,而且同一块根据地内的各地情况也不相同。一般来说,研究表明中共本来就擅长微观政治,只要把自己的政策灵活地适应当地环境,就能成功地在当地扎根。相比之下,试图改变当地环境以适应先定的意识形态的做法则是不成功的。关于各类根据地的研究论文,见Saich,David S.G.Goodman,Pauline Keating,and Joseph W.Esherick in The China Quarterly,No.140,December 1994,pp.1000~1079;and the Essays in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Goldstein(eds.),Single Sparks.China's Rural Revolutions(Armonk,NY,1989.In Addition See Lyman van Slyke,“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in John King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Part 2(Cambridge,1986).关于陕甘宁边区,见Mark Selden,China in Revolution.The Yenan Way Revisited(Armonk,NY,1995);Pauline Keating,Two Revolutions: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vization in North Shaanxi,1934~1945(Canberra:Ph.D.Dissertation,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9);and David E.Apter and Tony Saich,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China.关于安徽和江苏根据地见Yung-fa Chen,Making Revoluti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1937~194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86).关于河南,见Odoric Y.K.Wou,Mobilizing the Masses,pp.165~327.关于晋察冀,见Kathleen Hartford,Step by Step:Reform,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Ch'a-Chi Border Region 1937~1945(Stanford:Ph.D.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80).关于晋冀鲁豫,见Ralph Thaxton,China Turned Right Side Up: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New Haven,1983).
[155]Shum,The Chinese Communists'Road to Power,p.114.
[156]见《挽救时局的关键》,载《王明言论选辑》(北京,1982年),第546~554页。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795~802.
[157]政治局的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王稼祥、博古、任弼时、陈云、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王明、邓发和凯丰。
[158]《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第923~939页。
[159]《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加强乡村游击战争和创立游击根据地问题给江苏省委的指示》,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512~513页。
[160]出席会议的代表共56人,会议主席团由12人组成,包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陈云、刘少奇、康生、彭德怀、博古和王明。
[161]王稼祥在9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这一消息。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批准了开除张国焘的党籍。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574~575页。
[162]毛泽东:《论新阶段》,见Takeuchi Minoru编:《毛泽东集》第6卷,第163~240页。
[163]《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1965年),第213~217页。
[164]《战争和战略问题》,同上,第219~234页。
[165]关于组织问题的三个决议,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第203~209页。
[166]刘少奇的批判在他给中共中央的四封信中,最重要的信,见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卷,第803~812页。
[167]Perry,Shanghai on Strike,pp.110~111.
[168]关于这个协会,见Parks M.Coble,“Th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 as a Political Party,”in Robert B.Jeans(ed.),Roads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Boulder,1992).
[169]Ibid.,p.117.
[170]见《〈共产党人〉发刊词》,载Takeuchi Minoru编:《毛泽东集》第7卷,第69~83页。
[171]《新民主的政治与新民主的文化》,见《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1日。
[172]关于毛泽东对经济政策的极广泛的分析,见Andrew Watson,Mao Zedong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order Region:A Translation of Mao'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ble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173]该评论见《新中华报》第16期,1941年4月16日。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963~965.
[174]见1941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See Jiefang ribao(Liberation Daily),10 December 1941.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965~966.
[175]见1943年5月27日《解放日报》。英译文见Saich,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p.1143~1145.
[176]See William W.Moss,“Dang'an: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ives,”in The China Quarterly,No.145,March 1996,pp.112~129.
[177]这些回忆录分四个部分载于《中共党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114~179页;1982年第2期第168~218页;1982年第4期第50~135页;1983年第7期第143~22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