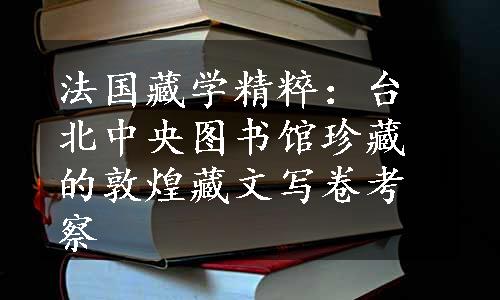
吴其昱
“台北中央图书馆”收藏有4卷敦煌藏文佛经写本,而且还是保存在该馆的敦煌汉文写本特藏中②。这4卷敦煌卷子的编号依次为:第7521、7550、7549和7547号。根据这些写本的影印件,我才得以进行考证,并作出如下解释:
一、第7521号敦煌卷子
本文献是用正楷字抄写在3页灰褐色的纸上的,而且还是首尾相衔地粘贴了起来,用横线格共分成了6页。前5页中各自包括21行,而第6页则仅有17行,这样算来,这6页就共包括122行,其中有一行为写本的跋。
该藏文卷子在一开始(第1行)就指出了其梵文标题:a pa ri mi tn a yur na ma ma ha ya na su tra(Aparimitāyur nāma mahāyāna sūtra,即《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在写本的起始(第1页,第2行)末(第6页,第16行)中两次提到了其藏文标题:
这部经文的一卷写本已由福田精斋以《西藏古写经》为题而影印发表,由于笔者无法与作者直接联系,所以只能约估可能是1926年左右在东京发表的。保存在伦敦的另外两卷写本已由科诺参照梵文与于阗文文本而发表在《大乘无量寿经》中,载霍恩尔所编辑的《东突厥斯坦佛经文献残卷》第1卷,第289—329页中了,于1916年在牛津大学出版③。
这卷佛经写本同样也被收入到《西藏大藏经》中了,见北京版本的《甘珠尔》中的《续部》(怛特罗),第16卷,见第243页背面,第6行,第249页正面,第5行;另一种译文载第16卷,见第249页正面,第5行,第254页正面,第2行;日本东京—京都于1956—1961年重版的北京版本的《西藏大藏经》,第361和362号,第7卷,第30l、303和305页。
我想在这里指出《大乘无量寿经》,这批写本,与科诺版本有一些重要的文字歧異处:(1)在台北中央国立图书馆所藏的第7521、7550和7549号敦煌卷子中,缺少了科诺版本第8—11、19和31段;(2)其汉译文的译师情况不详(《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卷,第936—937号),我们的藏文卷子中的《陀罗尼经》共多了16个音节;…tad dya(thva)tha(ta tha ga ta ya之后)…ga gna sa mu dga’te sva hba bha bi cuddhe(在第7521号卷子中为de,位于dhai ma te之后);(3)在第7550号和7549号敦煌卷子中,《陀罗尼经》共出现了24次,但在第7521号卷子中则缺少了第30段,《陀罗尼经》在其中共重复了23次。
在1924—1928年东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中,该经文的各种汉译本分别编入了第19卷中的第936和937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一卷,其译者的情况不详(可能为780—850年之间的人士);《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径》,一卷,译者是法天(973年)。请参阅《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卷,第1389号:《佛说无量寿大智陀罗尼经》,第907页;第19卷,第1000号:《成就妙法莲华经王瑜伽观智仪轨》第596页。
第6页的第17行记载了其抄写者的姓名:“()”,即由“(?)所抄写”④
但是,这一行的开始部分被一篇由反向印刷的文献所掩盖起来了,我在其中发现了3尊佛陀的圣像,而在佛像的上下部分则是一篇文献,肯定为梵文文献,但已经很难辨认了⑤。
二、第7550号敦煌卷子
三、第7549号敦煌卷子
第7550号敦煌卷子中包括一页灰褐色的纸,也就是说用横格线划分成了两页。第1页中包含有17行文字,而第2页中则有18行。第7549号卷子中包含有两叶灰褐色的纸,也就是说共有6页。前5页中各包括有18行文字,这样算起来,全部经文就共有128行,其中有两行为卷子的跋。
这两卷写本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第7550号敦煌卷子抄录了经文的起始部分,而第7549号卷子则抄录了经文的其余部分。从两卷写本中所使用的方块字来看,他们似乎是由同一人所抄,而且原来还可能是属于同一卷写本。
第7550号卷子的开始部分(第1行)提到了原经文的梵文标题:
a pa ri myi tha a yu na ma ha na ya na su tra(Aparimitā-yur nāma mahāyāna sūtra)。
第7550号敦煌卷子从第13行(第1页)开始,就提到了经文的藏文名称,在全文的末尾(第7549号敦煌卷子,第6页,第3行)中再度重复出现:
有关该经文的出版发行情况,见第7521号卷子中的第1段。
文尾还附有一位抄经师和数位校对者的姓名(分别见第6行和第9行):
(意为由周殿公(?)所抄写)⑥。
(头校为比丘法成(?),二校为法慈(?),三校为白乔)⑦。
四、第7547号敦煌卷子
这是一叶灰色的纸,也就是说是由横格线分成了两页。这两页中各包括15行文字,用方块字所抄写。
经文在开始部分(第1页,第1—2行)提到了其藏文标题。
《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也就是梵文的atasāhasrika-prajāparamitā,见第4节,第31卷⑧。
经文的末尾意为:“五根⑨与(五)根是不可分割(前者与后者相分离)的吗?”该文献已收入了《西藏大藏经》(北京版本的《甘珠尔》中的《般若经》第37卷和第256卷的开始部分,第267页正面第4行至第267页背面第6行;东京—京都重版的北京版本第730号,第17卷,第71页⑩。
《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藏文本的译者是:胜友、天帝觉和益西岱(智军),那塘版本的《甘珠尔》第26卷,《般若经》第4卷,第536页正面第5行中都提到过这些人名。参阅M·拉露小姐:《〈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藏译文本》,载《亚细亚学报》第214卷,1929年7—9月,第87—102页,尤其是第91页。
该经文的汉译文本则相当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由玄奘在660—663年间所译,第354卷:《初分》;第61卷:《多问不二品》(四),即《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0号,第6卷,第821页,第5—27行。经文的末尾部分则相当于:“五根……于……(五根)……为远离为不远离?”
这4卷写本中的两卷在敦煌的佛经写本中最为常见。除了梵文文本之外,还有藏文和汉文译文。梵文本的《大乘无量寿经》是晚期佛教中的密宗经典,曾先后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如和阗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和西夏文 。从这些写本语音转写方面的古老性、书写风格方面的独特性以及抄写者和校对者名字的拼写特点来看,所有这一切似乎完全可以证明它们均系年代久远的古老写本。一般来说,敦煌写本是藏文文献最古老版本的代表作,他们对研究西藏的历史文献中的语言学和佛教学都具有重大意义。
。从这些写本语音转写方面的古老性、书写风格方面的独特性以及抄写者和校对者名字的拼写特点来看,所有这一切似乎完全可以证明它们均系年代久远的古老写本。一般来说,敦煌写本是藏文文献最古老版本的代表作,他们对研究西藏的历史文献中的语言学和佛教学都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www.zuozong.com)
①1968年仲夏,承蒙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潘重规教授之美意,盛情地为我寄来了这4卷敦煌藏文佛经写本的影印复制件。数日之后,我又复函相告,本人对这些文献的考证。他于1968年8月1日在香港的《新亚学报》第8卷,第2期,第321—373页中发表了《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卷子题记》一文,文中提到了我的考证意见(详见潘重规文,第350—352页中有关这4卷写本的题记)。本文主要是以笔者1968年的考证结果为基础而撰写的,但更为完整详尽一些。在本文得幸发表之际,我再次向潘重规先生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他费心劳神地寄来了这4卷写本的影印件,从而才使我得以撰写此文。我同样也要向阿旺扎巴先生表示感谢,他非常盛情和友好地帮助我解决了第7548号卷子中一些难度较大的段落。
②据潘重规先生的前引文所披露,“台北中央图书馆”中的一大部分敦煌卷子是在上海(很可能还有香港)购买而来的,购置的时间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更具体地说是1940—1949年)。这批卷子有的是被李盛铎(1860—1937年)的女儿出卖的,有的是由叶恭绰及其女儿抛售的。
③1916年还曾发表过有关这一文献的两部著作,这就是:一、瓦勒赛:《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这是根据在尼泊尔发现的梵文手稿和藏汉文本译出,发表在《海德耳堡科学院会议纪要》,语言历史类,1916年度,第12册,附录部分;二、池田澄达,《梵文、臧文和汉文本的〈陀罗尼经〉校合》,载《宗教研究》杂志(旧编)第1—3期,1616年东京版,第649—564页。有关对该经文的汉译文的研究情况,见矢吹庆辉:《鸣沙余韵(解说)》,第2卷,第139—155页,1933年东京版。参阅《鸣沙余韵》中的图版第68,1930年东京版。
④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中,我们于Pt.第988和992号卷子之内发现了一个人名为________;在第1429号写本中又发现了de'u kon-che一名;在第987号写本中出现的则是________一名。这些不同的名字可能均系指同一个人,请参阅拉露:《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2卷,第7页,1950年巴黎版。在Pt.1429号写本的第359页背面,我们又看到其中记载说konn-ce为缮写员的名字,而________(可能指法成)是校对者的姓名(见台北藏第7549号敦煌卷子的跋)。他们二者可能是同时代的人。’
⑤前引潘重规文在图版10中影印发表了其中的第6页。
⑥在巴黎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1629号和1944号中,同样也记载有________一名(见拉露小姐所编:《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3卷,1961年巴黎版,第108、171页);在伦敦所藏的敦煌藏文写本(见德·拉·瓦累·普散:《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1962年牛津大学版,第41页、第17号写本)中则写作[B(rian-Ko)]。
⑦在伦敦所收藏的斯坦因敦煌写本中,同样也记载有(法成),(法慈)和(白乔)等人名,详见Ch.(斯坦因千佛洞藏卷).87.ⅩⅢ.b,Ch.87.ⅩⅢ.d号写本(《大乘无量寿经》,也请参阅瓦累·普散所编:《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101页,第310号写本)。在巴黎所收藏的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中,也经常出现一名,如第1322、1403、1404、1424、1429、1437、1438号(详见拉露:《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3卷,17、45—46、53、53—57页);有关伦敦所藏的敦煌写本问题,请参阅瓦累·普散:《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40页,第104号,第41页,第107号写本。
⑧巴塔巴岗特拉·瞿夏于1902—1914年在加尔各答发表了该部梵文文献的19卷,约占这一长经文的四分之一篇幅(相当于汉译文的第1—76卷),并于1888—1895年在加尔各答出版的《印度书目》第115卷中发表了藏文本中的3卷。参阅孔兹:《般若婆罗蜜多经文献》,1960年海牙版。
⑨在此之后,我又根据下列诸文献而增加了一个“与”字:1)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405号,第211页正面第10行;2)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422号,第212页正面第9行;3)《西藏大藏经》,北京版本的《丹珠尔》中的《般若经》第37卷,第267页背面第6行,东京—京都重版的北京版本第730号,第17卷,第71页。
⑩敦煌写本中对藏文《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具体分类与北京版本的《西藏大藏经》不同。在《西藏大藏经》中,该经文共包括有300卷,而敦煌写本中的该经文首先分成了4部,每部又包括75卷。拉露小姐在第一部中发现了第75卷,在第2卷中仅发现了第74卷,在第3节中发现了第75卷,第4节中发现了第63卷(见拉露小姐:《敦煌写本中的〈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藏文卷子》,载《亚细亚学报》,1964年,第252卷,第4期,第479—486页。参阅麦兹扎尔:《瑞士伯尔尼历史博物馆所藏藏文〈般若婆罗蜜多经〉抄本》,1964年哥本哈根版)。虽然写本中缺少了第2节中的第75卷,但这并不一定能说明该卷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台北所藏第7547号敦煌卷子和《西藏大藏经》中的一致性,完全可以证明它是存在的。在经过初步研究之后,两种藏文版本(即敦煌写本与《西藏大藏经》)的一致性又会使我们注意到以下情况:
75(d—1)+b=p。
其中d即节数的编号,b即卷数的编号,而p则是指北京版本的《西藏大藏经》中卷数的编号。
例如,台北所藏的第7454号敦煌卷子中的第4节,第31卷就是75(4—1)+31=256。
或者:
p/75=d-1+b/75,这就是说:商数+1=节的数目,其余的则等于卷数的数目。我们写本的情况是:256/75=4-1+31/75。这就是说:《西藏大藏经》中的第256卷则相当于敦煌写本中的第4节的第31卷。
 在潘重规先生的文章(同前所引)发表之后,我又得知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的第5卷敦煌藏文卷子,其编号为7548。在藏文文献的背面,我们又发现了汉文文献《大乘稻秆经随听疏》,由法成(hos-grub)所编纂,已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中,为第2782号,见第549—552页。仍然是潘重规先生的好意相赠,我们也得到了这一藏文卷子的复制件。这卷写本是用斜体字写成,它占据了一卷共有7页的灰褐色纸的前5页,全文共包括183行。在经过初步考订之后证明,它似乎是一卷有关敦煌地区在某一个虎年的税单。文中记载有许多人名和地名,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于这些名称,还有待我们分别进行研究。
在潘重规先生的文章(同前所引)发表之后,我又得知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的第5卷敦煌藏文卷子,其编号为7548。在藏文文献的背面,我们又发现了汉文文献《大乘稻秆经随听疏》,由法成(hos-grub)所编纂,已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中,为第2782号,见第549—552页。仍然是潘重规先生的好意相赠,我们也得到了这一藏文卷子的复制件。这卷写本是用斜体字写成,它占据了一卷共有7页的灰褐色纸的前5页,全文共包括183行。在经过初步考订之后证明,它似乎是一卷有关敦煌地区在某一个虎年的税单。文中记载有许多人名和地名,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于这些名称,还有待我们分别进行研究。
 A,有关于阗文本,请参阅:
A,有关于阗文本,请参阅:
1)霍恩尔:《东突厥斯坦的一种不为人所知的语言》,载1910年伦敦出版的《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第834—838页(原文为一篇学术报告),第1283—1300页(论文),尤其是第837页和1293页。
2)洛曼:《〈大乘无量寿陀罗尼经〉的起源,关于北方的语言和文学》,第56—83页;载《斯特拉斯堡科学院集刊》第10卷,1912年斯特拉斯堡版。
3)S.科诺:同上引文,参阅图版14—17。
4)贝利:《于阗文佛经文献》,1951年伦敦版,第94—100页。
B,有关回鹘文、蒙古文和满文等版本,请参阅石滨纯太郎的以下论著:
1)《敦煌古书杂考,〈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发表在1926年7月东京出版的《东洋学报》第15卷,第4期,第522—524页。
2)《考补》,载1927年7月出版的《东洋学报》第16卷,第2期,第223—231页。
3)《回鹘佛典杂考》,载1937年东京出版的《佛教研究》第1卷,第3期,第122—126页。
C,有关西夏文本,请参阅:
西田龙雄:《西夏语的研究》,1964—1966年东京版,第1版,第302页。
D,有关回鹘文和蒙古文版本,尤其请分别参阅以下诸作:
1)拉德洛夫和马洛夫《回鹘语论集》,1928年列宁格勒版,第148—151页,第89段,第35行(这一段则相当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卷,第936号,第84页)。
2)《蒙古文甘珠尔》,北京版,第366和367号,第15卷,第319—327、327—333页。
(译自巴黎1971年出版的《拉露纪念文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