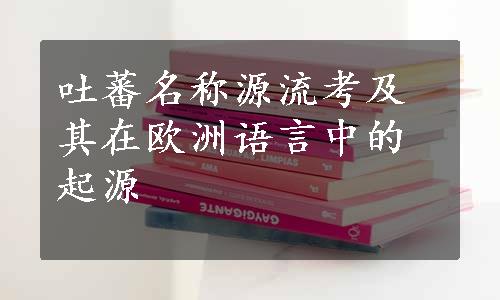
“吐蕃”名称源流考
路易·巴赞哈密屯
以Tebet、Thebet、Thebeth、Tgbot、Thibocht形式出现的“吐蕃”(Tibet)一名在欧洲语言中要上溯到18世纪中叶①。其中带有-h-的拼写法(如同th一样)②,可以不予考虑,因为它没有真正的语音意义,要归于一种继承用拉丁文拼写外来词③的中世纪传统,“吐蕃”(Tibet)一名的Tebet和Tibot等书写形式,都是由中世纪的欧洲旅行家们同时向其蒙古文形式T觟b觟t(见下文不远处)和向同一个名词在波斯语中的形式Tibit、Tibbit、Tibbet、Tibat、Tibbat、Tibbut、Tibbat等借鉴而来的③。至于该名词的波斯文形式,它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可能是以Tubbat的写法为基础的。它一般都被写作tbt、tbbt或Tubbat,这是阿拉伯文中的“吐蕃”名称,它就这样出现在9—13世纪之间的穆斯林史学家或舆地学家们的大量著作中④。然而,阿拉伯文的形式Tubbat却作为诸如粟特文中的Twp'yt那样的一种写法的正规对音。我们把这种粟特文形式读作Topet,它作为吐蕃的名称,而出现在可断代为9世纪第2个10年的喀喇巴勒哈逊三体文合壁碑文中粟特文行文第19行的开头处⑤。事实上,其阿拉伯文形式中的第1个开口元音-u-就相当于twp'yt中的开口元音-w-,Tubbat中的强开口浊辅音-bb-就相当于在阿拉伯文中付阙如的开口清辅音-p-。至于twp'yt中的两个粟特文字母,y可能标注的-e或--一类的半开口和中前唇元音(它在阿拉伯文中同样也付阙如)在Tupbat的尾音节中则用开口元音-a-来表示。吐蕃名称的twb'(')yt这种形式同样也出现在被断代为841至842年的拉达克粟特文碑铭中⑥。此外,在一篇很可能是于9世纪前后写成的帕拉维(pehlavi,中期波斯语)语的文献中,出现了用twpyi的词形来作为吐蕃的名称⑦。另外,11世纪的希腊医生西梅翁(Symeon)[塞特(seth)的儿子]可能把Touπáza或Touàz作为了麝香出产地的名称⑧。然而,吐蕃的名称在粟特文、帕拉维文和希腊文中的这些不同形式,都可以归结到一种雏形Topet。
在时代上继续向上追溯,在8世纪上半叶的鲁尼突厥文碑铭中,大家也发现在古突厥文中用T觟püt的形式来指吐蕃的名称⑨。然而,在我们读作T觟püt的鲁尼突厥文形式和我们读作Topet的粟特文、帕拉维文或希腊文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差异。这就是说,在第1种情况下,是于第2个音节上存在着一个开口元音-ü-;在第2种情况下,则是于第2个音节上存在着更为开口的元音-e-或-觟-。然而,诸如-e-或-覿-的第2个半开口元音与诸如第一个开口元音的结合,在突厥文中显得是很正常的;诸如-ü-那样的第一个开口元音分裂成一个诸如-e-或-覿-那样的半开口元音,则显得是特殊的。因此,我们就会趋向于假设认为,诸如Topet(也就是突厥文中的T觟p覿t)那样的一种形式,是于比从9世纪初叶而不是8世纪的T觟p覿t最多晚一个世纪的时候出现的,但它却应该是早于这后一种形式。
我们在这方面应重提一下从7世纪初叶开始,汉人在唐代用于指Tibet的形式出现的名词“吐蕃”(高本汉对音写作t'uo-piwen,浦立本认为是t'o-puan)⑩,这种汉文对音很可能在公元600年左右 来标注一种诸如T觟p覿h那样的形式。然而,T觟p覿n和T觟p觟t也完全具有同一个词t觟p覿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外貌,而该词很可能是一个意为“顶峰、高度、高地”
来标注一种诸如T觟p覿h那样的形式。然而,T觟p覿n和T觟p觟t也完全具有同一个词t觟p覿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外貌,而该词很可能是一个意为“顶峰、高度、高地” 的众所周知的突厥文,或者是它在一种阿尔泰语中的对音词。o-n-t的反复变化是蒙古文的特征,其中一方面是带-n的名词复数形式是通过由-t来代替-n而形成的;另一方面是名词中的尾音-n往往是不发音的:mori(n)意为马,其复数形式为morit;el ci(n)意为“使者,使节”,其复数形式为el cit;sumu(n)意为“箭”,其复数形式为sumut等。这种现象在突厥文中要不明确得多,此类反复变化于其中仅仅是偶然地和间断性地出现,没有形成诸如蒙古语中的那种正规体系。元音之后的哑音-n于其中以残存状况保持下来了:指示代词bu(n)附有一种没有附带成分的形式bu,以及带有变化的后缀之前的词根bun-(在回鹘文中变成了mun-;在大部分现代语言中,位置格为bunda或munda;其复数形式为bular或bunlar等)。如古突厥文ortu(中心,中央)和ortun(中央的),对于形容同tolu(充满的)也会造成同样的现象,但tolun ay意指“满月”(在奥斯曼语中作dolu、dolun·ag)。浦立本在一篇有关古汉语辅音体系的论文中
的众所周知的突厥文,或者是它在一种阿尔泰语中的对音词。o-n-t的反复变化是蒙古文的特征,其中一方面是带-n的名词复数形式是通过由-t来代替-n而形成的;另一方面是名词中的尾音-n往往是不发音的:mori(n)意为马,其复数形式为morit;el ci(n)意为“使者,使节”,其复数形式为el cit;sumu(n)意为“箭”,其复数形式为sumut等。这种现象在突厥文中要不明确得多,此类反复变化于其中仅仅是偶然地和间断性地出现,没有形成诸如蒙古语中的那种正规体系。元音之后的哑音-n于其中以残存状况保持下来了:指示代词bu(n)附有一种没有附带成分的形式bu,以及带有变化的后缀之前的词根bun-(在回鹘文中变成了mun-;在大部分现代语言中,位置格为bunda或munda;其复数形式为bular或bunlar等)。如古突厥文ortu(中心,中央)和ortun(中央的),对于形容同tolu(充满的)也会造成同样的现象,但tolun ay意指“满月”(在奥斯曼语中作dolu、dolun·ag)。浦立本在一篇有关古汉语辅音体系的论文中 ,阐明了非常著名的职官尊号“达干”(tarqan)的一种古突厥文tarpa的踪迹,以及与b觝ri同时存在的;用于指“狼”的一种形式是b觝rin
,阐明了非常著名的职官尊号“达干”(tarqan)的一种古突厥文tarpa的踪迹,以及与b觝ri同时存在的;用于指“狼”的一种形式是b觝rin ,“狼”是“达干”的某些大官吏们为纪念突厥人的神话先祖而享有的尊号。至于在蒙古文中很正常的以-n结尾的名词,那种带有-t的复数形式,它出现在古突厥文中以指特勤(tegin,其复数形式为tegit)和达干(targan,其复数形式为targat。人们普遍都会将此视为蠕蠕人(?)——古蒙古语的一种影响,这是非常可能的。但这个问题由于以-t结尾的复数形式,也存在于粟特语中的事实,而复杂化了。因为粟特语是一种东伊朗语,它曾为古突厥文提供了许多借鉴因素。此外,大家在突厥文中发现了许多与以-n结尾的名词和带-t词尾的蒙文复数形式相同的写法,但由于失去了一个复数名词的意义,所以突厥文Bayat(主,神)、蒙古文bayat(富翁)则是bayan的复数形式,突厥文süt(奶)在蒙古文中作süt,指“奶制品”,它是süt(奶)的复数形式。最后,古突厥文在alparut(勇敢的武士)元音之后,具有一种带有-t的复数形式(不带-n,可能是哑音的-n脱落了),它是laparu(在蒙古文中未出现过的词,在突厥文中系派生自alp一词,意为“英雄”)的复数形式,古突厥文qana-t(翼,请参阅蒙古文qana,意义相同)可能是以-t结尾的一种古老的复数形式,但却未受此影响,变成了单数(请参阅上文的süt一词)。
,“狼”是“达干”的某些大官吏们为纪念突厥人的神话先祖而享有的尊号。至于在蒙古文中很正常的以-n结尾的名词,那种带有-t的复数形式,它出现在古突厥文中以指特勤(tegin,其复数形式为tegit)和达干(targan,其复数形式为targat。人们普遍都会将此视为蠕蠕人(?)——古蒙古语的一种影响,这是非常可能的。但这个问题由于以-t结尾的复数形式,也存在于粟特语中的事实,而复杂化了。因为粟特语是一种东伊朗语,它曾为古突厥文提供了许多借鉴因素。此外,大家在突厥文中发现了许多与以-n结尾的名词和带-t词尾的蒙文复数形式相同的写法,但由于失去了一个复数名词的意义,所以突厥文Bayat(主,神)、蒙古文bayat(富翁)则是bayan的复数形式,突厥文süt(奶)在蒙古文中作süt,指“奶制品”,它是süt(奶)的复数形式。最后,古突厥文在alparut(勇敢的武士)元音之后,具有一种带有-t的复数形式(不带-n,可能是哑音的-n脱落了),它是laparu(在蒙古文中未出现过的词,在突厥文中系派生自alp一词,意为“英雄”)的复数形式,古突厥文qana-t(翼,请参阅蒙古文qana,意义相同)可能是以-t结尾的一种古老的复数形式,但却未受此影响,变成了单数(请参阅上文的süt一词)。
浦立本于其前引论文中,最终成功地在突厥文官号的最古老汉文对音中,辨认出了最后一个音节的元音之后的一种三项轮番变化的遗迹:-o~-n~-t(如指“达干”的tarqa~tarqan~tarqat,指“特勤”的tegi~tegin-tegit)。我们在t觟p覿(顶峰)~pt觟p覿n~t觟pāt(吐蕃)的形式中,重新发现的正是这种轮番变化。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那样,这同一种反复变化在蒙古文中是传统性的(morin~morin意为单数的“马”,morit则意为复数的“马”等)。t觟p覿所具有的“顶峰、高地”的意义,完全适用于指“世界屋脊”,也就是一个著名的高海拔地区。我们提议将一种突厥语或突厥—蒙古语的辞源归于吐蕃的这些名称(因而也是归于它们后来的阿拉伯—波斯文以及更晚期的西文名称)。
因此,我们的提议,与一般人根据藏文词Bod而提出的“吐蕃”名称的辞源是矛盾的,Bod是该地区的一个土著名词,有时与土著宗教的名称Bon(苯教)交替使用,有时又由其他藏文词作以补充以形成stod Bod(上部吐蕃)或mtho Bod(高部吐蕃) 等词组。这样的辞源是以藏语的近代发音为基础的,其中提到的具有“上部、高部”意义的形容修饰词,经受了一种语音损耗,从而把它们分别简化为to或t’o(t觟或t’觟)。因此,“吐蕃”的外来名称的各种不同写法,都要追溯到to-bod或t’o-b觟d(t觟-b觟d或t’觟-b觟d),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出现在8世纪前三分之一年代的古代突厥文碑铭中(鄂尔浑第1和第2碑)中的T觟püt(吐蕃)的形式了。但为了从辞源上进行证实,而依靠一种与所解释的事实晚1000年的发音,则具有冒险性。此外,这种假设也会与下述事实相抵触,汉文中“吐蕃”一名最古老(7世纪初叶)的异文就相当于T觟p覿n或一种类似的发音,无论如何是带有-n而不是-t的尾音,而这个时代的汉文对音明显地把尾音-t(或者是Bod中的-d)与-n区别开了。
等词组。这样的辞源是以藏语的近代发音为基础的,其中提到的具有“上部、高部”意义的形容修饰词,经受了一种语音损耗,从而把它们分别简化为to或t’o(t觟或t’觟)。因此,“吐蕃”的外来名称的各种不同写法,都要追溯到to-bod或t’o-b觟d(t觟-b觟d或t’觟-b觟d),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出现在8世纪前三分之一年代的古代突厥文碑铭中(鄂尔浑第1和第2碑)中的T觟püt(吐蕃)的形式了。但为了从辞源上进行证实,而依靠一种与所解释的事实晚1000年的发音,则具有冒险性。此外,这种假设也会与下述事实相抵触,汉文中“吐蕃”一名最古老(7世纪初叶)的异文就相当于T觟p覿n或一种类似的发音,无论如何是带有-n而不是-t的尾音,而这个时代的汉文对音明显地把尾音-t(或者是Bod中的-d)与-n区别开了。
8世纪的突厥文T觟püt不仅远不能驳倒一种以t觟p覿(顶峰、高地)为基础的突厥语或突厥—蒙古语辞源,而是更应该是由于第2个音节中的元音ü(而不是à),形成一种确认。因为文言回鹘突厥文(8世纪碑铭中突厥文的直接继承者)经常把这个指“顶峰”的名字写作T觟pü的形式。这里是指第2个元音与第1个元音的一种开口同化。大家在蒙古文中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其中除了其传统的(古老的)写法twyb’d=T觟b覿t之外,我们在近代发音中还发现了T觟w觟t(吐蕃,早在1240年左右的《蒙古秘史》中就已经写作T觟b覿t)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应该指出,蒙古文的写法(很可能是借鉴自突厥文)促使人读作T觟püt,而不是根据传统而自最早读音(8世纪的突厥文碑铭中的形式)所作的那样。同样,我们应该读作t觟pu(顶峰)而不是tüpü,后者是写作twypw的古典回鹘文形式,其中的音节wy标准为-ó-。请参阅新回鹘文t觟p覿、柯尔克孜文t觟b觟等,它们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应该指出,蒙古文的写法(很可能是借鉴自突厥文)促使人读作T觟püt,而不是根据传统而自最早读音(8世纪的突厥文碑铭中的形式)所作的那样。同样,我们应该读作t觟pu(顶峰)而不是tüpü,后者是写作twypw的古典回鹘文形式,其中的音节wy标准为-ó-。请参阅新回鹘文t觟p覿、柯尔克孜文t觟b觟等,它们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乌古斯”突厥文中带有覿第一个元音的形式(奥斯曼语t覿p覿,安纳托利亚语t覿p覿~d覿p覿,土库曼语d覿p覿,均意为“顶峰”)提出了一种历史语音的问题。如果它们代表着对一种旧有状态的保持,那就应该承认诸如t觟p覿这类的形式,经受了在后一个辅音p影响下的第一个元音的唇化过程。这样一种语音发展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我们在这个方言领域中没有找到例证,如动词t覿p-(尥蹶子、踢蹄子,指马匹)的音节t覿p,也完全出现在古典回鹘文和喀喇汗王朝的突厥文中了,它于其中明显与t覿pü中的词组t觟p(顶峰、颅顶)相对立 ,保持了元音覿(在奥斯曼语中作t覿p,在土库曼语中作d覿p,具有相同的意义)。但大家在奥斯曼语和安纳托利亚突厥语中观察到了一种相反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在古突厥语k觟p(qop-k觟p,意为“大批、全体”)的k覿p中的一种唇音的退化(p之前的元音非开口化
,保持了元音覿(在奥斯曼语中作t覿p,在土库曼语中作d覿p,具有相同的意义)。但大家在奥斯曼语和安纳托利亚突厥语中观察到了一种相反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在古突厥语k觟p(qop-k觟p,意为“大批、全体”)的k覿p中的一种唇音的退化(p之前的元音非开口化 。带有觟(t觟pü)的形式出现得要古老得多,大家最好是把它们视为历史上的早期写法。
。带有觟(t觟pü)的形式出现得要古老得多,大家最好是把它们视为历史上的早期写法。
这种考察导致了修改一种假设,即认为t觟p覿~t觟pü~t覿-p覿等词的蒙古文对音词,可能是词根d覿’覿-(古典蒙古文作d覿g覿-,其中的g表示在一个音节间,辅音脱落之后的一种误写),意指“在……之上”、“在上部”。它产生了各种派生词,带有后缀-r覿、d覿'覿r覿(13—14世纪)、d覿r覿、d覿r等,其辞意都为“在……之上”;带有后缀-tü、d覿l覿tü、d覿tü、d覿t等,意为“在上部”或“在高部” 。这种假设是以一种已得到明确证实的事实为出发点的,这就是在那些-p-普遍失去了其闭音的蒙文词中,便相当于具有音节间的一个-p的突厥文。大家发现了一种元音重复,稍后不久又带有一种结合。例如,突厥文qapa(封闭)~蒙古文qa’a(有时又写作qara-或qā,意为关闭、封闭)
。这种假设是以一种已得到明确证实的事实为出发点的,这就是在那些-p-普遍失去了其闭音的蒙文词中,便相当于具有音节间的一个-p的突厥文。大家发现了一种元音重复,稍后不久又带有一种结合。例如,突厥文qapa(封闭)~蒙古文qa’a(有时又写作qara-或qā,意为关闭、封闭) ,又会导致提出一种d覿p覿(甚至是d覿p覿)之雏形的假设(以解释突厥文的开唇元音)。这样就会引起多种异议。我们刚刚阐述了支持第1个元音觟(而不是覿)的原因。对于第2个元音来说,各种突厥语言的内在比较,使得一个觟的存在变得更为令人质疑了,元音o和觟似乎是原来就固有的,出现在保存于第一个音节中的突厥文中(o~觟在非起始音节的出现,是由于a~覿的开口音同化的次要现象,或增加一些与前面的词结合或合,并而失去重音的词汇的原因)
,又会导致提出一种d覿p覿(甚至是d覿p覿)之雏形的假设(以解释突厥文的开唇元音)。这样就会引起多种异议。我们刚刚阐述了支持第1个元音觟(而不是覿)的原因。对于第2个元音来说,各种突厥语言的内在比较,使得一个觟的存在变得更为令人质疑了,元音o和觟似乎是原来就固有的,出现在保存于第一个音节中的突厥文中(o~觟在非起始音节的出现,是由于a~覿的开口音同化的次要现象,或增加一些与前面的词结合或合,并而失去重音的词汇的原因) 。此外,蒙古文的声母d-的正规突厥文对应词是y-(蒙古文dai-sun~突厥文yari-sun,意为“敌人”,蒙古文da’aki、dāki~突厥文yapari-,意为“羊毛”;蒙古文dü-züg覿,意为马镫子,~突厥文yüzük意为环、索圈等
。此外,蒙古文的声母d-的正规突厥文对应词是y-(蒙古文dai-sun~突厥文yari-sun,意为“敌人”,蒙古文da’aki、dāki~突厥文yapari-,意为“羊毛”;蒙古文dü-züg覿,意为马镫子,~突厥文yüzük意为环、索圈等 。当然,这后一种论据并非是决定性的,因为大家在声母中发现了蒙古文d-和突厥文t-的对应关系。蒙古文d觟rb覿n~突厥文t觟r-t,意为“四”;蒙古文darpan~突厥文tarqan意指“达干”,是一个官号,请参阅上文;蒙古文dalai~突厥文taluy,意为“海洋”)。但这里也可能是指蒙古文中的古清辅音t-浊化为d-的过程,大家可以认为我们掌握了有关“达干”这个尊号的历史证据,所有的古老证据都因此而支持声母t-而不是d-的写法。于taluy和türt(无疑应为t觟rt)于8世纪时的首次出现,与dalai和d觟rb覿u在13世纪的出现之间,具有近5个世纪的间隔。古典蒙古文t-向近代蒙古文d-的浊化进程,在南部和东部的各种方言中,尤其是在鄂尔多斯蒙古语的相当数量的辞汇中,都已经出现了:古典词toqo(为马匹等备鞍子)、toqta-(坚持、保持坚定)、tasura-(折断、撕下或自我粉碎)、tusa(有益、有用)、tata-(拉、拽,请参阅突厥文tart-,其词义相同)~鄂尔多斯语doxo-、dorta-、dasur-、dusa、dusa、data-(具有同样的辞义)
。当然,这后一种论据并非是决定性的,因为大家在声母中发现了蒙古文d-和突厥文t-的对应关系。蒙古文d觟rb覿n~突厥文t觟r-t,意为“四”;蒙古文darpan~突厥文tarqan意指“达干”,是一个官号,请参阅上文;蒙古文dalai~突厥文taluy,意为“海洋”)。但这里也可能是指蒙古文中的古清辅音t-浊化为d-的过程,大家可以认为我们掌握了有关“达干”这个尊号的历史证据,所有的古老证据都因此而支持声母t-而不是d-的写法。于taluy和türt(无疑应为t觟rt)于8世纪时的首次出现,与dalai和d觟rb覿u在13世纪的出现之间,具有近5个世纪的间隔。古典蒙古文t-向近代蒙古文d-的浊化进程,在南部和东部的各种方言中,尤其是在鄂尔多斯蒙古语的相当数量的辞汇中,都已经出现了:古典词toqo(为马匹等备鞍子)、toqta-(坚持、保持坚定)、tasura-(折断、撕下或自我粉碎)、tusa(有益、有用)、tata-(拉、拽,请参阅突厥文tart-,其词义相同)~鄂尔多斯语doxo-、dorta-、dasur-、dusa、dusa、data-(具有同样的辞义) 。同样的现象从11世纪起就出现在乌古斯突厥语中了:daqi(也,普通突厥语作taqi,请参阅蒙古文taki~daki,意为“也”,借鉴自突厥文);d覿u覿(骆驼,古突厥语作t覿wa(y),t覿wi,请参阅蒙古文t覿m覿g覿n)等
。同样的现象从11世纪起就出现在乌古斯突厥语中了:daqi(也,普通突厥语作taqi,请参阅蒙古文taki~daki,意为“也”,借鉴自突厥文);d覿u覿(骆驼,古突厥语作t覿wa(y),t覿wi,请参阅蒙古文t覿m覿g覿n)等 。这种清辅音浊化的现象比出现在许多奥斯曼语、安纳托利亚突厥语和土库曼语中,正如前引d覿pa(顶峰)一样。它是过渡性的,因而对于辞源比较学没有多大意义。正如大家可以在古代和现代安纳托利亚突厥语的许多方言性犹豫不决中,所发现的那样:d覿p~t覿p覿,duz~tuz(盐)、dürlü~türlü(种类)等。那些古突厥文始终保留t-的辞汇,也都如此。
。这种清辅音浊化的现象比出现在许多奥斯曼语、安纳托利亚突厥语和土库曼语中,正如前引d覿pa(顶峰)一样。它是过渡性的,因而对于辞源比较学没有多大意义。正如大家可以在古代和现代安纳托利亚突厥语的许多方言性犹豫不决中,所发现的那样:d覿p~t覿p覿,duz~tuz(盐)、dürlü~türlü(种类)等。那些古突厥文始终保留t-的辞汇,也都如此。
在许多情况下,带t-词尾的一个古突厥文的对应词,则以带声母d-的形式出现。这里是指蒙古文向突厥文的借鉴,也正如对于前引daki和darqan一样。大家在已知的最古老的蒙古文献《蒙古秘史》(约为1240年左右)中找到了明确的例证,它于其中在t觟r覿和d觟r覿(法律、规则、习惯法)之间犹豫不决,这是向古突厥文t觟ra(8世纪)的借鉴 。在经过阐述我们对于在突厥文t觟p覿、t觟pü、t覿p覿等(顶峰),与蒙古文d覿'-覿(在上部、高部)之间的辞源比较,我们便认为,其辞义是出自“最高的”和“最好的”的突厥文yeg,其正常对应关系应为蒙古文中的-d~突厥文中的y-,d覿'-覿要上溯到d覿g覿-,保存在古典蒙古文的写法中
。在经过阐述我们对于在突厥文t觟p覿、t觟pü、t覿p覿等(顶峰),与蒙古文d覿'-覿(在上部、高部)之间的辞源比较,我们便认为,其辞义是出自“最高的”和“最好的”的突厥文yeg,其正常对应关系应为蒙古文中的-d~突厥文中的y-,d覿'-覿要上溯到d覿g覿-,保存在古典蒙古文的写法中 。这种考证又使我们趋向提议,将蒙古文dobo(山岭)作为突厥文t觟p覿(其今日尚无多见的意义仍是“山峰、山岭”)的对音词,我们倾向于将此视为向突厥文的一种借鉴,带有声母的浊化(请参阅daki、darqan和d觟r覿),最不常见的则是元音级的变化。
。这种考证又使我们趋向提议,将蒙古文dobo(山岭)作为突厥文t觟p覿(其今日尚无多见的意义仍是“山峰、山岭”)的对音词,我们倾向于将此视为向突厥文的一种借鉴,带有声母的浊化(请参阅daki、darqan和d觟r覿),最不常见的则是元音级的变化。
如若无这种变化,那么其辞源就很清楚了,在d觟p覿之前带有经浊化的声母的t觟p覿,清辅音p从古蒙古文时代就已经失去 ,p变成了bo就如同在向突厥文topraq(土地、腐殖层)借鉴的蒙古文tobraq~tobroq(近代作towror等)中一样,由此而产生了d觟b覿一词,它由于在蒙古文中常见的唇音结合的原因(其中的觟……覿和o……a的古老变化过程变成了由觟……觟和o……o的变化。请参阅T觟b覿t先变作T觟b觟t和后又变作d觟b觟、d觟w觟,而不是dob和dowo(均意为“山岭”)的例证。
,p变成了bo就如同在向突厥文topraq(土地、腐殖层)借鉴的蒙古文tobraq~tobroq(近代作towror等)中一样,由此而产生了d觟b覿一词,它由于在蒙古文中常见的唇音结合的原因(其中的觟……覿和o……a的古老变化过程变成了由觟……觟和o……o的变化。请参阅T觟b覿t先变作T觟b觟t和后又变作d觟b觟、d觟w觟,而不是dob和dowo(均意为“山岭”)的例证。
因此,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元音级的这种变化(对于同一个词在突厥文和在蒙古文中都带有等级的对立)是否为可能,其例证很罕见。如果排除了那些由于后缀i的不稳定性而变得不大可靠的例证的话,那就是由此而出现了i-i的反复变化,正如在突厥文bic-~bic(砍断)、bin-bin(千)等词中一样。但大家在突厥文(tarqan~t覿rk覿n,“干达”,官号,上文业已提及)和蒙古文(ratu-~g覿tul-,意为“穿越”,请参阅突厥文k覿c-)中的某些颇有意义的例证。至于那些对于同一个辞源相同的假设词,而使突厥文与蒙古文相对立的例证(唯有它们才使我们的假设合乎情理),则更为罕见,正如大家在或然性问题上所预料到的那样。因为在突厥文的i/a和在蒙古文中的i/b的一种可能性的组合,导致了在类似情况下的i/ab之可能性。但是,在排除了所有令人质疑的情节之后,我们却可以举出两个意义相反的例证(突厥文中的后部元音,蒙古语中的前部元音,或反之),它们的语意一致性是相当真实可信的:突厥文qarya~蒙古文k覿riy覿(乌鸦,qarira~k覿rig覿);西部奥斯曼和安纳托利亚突厥语觟b覿k(堆积,堆)~古典蒙古文obora(n)和近代蒙古语ow觟(n)(石堆、鄂博,俄文作obon,覿b覿g覿(n)-obaran)。突厥语中对于唇音中塞音的保留,在其他地方却会使人猜测到,其前面还有一个长元音的p的更古老的雏形觟p覿g覿(n)-oparu(n),因为短元音之后的b变成了西突厥语中的w或v(8世纪的碑铭突厥文中作ab,安纳托利亚语和奥斯曼突厥文中作av,意为“猎物、猎狩”)。请参古典蒙古文aba,近代蒙古语作aw,意为“围猎、哄猎”。
这后一个例证对于我们的假设具有下面一个词组的语音对应意义:突厥文觟p覿或觟p覿~蒙古文dobo(山岭),突厥文觟p覿k或觟b覿k~蒙古文obora(n)(堆积)。
因此,在结束这段有关辞源的冗长讨论时,我们提议根据该地名的最古老的汉文对音“吐蕃”(T觟p覿n,7世纪初叶,带有-n,从而否认了以藏文Bod来解释的辞源),它在突厥碑铭中出现的形式T觟püt(约为公元730年),及其在6世纪时的粟特文和9世纪中期的伊朗文形式(它们都代表着T觟püt),我们与突厥文t觟pa~t觟pü(顶峰、高处)相比较的所有形式,来解释其阿拉伯—波斯文,以及后来西文中的形式Tibet,吐蕃本来就是“世界屋脊”,也被人称为“高地”。
我们觉得t觟p覿t~T觟püt中的-t似乎是一种“阿尔泰语”(更确切地说是突厥—蒙古语)中的复数形式。但这种后缀在粟特文中也具有相同的作用。至于T觟p覿n一词中的-n,大家对此初看起来可能会联想到突厥—蒙古语中的哑音“-n”,这里也可能是指突厥—蒙古语中集合辞汇的古后缀,现在尚残存有某些踪迹:突厥文覿r~蒙古文覿r覿(雄性者、男子)、突厥文集合名词r n(男人)发展成了覿r覿nl覿r(同上) 。在蒙古语中,raqai(猪、野猪),阿尔泰语中的集合名词gaqan(野猪)则成了一个部族的名称;以-tu结尾的形容词派生词具有以-tan结尾的蒙古文的复数形式
。在蒙古语中,raqai(猪、野猪),阿尔泰语中的集合名词gaqan(野猪)则成了一个部族的名称;以-tu结尾的形容词派生词具有以-tan结尾的蒙古文的复数形式 。大家还可以列举带-(a)n~-(覿n)的后缀其他突厥文和蒙古文例证,其中有些具有一种集合名词的意义,余者则不具这种意义
。大家还可以列举带-(a)n~-(覿n)的后缀其他突厥文和蒙古文例证,其中有些具有一种集合名词的意义,余者则不具这种意义 。我们确实觉得在全部突厥—蒙古语中,应该在没有集合名词意义的哑音节中的-h(其最佳例证是蒙古文的第一人称单数的人称代词:bi(我)=bi(n)。请参阅突厥文b覿n(碑铭中的古突厥词-bin-),这种后缀-(a)n~-(覿)n其集合名词的功能仅仅是零星地残存下来了(在突厥文中,除了前面提到的集合名词覿r覿n之外,还有派生自or(u)i(孩子、儿子)的orian之外,后者仅仅在古突厥文中才有“孩子”的意义,在当代的用法中却指“小伙子”,与“少女”相对应。
。我们确实觉得在全部突厥—蒙古语中,应该在没有集合名词意义的哑音节中的-h(其最佳例证是蒙古文的第一人称单数的人称代词:bi(我)=bi(n)。请参阅突厥文b覿n(碑铭中的古突厥词-bin-),这种后缀-(a)n~-(覿)n其集合名词的功能仅仅是零星地残存下来了(在突厥文中,除了前面提到的集合名词覿r覿n之外,还有派生自or(u)i(孩子、儿子)的orian之外,后者仅仅在古突厥文中才有“孩子”的意义,在当代的用法中却指“小伙子”,与“少女”相对应。
在t觟püt的古老异体字top覿n中,正是其集合词的意义(“形成吐蕃的整片高地”)似乎最终需要保留下来。前引b觟rin(狼群,突厥可汗大官吏们的集团)派生自b觟ri(狼)。
无论对于现存的后缀(哑音-h本身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后缀)作什么样的解释,被比作突厥文t觟pp覿-t觟pü和可能还有蒙古文dobo的一组名词T觟p覿n、T觟p覿t、T觟püt,似乎完全属于阿尔泰语系,更具体地说应该是突厥—蒙古语族。大家可以认为这一语族的严密结构出自一种基本的一致性,或者是在很长期间的相互影响和前历史时代的互相借鉴 。吐蕃的蒙文名字在古典蒙古文中作T觟b覿t(《蒙古秘史》,约为1240年)和T觟b t,在近代蒙古文中作T觟w觟t,显得如同是借鉴自突厥文名称的不同写法T觟p覿t(而不是T觟püt)一般。
。吐蕃的蒙文名字在古典蒙古文中作T觟b覿t(《蒙古秘史》,约为1240年)和T觟b t,在近代蒙古文中作T觟w觟t,显得如同是借鉴自突厥文名称的不同写法T觟p覿t(而不是T觟püt)一般。
该名称在汉文对音中最早出现的形式“吐蕃”(T觟p覿n)要追溯到7世纪初叶。因此。汉人可能是通过一个属于操突厥—蒙古语族的民族,而于当时就知道了这种称呼,这要比它以带t的形式T觟püt在蒙古突厥人中的出现早一个世纪,而要比它以T觟püt的异体形式在伊朗—粟特文中的出现早两个世纪。
然而,大家恰恰知道具有这种语言属性的一个民族,于4—7世纪期间,占据了介于一方面是吐蕃和另一方面是汉人和蒙古突厥人之间的一种居间地理方位。这里是指吐谷浑人 ,他们是一个属于鲜卑种族的民族,约于公元4世纪初叶从他们在辽河流域的今满洲的发祥地,一直迁移到青海湖和柴达木地区,其王国在那里一直维持到633年,即当他们被吐蕃王国摧毁为止
,他们是一个属于鲜卑种族的民族,约于公元4世纪初叶从他们在辽河流域的今满洲的发祥地,一直迁移到青海湖和柴达木地区,其王国在那里一直维持到633年,即当他们被吐蕃王国摧毁为止 。这样一来,从公元4世纪到7世纪末左右,吐谷浑人在吐蕃本土的北方和东北方占据了一片辽阔的土地,青海湖周围从柴达木沼泽地直到罗布淖尔,在北方面对突厥人,在东北方和东方却面对汉人
。这样一来,从公元4世纪到7世纪末左右,吐谷浑人在吐蕃本土的北方和东北方占据了一片辽阔的土地,青海湖周围从柴达木沼泽地直到罗布淖尔,在北方面对突厥人,在东北方和东方却面对汉人 。
。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认为,吐蕃最早是通过吐谷浑人的媒介作用,而被突厥人和汉人所熟识的。他们双方为了指该地区而采纳了一种借鉴自吐谷浑语中意为“高峰、高地”的名称,汉人直接采用了以-n结尾的集合名词形式T觟p覿n;突厥人为了更为清楚起见(以-h结尾的集合名词在突厥文语很罕见),而采纳了以-t结尾的复数名词的突厥—蒙古语形式T觟p覿t(传到了粟特文中),在8世纪时变成了T觟püt(蒙古人稍后以T觟püt的名字采纳了它),又先变作T觟p觟t,后变作T觟w觟t。其最早的不同形式为T觟p覿t,即根据一种保留了这种不同形式的突厥口语,这也是黠戛斯语的原形t觟b觟(高地),其单数形式t觟p覿在黠戛斯语中很正常地向t觟b觟发展。
在8世纪初叶,大部分吐谷浑人都逃亡到了鄂尔多斯地区,因而也就是位于中国京师长安与鄂尔浑河畔的突厥都城之间的大道上 。然而,在阙特勤的鲁尼突厥文碑铭中,于重新提及阙特勤在731这个羊年的薨逝和732年的猴年立墓碑之后,该墓志铭东北角的一行文字就这样结束了该句子:“吐谷浑(Tuy(u)run)部族的首领带来了同样多的装饰匠人。”或者更应该是:“(从汉地)带来如此之多装饰匠人者是吐谷浑部族的首领。”
。然而,在阙特勤的鲁尼突厥文碑铭中,于重新提及阙特勤在731这个羊年的薨逝和732年的猴年立墓碑之后,该墓志铭东北角的一行文字就这样结束了该句子:“吐谷浑(Tuy(u)run)部族的首领带来了同样多的装饰匠人。”或者更应该是:“(从汉地)带来如此之多装饰匠人者是吐谷浑部族的首领。” 大家确实通过该碑南侧第11—13行而获知,毗伽可汗从当时位于长安的中国天朝宫廷中请来了其弟阙特勤墓志铭的装饰师
大家确实通过该碑南侧第11—13行而获知,毗伽可汗从当时位于长安的中国天朝宫廷中请来了其弟阙特勤墓志铭的装饰师 。此外,大家还知道,吐谷浑部族的首领在731—732年间,应该是在位于灵州和五原郡之间的黄河河套地区行使职权。这就是说,它恰恰位于汉族装饰师为了从中国宫廷,前往位于鄂尔浑河流域的突厥京师沿途的领土上
。此外,大家还知道,吐谷浑部族的首领在731—732年间,应该是在位于灵州和五原郡之间的黄河河套地区行使职权。这就是说,它恰恰位于汉族装饰师为了从中国宫廷,前往位于鄂尔浑河流域的突厥京师沿途的领土上 。因此,我们觉得很明显,当时从汉地边境护送这批汉族匠人,一直到达鄂尔浑河流域的Tuy(u)run(吐谷浑,见上)部族首领,正是被对音作吐谷汗的突厥或蒙古部族首领的名字。
。因此,我们觉得很明显,当时从汉地边境护送这批汉族匠人,一直到达鄂尔浑河流域的Tuy(u)run(吐谷浑,见上)部族首领,正是被对音作吐谷汗的突厥或蒙古部族首领的名字。
Tuy(u)run的第一种意义应为“隼”或“白色苍鹰”。勒·柯克(Le Coq)于其论文《突厥驯鹰术考》就已经指出,在“蒙古的鲁尼突厥文碑铭中”出现的Tuyrun或Tog-run一词,可能相当于隼或一种白色苍鹰的名字 。拉德洛夫(Radloff)于其巨著《突厥方言辞典》
。拉德洛夫(Radloff)于其巨著《突厥方言辞典》 中指出,在察合台语、巴拉巴的塔塔儿语和黠戛斯语(应为哈萨克语)中,Tuyrun意为“白隼”,但儒达克辛(Judaxin)于其在一般情况下更为明确具体的吉尔吉斯语—俄语辞典(1965年)
中指出,在察合台语、巴拉巴的塔塔儿语和黠戛斯语(应为哈萨克语)中,Tuyrun意为“白隼”,但儒达克辛(Judaxin)于其在一般情况下更为明确具体的吉尔吉斯语—俄语辞典(1965年) 中,却赋予了该词“白色苍鹰”的意义,我们无疑更应该倾向于后者。辞书作家们往往会把苍鹰和与之颇为相似的隼相混淆。因此,吐谷浑首领于8世纪正是取了Tuy(u)run(白色苍鹰),无疑是由于其狩猎的本领而负盛名和因其颜色而引人注目的飞鸟之名。其部族正是由此而获名,他们当时生活在满洲辽河以西的辽西
中,却赋予了该词“白色苍鹰”的意义,我们无疑更应该倾向于后者。辞书作家们往往会把苍鹰和与之颇为相似的隼相混淆。因此,吐谷浑首领于8世纪正是取了Tuy(u)run(白色苍鹰),无疑是由于其狩猎的本领而负盛名和因其颜色而引人注目的飞鸟之名。其部族正是由此而获名,他们当时生活在满洲辽河以西的辽西 。此外,在邻近的高丽存在有“白色苍鹰”的事实,又特别是由于1851年由一名阿拉伯旅行家和商人苏莱曼(Sulayman)提及
。此外,在邻近的高丽存在有“白色苍鹰”的事实,又特别是由于1851年由一名阿拉伯旅行家和商人苏莱曼(Sulayman)提及 。雷米·多尔(Remy Dor)还在一条注释的手稿中,向我们具体解释说,黠戛斯人中的Tuyrun“这类白色苍鹰”又使人联想到了“一名勇敢的英雄”。
。雷米·多尔(Remy Dor)还在一条注释的手稿中,向我们具体解释说,黠戛斯人中的Tuyrun“这类白色苍鹰”又使人联想到了“一名勇敢的英雄”。
在以《辽史》为基础的一幅各民族和部族的统计表中,魏特夫和冯家昇 特别参照了伯希和的观点
特别参照了伯希和的观点 。他们重新提出,大约到了唐代末年前后,“吐谷浑”一名的汉文对音经常被简化为“吐浑”或“退浑”。他们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对音可能是代表着鄂尔浑突厥文中的尊号Tuyrun,被拉德洛夫子其辞典(第3卷,第1424页,并非是魏特夫和冯家昇所指出的那样是第1432页)解释为“一种显职高位”。它应被解释为“注意或感觉到的人”,来自突厥文tay(注意、感觉)。然而,据我们看来,这种解释与以“白色苍鹰”来解释tuyrun的做法,没有任何矛盾,甚至还倾向于证实这种解释。因为自突厥文tuy(感觉)派生来的tuy-run一词(“感觉”。请参阅奥斯曼语duy-,意为“感觉”和“敏感”;派生词duyrun意为“敏感的”)非常适用于指这种猛禽,以指其感觉的敏锐度(尤其是视觉的敏锐度),这是猎禽的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特征。它也适应于吐谷浑的名祖之名。此外,“白色的苍鹰”除了具有英雄主义和尊贵特征之外,还会使人联想到首领头人的主要本领——目光敏锐犀利
。他们重新提出,大约到了唐代末年前后,“吐谷浑”一名的汉文对音经常被简化为“吐浑”或“退浑”。他们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对音可能是代表着鄂尔浑突厥文中的尊号Tuyrun,被拉德洛夫子其辞典(第3卷,第1424页,并非是魏特夫和冯家昇所指出的那样是第1432页)解释为“一种显职高位”。它应被解释为“注意或感觉到的人”,来自突厥文tay(注意、感觉)。然而,据我们看来,这种解释与以“白色苍鹰”来解释tuyrun的做法,没有任何矛盾,甚至还倾向于证实这种解释。因为自突厥文tuy(感觉)派生来的tuy-run一词(“感觉”。请参阅奥斯曼语duy-,意为“感觉”和“敏感”;派生词duyrun意为“敏感的”)非常适用于指这种猛禽,以指其感觉的敏锐度(尤其是视觉的敏锐度),这是猎禽的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特征。它也适应于吐谷浑的名祖之名。此外,“白色的苍鹰”除了具有英雄主义和尊贵特征之外,还会使人联想到首领头人的主要本领——目光敏锐犀利 。
。
另外,我们提到在阙特勤(k觟l Tegin)碑内南侧的一行文字(因而与包括有Tuy(u)-run一词的东北侧一行文字正好相对)中存在着一种似乎代表着Tuy(u)rut的形式,它是Tuy(u)run的带-t的复数写法。令人遗憾的是该行的这部分文字残缺不全,大家只能有把握地阅读出如下内容:“样磨(Yaghma)和吐谷军部族。” 样磨是出自九姓乌古斯的一个操突厥语的重要部族名称,他们至少从10世纪起就居住在疏勒地区
样磨是出自九姓乌古斯的一个操突厥语的重要部族名称,他们至少从10世纪起就居住在疏勒地区 。至于与Tuy(u)run并列在的Tuy(u)rut的形式,它似乎证明了吐谷浑语言中用于指民族的习惯用法,即使用带-t的复数形式与带-n的集合名词形式的交替变化,正如我们在T觟p覿n-T觟p覿nt的例证中所猜测的那样。
。至于与Tuy(u)run并列在的Tuy(u)rut的形式,它似乎证明了吐谷浑语言中用于指民族的习惯用法,即使用带-t的复数形式与带-n的集合名词形式的交替变化,正如我们在T觟p覿n-T觟p覿nt的例证中所猜测的那样。
所有这些比较都发生在一种“阿尔泰语”(更具体地说是突厥—蒙古语)的语言背景中,它们提出了与相继由不同作家触及到的吐谷浑人的语言属性直接相联系的诸问题,其中有些人把吐谷浑人视为通古斯人,而其他人则把他们看做是操蒙古语言的民族。这后一种观点于1921年受到了伯希和的支持 。为了支持他们是古蒙古人的假设,伯希和提出了一种历史证据(在唐代于鲜卑的后裔室韦人中有一个蒙兀民族的存在,它使人联想到了蒙古人的部族)。但他最重要的还是提出了一些语言论据:在根据汉文的对音的吐谷浑语言中,存在着一个第二人称单数的人称代词cu或cü,它就相当于蒙古语中的ci(你);还存在着一个词aqan,它与蒙文aqa(哥哥)具有相同的意义。但在“吐谷浑”中却带有一个哑音的-h;此外还存在一个词bara(父亲),同样也与作为尊号使用的蒙古文abara(叔父、伯父)等作了比较
。为了支持他们是古蒙古人的假设,伯希和提出了一种历史证据(在唐代于鲜卑的后裔室韦人中有一个蒙兀民族的存在,它使人联想到了蒙古人的部族)。但他最重要的还是提出了一些语言论据:在根据汉文的对音的吐谷浑语言中,存在着一个第二人称单数的人称代词cu或cü,它就相当于蒙古语中的ci(你);还存在着一个词aqan,它与蒙文aqa(哥哥)具有相同的意义。但在“吐谷浑”中却带有一个哑音的-h;此外还存在一个词bara(父亲),同样也与作为尊号使用的蒙古文abara(叔父、伯父)等作了比较 。吐谷浑(Tuyrun~Tuyrut)和吐蕃(T觟p覿n~T觟p覿t)等名词所代表的以-h结尾的集合名词,与以-t结尾的复数形式,似乎同样也支持了古蒙古语的论点。
。吐谷浑(Tuyrun~Tuyrut)和吐蕃(T觟p覿n~T觟p覿t)等名词所代表的以-h结尾的集合名词,与以-t结尾的复数形式,似乎同样也支持了古蒙古语的论点。
最后,希伯和于其1921年文 的一条附注中,通过蒙古文而解释了汉文对音中简化三至两个音节的做法(见上文):“吐谷浑或退浑之间的交替使用,似乎与蒙古文同源对似词ruyu-和rui(要求)、güyü-和güi-(奔驰)的轮番变化属于同一类。事实上,从由汉文对音反映出的Tuyurun(吐谷浑)到Tuyrun(吐浑、退浑)的变化过渡,似乎证明了同时在蒙古文和突厥文中出现的一种历史性语音发展:由于中间(非重音的)元音的脱落,而使三音节变成两音节词的变化。这样一来,古典蒙古文abala-(围猎)在近代蒙古文中作awla-(请参阅突厥文avla-,意为“狩猎”),古典蒙古文覿mün覿在近代蒙古文中作觟mn觟(前面)等,古突厥文yügürük在喀喇汗突厥文中作yügrük(疾速,出自意为“奔驰”的yügür-),碑铭中的古突厥文abi觢ran在回鹘文中作tawisran,在近代语言中作taw觢an、tav觢an等,意为“兔子”(请参阅蒙古文taulai,其意义相同)。
的一条附注中,通过蒙古文而解释了汉文对音中简化三至两个音节的做法(见上文):“吐谷浑或退浑之间的交替使用,似乎与蒙古文同源对似词ruyu-和rui(要求)、güyü-和güi-(奔驰)的轮番变化属于同一类。事实上,从由汉文对音反映出的Tuyurun(吐谷浑)到Tuyrun(吐浑、退浑)的变化过渡,似乎证明了同时在蒙古文和突厥文中出现的一种历史性语音发展:由于中间(非重音的)元音的脱落,而使三音节变成两音节词的变化。这样一来,古典蒙古文abala-(围猎)在近代蒙古文中作awla-(请参阅突厥文avla-,意为“狩猎”),古典蒙古文覿mün覿在近代蒙古文中作觟mn觟(前面)等,古突厥文yügürük在喀喇汗突厥文中作yügrük(疾速,出自意为“奔驰”的yügür-),碑铭中的古突厥文abi觢ran在回鹘文中作tawisran,在近代语言中作taw觢an、tav觢an等,意为“兔子”(请参阅蒙古文taulai,其意义相同)。
-run这个音节是一种后缀,该动词的词根在古代可能为tuyu,后来变作tuy-,完全如同在突厥文中一样。突厥文和蒙古文之间的比较提供了蒙古文中的双音节和突厥语中单音节动词词根的许多例证:蒙古文uqa-(设想、理解)和古突厥文uq-(词义相当多)、蒙古文Sana-(想)和突厥文San-(词义相同)、蒙古文tata-(派生自tarta-,意为“拉拽”)在突厥文中作tart-(词义相同)等。甚至在蒙古语中,某些动词词根(如伯希和所指出的那些)都代表着在双音节和单音节写法之间的犹豫不决:ayu~ai-(受惊,请参阅古突厥文,带有-n的自反动词,如ayin-,其意义相同)、abu-~ab-(取、拿)等。
因此,从“吐谷浑”向“吐浑”的发展,既可以通过突厥文,又可以通过蒙古文来解释。同样,T觟p覿n和T觟p覿t~T觟püt作为t觟p-t覿pü的派生词,而带有-n和-t后缀的做法,可以严格地通过突厥文来解释。带有-n的名词的-t的复数形式,以及以-n结尾的集合名词,都于其中零散地出现了。然而,t觟p覿面对蒙古文dobo显得如同是一种突厥文形式,tuy一早在8世纪时就已经出现在突厥文中了 。据我们所知,它在蒙古文中没有对应词,该名词和该动词很可能是出自突厥文辞汇。
。据我们所知,它在蒙古文中没有对应词,该名词和该动词很可能是出自突厥文辞汇。
因此,我们也如同希伯和一样,倾向于把吐谷浑人视为一个受到了古突厥文化强烈影响(至少在其辞汇中如此)的古蒙古部族集团。他们特别是借鉴了t觟p覿(高地)一词,但却把它以一个古蒙古文后缀的方式作了处理:蒙古文dobo(山岭)可能也是借鉴自t覿p覿,仅仅在元音音级上有所变化,并使辅音浊化:古蒙古文t觟pa可能很正常地产生了蒙古文t觟'覿。同样,其名祖的名称吐谷浑(白色苍鹰)可能起源于突厥文。现知的最古老蒙文文献《蒙古秘史》(约为1240年),就包括相当多的由蒙古人享有的突厥文名字。
“白色苍鹰”的名字,可能同样也以无疑应读作turun的形式,出现在10世纪的一篇回鹘文短文中,被了草地书写在敦煌藏经洞的一卷汉文佛经的背面 。下面就是这篇文献,它可能代表着一句谚语并被记载了两次:“所以,在谚语中就有:飞鹰的后裔共有九只。这九只之中,有一只白鹰。因为它是苍鹰,所以它是猛禽;由于它很凶暴,所以它很善于捕食。”大家可以认为苍鹰的九只鹰雏,代表着被王族统治的“十姓回鹘”中的另外九姓,尤其是白鹰在某种意义上是回鹘人的象征,甚至指回鹘人的uyrur一名本身在汉文中也被用意为“回旋轻捷如鹘”的两个方块字来对音作“回鹘”。至于turun这种写法,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里确实是指白色苍鹰。在933年,也就是在大致相当于我们文献的时代,甘州的回鹘夜落隔可汗向后唐明宗皇帝进白鹘(白鹰)一联
。下面就是这篇文献,它可能代表着一句谚语并被记载了两次:“所以,在谚语中就有:飞鹰的后裔共有九只。这九只之中,有一只白鹰。因为它是苍鹰,所以它是猛禽;由于它很凶暴,所以它很善于捕食。”大家可以认为苍鹰的九只鹰雏,代表着被王族统治的“十姓回鹘”中的另外九姓,尤其是白鹰在某种意义上是回鹘人的象征,甚至指回鹘人的uyrur一名本身在汉文中也被用意为“回旋轻捷如鹘”的两个方块字来对音作“回鹘”。至于turun这种写法,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里确实是指白色苍鹰。在933年,也就是在大致相当于我们文献的时代,甘州的回鹘夜落隔可汗向后唐明宗皇帝进白鹘(白鹰)一联 。此外,很可能是9—10世纪敦煌的这句回鹘谚语中的turun一词在意指“吐谷浑”的同时,还可能变成了回鹘人的第9个部族。因为大家知道,当时在敦煌汉文写本中主要是被称为“退浑”的吐谷浑人,至少直到9世纪末,仍如同回鹘人一样生活在甘州地区
。此外,很可能是9—10世纪敦煌的这句回鹘谚语中的turun一词在意指“吐谷浑”的同时,还可能变成了回鹘人的第9个部族。因为大家知道,当时在敦煌汉文写本中主要是被称为“退浑”的吐谷浑人,至少直到9世纪末,仍如同回鹘人一样生活在甘州地区 。对于回鹘文写本中的TWXWN一词的写法,它似乎是指Turun而不是Tuyrun。据我们来看,这里更应该是指一种不同写法、一种遗漏或书写错误,尤其是在这卷抄写得非常漫不经心的写本中更为如此。事实上,大家丝毫无法理解,一直将二合元音-uy-保持到我们当代的这个具有“白色苍鹰”之意义的词,怎么会在9世纪时失去了这个二合元音中的第2种成分呢?此外,“退浑”这种对音法在9世纪末,还被用于表示吐谷浑的名字。它明确地说明,其名字中第一个音节Tuy-的发音,而“吐浑”的对音恰恰又具体采用了“吐谷浑”最古老对音中的第1个和第3个字,它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机械性简化来解释。
。对于回鹘文写本中的TWXWN一词的写法,它似乎是指Turun而不是Tuyrun。据我们来看,这里更应该是指一种不同写法、一种遗漏或书写错误,尤其是在这卷抄写得非常漫不经心的写本中更为如此。事实上,大家丝毫无法理解,一直将二合元音-uy-保持到我们当代的这个具有“白色苍鹰”之意义的词,怎么会在9世纪时失去了这个二合元音中的第2种成分呢?此外,“退浑”这种对音法在9世纪末,还被用于表示吐谷浑的名字。它明确地说明,其名字中第一个音节Tuy-的发音,而“吐浑”的对音恰恰又具体采用了“吐谷浑”最古老对音中的第1个和第3个字,它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机械性简化来解释。
由于我们在西藏学方面没有任何资格,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对于“吐蕃”的“西方名字Tibet起源于“突厥—蒙古语”的假设,与由最有资格的藏学家们普遍接受的起源论背道而驰。它可能过分大胆冒昧了,甚至是过分不太恰当适宜。尤其是在一篇为该地区最大的藏学专家乌瑞编辑的纪念文集中,这样讲就更为不妥了。因此,我们非常谦虚地提出这种假设,不是作为一种定论,而是作为我们所希望的一种讨论内容。
这样一来,为了促进辩论,我们应该简单地概括总结一下自己的主要论据了。
1.藏文辞源,于其传说开头部分提出的两种不同说法,非常符合逻辑地是以把第2个音节,与吐蕃的土著名称Bod等同起来为基础的,它有许多障碍。对于第一个音节,它是以stod(或mtho)在一种假想的词组中(意为“上部吐蕃”)的近代发音为基础的。据我们所知(这种所知无疑是不充分完整的),人们尚未能确定stod(mtho)在当时的发音。因为当时要比大家认定的该名称的出现时间,早近1000年。其汉文对音“吐蕃”从公元7世纪初叶就已经出现,它大致可以被复原为对T觟p覿n的对音。它出现在一个汉文对音明确地把尾音-n与-d~-t(被用t表示)区别开的时代,它在第2个音节中并不适用于-bod。
2.9世纪时的伊朗—粟特文对音,并不会由于这后一种异议的障碍而不能成立,因为它们确实表现了首先保存在“吐蕃”的阿拉伯—波斯文中,或后来的“西文”名字中的尾音-t。它们实际上可能是对T觟p覿t的对音,我们必须把这种形式与吐蕃的突厥文名称T觟p t作以比较,后者在8世纪时就已经清晰地出现在蒙古的碑铭中了。但T觟p t完全可以被认为是T觟p覿n的一个以-t结尾的“阿尔泰语”(突厥—蒙古语,尤其是蒙古语)的复数形式,这就证明了T觟b覿t(近代作T觟w觟t)的古典蒙古文形式,以-d结尾的古典蒙古文中的写法(以t结尾的复数形式,这与元音后缀之前的带-d-的清辅音浊化相似),从语音上来看并不是合情合理。至于8世纪时的突厥文T觟püt,具有一种第2个音节唇音的同化现象,如同在近代蒙古文中一样(或者是1240年左右在《蒙古秘史》中就已经作T觟b觟t了),却是带有一个ü而不是觟(元音o~觟一般不出现在古突厥文的第一个音节中)。这种唇音化现象也出现在古突厥文(碑铭文和回鹘文)中的t觟pü(顶峰、高地)中,它是自t觟p覿(被保留在新回鹘文中了)变化而来的,而后者本身又是诸如黠戛斯语中的t觟b觟等写法的原形,其未被唇音化的元音被保留在安纳托利亚语和土库曼语等突厥语中了,分别作t覿p覿和d覿p覿(此外,带有由于-觟p-异化作-覿p-的非唇音化现象,就如同在奥斯曼语h覿p中一样,其古老的形式作k觟p)。T觟p覿t(古典蒙古文作T觟b覿t,无疑出自突厥文)~T觟pü,意指吐蕃,t觟p觟覿~t觟pü(顶峰、高地)在语音上异体字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与下面的一种事实结合在一起了,-t与一个以-h结尾的名词(无论是否集合名词)相比较而相当于一个正常的复数形式,这就可以使人把T觟p覿t~T觟püt解释得如同一个用于指“世界屋脊”的“高地”的古老复数名词。
3.作为吐蕃名称的阿拉伯—波斯文Tubbat或Tibbat,于其不同的写法中,表现了在u和i之间的犹豫不决。无论是在阿拉伯文中,还是在波斯文中,都不存在觟,u表现了其唇音特征,i则表现了其腭音特征。其中所拥有的第3个阿拉伯—波斯文元音a无论如何也是不恰当的。它似乎完全应该上溯到了T觟p覿t(~T觟b覿t)。“吐蕃”的“西文”名字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波斯文(它是中世纪西域的通用语言),更应该是以其Tibat的形式出现,很可能是读作Tib覿t(Tibet及其近似形式均由此而来)或Teb覿t(请参阅马可·波罗的写法Tebet)。但它没有重复阿拉伯文中的双辅音b,仅仅以单一的b来区别之。阿拉伯—波斯的科学传统,似乎向突厥人或西域的伊朗—粟特人借鉴了该词。这个问题值得作一番历史研究。
4.附带的假设(与前者有着无关宏旨的联系)。汉人和突厥人(接着可能由于后者而先涉及伊朗—粟特人,再其后又是蒙古人)可能接受了吐谷浑人对“吐蕃”的称呼T觟pan~T觟p覿t~T觟püt的名称,吐谷浑人是一个“阿尔泰”民族集团,于公元4世纪初叶自满洲和辽河地区起,经东部甘肃而定居在青海湖和柴达木地区,甚至一直延伸到罗布淖尔和塔里木盆地南缘。他们直到663年被吐蕃人击败之前,一直统治着这片辽阔的领土。其后,他们的主要首领和大部分吐谷浑部族都逃向了甘肃和鄂尔多斯地区。吐谷浑人在一方面是吐蕃和另一方面是汉人与突厥人(无疑还有粟特人)之间,居于媒介地位以及他们与吐蕃人接触时代,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人把他们视为T觟p覿n(后来作T觟pat,在东突厥语中变成了T觟püt,但在突厥方言中保留作T觟p覿t。末将t觟p覿变为T觟pu)一名的创始人,该词义为“高地”。该名从公元7世纪,就已由汉人以T觟p覿n(吐蕃)的形式所采纳,在8世纪的第一批突厥文献中,就已经以T觟put的形式出现,但它却以稍微更古老一些的形式T觟p覿t,而传给伊朗—粟特人(或通过突厥人,或直接传播)。
5.这些吐谷浑人取名自他们的名祖“白色苍鹰”(Tuy(u)run)。其名称的汉文对音代表着其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在汉文史书中要追溯到公元3世纪)的Tuyurun,后来自9世纪起为Tuyrun(大家可以参阅在732年在阙特勤鲁尼突厥文碑铭中就已经出现的Tuy(u)run一词及其复数形式Tuy(u)rut)。如果我考虑到最后一个时代的汉文对音“退浑”(它更显得如同仅仅是“吐谷浑”的一种简称)的话,那也可以写作Turun。根据各种可能来看,先是名祖英雄的名字和后为部族集团的这个名字,与“白色苍鹰”(Tu-yrun)的名字相同,它在突厥社会中是一种象征英雄行为的飞鸟,其名可能是派生自突厥文tuy-(感觉),以使人联想到猛禽犀利敏锐的目光。这些吐谷浑人语言中的那些罕见的残余均属于“突厥—蒙古语”族,带有在他们的突厥文或古突厥文属性方面的矛盾征象。对这些残余的研究更会使人将此视为古蒙古语,其语言在辞汇中受到了突厥语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有关tuyrun和t觟p覿等词的问题上更为如此。
附 记
在此文写作的最后一刻,由于今天刚从撒马儿罕前来的西姆斯—威廉姆斯博士使我们获到了“吐蕃”名称的一种twpt的写法。它是由利夫希克(Liv觢ik)教授从阿夫拉锡亚卜(Afrāsiyāb)发现的一幅壁画中抄录下来的,那里是撒马儿罕的一个古遗址。twpt mrty(吐蕃人)的题识于壁画中系指一个人物塑像。这里实际上指人们在继汉文对音“吐蕃”之后,直到今天所遇到的西藏地区名字的最古老的形式,因为这里所涉及的题识被考古学的证据断代为公元7世纪的下半叶。然而,twpt的记音带有第一个唇元音,并普遍都会包含有a或覿的第2个音节中元音的一种有缺项动词的字体,它显得完全可以与我们上文作为吐蕃名称的第一种形式而提出的t觟p覿t类的名称兼容并蓄,因而它的古老性就这样得到了证实。
此外,也是在最后一刻,蒲立本教授的文章《黠戛斯名称考》(载《西域学报》第34卷,第1—2期,1990年,第98—108页,我们刚刚获悉了它),又向我们提到了用于指黠戛斯人的整整一大批汉文对音的存在,其中有一些都相当古老了,这就是“隔昆”(公元前2世纪)、“坚昆”(公元前1世纪)、“契骨”和“纥骨”(公元6世纪),同时还有公元6—8世纪的“结骨”。然而,尽管蒲立本先生提出了相当大胆的假设(据他认为,这里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可能是指Qirqir,它是由Qirqiz滥用颤音r而造成的一种不同写法。我们觉得公元前的这两种对音也都清楚地记下了Qirqun之音,而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另外三种不同的对音也非常清楚地记下了Qirqut之音。民族名称Qirqun~Qirqut的不同写法可能分别为qirq(四十部族,当时的Qirgiz代表着以Z-结尾的另外一个复数形式)的以-n结尾的集合名词和以-t结尾的复数形式。因此,它们也完全如同我们刚才研究过的Tuy(u)run~Tuy(u)rut和T觟pan~T觟p覿t等写法相似。
注释:
①尤其是在马可·波罗、鲁布鲁克(Rubrouck)、柏朗嘉宾(Plan Carpin)和鄂多立克(Odoricde)的著作中更为如此。请参阅布勒士奈德(E·Bretschneider):《中世纪研究》第2卷,第24—25页,特别是列昂·费尔(Léon Feer):《吐蕃名称的辞源、历史和拼写法》,其摘要载《第7届国际东方学代表大会论文集》(维也纳1886年版,第63—81页),维也纳1889年版,第1—19页。由列昂·费尔根据藏文bod而提出的吐蕃名称的辞源,至今在学术界仍然广泛受到支持,正如梅维恒(Victor H·Mair)的近作所证明的那样,见《吐蕃与吐鲁番,论吐蕃和吐鲁番古代汉名的起源》,载《西域和内陆亚洲研究》第1卷(1990年),第14—70页,他重复了费尔的所有论据。此外,正是梅维恒这后一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本文解释吐蕃名称的尝试。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梅维恒在《中国—柏拉图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宾夕法尼亚大学东方研究系)第18卷,1990年5月,第B—8和B—9页。
②请参阅在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注释》中罗列的t-th之间交替变化的大量例证(第1—3卷,巴黎1959—1973年版),诸如Catay-Cathay来自Qiray(契丹)、Temu-Themur来自突厥文t覿mür(铁)、Themur i与T覿mür觭in(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名字)、Tauris-Thauris系指波斯城市讨来思或大不里士等,在其他地方还有Alcai-Alchai-Altai用于指阿尔泰山等。
③请参阅德麦松(pierre Desmaisons)的《波斯文—法文辞典》(第1—4卷,罗马1908—1914年版),第1卷,第459页,第2行;斯登加斯(F·Steingass)的《综合波斯文—英文辞典》(伦敦1892年版)第279页第2行。
④有关提及吐蕃的中世纪各种穆斯林舆地文献,请参阅费郎(Gabriel Ferrand):《阿拉伯波斯突厥东方古文献辑注》,巴黎1913—1914年版,第2卷索引第730页有关吐蕃的条目。大家还可以参阅在由若贝尔(A·jaubert)刊布的《埃德里奇舆地书》(1836—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490—943和498页;第2卷,第221和350页)中将吐蕃名称记作tbt的形式。有关tbbt和tubbat的写法,请参阅米诺尔斯基(V·Minorsky)版本的《世界境域志》第92—93页,同时也请参阅其《马韦奇论中国、突厥和印度》第42节,第27—28页和16—17页。
⑤我与奥拉夫·哈桑(Olaf Hasan)的读法不同,他在这条题识的第一个版本中,于此在第19行读作twp'wt'hy(吐蕃人)。请参阅哈桑:《粟特文书和喀拉巴勒哈逊碑解读》,载《芬兰—乌戈尔学会会刊》第44卷,第3期,赫尔辛基1930年版,第20和24页。哈密屯(J·Hamilton)于60年代根据拉科斯特(Lacoste)的拓片而对该碑的释读中读作Twp'yt'ny,而且也如同粟特文专家吉柯丰在他对喀拉巴勒哈逊碑的粟特文进行释读时所作的那样,其文载《内陆亚细亚研究》第28卷,1988年,第34、37和47页。
⑥有关拉达克的碑文,请参阅米勒(F·W·K·M lle):《拉达克的粟特文碑文》,载《普鲁斯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1925年,第371—373页;邦文尼斯特:《粟特语考证》,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9卷,1938年,第502—505页;普雷斯登(Mark Presden):《粟特语及其文献》,载《剑桥伊朗史》第3卷,第2册,第1229页。这篇简短的碑文已被断代为210年,无疑属于伊嗣俟(Yaztigird)统治时代,它以这样一段文字结束:“致吐蕃(Tw p'(')yr)可汗的信”。字母之间的一细横笔(')以及吐蕃名字中的y(大家有时也读作Twp'nyt和Twp'yyt)应该相当于石碑上的一处瑕疵,而不是一个字母。
⑦载《〈耶斯那(Yasna)〉注释》第4卷第58页,请参阅《〈耶斯那〉注释和三种帕拉维语残卷》,由安克莱萨里亚(Anklesaria)发表的原文、对音转写文和英译文,孟买1957年版,第34页。有关对该文的可能断代,请参阅吉努(P.Gignoux):《论〈阿维斯陀(Avesto)〉中的〈耶斯那)之存在》,载《亚洲研究学报》第32卷,1986年,第53—64页。
⑧请参阅前文注[1]中所引列昂·费尔:《吐蕃名称的辞源、历史和拼写法》,第12页注[1]。
⑨尤其是在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第4—5行中,分别于东侧或其他地方。请参阅汤姆森(V·Thomson):《鄂尔浑碑铭释读》,载《芬兰—乌戈尔学会论丛》第5卷,1896年,第98、114、115和140页;奥尔昆(H·N·Orkon),《古代突厥碑铭》第1卷,第24、30和52页,第1卷索引第169页。有关在第一个音节中带有觟(而不是ü)的句子的读法,请参阅下文不远处。
⑩有关“吐蕃”的名称,请参阅诸桥辙次(Moroha shi Tetsuji)《汉和辞典》第3300—3373页条,第3卷,第842页。有关这些汉文方块字的古代发音,请参阅高本汉B·Karlgren):《汉文典修订》(1957年斯德哥尔摩重版)第62d条,第37页和第195m条,第71页;还可以参阅蒲立本:《中古汉语,历史语音研究》,温哥华1984年版,附录1,第232—237页有关中古汉语的发音问题和晚古汉语的问题。(www.zuozong.com)
 为了解释说在公元7世纪左右之前,人们在汉文文献中未发现指西藏人的专用名词(也就是“吐蕃”),大家无疑应假设认为汉人直到那时为止实际上并不了解他们。有关这一问题,特别请参阅莫勒(G·Mole)的著作:《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人》,罗马1970年版,第172页注[473]。我们于其中在有关641年事件的问题上,可以读到对吐蕃名称的论证。
为了解释说在公元7世纪左右之前,人们在汉文文献中未发现指西藏人的专用名词(也就是“吐蕃”),大家无疑应假设认为汉人直到那时为止实际上并不了解他们。有关这一问题,特别请参阅莫勒(G·Mole)的著作:《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人》,罗马1970年版,第172页注[473]。我们于其中在有关641年事件的问题上,可以读到对吐蕃名称的论证。
 克洛松(G·Clauson):《13世纪之前突厥辞源辞典》,牛津1972年版,第436页;多尔菲(G·Doerfer)《新波斯语中的突厥和蒙古语成分》第2卷,威斯巴登1965年版,第172条,第450—452页。
克洛松(G·Clauson):《13世纪之前突厥辞源辞典》,牛津1972年版,第436页;多尔菲(G·Doerfer)《新波斯语中的突厥和蒙古语成分》第2卷,威斯巴登1965年版,第172条,第450—452页。
 蒲立本:《古汉语中的辅音体系》第2部分,载《泰东》杂志第9卷,第2期,1963年,第226—262页。
蒲立本:《古汉语中的辅音体系》第2部分,载《泰东》杂志第9卷,第2期,1963年,第226—262页。
 同上引文第261页。
同上引文第261页。
 特别请参阅本文开始时引证的费瑯和梅维恒的论文,同时还可参阅格李默德(Grenard):《西藏》(巴黎1904年版),第242页注①;哈密屯:《五代回鹘史料》(巴黎1955年版)第20页注[3]。
特别请参阅本文开始时引证的费瑯和梅维恒的论文,同时还可参阅格李默德(Grenard):《西藏》(巴黎1904年版),第242页注①;哈密屯:《五代回鹘史料》(巴黎1955年版)第20页注[3]。
 海涅什(E·Haenisch):《〈蒙古秘史〉中的辞汇》,莱比锡1939年版,第183页。
海涅什(E·Haenisch):《〈蒙古秘史〉中的辞汇》,莱比锡1939年版,第183页。
 上引克洛松:《13世纪之前突厥语辞源辞典》,第435页和436页;杰夫纳朱尔斯基(Drevnetjursij):《辞典》(列宁格勒1969年版)第552页和580页。
上引克洛松:《13世纪之前突厥语辞源辞典》,第435页和436页;杰夫纳朱尔斯基(Drevnetjursij):《辞典》(列宁格勒1969年版)第552页和580页。
 上引克洛松书,第686页;杰夫纳朱尔斯基:《辞典》第317页。
上引克洛松书,第686页;杰夫纳朱尔斯基:《辞典》第317页。
 上引海涅什书第34页的de'ere;第35页,dege'unuber,带有一个保留下来的-g-。
上引海涅什书第34页的de'ere;第35页,dege'unuber,带有一个保留下来的-g-。
 上引海涅什书第54页,ha'ahu(环绕)。有关已清楚地知道的蒙古文或突厥文形式,请参阅大家常用的各种辞典。
上引海涅什书第54页,ha'ahu(环绕)。有关已清楚地知道的蒙古文或突厥文形式,请参阅大家常用的各种辞典。
 出现了婆罗谜(Brāhmi)文字的突厥回鹘语中的非开始音节中的o—觟的写法(当不是指未参照语音差异的机械记音时)应该是对由t-ü的造成的结果(比较开放)的特殊差异的记音,没有采用在语位学上的合适做法。在回鹘语中,诸如bir觟k(在……情况下)那样的写法标志着oq-觟k失去重音词的结合(上引杰夫纳朱尔斯基《辞典》第1卷,第103和369页,第4卷第382页);奥斯曼语中现在时的后缀是一个古老的失去重音的辅动词yori-(行走,前往等)。
出现了婆罗谜(Brāhmi)文字的突厥回鹘语中的非开始音节中的o—觟的写法(当不是指未参照语音差异的机械记音时)应该是对由t-ü的造成的结果(比较开放)的特殊差异的记音,没有采用在语位学上的合适做法。在回鹘语中,诸如bir觟k(在……情况下)那样的写法标志着oq-觟k失去重音词的结合(上引杰夫纳朱尔斯基《辞典》第1卷,第103和369页,第4卷第382页);奥斯曼语中现在时的后缀是一个古老的失去重音的辅动词yori-(行走,前往等)。
 特别请参阅鲍培(N·Poppe):《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威斯巴登1960年版,第22—23页。
特别请参阅鲍培(N·Poppe):《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威斯巴登1960年版,第22—23页。
 鲍培:《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赫尔辛基1955年版,第102—105页。
鲍培:《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赫尔辛基1955年版,第102—105页。
 11世纪的回鹘语方言中由t-到d-的浊音化,已由喀什噶里(Kasgari)所指出,请参阅阿塔赖(B·Atalay):《突厥语大辞典》,安卡拉1943年版,索引第165—166页。
11世纪的回鹘语方言中由t-到d-的浊音化,已由喀什噶里(Kasgari)所指出,请参阅阿塔赖(B·Atalay):《突厥语大辞典》,安卡拉1943年版,索引第165—166页。
 海涅什:同上引书,第37和151页;杰夫纳朱尔斯基:《辞典》第580和581页;上引克洛松书,第531页。该突厥文就如同对于t觟p覿-t觟pü一样,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尾音-覿~-ü),t觟r覿-t觟rü。在这两种情况下,正是带-ü的一些不同写法出现在8世纪的碑铭文献中了。
海涅什:同上引书,第37和151页;杰夫纳朱尔斯基:《辞典》第580和581页;上引克洛松书,第531页。该突厥文就如同对于t觟p覿-t觟pü一样,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尾音-覿~-ü),t觟r覿-t觟rü。在这两种情况下,正是带-ü的一些不同写法出现在8世纪的碑铭文献中了。
 汉文对音转写词在a覿ga'ün中保留了带有-g-的d覿g覿-,海涅什作dege' n,上文业已引证)。
汉文对音转写词在a覿ga'ün中保留了带有-g-的d覿g覿-,海涅什作dege' n,上文业已引证)。
 上引鲍培《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第93—98页。
上引鲍培《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第93—98页。
 杰夫纳朱斯基:《辞典》第176页;上引克洛松书,第232页。土耳其的近代突厥语中的erenler是伊斯兰教苦行僧们的呼吁术语。
杰夫纳朱斯基:《辞典》第176页;上引克洛松书,第232页。土耳其的近代突厥语中的erenler是伊斯兰教苦行僧们的呼吁术语。
 上引鲍培书:第176—177页;韩百诗:《蒙古书面语言语法》,巴黎1945年版,第3页,第2条。
上引鲍培书:第176—177页;韩百诗:《蒙古书面语言语法》,巴黎1945年版,第3页,第2条。
 有关蒙古文,请参阅上引韩百诗(Louis Hambis)书。作者指出,在古蒙古文中,hoqan指“犬”,qularan指“盗贼”,此外还有前文已引证过的raqan。但名词的哑尾音-n则相当于一种单数形式,与以-t结尾的复数形式相对:mori(n)指“马”的单数,morit指“马”的复数。在安纳托利亚突厥语中,qizan是“少女”、“童贞女”的古代集合名词,但在地区性的意义上也具有“青年小伙子”(童男)的意义。在其他地区,派生词t覿mr覿n(派生自t覿mir,意为“铁”)指“箭矢或矛枪上的铁”;k k n(派生自k k,根)意为“起源”,或者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把、根柄”(指甜瓜或西瓜把)。但它们后来都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有关蒙古文,请参阅上引韩百诗(Louis Hambis)书。作者指出,在古蒙古文中,hoqan指“犬”,qularan指“盗贼”,此外还有前文已引证过的raqan。但名词的哑尾音-n则相当于一种单数形式,与以-t结尾的复数形式相对:mori(n)指“马”的单数,morit指“马”的复数。在安纳托利亚突厥语中,qizan是“少女”、“童贞女”的古代集合名词,但在地区性的意义上也具有“青年小伙子”(童男)的意义。在其他地区,派生词t覿mr覿n(派生自t覿mir,意为“铁”)指“箭矢或矛枪上的铁”;k k n(派生自k k,根)意为“起源”,或者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把、根柄”(指甜瓜或西瓜把)。但它们后来都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笼统泛指的“孩子”(儿子或女子)的意义(中性)也残存于安纳托利亚突厥语中,如qiz orlan(qir具有“童男”的意义,与“少女”的意义共存),它原来是指“童贞孩子”(请参阅前一条注释,安纳托利亚语中作qizan),它与具有“姑娘”、“少女”之意义的qiz,在一个初看起来很奇怪的短语中,形成了一个定语词组qiz orian qiz(童贞女)。
笼统泛指的“孩子”(儿子或女子)的意义(中性)也残存于安纳托利亚突厥语中,如qiz orlan(qir具有“童男”的意义,与“少女”的意义共存),它原来是指“童贞孩子”(请参阅前一条注释,安纳托利亚语中作qizan),它与具有“姑娘”、“少女”之意义的qiz,在一个初看起来很奇怪的短语中,形成了一个定语词组qiz orian qiz(童贞女)。
 在阿尔泰语范围内,具有遗传性衍生关系的突厥—蒙古语的一种在不同程度上是传统性的辞义倾向于取代另外一种主要是由多尔菲阐明的理论,此人在承认突厥—蒙古语比较研究对于重新复原古突厥语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又承认蒙古语(仅仅从13世纪起才以活跃的方式出现,而突厥语却是自8世纪起开始出现的)则是一种具有其他起源的语言,但它在其辞汇和甚至是其语法中,都深受先是古突厥文,后是历史突厥语的影响,甚至是改变,以至于在它以文字定形时,就显得如同是与突厥语组具有亲缘关系。请参阅巴赞:(Louls Bazin)《突厥—蒙古问题辨析》,载《突厥学报》第15卷,1983年,第31—58页。
在阿尔泰语范围内,具有遗传性衍生关系的突厥—蒙古语的一种在不同程度上是传统性的辞义倾向于取代另外一种主要是由多尔菲阐明的理论,此人在承认突厥—蒙古语比较研究对于重新复原古突厥语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又承认蒙古语(仅仅从13世纪起才以活跃的方式出现,而突厥语却是自8世纪起开始出现的)则是一种具有其他起源的语言,但它在其辞汇和甚至是其语法中,都深受先是古突厥文,后是历史突厥语的影响,甚至是改变,以至于在它以文字定形时,就显得如同是与突厥语组具有亲缘关系。请参阅巴赞:(Louls Bazin)《突厥—蒙古问题辨析》,载《突厥学报》第15卷,1983年,第31—58页。
 有关汉文字的古代发音问题,请参阅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斯德哥尔摩1957年再版)第62d—1202a条(但该字应如同第1202d那样读音),和第458b条。大家还可以参阅蒲立本:《中日汉语,历史语音学研究》和《晚古汉语》。有关该名词的对音与发音,还可以参阅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载《东方丛刊》第41卷,罗马1970年号,第1期,第66—67页。大家将会于其中发现有关汉文史料和年代的全部具体解释。
有关汉文字的古代发音问题,请参阅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斯德哥尔摩1957年再版)第62d—1202a条(但该字应如同第1202d那样读音),和第458b条。大家还可以参阅蒲立本:《中日汉语,历史语音学研究》和《晚古汉语》。有关该名词的对音与发音,还可以参阅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载《东方丛刊》第41卷,罗马1970年号,第1期,第66—67页。大家将会于其中发现有关汉文史料和年代的全部具体解释。
 请参阅伯希和《吐谷浑和苏毗考》,载《通报》第20卷,1921年,第323—331页;莫莱,同上引书,第12页以下。
请参阅伯希和《吐谷浑和苏毗考》,载《通报》第20卷,1921年,第323—331页;莫莱,同上引书,第12页以下。
 有关大批吐谷浑人在663年被吐蕃人击败后离开青海湖地区、并接着定居在甘肃东部和鄂尔多斯地区的情况,特别请参阅上引莫莱的著作第58—63页和相对立的注释。
有关大批吐谷浑人在663年被吐蕃人击败后离开青海湖地区、并接着定居在甘肃东部和鄂尔多斯地区的情况,特别请参阅上引莫莱的著作第58—63页和相对立的注释。
 请参阅上引莫莱书,第59—61页。
请参阅上引莫莱书,第59—61页。
 请参阅汤姆森:《鄂尔浑碑铭释读》第2分册,载《芬兰—乌戈尔学会论丛》第5卷,赫尔辛克府1896年版,第119—120页;奥尔昆:《古代突厥碑铭》第1卷(伊斯坦布尔1936年版),第52—53页;塔拉·特肯(Talat Tekin):《鄂尔浑突厥文语法》(布卢明顿1968年版)第237页和272页;克洛松:同上引书,第568页。将部族名称Tay(u)-run吐谷浑和相当于汉文“大官”的t(a)y-qu(a)n之间的混淆,也出现在间一篇碑文东南侧的1行文字中。克洛松误解了这一段文字。
请参阅汤姆森:《鄂尔浑碑铭释读》第2分册,载《芬兰—乌戈尔学会论丛》第5卷,赫尔辛克府1896年版,第119—120页;奥尔昆:《古代突厥碑铭》第1卷(伊斯坦布尔1936年版),第52—53页;塔拉·特肯(Talat Tekin):《鄂尔浑突厥文语法》(布卢明顿1968年版)第237页和272页;克洛松:同上引书,第568页。将部族名称Tay(u)-run吐谷浑和相当于汉文“大官”的t(a)y-qu(a)n之间的混淆,也出现在间一篇碑文东南侧的1行文字中。克洛松误解了这一段文字。
 汤姆森:同上引书,第119页;奥尔昆:同上引书,第1卷,第28页;特肯:同上引书,第232页和263页。
汤姆森:同上引书,第119页;奥尔昆:同上引书,第1卷,第28页;特肯:同上引书,第232页和263页。
 莫莱:同上引书,第189页注[518]。
莫莱:同上引书,第189页注[518]。
 柯克:《突厥驯鹰术考》,载《巴斯勒档案》,第4卷,第1期描印本,莱比锡和柏林1913年版,第2页注[2]和第10—11页。
柯克:《突厥驯鹰术考》,载《巴斯勒档案》,第4卷,第1期描印本,莱比锡和柏林1913年版,第2页注[2]和第10—11页。
 拉德洛夫:《突厥方言辞典》(4卷本,圣·彼得堡1893—1911年版,第3卷,第1424页(而不是1432页)。
拉德洛夫:《突厥方言辞典》(4卷本,圣·彼得堡1893—1911年版,第3卷,第1424页(而不是1432页)。
 儒达克辛:《吉尔吉斯语—俄语辞典》,第2版,莫斯科1965年版。请参阅tujgun-条目。
儒达克辛:《吉尔吉斯语—俄语辞典》,第2版,莫斯科1965年版。请参阅tujgun-条目。
 请参阅莫莱:同上引书,序言第12页和正文第1—3页。
请参阅莫莱:同上引书,序言第12页和正文第1—3页。
 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东方古文献辑注》,第1卷,巴黎1913年版,第46页;同一位作者:《851年写成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印度和中国旅行记》,巴黎1922年版,第72—73页。
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东方古文献辑注》,第1卷,巴黎1913年版,第46页;同一位作者:《851年写成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印度和中国旅行记》,巴黎1922年版,第72—73页。
 魏特夫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纽约1949年版,第105页,第25和26条。
魏特夫和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纽约1949年版,第105页,第25和26条。
 伯希和:《吐谷浑和苏毗考》,载《通报》第20卷,1921年,第323页。
伯希和:《吐谷浑和苏毗考》,载《通报》第20卷,1921年,第323页。
 前引莫莱的精辟论著:《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浑谷人》第67页。他于其中在有关对吐谷浑一名进行解释的历史问题上,出现了一个错误。这并不是拉问德洛夫(《辞典》第3卷,第1432页)把阙特勤碑中的官号Tuyrun与吐谷浑联系起来了,也不是他将该词视为动词fuy(感觉)的派生词。事实上,拉德洛夫于其《辞典》第3卷第1424页(并非是1432页,这是魏特夫和冯家昇的错误)仅限于指出(就如同是两个不同的词和未提及的动词tuy-一样):(1)tu-jrun——一种官衔;稍后不远处又在(2)Tujrun——白色苍鹰。正是魏特夫和冯家昇于1949年(同上引书,第105页注[26],在有关“退浑”的对音问题上)都想到了把吐(谷)浑的名称与由拉德洛夫(《辞典》第3卷第1432(1424)页)提及的尊号tujrun作以区别,并且以动词tuy-(感受)来解释之。但并未因此而联想到像勒柯克曾作过的那样,将这种写法比作由拉德洛夫于下文不远处作出的“白色苍鹰”的解释。
前引莫莱的精辟论著:《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浑谷人》第67页。他于其中在有关对吐谷浑一名进行解释的历史问题上,出现了一个错误。这并不是拉问德洛夫(《辞典》第3卷,第1432页)把阙特勤碑中的官号Tuyrun与吐谷浑联系起来了,也不是他将该词视为动词fuy(感觉)的派生词。事实上,拉德洛夫于其《辞典》第3卷第1424页(并非是1432页,这是魏特夫和冯家昇的错误)仅限于指出(就如同是两个不同的词和未提及的动词tuy-一样):(1)tu-jrun——一种官衔;稍后不远处又在(2)Tujrun——白色苍鹰。正是魏特夫和冯家昇于1949年(同上引书,第105页注[26],在有关“退浑”的对音问题上)都想到了把吐(谷)浑的名称与由拉德洛夫(《辞典》第3卷第1432(1424)页)提及的尊号tujrun作以区别,并且以动词tuy-(感受)来解释之。但并未因此而联想到像勒柯克曾作过的那样,将这种写法比作由拉德洛夫于下文不远处作出的“白色苍鹰”的解释。
 汤姆森:同上引书,第120页;拉德洛夫:《蒙古古突厥碑铭》,圣彼得堡1895年版,第38—39页;奥尔昆:同上引书,第1卷,第54页;特肯:同上引书,第238和272。
汤姆森:同上引书,第120页;拉德洛夫:《蒙古古突厥碑铭》,圣彼得堡1895年版,第38—39页;奥尔昆:同上引书,第1卷,第54页;特肯:同上引书,第238和272。
 伯希和:同上引书,第325—330页。
伯希和:同上引书,第325—330页。
 请参阅伯希和:同上引书,第328—329页。稍后不久,伯希和又在《通报》第29卷(1932年)第26页中,可能摒弃了他对于汉文对音“出”与蒙文觬i(你)之间对应关系的假设,更主张相当于蒙古文覿b或。请参阅蒲立本:《古汉语的辅音体系》第2部分,载《泰东》杂志,第9卷,第2期,1963年,第261页;莫莱:同上引书,第70—71页。事实上,我们似乎应该把汉文“出”视为i、而不是i的对音,因为蒙古语中的第二人称代词sg、i、gcn,inu(而不是inü)都应该是古代的i(晚期了)。
请参阅伯希和:同上引书,第328—329页。稍后不久,伯希和又在《通报》第29卷(1932年)第26页中,可能摒弃了他对于汉文对音“出”与蒙文觬i(你)之间对应关系的假设,更主张相当于蒙古文覿b或。请参阅蒲立本:《古汉语的辅音体系》第2部分,载《泰东》杂志,第9卷,第2期,1963年,第261页;莫莱:同上引书,第70—71页。事实上,我们似乎应该把汉文“出”视为i、而不是i的对音,因为蒙古语中的第二人称代词sg、i、gcn,inu(而不是inü)都应该是古代的i(晚期了)。
 伯希和:同上引书,第331页。
伯希和:同上引书,第331页。
 杰夫纳朱尔斯基:《辞典》第584页;上引克洛松书,第567页。
杰夫纳朱尔斯基:《辞典》第584页;上引克洛松书,第567页。
 这里是指分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中的一卷写本,分别被编为or·8212(116)号和P.2969号。请参阅在哈密屯版本中对卷子背面回鹘文书的研究:《9—10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第1卷,第17号文书,第97—101页。
这里是指分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中的一卷写本,分别被编为or·8212(116)号和P.2969号。请参阅在哈密屯版本中对卷子背面回鹘文书的研究:《9—10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第1卷,第17号文书,第97—101页。
 哈密屯:《9—10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同一位作者:《以五代回鹘史料》,第79和93页。
哈密屯:《9—10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同一位作者:《以五代回鹘史料》,第79和93页。
 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西姆斯—威廉姆斯(Sims-Millams)和哈密屯:《敦煌9—10世纪突厥—粟特文献汇编》,收入了《伊朗碑铭集》第2套第3卷,伦敦1990年版,其中第63—76页是对G号写本的研究,尤其是注G16和其中所涉及的汉文写本第42—47幅图版。
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西姆斯—威廉姆斯(Sims-Millams)和哈密屯:《敦煌9—10世纪突厥—粟特文献汇编》,收入了《伊朗碑铭集》第2套第3卷,伦敦1990年版,其中第63—76页是对G号写本的研究,尤其是注G16和其中所涉及的汉文写本第42—47幅图版。
 例如,可以参阅上引哈密屯和西姆斯—威廉姆斯书,图版43—45。它是保存在伦敦的斯坦因敦煌汉文写本,应断代为884年或885年。
例如,可以参阅上引哈密屯和西姆斯—威廉姆斯书,图版43—45。它是保存在伦敦的斯坦因敦煌汉文写本,应断代为884年或885年。
 这篇联袂署名的文章的出发点是两位作者分别得出了这样一种坚信,即“吐蕃’的“西文”名称应通过参阅突厥文T觟p覿~t觟pü(顶峰、高地)来解释,从8世纪起就出现的“吐蕃”的突厥文名称T觟püt是t觟pü带尾音-t的复数形式,意为“高地”。
这篇联袂署名的文章的出发点是两位作者分别得出了这样一种坚信,即“吐蕃’的“西文”名称应通过参阅突厥文T觟p覿~t觟pü(顶峰、高地)来解释,从8世纪起就出现的“吐蕃”的突厥文名称T觟püt是t觟pü带尾音-t的复数形式,意为“高地”。
哈密屯又以汉文和伊朗—粟特文领域中继续进行了研究,解释了“吐蕃”名称的汉文和伊朗—粟特文对音。他认为此名是经由吐谷浑人传给汉人和突厥人的。他又将“吐谷浑”一名比定为Tuyrun(白色苍鹰)。
路易·巴赞则从突厥—蒙古语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了所提出的语音问题。
 请参阅上引德麦松:《波斯语—法语辞典》第1卷第459页,第2行。
请参阅上引德麦松:《波斯语—法语辞典》第1卷第459页,第2行。
(译自维也纳1991年出版的乌瑞纪念文集《西藏历史和语言》一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