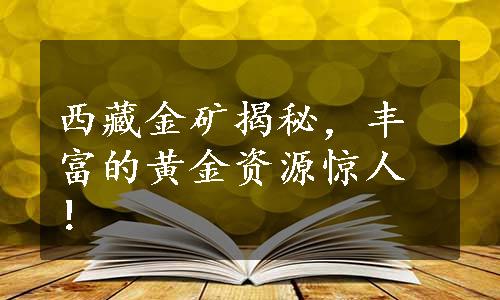
西藏的金矿
布尔努瓦
西藏史书中经常提到该地区盛产黄金。这不仅仅始终是西藏人和西藏的所有近邻熟悉的一件事,公众舆论、旅行家和作家们的记述,又把这种消息传到了欧洲,而且从中世纪起,甚至从希腊—罗马古代起就如此了。数世纪以来,由西藏向印度、尼泊尔,以及中国中原地区输出金砂,已形成了一种持续的潮流,源出于西藏这一大水塔的所有河流(从昆仑山流向北方、从喜马拉雅山流向南方、从东山流向汉地)都夹裹有金砂。所有这一切都扩大了有关对西藏蕴藏有丰富黄金的可信度。其次,某些确实曾到过西藏的旅行家、远征军士兵和传教士们,也不断地重复说,在某某地区蕴藏着金矿。某些神奇的传说最终形成了。这种传说甚至比锁国政策还顽固。确实那里很早就不允许前往就地核查这一切是否真实。西藏未知的金矿始终都富有奇迹色彩,再没有比有关这种金属的传闻更为根深蒂固的奇迹了。
甚至在西藏本地,古代史著也追述了一种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的热冶金属的学问,在这些金属中就有黄金。《拉达克史》把木炭和熔化金属矿物铁、银、铜的发明归功于布岱贡杰赞普(吐蕃最古王朝的第9代赞普)时代。另外一种西藏编年史却把冶炼黄金(热炼)也归于了这一时代。这些创造和发明的古老历史及其传奇性,也出现在以下事实中:有人把架设桥梁,使用牛轭,木工、灌渠(也就是说当地物质生活的基础)的发明也归于了同一政权时代。正如汉地神话把农业、养蚕业和文字的发明归功于传说中的某位皇帝一样。
我仅举对制造木炭法的记载为例,这种燃料在全世界,一直到当代仍是冶金业的基础。这就意味着要有茂密的森林。冶金业的发展有时也成了这些森林的破坏因素。我们甚至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冶金业在非常古老时代的发展,只出现在西藏等几个被认为是植被很好的少数地区(尤其是东南部)。另外,如果西藏现今的无树地区当时覆盖着森林,那么该地区的木炭发明就可说是非常古老了。
西藏编年史中还记载说,热冶黄金术是与以水冲刷的冷淘金完全不同的一种工序。黄金几乎与所有的其他金属相反,它常常可以在完全不用燃料的情况下经营开发,特别是呈粉砂和片状冲积金的情况更为如此。
这无疑就是“蚂蚁金”(Paippilika),即出现在《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梵文词。这部印度史诗被断代为发明木炭的印度国王时代,或者还要古老一些,其各部分无疑是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完成的。这是对我们可以归于喜马拉雅地区的黄金之首次记载。因为据该史诗记载,这种“蚂蚁金”在某一更为遥远的时代,而由生活在北部高山以远地区的民族作为贡物奉献给印度国王,该地区就是喜马拉雅山区某地,也可能就是西藏本土。莫尼埃—威廉姆斯的《梵文英文辞典》指出,Pipilaka是一种被认为是由蚂蚁采掘出的黄金,该词与其他某些均指蚂蚁的各种词汇并列。我们还将有机会来重新论述这些蚂蚁。
但我们首先应具体说明,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以吐蕃(其他史料中分别称为Tubbet,Tabat、Tebet、Bhot、Bhoutan,西藏、藏、乌斯藏、西番、唐古特或Bagharghor)之名所称呼的地区,不仅仅包括现今中国的整个西藏自治区,而且还包括青海省的一大部分和拉达克(今印度克什米尔邦的一个县,历史上的记载中也往往称之为“吐蕃”)。在18世纪时,“西藏”在很大程度上也指列城。但“西藏”主要是包括一块以一条令人赞叹不已的山脉城墙环绕的辽阔高原(海拔分别为4000、4500、甚至6000米高),南部以珠穆朗玛峰(8884米)为最高点,它是世界的屋脊,北部是海拔超过7000米的昆仑山,西部和东部是其高峻程度也并不逊色的山脉。在不同的时代,大家所使用的这个地理名称则分别指该地区的部分或全部地段。但在大部分时代中,一旦当使用一个具体名称指该地区时,我们都发现它与产金有关。
《旧唐书》(618—907年中国的断代史)就认为吐蕃盛产金、银、铜和锡等矿物。
在古波斯文舆地书《世界境域志》(982年的作品)中,就提到了吐蕃的Ràng rong(rong在藏文中意为“河谷”)之金矿,作者把该地区描述成了一个由游牧民居住的非常贫瘠的地区,与印度斯坦和中国中原相毗邻。在这些山区中有金矿,在那里可以发现有“互相连在一起的几颗羊头大的”天然金块。“无论任何人采集到这种金块并将之带回家中,死亡就要袭击全家,直到把金块放回采出的原地为止”。同一部著作还指出在吐蕃的N.Zvān地区出产金矿。
据《拉达克史》记载,某一位拉达克国王在930年晏驾之前,将其王国划分给了膝下主子:长子分得了拉达克、东部的日土以及“戈人的金矿”。我们可以把该金矿考定在西藏西部、印度河上游以东的某处。
13世纪时,马可·波罗指出,在“吐蕃”有多处可以采掘到大量金片的湖泊和江河地。
在同一时代,鲁布鲁克(他本人从未亲自前往吐蕃,但在他的蒙古之行期间曾风闻吐蕃的情况)叙述说,吐蕃“盛产黄金,以至于使那些需要黄金的人,只要掘地就可以尽量采掘,然后再把剩余者掩埋起来。如果他们用黄金装满了自己的箱子或房间,以使那里成为宝库,那么他们就认为上天将使他们失去埋藏在地下的黄金”。
米儿咱·海答儿(柏柏尔皇帝的堂兄弟)于1532年为疏勒王之请,而对西藏发动了战争。该穆斯林王子希望把这次征战视为一次圣战行为,以得到大食人的青睐。但他也可能怀有某种经济目的,而抢劫“金地”(Altunji)所拥有的财富。“金国”之名颇有意义地赋予了这一盛产黄金的地区。米儿咱·海答儿在一部叫作《拉失德史》的史著中,提供了对16世纪中叶西藏和拉达克地区的一种富有意义的描述,其中在叫作《西藏珍异记》的一章中,论述了金矿。
在康人(作者用该词泛指所有的西藏游牧民)的大部分县中,都可以找到金矿。
在这些金矿中,有两个十分引人注目:其一被蒙兀儿人叫作西藏的金地,为杜勒巴人开采,由于那里气候极为寒冷,他们每年只能在那里工作40天。在平坦的地面上挖掘了许多相当大的沟壑或土洞,以至于人也可以从中穿行。很大一部分或大部分洞都从其两端与其他洞互相连接。据称有300名族长就长期生活在这些壕沟土洞中。他们从遥远的地方监视着蒙兀儿人的到达。当蒙兀儿人接近时,这些人就蜷缩起来并爬进其土洞中,任何人都无法在那里找到他们。洞中不点任何灯盏,唯有用绵羊奶制成的酥油。他们从这些洞中挖掘土,然后再淘洗(记叙这一故事的人敢于作保),据称从这种矿内挖掘的一筛子土中,就可以得到几米特喀勒的黄金。一个人独自掘土挖矿并运输和淘洗,他在数日内可以精选满满的20筛子矿土。虽然这一切可能显得不可思议,但我在西藏到处都能听到证实这种情况的话,所以我才记录了下来。
古格有200个堡塞和村落。该地区的长度有3日行程的距离,在那里到处都可以发现金矿,到处都有人挖土。如果在那里铺上一块绢,那么就会从中得到黄金。金粒几乎有一粒扁豆和豌豆大小,人称在该地区有时会得到大如羊肝般的金块。我在古格征敛贡物时,一些社会名流向我介绍说:某人近来正在挖掘一片土地,当其镐头用力刨,嵌入某种东西时,他用尽全力也无法拔出来。他清理了土层后,发现这是一种中间含有黄金的石头,其镐头正好嵌在其中。他将镐头留在原地,然后去报告官员。数人立即赶到现场,拔出镐头,砸碎石块,从中得到了重一千五百西藏米特喀勒的纯金(一西藏米特喀勒相当于1.50普通米特喀勒)。上天造就了这种土壤,以至于当人们从土中挖金时,敲打、煮沸和压挤均徒劳无益,其体积都不会变小,而只能以火熔之。这是令人最为惊奇的现象,那些试验者们认为它非常奇特。此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未曾遇到过这种特点。
我们于下文再回头来论述这段文字记载与其他文献的相似处。我们现在就应仅注意到,Altunji一词被翻译家们译为“金地”。这不是一个藏文词,它非常强烈地使人联想到起源于蒙古文和突厥文的那些意为“金”的名词:Altan、Altoun、Altyn等。我们还在许多地名中,甚至在一个起源于蒙文指钱币的古俄文字altyn中,也发现了该词的踪迹。令人奇怪的是大家在一幅18世纪的印度和中国地图中,也发现了该词。这幅地图是由伊斯勒的法国地理学家纪尧姆绘制的,该地名恰恰是西藏的产金地,正如我于下文将要看到的那样。但是如果说米儿咱·海答儿的文献似乎是指位于西部西藏(日土、古格等)的金矿区,那么纪尧姆的地图则把金矿区置于西藏东部。
在《拉失德史》问世的40多年以后,《阿克巴尔纲要》(由阿克巴尔的大相和朋友阿布勒·法兹勒编纂,成书于1597年)也提到了西藏的金矿,但却认为其收益甚小。“虽然印度斯坦有黄金出口,可以在该地区北部山区找到丰富的黄金,在西藏也可以通过萨伦的办法,而在恒河和印度河以及其他数条江河的沙子中淘得黄金,但所付出的辛苦和开支大大超过了利润”。据乔治·瓦特的印度经济辞典认为,萨伦采金法即淘金。
在17世纪时,威尼斯人尼古拉·玛努奇在1656—1717年生活在印度(他遇到贝尔尼埃,还很可能遇到了白乃心和吴尔铎,我于下文再来论述),他也重复说Botand(西藏)蕴藏有“丰富的金矿”,但没有具体指出在哪个地区。相反,塔维尼埃(法国商人,他于1640—1675年间曾在印度长期居住)通过他在巴特那遇见的西藏人(他们前往出售麝香)而获悉,在Boutand(西藏)确实有一银矿,但无法告诉他该矿位于什么地方。至于黄金,“他们所拥有的少许是自利凡得(东方)来的商人带给他们的”。这种说法,与直到那时为止和于此之后所获得的看法相抵触。但大家知道,塔维尼埃并未亲自前往西藏,他所记载的一切都被我于下文谈到的18世纪初叶的德希德里认为是不严肃的。
至于贝尔尼埃,他是为蒙兀儿人奥伦宰卜服务的法国医生,也曾于17世纪下半叶随皇帝前往克什米尔旅行,参与过该蒙兀儿人与前来拜访他的拉达克国王之间的对话。拉达克国王极力使该蒙兀儿人相信其王国很贫穷,只产少量的水晶、麝香、羊毛和优质甜瓜,而并不像有人使皇帝相信的那样蕴藏有黄金……这是否是一位不太强大的国王由于非常害怕奥伦宰卜的征服野心,而采取的谨慎态度呢?他可能想起了古代的征服就曾以“金地”和宝藏为导火索。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也证实,当时存在有关于金矿藏的流言。
传教士白乃心神父在吴尔铎神父的陪同下,于1661—1662年间穿行西藏,是从中国前往印度。他在位于青海湖和拉萨之间的地区穿行,并对该地区作了描述。其游记已于1667年由祈尔歇用拉丁文刊布于《中国图志》中了,其法译文于1670年出版。他记载说(法文版第317页):“青海湖的边界在东部是陕西省那高不可攀的山脉,那道高大而神奇的长城就结束于那里,在南部是Changur地区,那里因为14座金矿而变富,其中大量向印度诸邦供应,该地区被置于西番国王的控制之下,而西番王实际上就是巴兰托拉国王”。
我们从其中的Xemsy中辨认出了陕西省(今陕西省由甘肃的一片与青海相隔),那道“高大而著名的长城”则毋须解释(系指万里长城)。巴兰托拉就是拉萨的别称(我们在许多地图上都可以发现之)。其中的Sifanie明显来自“西番”一词(其字面意义为“西部番人”),这是汉人用来或泛指西藏人,或特别是指西藏东北部(这部分在现今的政区划分中横跨青海和四川)的名称。我们从18世纪的多种地图上都会发现“西番国”,始终都位于青海的南—东南部。
白乃心在另外一段文字(第318页)中又具体解释说,西番王国和拉萨王国共有一王,该王拥有相距14日行程的两都,其一在“巴兰托拉或拉萨”;其二是西番王国的首府,叫作“Changur,那里有14座金矿”。
这一有两个王国和两座首府的国王,会使人联想到17世纪下半叶在西藏形成的局势,西藏当时实际上并不是以达赖喇嘛(同时为活佛、神权和世俗首领)为首的神权政体,那里当时还有一位世俗王管理世俗事务,不过这并不妨碍达赖喇嘛(活佛和无可争议的宗教领袖)拥有很大的世俗影响。正巧当时有一位青海的蒙古王公(西蒙古人)在拉萨占据王位,他因此而统治了蒙古诸旗和西藏。我们肯定应如此理解“西番王”拥有两都一事。我们尚有待于确定第2个首府的地望,白乃心将之置于了距拉萨有15日行程的地方。在地图中找到一座首府看来应该是很容易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并非如此。
祈尔歇本人著作中的地图过分简单了,其中未标明Changur。
我们现在可以假设认为,由于多种语言对音(藏语、汉语、白乃心的德语或拉丁语,译者达尔基埃的法文)之关系,以及一种在地图史上并非罕见的现象,Changur可以读作Tchankour,而我们恰恰发现了Tcharlkour,它在丹维尔的地图中作为一堡塞城而出现(《根据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地图和论文而绘制的西藏之地图》,1733年巴黎版)。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该地图反映了“喇嘛”们的测绘结果。这就是于1711—1718年间,由经负责绘制中华帝国地图的欧洲耶稣会士们培养的汉族和藏族地理学家们,在西藏从事的测绘。丹维尔这幅地图中的地名都是由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所作的对汉文方块字的拼音,而汉语名称则从语音学角度表达了由喇嘛舆地学家们在当地听到的藏文和蒙文字,或者是在他们参阅的道路图中的藏文字。
在1733年丹维尔的地图中,我们一方面可以辨认出Tchankour一词。它写于一个表示地区的地理符号一侧,位于一条江河(它似乎叫作Tan Tchankour)之北,也就是说,这一术语始终是根据江河而发展的,其后未带有字母“R”,但丹维尔始终未增加这一表示“江河”的缩写字。该河于下文又变成了金沙江(它实际上是扬子江在这些地区的名称),丹维尔的地图中明确指出金沙江(但稍后又作Tchankour)是“夹裹着金砂的河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Tan Tchankour为近代地图中的“通天河”(通天河的下游即扬子江,于其上游还有另一个名称:木鲁乌苏河)。这就是古代和近代地图上的河流网的相似性,向我们提出的解释。在丹维尔的地图中,这两个Tchankour和Tan Tchankour恰恰位于西番国以西,距打箭炉西北很远的东方,介于北纬32°—33°、东经116°—117°之间(其地图上的经纬度,而不是我们的那一种)。Tchankour城位于Tan Tchankour之北。
如果我们把丹维尔的地图与一幅高质量的近代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出版了1∶300万的一幅汉文地图,而华盛顿的国家地理学会同样也发表了一幅中国地图)进行一番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对18世纪有关西藏这一东部地图的江河体系的准确性,感到吃惊。这样就会使我们在想象中把Tchankour一地置于其江河背景中去考虑,也就是应将之置于通天河或扬子江的上游的东(左)岸,距江河不远的地方,大约位于东经98°30′和北纬32°的地方。在现今的行政区划中,该县位于四川省,非常靠近西藏自治区。这种区划是新近作出的。从前在1930—1958年,它地处中国的西康省。在18世纪时,中原—西藏的边界经打箭炉(今康定),其北部的西宁位于该帝国的边陲,一种理论上的附庸关系把该线以东的西蒙古诸旗与汉地联系起来了。但17世纪时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否还存在着一个古首府的踪迹呢?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我们于现代地图上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小城德格(根据不同的罗马拼音而分别作Dege或Tehko)。
我们还应补充说明,在丹维尔的地图中,西番国位于Tchankour以东,而不是像白乃心所希望的那样位于该“首府”之北。丹维尔在西番人与“青海鞑靼人”之间作了区别,认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集团,但其形势在1661—1730年间确实起了变化。最后,我还应补充说明,如果这里是指蒙古王公,那就应该联想到该“首府”并不一定是一座能留下建筑遗址的土木建筑城市。这些游牧王公们经常有双牙帐,一为冬牙,一为夏牙,而夏牙常常仅为一营地。所以大家很难在18世纪的地图上找到诸如比库库诺尔王公们更为强大的著名王公首府。准噶尔汗浑台吉,他征服了西藏并与汉地分庭抗礼。其夏牙位于伊犁河畔,俄国人称之为“浑台吉的库伦”。我们不应将此与蒙古的库伦相混淆,只有在很小的地图上才捕捉到了它。因此,如果这一首府Tchankour(如果它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已完全消失,那也没有任何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再作出一次尝试以重新找到该地。我们把丹维尔的地图与出于同一次“喇嘛们勘测”的同时代的汉文地图作以比较,如1760年清代的全国图,丹维尔的地图是与该图最接近的兄弟图。我们一般都可以在这两幅地图中发现同样的地貌,其中一幅地图中的地名,就是另一幅图中的地名对音,其原因就不必说了。
在本应该找到我们所说的Tchankour的地方,以及在一种完全相似的水系中,1760年的汉文地图中两次提到了丹冲科尔,它完全可以译作Tan Tchankour。在其中之一的情况下,该词后面附有“珠克特亨”(很可能是一个满文词),它在该地图上写于城市名称之后,附带有一个代表重要城市的地理符号;在第2种情况下,其后面附有两个汉字,也很可能是另一种满文词尾。我们不懂其意义,但它很可能是一条江。因此,我两次找到了Tan Tchankour,而没有单独使用Tchankour的地方。另一方面,该地在汉文地图中位于Tan Tchankour江的河道以南,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两幅地图,那么这一丹冲科尔在丹维尔地图中是唯一可能被译作Tchankour者。我们这样定位的地点,是否在像白乃心所写的那样距拉萨有15日行程的地方呢?当然不可能。如果每天行程25或30公里(据那些曾在这条路上旅行过的大部分旅行家认为,这是平均日行程),那么在15天内,就可以行进至375到450公里之间。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近代地图,那就会使人坚信其距离约为一倍。
我还应该指出,我们无论是在自己能够参阅的所有18或19世纪的任何地理书中,还是在收入这些著作中的地图上,或者是在详细列举各驿站时,从未提到过任何冲科尔、丹冲科尔,也未提到过任何与此相似的名称。
因此,是否有一首府被这些记载遗漏了呢?严格地说来,它可以不出现在由汉族官吏们所描述的路线图上,因为他们是为了宫廷或军队而撰写这些著作的。但如果他们遗漏了一座重要城市,那是令人惊奇的;如果一座重要城市未出现在通商路线图上,那同样也是令人费解的。后来,它又确实在1711—1718年左右,被皇帝委任对西藏进行地理测绘的专家们发现了,因为它出现在以这些勘测为基础的1725—1760年的地图中。这可能吗?它在该地图中甚至用一种相当大的城市的地理符号来表示。无论该城如何,它可能自1718年勘测以后就消失了,究竟是在一次战争中被毁的呢?或者是否已完全改变了名称呢?
至于1661年向全印度供货的14个金矿,它们在后来变得怎样了?我们在此名下没有找到它们。但最为合乎情理,甚至最为可能的是,整个这一地区都盛产黄金。
同在白乃心和吴尔铎时代,或更为具体地说是在25年之后,居住在西藏的某些亚美尼亚商人在那里采购黄金,其中有一部分似乎来自西宁地区。至少这是从亚美尼亚商人霍夫罕(他于1686—1691年间居住在西藏)的账单中看到的情况,该账单大约是在12年前,于葡萄牙的一图书馆中发现的。
我们现在来研究另一种早于丹维尔的文献,即1705年伊斯勒的纪尧姆的《印度和中国的地图》。我们从中看到,在“青海湖”和西宁的正南方,也就是黄河之正南和“索撒玛湖”(其形状令人想到扎陵和鄂陵两大湖,位于黄河的真正源头附近)以东,有一个叫作“金地”的地方。该地图谬误百出,尤其是在水系方面更为如此。但我们可以试把该地区(东部以四川边界为限,西部由上述两大湖为限,北部以西宁为标志,南部以唐古拉山为界)置于下述限界范围内:东经97°—99°,北纬32°—35°。它包括了巴颜喀喇山的一部分和塔玛拉山脉以北地区。换言之,它部分地相当于由丹维尔记载中的Tchankour地区。
我们顺便再谈一下Alountchi一词,它使人联想到了米儿咱·海答儿的文献,以及在这些地区的地名中,经常出现的意为“金”的词。
在伊斯勒的纪尧姆地图及其“金地”的文献问世25年之后,在欧洲又出现了斯特拉伦堡的鞑靼大地图,它实际上是西伯利亚、蒙古、西域的全部地图。这名瑞典军官于1709年在波尔塔瓦战役中被俄国人俘虏,后又如同其他许多瑞典军官一样被押解往西伯利亚,处于半自由状态。他于1709—1721年间滞留在那里,后于1722年返国。此人有关其居住和冒险的记述,于1730年发表,成了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在他于西伯利亚度过的12年中,长期调查并绘制了这份地图,其中仅有一小部分涉及西藏。我们恰恰可以从中发现:“Tartschinda山或Altun chi,这里有一座银矿。”Altum chi山脉恰恰位于西宁以南,青海湖稍偏东南和索丰湖的东北。所以,它比伊斯勒的纪尧姆图中的Altoutchi稍偏南,但仍基本上位于同一地区,它环抱西北的四川省和南部的黄河。唯有斯特拉伦堡一人在那里发现了一座银矿,而不是金矿。正如我们下文将要看到的那样,斯特拉伦堡特别不相信金矿,其鞑靼地图中也未指出任何金矿。我们相反却可以从中发现多处银矿,其中就包括这一座。我将在另一章中再来论述这些银矿,本处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再一次使用了Alturn chi一词。
在18世纪初叶,西藏的金矿资源及其开发状况也由数位证人作过第一手观察和叙述。一方面是天主教传教士、嘉布遣会士(托钵僧)或耶稣会士,他们长期以来居住在西藏本土上;另一方面是汉地的文武官员,他们受帝国政府派遣以前往开展军事行动和地理考察。这是根据清朝政府对西藏的新政策行事的,而新政策又受当时威胁清帝国的厄鲁特或准噶尔蒙古小王公们扩张政策的主宰。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德希德里企图使西藏接受基督教的归化。他于1716年7月18日经北印度和拉达克到达拉萨,并在那里滞留5年。他于1715年穿越拉达克(他称之为“第二个西藏”或“山地”,该地区贫瘠而令人望而生畏)。此人指出“在山脚下的河谷中以及在靠近江河的地方,土著人发现了不少黄金,但不是呈很大的天然金块状,而是呈金砂状”(英文版本第78页)。接着,他在1715年10月间穿过了羌塘,其次经过了阿里和冈底斯山附近。在冈底斯山以西有一个被认为是恒河源头的Retoa湖(正如其整个背景所提示我们的那样,这里无疑是指玛法木湖)。在该湖的两岸和沙滩中,可以发现由暴雨和融雪从阿里琼噶尔山上冲刷下来的大量黄金。西藏人和各方商贾不时前往那里采集金砂并赚取大量利润。该湖也是朝圣地。德希德里接着指出(第85页):“该地区虽然很荒凉,又尚未开发,但同样可以由那里采集到的大量黄金,以及由畜群提供的大批优质酥油,而为大喇嘛获得良好经济收益。”
德希德里还写道:“康地蕴藏有优质黄金和白银。事实上,在西藏到处都可以找到黄金,但却并不像在其他地区那样存在着矿藏。土著人仅满足于以下述方式将之与泥沙分开。西藏人在江河附近费力地搬运大块岩石并从其下挖掘出沙土。他们再把沙土抛入水槽中,槽中铺有大块草皮,然后再从上部灌入大量的水,水在流动时冲走泥土、大块沙和小石块。黄金和细沙被这些草皮中的粗硬的草阻滞,然后再反复冲淘,直到不剩有任何东西为止。在一般情况下,这里的黄金就如同沙子一般,不存在天然金块。人们一般在山脚下的平地,或奔腾于两山之间的河流沿岸才能发现黄金,因为暴雨把泥沙和黄金都冲到了下游。很明显,如果西藏人懂得在这些贫瘠而荒凉的山脉中挖掘矿洞,那么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黄金。任何人一旦获得了县政府的特许证之后,便有权在那里采金,但他要把其所获黄金中的一小部分奉献给县政府。”
德希德里还指出西藏东部的叶、洛洛和贡波也是产金地。他本人一直到达塔克波地区。他确实曾写道:“在叶地比西藏其他所有的地区都有更多的黄金。”叶地似乎应被置于拉萨南部的泽当城与托克波地区之间。德希德里补充说,叶地的黄金是以较大的天然金块状存在的。他还说:“在塔克波土伦(塔克波的一个地区)与大山之间……在泽里附近有一个叫作洛洛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得到很大的天然金块。它的南部靠近一个叫作洛巴的民族。”他在下文不远处又认为这是一个“蒙昧民族,在森林中以狩猎和采摘为生,有时还是食人生番”。他们严禁任何外人穿越其地区,否则从西藏到孟加拉则是很近,也很容易的。“洛巴人”的意义仅仅为“南方人”,有时又指不丹人。但我觉得在此情况下,则很少可能是指阿博尔人或米什米人。因为德希德里对他们所作的描述完全与出现在18和19世纪汉文著作中的狢 蒙昧人相似。这些蒙昧人居于不丹以东。作家们把这些人与被他们称为布鲁克巴的不丹人区别开了。
蒙昧人相似。这些蒙昧人居于不丹以东。作家们把这些人与被他们称为布鲁克巴的不丹人区别开了。
最后,德希德里认为,“如果穿越塔克波地区并一直向东行,那就可到达沙漠和荒凉的工布。但我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由于黄金而变富裕的人”。
一名叫作焦应 的汉族军官于1720年参与了清朝在西藏反击准噶尔人的战斗,因而与德希德里同时在西藏,他为我们留下了可作军事使用的一小本西藏指南《西藏志》。他与自西部进入西藏的德希德里相反,对于拉萨以西经度地区一无所知。他的《西藏志》涉及西半部的内容很少,相反却对拉萨—西宁地区作了详细描述,对成都—打箭炉—昌都—拉萨一线的描述最佳。但《西藏志》仅提到一处出产黄金,即说板多:“说板多山后有金厂,有黑帐篷(即一个游牧民地区)。”我们在所有的近代地图中,都于东经约95°5′和30°50′之间找到说板多,它位于念青唐古拉山的正东方。包括这个有关说板多金厂的句子,几乎逐字地重复出现在18和19世纪的地理书中,完全如同中国史学家们经常所作的那样。众人对这一藏文地名作了多种不同的汉文对音,但都很容易辨认出来。稍后在20世纪的“民国”时代,中国地图上也提到了一个叫作硕督的地方,它很可能就是指说板多。据19世纪的修道院长德格丹向我们提供的详细情况来看,该地距产金区不远。
的汉族军官于1720年参与了清朝在西藏反击准噶尔人的战斗,因而与德希德里同时在西藏,他为我们留下了可作军事使用的一小本西藏指南《西藏志》。他与自西部进入西藏的德希德里相反,对于拉萨以西经度地区一无所知。他的《西藏志》涉及西半部的内容很少,相反却对拉萨—西宁地区作了详细描述,对成都—打箭炉—昌都—拉萨一线的描述最佳。但《西藏志》仅提到一处出产黄金,即说板多:“说板多山后有金厂,有黑帐篷(即一个游牧民地区)。”我们在所有的近代地图中,都于东经约95°5′和30°50′之间找到说板多,它位于念青唐古拉山的正东方。包括这个有关说板多金厂的句子,几乎逐字地重复出现在18和19世纪的地理书中,完全如同中国史学家们经常所作的那样。众人对这一藏文地名作了多种不同的汉文对音,但都很容易辨认出来。稍后在20世纪的“民国”时代,中国地图上也提到了一个叫作硕督的地方,它很可能就是指说板多。据19世纪的修道院长德格丹向我们提供的详细情况来看,该地距产金区不远。
我还将指出,焦应 与德希德里相反,完全没有强调说明西藏的金产量,我还将有机会论述汉人的这种缄默。
与德希德里相反,完全没有强调说明西藏的金产量,我还将有机会论述汉人的这种缄默。
几乎与德希德里出于和黄金没有任何关系的原因,而穿过克什米尔前往西藏之行的同时代,却有一名帝俄臣民专为寻找西藏黄金而进行了一次惊人的探险。这次调查几乎产生了持久的政治后果。
1714年,在作为彼得大帝政治的典型特征——卖力寻求黄金的气氛中,通过不同渠道向莫斯科传递了3种消息:在阿姆河流域、希瓦和布哈拉汗的领土上蕴藏有黄金;在叶尔羌河流域、小布哈拉(当时对喀什噶尔的称呼,今新疆的东部,中国的西域部分)和浑台吉或卡尔梅克汗(俄国人对厄鲁特人或准噶尔人的称呼,他们当时在西藏的北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蒙古王国),也蕴藏有黄金;最后是在青海湖畔和南部以及达赖喇嘛的领土上,或者是在卡尔梅克人、汉族人和藏族人的各小邦中都有黄金。这后两种新闻是由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公爵(其首府当时设在托博尔斯克)呈奏沙皇的。加加林曾从托博尔斯克派遣一名叫作特鲁斯尼科夫的“西伯利亚贵族”前往探险,其旅行时代介于1713—1714年间。
我将在其他地方再解释沙皇怎样试图掠夺阿姆河和叶尔羌河流域的黄金,即通过贝科维奇、布霍尔兹、温科夫斯基的远征,本处所涉及的仅仅是特鲁斯尼科夫的旅行。
某些作者把宣布这一消息和把由该旅行家携回的黄金,奉献给沙皇的时间,定于1714年,其他人则认为是1716年。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应把特鲁斯尼科夫从托博尔斯克的出发时间定于1713年,把他据说一直到达青海湖旅行而返归的时间定于1714年。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当时行程的持续时间,那么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两年。对其旅行路线的描述不太详细,这一含糊其辞的记载导致了诸家纷注的局面。
我们仅仅注意“内阁秘书”马卡洛夫1725年9月3日对此的记载,也就是仅仅在他返回的11年之后。这是他在致医务官布鲁蒙特洛斯的一封信,即有关彼得大帝的珍异物陈列室的信中提到的(这里涉及艺术珍藏室问题,因为黄金的样品就收藏在那里)。下面就是这封信告诉我们的情况。
特鲁斯尼科夫于1714年携带200两黄金(约7.56公斤)返回,这是他在开采地向汉人和卡尔梅克人购买的。下面就是这封信告诉我们的情况。
首先,在到达中国的西宁市之前,有两周的行程。该城建于喀勒干长城以远处,紧傍青海湖,被称为和硕特部的卡尔梅克人就沿该湖游牧。其黄金采自小河和自大山一倾而下的河源附近。特鲁斯尼科夫以7卢布——中国两黄金的价格采购之。他在大道旁的开采地看到了150多人,前往这些开采地寻求黄金的人向他宣称,一个人在一年内各自可以得到20、30和100两(即分别为756、1134和3780克左右)黄金。
此外,从该湖的右边起,“这些台吉以及人们称为唐古特的一个特殊部族,从阿尔泰·科尔玛以及其他的小河中采金”。
最后,“于上文已提到的长城以远地区,在距长城有3俄里的中国达巴城以及有20俄里的西宁城”,也从河里采出了天然金。他在两个地点看到了这种开发。汉人在河里淘金,他用7个卢布向他们购买。这些淘金者每人每年向其汗的金库交纳一左洛特尼克(4.26克)黄金。
马卡洛夫1725年9月3日的信同样也指出,这200两金砂要装在皮包中,于1725年2月5日根据沙皇的敕令被熔化,以供使用,同样还作为样品向珍品收藏处交2斤25左洛特尼克(约925克)黄金。
我们现在试着在地图上为这些地区定位。
第一个开发点:青海地区,西宁。它从前是进入汉地的一个重要关隘,也是汉人、西蒙古人和西藏人之间的贸易基地。塔巴就在对面偏西,俄国商人们非常熟悉它,它也出现在当时的某些地图中,如在杜赫德神父书的插图中,以及在斯特拉伦堡的书中,塔巴与西宁为同一城:“塔巴西宁,又叫西宁”。当时的俄文文献就经常提到“西宁和塔巴”,把它们作为从事大规模交易的中国城市。白乃心在祈尔歇的《中国图志》中收有一种对该地1661—1662年形势的描述。“长城”似乎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它在这一段的走向已由杜赫德标注出来了。那些比较晚期的旅行家们也都指出,万里长城事实上并没有延伸到西宁。那些线条图说明,西宁城在杜赫德时代由一段孤立的城墙保护,该城墙并未与万里长城相接。但另一方面,斯特拉伦堡的地图说明,西宁处于万里长城的保护之下,在长城的东部略有收缩。古伯察(Huc)神父确实在他前往拉萨旅行的游记中写道,在西宁和东科尔(较晚期的地图中作Donkyr,可能位于西宁的西部),他曾两次翻越万里长城。
我们当然毫无困难地就可以考证出库库诺尔(其汉文名称“青海”)和被称为和硕特的卡尔梅克人,在这个句子中难以澄清的是“两星期的行程”一句。事实上,距青海湖有两周行程(即使其西岸也罢)的地方不可能是西宁和塔巴。按每天25或30公里的速度(这是大部分估计中的平均日行距离),两周行程代表着250—420公里的旅程。但青海湖的东岸距西宁只有3日行程,如亲自走过这段路的白乃心就是这样认为的,古伯察神父认为也不会太远。此外,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理解两周的行程不可能是这两座中国城和青海湖之间相隔的距离。这两周是以哪里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的呢?肯定不是从托博尔斯克出发,那里距该湖有数月的行程。据俄国作家们认为,特鲁斯尼科夫经克什米尔人的领土而被遣往汉地。所以他很少可能是从西北来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第一个金矿址置于西宁西北350—400公里处。
无论如何,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曾多次提到青海湖地区为产金区。如在1844年,古伯察神父经西宁从青海湖的南部穿越该地区,他告诉我们说该地区的29个旗(蒙古部落)均属于清朝皇帝。这些蒙古人每两年一次入京以尽臣属义务,并进奉他们“采自其河沙中的天然金块与金粉”。古伯察神父叙述说,他在穿越西藏时,经常遇到忙于在牛粪(那种用作燃料的干牛粪)火上的坩埚中精炼金粉的情况。这是他们在放牧其畜群时在各地搜集到的。奉献给皇帝的贡物一般由地方特产组成,产金部族当然会在他们那象征性的寄送物中放入黄金的。
第2个开发点:在从青海湖起的右部,位于唐古特人地区。“台吉”一词在当时的俄国作家中,用以指卡尔梅克王公或其领土;“唐古特”在当时或是泛指西藏人,或特别是指东北部的西藏人。后者恰恰指青海地区,在蒙古人征服之前,那里还存在过一个很大的王国(包括今甘肃),中国史学家们称之为西夏国,其他人则称之为唐古特国。
阿勒泰·科尔玛江无疑就是阿勒坦河或金河(又是Altan一词),这恰恰是蒙古方言中对黄河上游(除了其发源地之外)的称呼。黄河在成为中国的主要江河之一以前,发源于西藏地区之扎陵湖,位于青海湖之南很远的地方(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它发源于青海湖)。其流程形成了几道河套,并经过青海附近,在该地区则以阿尔金河之名而著称。我们不要把“金河”与另一条几乎同名的金沙江相混淆,后者是巴塘以南的扬子江(从巴塘到叙江府一段的流程)。
在万里长城以远,于上文已提到的西宁和塔巴城周围,淘金工程是不会令人惊奇的。在20世纪时,于西宁之东又存在着一些开采区并处于开发中。“在长城以远”、“在长城之后”等短语说明,这里指的是中原地区,位于长城以内,那名俄国旅行家其实是在中原之外更靠西部的地方。所以,如果从事这项活动的是汉族臣民,那也是正常的。他们的纳税对象就是中国皇帝,而蒙古人在其地区则称之为“博洛达汗”(天可汗)。
每人每年应向该可汗交付一左洛特尼克(4.26克)黄金的赋税一事,令人联想到了淘金者们的年税,赴西藏的旅行家们后来经常提到应交一“萨尔索”,也就是一小砂金袋约为5.8克或稍多一些的金砂。本处所提到的税略低一些,但也属于同样的数量范畴,这名俄罗斯旅行家简单地采取一个整数,以使之换算成俄国的通用衡量单位左洛特尼克(这是用于贵重金属的一个衡量单位,该词明显是自Zoloto,即“黄金”派生而来)。同样,他明显武断地把其他数字也聚零为整了,即卢布和中国两。我们确实很难设想一两黄金所获得的卢布也为一整数。另外,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处于汉地司法管辖权之下的,所以纳税比例不应相当于西藏的制度,而应符合汉地制度。当时的左洛特尼克在重量上则相当一钱一分或一钱二分,即4.14或4.15克。
到此为止,人们在研究特鲁斯尼科夫所提供的资料时,都以1725年9月3日马卡洛夫的书信为基础。我在该文献的其他文本中又发现了某些不同的讲法。如发表在俄文刊物《著作和翻译》1760年1月号中的文本。这篇有关金砂的文章的作者,斩钉截铁地说他曾进入过托博尔斯克档案馆,在他于1732—1734年的西伯利亚之行中遇到了许多证人(但从1714年之后,任何人都再未遇到过特鲁斯尼科夫)。据1760年的这种说法认为,有人对靠近青海湖的第一个采金点作了与第一种文本相同的描述。对于第2个采金点,它又被具体指出“更偏南一些的地方,同样是那些卡尔梅克人和被称为唐古特的民族,在深山和金河两岸以及其小河畔采金”。
在这种说法中,这些地区的卡尔梅克人也叫和硕特人(Khotote),它可能是由于下述原因而造成的,俄文中的ch和t在草书中很容易相混淆。
最后,“于距青海湖20日行程的地方,在穿过被蒙古人称为喀勒干的中国长城之后,他在塔巴和西宁城(前一城距长城有3俄里,后一城距那里则有20俄里)附近,发现汉人在两个地方于河中采集金砂,他在该长城之外向他们购买黄金。这一批人同样也从地下开采纯金。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全年都要向其可汗交纳一左洛特尼克的黄金”。
斯帕斯基于1827年基本上又重复了这第2种说法,其文常常被稍晚的作家们奉为基础。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从青海湖起经20天的行程之后,不会只到达西宁,那里要近得多。另外,1725年的信件,则指出是两星期的时间。“两星期”完全可以这样来解释:在到达西宁之前,每天20里的行程则代表着500—600公里,那样就很可能确实会把我们带到产金区,但肯定不在西宁附近。这样来看,15日的行程是否是指向西宁之西北行,而20日行程则是取道其南部呢?实在说,在蕴藏黄金的问题上,这两种说法都是可能的,后来在这些地区也发现过黄金。
其中有关民族和政治划属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所得到的,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些令人迷惑不解的资料。
我们发现在汉人地区(西宁是一座汉人城市,而在“长城以远”,亦指中原),汉人向其皇帝纳税,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其次是一些“台吉”(蒙古人或西蒙古人的王公)和“卡尔梅克人和硕特人”(西蒙古和硕特的一支),我们对这些人的了解甚多。我们应认为他们已内附中原,因为我们上文刚才提到的那篇1760年的俄文文章指出,特鲁斯尼科夫“向汉人和内附汉人的卡尔梅克人”采购黄金。我们可以把该叙述中的这些人的地望,置于金河(长江)流域和青海湖畔(南北两岸)。
我们最后还应讲一下唐古特人的问题。据记载,他们就是生活在金河流域以及“青海湖右(西)方的唐古特人和西藏人”。他们是否基本上尚未归附任何人呢?
事实上,就在1713年,特鲁斯尼科夫可能旅行于北纬34°—38°和东经98°—102°之间的地区。对于该地区的政治属划,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位和硕特汗——拉藏汗同时也为藏王。他完全受到了清朝的支持并从1710年起向清朝纳贡。但如果说他掌握了世俗权,那么他也要考虑受到全部藏民崇拜的达赖喇嘛无限的神权。但当时有关达赖喇嘛的情况非常复杂。六世达赖喇嘛已于1706年圆寂,但这第六辈转世活佛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一名新的“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已被发现,即出生在藏汉走廊理塘地区的一名新生婴儿。清朝皇帝承认了他,和硕特人奉他为唯一真实的活佛。但西藏人在权力之争中,极力排斥扎什伦布寺的班禅喇嘛,所以否认该世达赖的合法身份。和硕特部沸腾起来了。因此,特鲁斯尼科夫是在紧张时期到和硕特地区旅行的。所以,和硕特人完全可能正式内附清朝皇帝。我们很难说,当时作为藏王的和硕特汗能于1713年对那里真正行使政权。在特鲁斯尼科夫报告中提到的这些唐古特人或西藏人,是否未归附汉人与和硕特人呢?沙皇似乎就是按照这种意义,而理解那些所谓产金地属于达赖喇嘛管辖的资料的。
特鲁斯尼科夫为向卡尔梅克人和汉人采购黄金时,每两付7卢布的价格,又重复出现在历代俄国史学家们的著作中,无一例外。但我应于此提及一例。我们于下文在有关西藏黄金不同价格的章节中,再来讨论它。我于此仅仅指出,这种价格对俄国人似乎非常有利,由此而产生了沙皇的远征计划。
对于彼得大帝为得到黄金,而对传闻中布哈拉的阿姆河流域以及准噶尔人领地中的叶尔羌河流域(正如某些地图所证明的那样,当时似乎认为叶尔羌河是额尔齐斯河的一支流,以至于大家认为,只要逆额尔齐斯河而上就会到达叶尔羌河)存在的金矿炮制的控制计划,我们于此无法展开讨论。但在与我们宗旨有关的特鲁斯尼科夫的发现问题上,沙皇肯定是有其打算的。1721年1月19日(旧历)的国会诏书(《法律集》第6卷,第3716号)即为明证。与此有关的是“与浑台吉缔结和约并与之建立贸易关系”的沙皇敕旨。
在俄国作家们的著作中,浑台吉是指准噶尔汗,当时就是策旺·阿拉布坦。雅姆切夫斯卡娅堡是额尔齐斯河畔沙俄的一重要基地,1715年布霍勒斯和1719年哈列夫出师不利地对准噶尔领土的征服,就是从这条河起兵的。同一时代,即1717年,又爆发了贝科维奇—柴卡西对希瓦方面的致命远征。总而言之,在六七年间,彼得大帝为得到西域和高地亚洲的黄金所作的全部努力都失败了。此外,在1718—1721年间,赴中国的骆驼队绝迹了,因而断绝了由该地区流入的黄金。
下面就是1721年的沙皇敕旨:
巩固雅姆切夫斯卡娅堡并安置居民,拆毁除雅姆斯卡娅之外的其余所有新工事。与浑台吉媾和并与之通商,同时既与西宁和塔巴等中国城市,又与达赖喇嘛的驻地建立贸易关系。如此通商并非为了赢利,而是为了与商人同时向那里派遣精明能干之士,以研究有关黄金的问题。这就是要知道它出自何处、有多少储量和路线如何;如果希望抵达那里,是否困难,能否夺取这一地方。
文中确实写作“夺取”,可见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远征计划。此外,我们还可以把这道1721年的敕旨与同时代的其他敕旨,或者是由史学家们稍晚记载下来的,涉及阿姆河或叶尔羌河流域黄金的秘密训令,进行比较。我们于其中发现了一种同样的思想状态:派遣在矿业专家们陪同下的游说和考察团。如果游说失败,便试用征服。除此之外还应有计谋:在商团的掩护下派遣矿业专家,或者仅仅是一些刺探情报的人。德希德里1721年提到的拉萨的“莫斯科人”,是否就扮演了这种角色呢?
彼得大帝在有关征服希瓦和布哈拉汗国以及准噶尔人驻牧地的可能性问题上,似乎大错而特错了。至于征服西藏,他甚至未敢尝试。
此外,为此则必须穿越浑台吉的辖地。但当时准噶尔人的势力却十分强大。准噶尔人从1717年末便成为西藏的控制者,征服了拉萨,他们甚至成为大清天朝的可怕对手。清朝于1718—1719年发动第一次征战以便把准噶尔人从西藏驱逐出去,但失败了。1720年发动的第二次远征才告捷。沙皇很可能在1721年1月间对这一切都不大了解。在这道敕旨颁布之后,又进行一系列的交易,其中之一的目的是使俄国人获许勘探准噶尔人辖地中的贵重金属。这些交易包括互换使节,紧接着就是文可夫斯基于1722年2月—1723年9月的出使。俄国向策旺·阿拉布坦提议一种“保护”地位,就如同主宰他们与定居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西卡尔梅克汗阿玉奇那样的关系。正在与清朝军队对抗的厄鲁特汗,也想提前获得出卖自身为奴的代价,即俄国人迅速提供对抗清朝的军援。他们之间的谈判持续了数月,甚至数年,最后终因清康熙皇帝的晏驾(1722年12月20日)而夭折。因为清朝新皇帝立即与准噶尔人议和。随着这种新局面的出现,准噶尔人未允俄国人勘探贵重金属的要求。文可夫斯基的出使以失败而告终,所有在属于准噶尔人的领土上采取行动的希望都破灭了,准噶尔汗对他与俄国人的关系也保持着距离。最后,彼得大帝于1725年2月8日几近于暴卒的死亡,其计划也随他而寿终正寝了。在俄国不再谈论达赖喇嘛的黄金了。
特鲁斯尼科夫探险的另一个方面,也由斯特拉伦堡男爵(我上文已提到了其地图和游记)那惹人注目的资料提及。我再重复一遍,他于1709—1721年间生活在西伯利亚。但斯特拉伦堡并不相信特鲁斯尼科夫所说的黄金。更确切地说,他不相信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所叙述的一切。他认识此人,并认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是一个贪得无厌、谎话连篇、坏事做尽的人。他认为加加林的真实目的,是企图利用民间对沙皇的任何一点不满情绪(沙皇的改革很不受欢迎),以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从而成为事实上独裁的和独立的西伯利亚国王。加加林的历史确实有累累的舞弊和反叛行为。据斯特拉伦堡认为,他所希望的是枪炮和辎重,这些军用品的出售受到了沙俄政府的严密监视,不大愿意向其亚洲近邻们提供。加加林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得这一切。所以,据那位瑞典军官的记述,他仅仅是利用特鲁斯尼科夫旅行的借口,而杜撰有关叶尔羌河流域、青海和其他地方黄金的虚假传说。甚至他携回俄京并入存彼得大帝的珍宝馆中的黄金,可能也仅仅是他经其手下人从布哈拉的许多淘金人手中采购的,那里有数条河流冲击着金砂。斯特拉伦堡于是便写道,加加林向沙皇神秘地揭示了金矿的存在,并使他相信这些黄金距其西伯利亚的政府所在地不远,能很容易地到达那里,但卡尔梅克人(准噶尔人)从不会忍痛让别人掠夺其金沙。所以,如果沙皇真正希望调拨给他约10万人所需的军备,并允许他随军带去某些军械师和火药匠,那么他就建议夺占该地区(法文版,第1卷,第188页和193—196页)。
沙皇错误地估计了厄鲁特人的势力,于是便组织了对布霍勒斯的远征。这支远征军于1715年12月,在雅姆切夫卡娅被困以后,于1716年撤兵班师。1716年初,派去救援他的一哨人马完全被卡尔梅克人俘虏,同时被缴去的还有随军押送的属于国库的二万卢布。加加林制订的各种方案,没有一种不是以遭到重大损失而告终的。但加加林本人却变得无限富裕和强大了。这条老狐狸(正如斯特拉伦堡称呼他的那样)最终还是受到了质疑和入狱,受审后被判处极刑,于1721年被绞死。
斯特拉伦堡几乎完全否认了所谓在布哈拉、喀什噶尔(他最后还是在该地的问题上犯了错误)等地,存在任何金矿的说法。其地图(《对鞑靼地理的新描述》一书之插图)中没有指出任何金矿,相反却标出了多处银矿,都在西藏的北部和今新疆一带。
俄国作家们不否认特鲁斯尼科夫的旅行。但在发生了1718年对加加林起诉案件的时代,沙皇自己也似乎很怀疑这一故事。其1719年1月28日的敕旨,即可证明之。他派遣利哈列夫少校出征卡尔梅克人辖地,委托给他的使命中,特别包括调查由加加林提供的有关黄金的情报,并利用所有手段证实“这一切真实与否”。
我应该明确地指出,大家并不知道这次旅行的具体路线,特鲁斯尼科夫自从他于1714年返归之后再未露面。我们现在已知的所有探险,都产生了详细报告及具体路线图,而特鲁斯尼科夫的旅行,则仍处于极大的含糊之中。他是怎样穿越非常不信任俄国人的民族卡尔梅克人辖地的呢?他是否化装旅行呢?将来某一天神奇地发现的某种档案是否能向我们解开这个谜呢?这是一种冒险还是冒充呢?但现在是离开沙皇疯狂的计划,并回到西藏问题上的时候了。
乔治·博格勒于1714年被孟加拉总督哈斯丁派遣,出使扎什伦布寺的班禅喇嘛。他的使命之一,就是了解在西藏获得小巧的高价商品之可能性,如黄金、白银、宝石、麝香、大黄、茜草等。他在报告中指出,西藏不仅产黄金,而且还大量开采以向所有邻邦出售。
同一位班禅喇嘛于1780年圆寂于北京,我下文再来论述当时的形势。其弟夏玛尔喇嘛立即亡命于尼泊尔,为博得该国国王的支持和青睐,向他泄露了“拉萨附近的金银和其他矿藏的情况”。这一切都记载于一名英国经纪人获得的波斯文文献中,该文献后来刊布于契尔帕特利克的名著中了。这一资料更增加了对扎什伦布寺宝藏之添枝加叶般的描述,进一步刺激了土邦王子的贪欲并促使他进攻西藏。
俄国低级军官伊夫雷莫夫在布哈拉被囚禁了7年之后,成功地越狱并于1781—1782年穿越了拉达克,在他于1784年返回俄国后,也证实了“西藏的山脉中蕴储着大量矿藏。在卫、藏、羌、工布、东各和康地等地区都有丰富的金矿,在藏地还有银矿……大家在那里既从河沙中,又从矿脉中采掘到大量黄金。人们用黄金制造钱币,却仅在商业交易中作通货使用。汉人每年都用其地的产品和商品交换大量的这种金属”。他在稍后不久又具体解释说,居民可以用黄金、白银或皮货纳税。(www.zuozong.com)
1784年被派遣出使班禅活佛的端纳(波格尔的继承者)强调指出了“西藏有无法估量其价值的黄金”。此外,在有关该地区普遍表现出来的贫瘠和西藏人不可能拥有繁荣农业的印象时,他又指出:“由于缺乏肥沃的土地和精湛的工艺,该民族缺乏一切东西。但他们既由于其丰富的地下宝藏,又以广泛的手段获得这一切。他们的矿藏和金属都可以为他们打开无尽财源,以至于仅以此就足可以使他们购置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仍是据端纳认为,“偶然性再加上创业思想和调查活动,就已经能使他们在西藏发现许多矿藏和高价金属了。其中黄金名副其实地名列榜首。人们可以大量发现它,而且往往还是非常纯洁的。人们在河床中可以发现以砂金状存在的黄金。在河流回旋的地方,黄金一般都依附于小石块上。根据各种迹象来看,这些小石块原来都是一块较大石头的组成部分。大家有时也能发现大堆的、大块的或不规则的矿脉。黏结在一起的岩石一般都是燧石或石英石。我有几次也看到了一种宝石,不太纯洁,处于半形成状态,蕴藏在石块内”。
我还将指出,由端纳亲自参观过的该地区,就是延伸在不丹和扎什伦布寺之间的地方。
汉密尔顿于1802年—1803年居住于尼泊尔,后来又于数年间居住在北印度的尼泊尔边界。他曾听说位于玛法木错湖东北和“埃模图斯的第2条山脉以远处的一座非常壮观的西藏金矿”,唯有夏季才能开发该金矿。开采者只交纳微薄的税,把所有重量超过3马斯(2.8克)的金块统统上交西藏土司,自己保留下最小的颗粒。
契尔克帕特利克根据他1793年在这些地区获得的信息而写了一份有关与尼泊尔通商之可能性的备忘录,他认为英国通过尼泊尔的中间人确实可能从西藏获得金粉、金锭、硼砂和麝香。
由于这些无畏的英国探险者,西藏黄金的名声得以越来越远地向外传播,并得到了证实,同时逐步渗入到东印度公司负责人的意识,以及冒险家和商贾们的梦想中了。
在同一时代,两位汉族作家冯少云和梅溪盛的报告(这就是《卫藏图识》,后由柔克义译作英文),在1791—1792年间,以比较平淡的口吻作了描述。该书也似乎心不在焉地讲到了黄金的存在,但没有使用过分华丽的辞藻,更没有欣喜若狂的情绪。书中指出了在理塘城和达隆宗(拉里东南)地区的金砂。据1759年的另一种汉文史料记载,这种黄金存在于说板多山中,《西藏志》也把金矿确定在该地区。
所以,从各个方面(北部的俄罗斯人一侧,东部的汉人一侧,南部和西部的印度、英国人一侧)或由于各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一种在该地区拥有黄金这一巨大财富的思想在西藏附近和世界上都以不同的速度而形成了。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还有下面的推理:怎样掠夺这些财富?
从欧洲人一方来说,这种寻求西藏黄金的心情,导致了19世纪那段奇怪的插曲。
英国人莫尔克洛夫特于1819—1820年间,为购买马匹从印度前往布哈拉,途中穿越了拉达克。他提到了在河流(萨约克河和印度河上游)中从事淘金的活动。他还获悉,在位于拉萨东南的羌塘地区,可以找到金矿。但由于我们将于下文提到的各种迷信,在开采中有许多保护区和禁区。“羌塘”一词用以指整个西藏高原的荒凉地区,但在莫尔克洛夫特的书中则特别指阿里地区,即从西部的印度边境一直到拉萨界内之间的辽阔地区。
26年之后,一名有学问的英国军官坎宁安(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是普鲁塔克著作的阅读者之一,后来成了最著名的亚洲古地理学家之一)又步亚历山大大帝后尘,于1846—1847年间也穿越了拉达克,在那里的印度河和萨约克河的沙滩中发现过淘金活动。他也听说过羌塘地区的黄金,一些迷信遏制了西藏黄金的开发(而且他在这一问题上也引证了莫尔克洛夫特的文章)。当地居民还向他指出,在下游稍远一些的地方,于印度河和萨约克河两岸,以及阿富汗的达尔德人地区,黄金更为丰富。
这些达尔德人告诉了坎宁安某些情况,当时他的希腊—拉丁学识尚未在记忆中消失。他们向他追述了老普林尼听说的达尔德人(Dardae)。公元70年左右写书的老普林尼在其《自然史》第6卷第19章中记载说:“达尔德人地区盛产黄金。”但过去在拉达克发现的(现在仍在提及)达尔德人则为拉达克河和阿富汗河之高谷和深山中的居民。如果大家从此之后大量讨论了他们的民族真相,以及他们占据的具体地望,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至少其名字自数世纪以来就长期存在下来了,并且与居住在不大容易进入高山峻岭中,一个其气质有些粗野和充满活力的民族有关。我们必须将他们与普林尼所说的达尔德人作一番比较。但下面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坎宁安在其旅行中看到了一些旱獭在挖掘洞穴(这件事本身微不足道),但它们挖掘出的泥土中含有小金片(我们始终是讲印度河与萨约克河上游)。当地居民们告诉他说,大家在该地区有时也会采到这种黄金。这明显是对坎宁安的一种启迪,也明显是对老普林尼书中另一段文字(第11卷,第36章)的解释。
印度蚂蚁的角悬在厄里特利亚(伊奥尼亚的一个城市)的朱比特庙上,真是咄咄怪事!在被称为达尔德人的北印度人地区,它们能从土洞中掘出黄金来。这些蚂蚁自己则具有猫的皮色和埃及狼般的身材。印度人在盛夏的酷热中盗走它们于冬季挖掘出来的这种黄金,即当蚂蚁由于热浪而躲在地穴中时。但这些蚂蚁由于气味而得到报警,于是便冲向前丢、撕碎那些逃亡者,无论他们骑的骆驼跑得多快,它们该多么灵巧和残酷啊,这一切都与它们对黄金的酷爱有关。
在普林尼时代,这种故事已经不新鲜了。它可以追溯到5个多世纪之前,即公元前430年左右著书的希罗多德时代,至少有关蚂蚁的故事几乎完全一样,但希罗多德未提到过“达尔德人”,而仅满足于讲“印度民族”。但在引证25个世纪以来,使其所有读者都感到茫然无措的这个蚂蚁故事之前,我们还应具体解释一下它出现的历史背景,希罗多德为了撰写其有关东亚的“调查”部分时,曾滞留在波斯人的苏萨城内。他有关印度的资料,主要来自波斯人中。波斯人自己又不仅仅通过其邻邦而获得有关印度人的资料,而且还因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大流士曾派遣卡利安德的斯拉克斯出征。此人从卡斯帕提洛斯(明显是印度河畔距大陆很远的一座城市)兴师,沿河顺流而下直逼大海(但希罗多德认为印度河向东南,而不是向西南流去),后来又从那里出发沿印度海岸向西航驶。当时的人认为该海岸几乎以直线由西向东延伸,尚未有其半岛形状的概念,完全如同隐没了的非洲南半部一样。最后,斯拉克斯经海路班师回朝。希罗多德认为,印度和印度河(假如确实是指此地)是无人居住的世界东限,其以远地区仅有一片沙漠石碛。我们将看一下在这些瀚海中发生的情况。
印度居民众多。希罗多德曾说印度人形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并描述了其中的几个部族,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大流士的军队中作战。这些人形成了波斯帝国的第20个行省。在纳贡方面,他们自己交纳的数额几乎与其余19个行省所纳贡的总和一样多,他们的贡物用黄金交纳,而几乎其他所有民族则都用白银交纳。贡品多达360个优卑亚岛塔兰(每个重25.920公斤,这样总共约为9331公斤)的金砂。下面就是希罗多德的记载:
印度人大量拥有黄金,并从中提取一部分向国王交纳上文提到的金砂贡赋,他们是以我即将叙述的方式而获得的……印度的其他部族都与卡斯帕提洛斯城和帕克提人地区为邻。对于其他印度人来说,他们位于大熊星座和北风一侧。这些人基本如同大夏人一样生活。他们是印度人中的最大的黩武之士,也正是他们前往寻求黄金,因为被风沙变为沙漠的地区就位于这一侧。在该戈壁和沙漠中,生活着一些并不完全有狗身大(但却超过了狐狸)的蚂蚁。波斯国王也有几只这样的蚂蚁,都是从那里捕捉的。这些蚂蚁在掘其土洞时,便把沙土掘出了地面,正如我们的蚂蚁在希腊所作的那样,而且它们也与希腊蚂蚁完全相似。但它们掘出的沙土中含有黄金,印度人前往沙漠中寻求的正是这种黄金。他们每人乘一辆三匹骆驼一套的车,母骆被套于中间,左右各有一匹被套绳拴着的公驼。采金人骑在母驼上,为了这项工作而必须用心将它与很幼小的骆驼分开。骆驼奔驰得至少也和马匹一样快,而且还可以驮载很重的负荷物……这就是前往寻金的印度人之装备。他们为能在最炎热的时候,采集到黄金而精心计算其行程,因为当时太阳的热度迫使蚂蚁藏身于其洞中。阳光在这些地区于黎明时(而不是如同在世界其他地区那样于正午)的热度最强,即从它升起到集市结束(正午前)之间的温度最热。据说它于此刻在那里的热度比在希腊的正午还强,以至于使印度人在每天的这一时辰都被迫钻到水中。在每天正午时,太阳在印度人中并不比在其他地区更热;在午后,其热度也变得比在其它地方的清晨还弱;热度随着太阳的西垂而减小,一直到它西落时,大地就变得非常凉爽了。
当印度人来到他们选中的地点时,便用这种沙土装满他们携带的所有口袋,并匆匆忙忙地返程。因为据波斯人说,由于气味而惊动了的蚂蚁会群起而追击。而据传说,任何一种动物都没有它们跑得快,以至于在它们集结时,未能向前逃跑一段距离的人,都会在那里丧生。跑得比母驼慢的公驼很快被甩在后面。人们于是便只有把它们解脱,但要一个接一个地解开。希望尽快回去照顾它们留下的小驹的母驼,永远不会放慢速度。据波斯人声称,印度人就这样采集了其大部分黄金,他们也从自己的地下开采,但数量要少得多。
这一故事经过了坎坷的历程。从那些坚信不已的编纂人到抱有怀疑态度的译者,它在西方(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和欧洲的主要语言)著作的范围内,经历了所有这些时代。许多人都试图解释清楚它,但又零星地增加了一些进一步使其神秘化的细节。
在希罗多德于苏萨城撰写他的著作与其文要晚3个多世纪的老普林尼之间,又产生了对了解东方是至关紧要的一系列事件:亚历山大征服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卒殁于公元前323年)在征服了大夏之后,无疑曾进军到旁遮普。希腊人在这些地区停留了很长时间。亚历山大的战友尼亚格奉他的将令出兵刺探情报,以便为希腊人确定一条从印度河口经海路回师的道路。因此,尼亚格与卡里安德的斯拉克斯作了几乎是同样的旅行,一直沿印度河顺流而下,然后又长期沿印度西海岸航行,那里生活有以鱼为食的人……大家知道尼亚格的船队是怎样几乎全军覆没,以及尼亚格和亚历山大是通过什么奇迹而会师的。尼亚格不会不带回有关所经过地区的许多资料,希腊舆地学家斯特拉波(卒于公元25年)在其舆地书第15卷中,为我们保留了他的记载。斯特拉波同样也使用了梅加斯特纳的资料,后者也与亚历山大本人同时代,曾任第一位塞流西国王派驻于一位印度国王处的大使。尼亚格和梅加斯特纳这两名证人又使该故事返老还童了,甚至更增加了我们的疑惑不解。公元1世纪的斯特拉波和普林尼,以及后来到2世纪时的阿里安,在其有关印度的著作中,也都如同希罗多德一样使用了他们的资料。
我们于上文不远处已看到,普林尼为希罗多德的记述增加了达尔德人的名称。斯特拉波又增加了某些新内容。我们再回到能寻找黄金的蚂蚁问题上来,尼亚格声称曾见过它们的皮,并且还说完全与豹皮相似。
至于梅加斯特纳,他在这一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下述一些细节。他说:“在达尔德人(大家就是这样称呼印度东部和山区的主要民族之一的)地区,有一片其四周约为3000里行程的高原,其山脚下就是金矿,完全由魔怪般的蚂蚁挖捆,这些蚂蚁至少可以说完全如同狐狸那样大,而且具有特别快的速度,仅以捕捉猎物为生。这些蚂蚁在冬季掘土。它们如同鼹鼠一般,以清理出来的泥土在洞口筑成一座座小丘。这些清理出来的土实际上是金砂或尘埃状的黄金,只需要稍微以火加热。所以附近居民以骡子驮载的方法,运走尽量多的金土,但却要分外注意藏身。因为如果他们公开行动,那么他们就将受到蚂蚁的攻击,被蚂蚁驱散和受到追击。如果蚂蚁追上了他们,那么甚至会把他们及其骡子统统扼死。为了使蚂蚁的监视落空,达尔德人到处都陈放一些肉块,当蚂蚁散开时,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挖取金砂了。此外,他们还被迫出卖粗沙,用随便什么价格就可以出售给前来拜访他们的商人,因为他们对于冶金属一窍不通。”
与希罗多德的著作相比,本处的新内容是用骡子取代了骆驼,而且也不再牺牲牲畜以拖延蚂蚁的追袭了。他们用一些肉块来吸引它们,再没有等待其小骆的母骆了。此外还有另一种对冶金史专家们颇有用的资料:达尔德人(Derdes,无疑就是数年之后普林尼所说的Dardes)不懂得加工金属而是出售粗矿砂。
斯特拉波在其同一部著作的第15章中,也补充了一种来自某部鲜为人知的史书中的资料,但他未作具体说明(既不是尼亚格,又不是梅加斯特纳的著作)。它为我们的这种含糊的印象,又增加了一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细节:有些寻金蚂蚁长有翅膀。
印度和波斯的这种残酷、食肉、疾驰、炎热时入睡,如同肥胖狐狸一般大,皮毛之颜色如同猎豹,长角、长翅、善于掘洞大采金又使人无可奈何的动物,到底是什么呢?从来没有人描绘过这种神秘动物的草图,无论毕丰、格斯奈——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书的绘图者,还是利斩玛书插图的绘制者们,都一概如此。但这一切都使我们分别联想到了麝麂、蝾螈(无论是真还是假)、牦牛和龙。那些为我们描述安尼德特和耶蒂人的形象者们,也基本如此。他们是否属于一种已消失的人类呢?他们是否是对一些臆想的和荒诞古怪之故事的七拼八凑呢?为什么我们对这一切都没有掌握任何资料呢?他们是否是乌拉尔河上游的独眼阿里马土波人(另一种采金人),经常与之拼斗的一种狮身鹰头鹰翼怪物的同类呢?
我们实际上不知道这种动物的任何形象。现在应该指出,继斯特拉波和普林尼之后,这一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已被简化并失去吸引力了,它在传播过程中又失去了某些细节。公元2世纪的阿里安,就已经仅仅提供了一种经简化后的说法,而且他本人对此也略有怀疑。尼亚格和梅加斯特纳证明了这一故事,但应再重复一遍,他们仅仅是通过传闻而获悉的。尼亚格在希腊人的营地发现了这种动物的皮、常有人为他们带来这种皮货。梅加斯特纳未亲眼见到一切,只是有人向他叙述过甚至比狐狸还大的巨蚁,挖掘金土作穴。阿里安写道:“至于我本人,由于我对这一问题不能叙述任何可靠的情况,所以我更主张对这一有关蚂蚁的故事置之不理。”由于这一事实,任何人都未亲眼见过这种抢夺黄金的场面,甚至有关其皮和角的证人,在公元1世纪之后也后继无人了。被视为传说中的希罗多德的蚂蚁,很快就从严肃的史著中消失了,一直到某名于印度服役的英国军官,在印度河畔发现了在一片金土中掘洞的旱獭那一天为止。旱獭可能很久以来就这样作了,而在当地未曾引起过如此之注意。但需要等待旱獭、黄金和19世纪拉丁化的欧洲人的机缘,才能使这一故事有了新的起点。
如果有人在1846年能看到对老文献作的生动的说明,那么这一故事为什么不可能是真实的并应归于该地区呢?坎宁安还写道,这些印度的蚂蚁“无疑就是西藏的旱獭和鼠兔,它们在挖穴时把含有金属的沙土抛到了地面”。因此,它们不是一些特大的神奇爬虫,而是很小的哺乳动物。
50年之后,基督教传教士弗兰格(他的大量出版物现在仍受重视)也提供了一种类似的证据。他在1900年之前于数年间,生活在印度河上游北岸的卡拉兹(位于列城和卡尔吉尔的经度之间,也就是在藏斯喀尔谷稍西和苏卢谷稍东处,今天仍有某些人认为那里是著名的蚂蚁区),曾向当地居民调查过有关该地区采金动物的故事。他提出的问题,不久就得到了回答。他在数日间就搜集到了两种有关动物采金的长篇故事,甚至还有人向他指看正在这样做的动物。它是一只很小的走兽,比一只狗或狐狸还要小得多(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未提供其名称)。但该传教士又补充说,这一故事在印度和希腊之间得到了广泛传播。他本人未亲眼看见从事这种活动的动物,而相反却沿印度河两岸(从萨斯波拉到达特锡克)看到了古代采金的许多遗迹。仍在同一地区中,在80公里的大地上挖得满目疮痍。在他生活于拉达克这一地区的时代,大家开始关心搜集这些矿址中的金属了。
无论如何,这里的神秘性并不在于黄金的存在,而是其名令人无所适从的那种谜一般的动物。
在今天,由希罗多德使用的那个希腊字murmex(拉丁作家们忠实地重复了它),在这段文字中作了很笼统的解释,如同指一种哺乳动物。本来意指爬虫的“蚂蚁”,仅仅是大家所赋予其意义的第一种(如在尚特兰的辞典中)。这种情况在动物名称史上并非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只不过是在使用法文的例证中,我们就知道有海象、猫头鹰(又叫猫)、蝙蝠(秃鼠)。因此,如果某种“蚂蚁”并非真正的一种爬虫,那也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同一种现象,在我们上文已大量论述到的印度史诗《蚂蚁之黄金》中“蚂蚁之金”又起了同样的作用。这些“蚂蚁”是否也是哺乳动物呢?或者有的地方是指蚂蚁,而其他地方又指哺乳动物呢?莫尼埃—威廉姆斯的梵文辞典从未说明Pipilaka一词是指一种被认为系由蚂蚁挖掘出的黄金,它可能是指这种爬虫之外的另一种动物。
但坎宁安的心中却有类似的想法。因为他指出了一种他个人觉得应引起注意的巧合:旱獭皮很多见,此种动物在该地区广泛存在,西藏人称之为phyi-pa、chlipa或chupa(我们还记得,这些字都按英文方式转写过),印度人是否在phyi-pa和梵文或孟加拉文pippilaka之间混淆了呢?
但我们应注意它们之间在语音或拼写方面的相似性,它们是否是两千年或更久之前的发音(谁又知道其发音如何呢?)。我们不要沿这条路走得太远了。此外,还有许多其它谜底。
坎宁安有关拉达克的著作出版于1854年。无论人们对《摩坷婆罗多》中的蚂蚁作何感想,我们总可以说,人们从此已不再讨论对这种动物不是一种爬虫,而是一种哺乳动物的信仰了。其余的问题仍在继续讨论。由希罗多德的帕克提人和卡斯帕提洛斯到普林尼的达尔德人,在确定产金区的地理问题上实际上没有困难。
我首先应指出,希罗多德没有使用“达尔德人”一名,甚至也没有提到与之相似的任何民族。他没有指出当时是以什么名字称呼前往寻金的印度部族的。他仅仅指出这些印度人与其他印度人相比,居住在北方,与卡斯帕提罗斯城和帕克提人(疑为指帕提亚人,即安息人。——译者)相毗邻,是一个比较尚武的民族,他们的生活基本上与大夏人相一致。但是,如果说他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了大夏人(大夏人很久以来就被考定为巴克特利亚人),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从未向我们指出过他们是怎样生活的,即他们究竟是游牧民还是定居民,是牧民还是农民,他们信奉的神祇和风俗习惯如何等等。我们知道他们属于波斯帝国的第12个行省,用白银纳税,大流士把那些他希望惩罚或使之无法作乱的民族和人士,都驱逐并流放到了大夏。在波斯大军中曾提到过这些大夏步兵和骑兵,还有他们使用的芦苇弓弩和短矛枪。我不再于这些寻金人的问题上作进一步论述了。
对于帕克提人和卡斯帕提洛斯城(也可能为他们的主要城市),我只知道他们属于波斯帝国的第13个行省,用白银纳税,身穿裘皮衣(因此,他们可能来自某一寒冷地区),在大流士部队中作战,以弓弩和短剑武装。曾奉大流士的将令,而前往侦察印度河流域的探险者斯基拉克斯,也是从卡斯帕提洛斯出发的,因此该城位于印度河畔。他可能从那里沿印度河向东而下一直到达海洋,然后又从那里经海路返回埃及(希罗多德描述的该河的流向,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了)。
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一致认为帕克提人地区是今阿富汗的东半部(现在尚叫作帕克提亚,即当时的帕提亚人或安息人)。对于卡斯帕提洛斯城,人们的看法上有分歧,或者是把它确定在印度河上游的某一地点,或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或者是把它确定在几个纬度线以南的地方,此地被考定为古印度的卡西亚帕布拉或托勒密所说的卡佩斯拉城,大家认为它就是今天拉维河畔的木尔坦,位于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的北纬30°稍偏北的地方。这第2种比定法是由坎宁安本人于1871年提出的。印度沙漠距那里确实不远,这也是由巴尔盖在希罗多德的《七诗圣》版本中所选择的定位。另一位译者拉卡里埃尔,似乎也断定托尔沙漠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位于印度东部的沙漠。
事实上,从木尔坦(可以被视为位于更靠印度河上游的一个地方)起,沿河直下就可以到达海洋,即使该海不在东部也罢。
但普林尼毫不犹豫地写道,前往向蚂蚁争夺金矿者是被称为达尔德的民族。他提供了与希罗多德相同的细节(蚂蚁在炎热时入睡,当骆驼的气味惊醒它们后,便向骆驼扑去等)。他还补充了有关这些蚂蚁的皮毛、身材和角的某些细节。继他之后,人们往往普遍把希罗多德所说的蚂蚁故事确定在普林尼所说的达尔德人地区,后来西方人在19世纪时就认为达尔德人即今之达尔都人(尚需考证),因为这些名称恰恰相似。由于旅行家们在印度河上游河谷及其支流萨约克河中,亲眼看到或在当地听说了,有关由动物如此开采的金矿之事。
我们不能毫无保留地使用“达尔德人”一名。大家在普林尼和斯特拉波的著作中就发现了它,并有人将之比定为梵文Darada。但它主要在19世纪时才重新出现(它今天已有了一种新的用法)。据作者们认为是指吉尔吉特、奇拉斯或位于北纬37°—35°和东经73°—74°3′之间的整个地区,也可以仅仅指巴勒蒂以西的居民。Dard或Dardou这些名词往往具有比较广泛的意义,在位于偏南的平原地区居民口中,用以泛指印度河流域山区的部族,那些粗犷和尚武的人。有人也很想把他们的先祖说成是野兽(这种特别黩武的性格明显使人联想到了希罗多德,但该资料微不足道)。我们还将指出,达尔德人从来不这样称呼自我,而任何一个民族也未曾说过“我们是达尔德人”。总而言之,达尔德完全是另一回事。
另一方面,最近有人希望更具体地重新考定寻金者达尔德人的地望,特别是在流经卡吉尔的印度河支流苏卢河的山谷。该地区比吉尔吉特和希拉斯的达尔德人地区更为偏东。最近的旅行家们也谈到了该谷地中的“达尔德种族”。这里很偶然地把一个如此古老的名字运用到了一个现代人集团,即在那些许多战争和入侵使各民族迁移、动荡和互相杂混的地区。就在20世纪后半叶,我们有时仍有这种确切考定由古代希腊和拉丁作家所描述事件的舞台的愿望,这无疑是19世纪欧洲人思想状态的残余,他们都希望前往亚洲腹地寻求其发祥地和希腊佛教艺术之源。
藏斯噶尔河谷、苏卢河谷、印度河和萨约克河上游,东经76°和77°之间地区,都可以被视作在数世纪期间属于吐蕃的辖地范围。那里的文化现在大部分还都属于西藏文化。我们确实可以说该地区属于对西藏黄金研究的范畴。但我们对于阿富汗的帕克提亚却不能如此武断地下结论,而希罗多德确实认为寻金的印度人是帕克提人的近郊,达尔德人在历史的过程中有过迁徙。所以,对现今所谓达尔德人地区的定位,从文献的逻辑来看是可取的。但我觉得把这些河谷视为希罗多德所说的那些谷地,似乎还有一种巨大障碍,即有关骆驼的故事。实际上,印度人抢金的全部技巧,都是以骆驼的高速度逃跑为基础的,更具体地是指就是失去了它们那尚在哺乳的驼驹的母驼。“蚂蚁”是奔驰最快的动物。但我在所有的游记故事和该地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什么呢?那里仅是一些危险的通道,难以通行的道路,陡峭的羊肠小道,不时有滑坡、大雪和湍流;到处是山,山,还是山;苏卢河谷在5000—6000米的高峰之间奔流,大家在那里骑着普通马、小矮马和骡子缓慢地前进或步行。近代少有的几条路都要付出无数辛苦,而且也相当危险。谁可以在类似的道路上奔走呢?母驼的全部历史会使人联想到一片草原,至少对于金矿址本身来说是这样的,位于一片其距离相当远的地方,以使印度人在偶然重新到达山脚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摆脱”其追击者。但如果考虑到失去其小驹并急于重新找到其“子女”的母驼的情况,那么其出发点也不可能距金矿址有数日行程之远。母驼在离开其驹的数小时之后,很可能便开始希望返回。因此,肯定无法使它们在很长时间内向沙漠前进,即使是强行也罢。它们很快就会尽一切努力返回其驼驹处。金矿址可能位于不足一整天奔驰的地方。我们应该承认,所有这一切丝毫不会便利我们的定位工作,在距我们刚才讲到的地区附近,很难找到任何一块可以使极快的骆驼奔驰的平原或荒凉的沙漠高原。
我还需要或把卡斯帕提洛斯城置于木尔坦(正如坎宁安所作的那样),并把我的研究引向托尔沙漠。但据我所知,该地区没有任何产金的名声或传说。所以印度河上游地区的产金特征是众所周知并得到明确证实的事实。我们或者是把他们的地望大大地向东和东北推进,置于塔里木盆地或西藏高原。
现在属于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西部有数条江河流经(叶尔羌河、于阗河、尼雅河和克里雅河)。在18世纪时,该地区叫作喀什噶尔或小布哈拉,它当时是产金区。我们是否还应证实从希罗多德时代起,就在那里收获黄金呢?如果不越过难以跋涉的山口和危险的道路,那么就不会到达这些山谷,无论是从哪里来,甚至即使把帕克提人推向比今阿富汗更偏北的地方也罢。但至少就其地域而言,这些具有几十公里的地区,有时也有平原,那里可能会使母驼疾驰,一直到达西北的喜马拉雅山或帕米尔那些令人生畏的山脉脚下。无论人们转向哪一侧,都必须翻过这一关隘。
我最后还应指出,我在塔里木盆地,没有搜集到与希罗多德的蚂蚁故事相似的传说。但这种定位法却吸引了某些作者:雅库布在其1831年的《贵重金属史》,海伦和瓦尔特海姆于1834年都是这样做的。此外,这后一个人还有一种有创造性的见解:由尼亚格所观察到的动物皮,被认为是能找金矿的神秘动物脱下的。如果我们确实希望采取这种新词义,那么它可能仅仅是鼬狐(沙漠地带的一种小狐狸,在西域很普遍)的皮。鼬狐皮被世界许多地方,尤其是西域产金地区的土著人用来采集金片。他们在河流底部铺上带毛的皮,常常是绵羊皮,金片被挂在毛上。只要把皮子从河中取出并晒干,然后再摇动和用刷子刷洗就可以搜集到金片。
有人会反驳我说,鼬狐没有角,应该找到一种长角的小动物。我对此尚无对策。这些事件甚至还会变得更加复杂。事实上,在1868—1869年间,希罗多德有关蚂蚁的故事,得到了一次奇怪的复活。
为了能应对禁止欧洲人进入尼泊尔和西藏进行测绘,英国在印度的机构曾组织、培训过土著地形地貌考察家。这些人化装成朝圣者或商贾,有时也成功地躲过尼泊尔,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当局的不信任情绪,这就是同样也很著名的蒙哥马利的著名“班智达”。英国有关这些被严密封闭地区的最早地形考察结果,就应归功于他们。这些“土著考察人”中最为积极者之一辛格于,1867—1868年间成功地进入了西藏腹地。在这次长途跋涉中,他经过了一些金矿址,其中有的已被开发,余者明显已被遗弃。这些地区的藏文名称分别为:托克雅伦(东经81°40′和北纬32°25′)及其附近地区托克娘莫、托克萨伦、托克拉约克、托克达伦、托克巴贡、萨伦等,所有这些地区都位于约为东经81°和82°与北纬32°25′和33°之间。该地图发表于1868年伦敦的《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中,并且附有蒙哥马利上校据班智达的报告,而作的有关此人从尼泊尔到拉萨,又从那里沿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进行旅行的游记,其中对矿藏的记述刊布于1869年同一刊物的下一卷中。
该班智达并非出于偶然而前往该地区,相反却是由蒙哥马利所要求的,他确实曾计划获得有关这些金矿的确切资料,当时已通过传闻而获悉了其存在的规模,但其地望却仍不明确。斯特拉赛于1846年得以成功地抵达玛法木错湖,他根据传闻而把主要金矿置于“盐矿”的北部或东北部十日行程的地方,而盐矿本身又位于玛法木错湖北方很远的地方。顺便说一下,这里是否指康地的西北边境呢?或在一个叫作萨尔—巴希亚的地方。
我们的班智达于1867年,通过拉萨和甘托克的西藏人向他提供的资料,而对要前进的通路获得了一种比较明确的看法。最后,当他再次出发(这次是从巴德里纳特峰开始)后,于1867年7月翻越了马纳山口,由熟知路线的商人陪同。他于8月末到达该地区的主要金矿址托克雅伦。由于西藏当局为他制造的障碍,他仅在那里停留了数日。
下面就是由蒙哥马利根据路途中的记载(只要土著探险者们还在活动,这些人的名字就不会公布)而撰写的对辛格及其同伴们参观过的矿藏的描述。
因此,他从西南而来,再次自珠穆朗玛山口而下,在一块孤立的大平原中发现了托克雅伦营地,其帐篷的主要颜色为棕红色,该营地与西藏的所有营地都相似,但更大一些。该地位于海平面之上16330法尺(其海拔高度为5000多米)。他参观了营地长官约达克·明·玛尔的帐篷,这是一座竖立于一条宽大壕沟底部的圆帐篷,位于地面七八法尺(约2.50米)之下,设有阶梯。他怀着赞赏而又不愉快的心情提到了那些大黑狗,它们随时准备扑向任何接近帐篷的人。金矿址中已被开发的部分是个长100—200步和约25法尺(近8米)深的大洞,人们只能通过阶梯和一个斜面才能进入其内部。随着挖掘,掘的土便被抛向四面。当班智达参观开发金矿时,该洞约一英里(1609米)长。他们用一种长柄镐挖地,偶尔也使用铁锄。用以制造这些用具的铁,来自比萨希尔和拉达克等地。就在营地本处,便有一个能修理这些农具的铁匠。
一条河沟通过矿区,这就使矿洞的底部在白天更像是一片沼泽泥潭,但河沟有益于淘金。他们用一条大堤把水阻拦起来,让水通过一条斜坡小渠流出山堤外。他们在渠底铺一块布,用一些石块将之维持在水底,以使水底不呈平面状。当一名矿工把从洞中掘出的土带来并撒在水渠中时,另一人则用皮囊使水流入小渠中。水冲走了较轻的土块,但黄金微粒便沉入了不太平坦的底部,只要掀起石块就很容易收起黄金。收获似乎甚丰,有时甚至可以得到很重的金块,班智达曾见过超过两英镑(900克左右)的一块黄金。班智达还叙述了该地区极端寒冷的气候,甚至在9月间即如此了,冬季必须穿皮衣。他指出那里的帐篷都支在有7—8英尺深的洞底以便防风。但尽管寒冷,西藏人仍喜欢在冬季工作,夏季有300顶帐篷,冬季可达6000帐。因为冬季地冻,能经得起重负荷而又不会有因塌方受碍的危险。
我介绍这些细节,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班智达所记述的这段文字,后来确实如同或超过了对我们上文已提到的希罗多德的那一段著名文字的研究、分析和剖析。
该文献于1868—1869年间就被文人界所熟知了。从1869年3月16日起,我们可以在伦敦的《保尔·玛尔》杂志中读到劳林逊的一篇考释文,因为劳林逊本人也关心亚洲的古代地理学。作者在这篇考释中,立即在班智达和希罗多德的文献之间作了比较:“任何人都不能阅读班智达有关西藏矿工的记述,他们生活在地面之下7—8尺的帐篷中,在淘洗其中所含的黄金之前,挖掘出的土堆得就如同小山一般。这尚无须提及希罗多德著作中对蚂蚁的描述”。
由此开始使出现了一批受某种狂热支配的西方的希腊和东方学家。这里证明了辛格所说的西藏矿工和希罗多德所说的蚂蚁,是同一种表现形式,说明西藏才是希罗多德所描述的地区,那里与帕克提人和卡斯帕提洛斯人为邻。我们还应从这种比较中一一排除逻辑中的障碍,这类障碍是不乏其例的。思想中的创造性会带来奇迹。我于此仅能对形成了学者们之间生动辩论的一系列方法、感想和驳辩进行一番概述,这场辩论今天仍未了结。
有关这一问题的最为可观的工作,是丹麦教授谢尔恩的论著。它首先于1870年出版,后又于1873年分别用丹麦文、德文和法文3种文字在哥本哈根出版,接着于1875年又根据略作删节的法文版而出版了英译本。我们可以从其中发现于此之前发表的全部著作的长篇书目,其中包括古代作家们有关一问题的段落(请读者参阅这些出版物,我们不认为于此重复这些书目是必要的)。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各种讨论:对动物所作的定义、对帕克提人和卡斯帕提洛人地望以及金矿址地望的确定,排除明显的矛盾等。
第一种排除:在第一种希腊史料中是否仅仅是对murmex(旱獭)一名的误写呢?但这种由某些人提出的假设,在事实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上文所提到的古代梵文文献,也在以有关这种我们不得不注意的特殊方式开采的黄金问题上,使用了一个泛指爬虫的词。
我还应补充说明,我们通过这种论据便可以回答由波斯人或其他民族,为了向猎奇者们掩饰其黄金的真正来源,而故意散布的一种错误流言的假设。这类“流言”在历史上也并非罕见,但它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传播的。
从1870年起,流传最广的看法认为这里确实是指一种动物,不是一种爬虫,而且还是一种掘地穴的哺乳动物。我们可以发现有人曾认为是鼬狐、鬣狗、豹、仓鼠,或者据坎宁安认为是旱獭或兔子。坎宁安的假设在这一点上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推理,而是直接观察的结果。他亲眼看到了挖掘金土的旱獭,还有人向他断言巴尔蒂人有时也搜集这种土。但当时某些人指出,希罗多德所说的动物特别凶暴、敏捷,而旱獭却温和、迟钝。这就是其症结所在。但如果这些动物中没有任何一种适合此种描述,那么也可能是指一种已完全绝种的动物。正如维吉尔所说的那样,它成为“追求黄金的可恶渴望之受害者”,最后被人类完全灭绝了。由关心该问题的一位学者提出的这种论据,则被谢尔恩教授当做幼稚可笑而摒弃了。今天,那种认为由于诸如“生态学”那样的原因,而使某种动物灭绝的思想,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坚持这种假设,那么有关动物掘洞采金和后来的整个讨论,就一去不复返了,多么遗憾啊!
但谢尔恩教授则持另一种看法,他是受一种视觉相似性的启发(至少是想象的视觉,因为他从未亲眼看见过):为了防风而在沟底建立如此之多的帐篷,以及抛在沟边形成小山般的掘土,从远处望去不是与洞穴不可思议地相似吗?它们难道始终都不是那些由班智达提及的圆锥形小丘和洞,那些由于严寒而从头到脚都有穿有皮衣,并在附近挖掘与活动的西藏人吗?其次,这里也是指一片沙漠。古代那些提供资料的人在遥远的地方,是否把穿着以这些动物裘皮的服装者视为野兽了呢?我们还应提一下,从前丹麦人是如何发现了穿驯鹿皮的拉普兰人时,几乎把他们看作是驯鹿(谢尔恩书,第229页)。所以,西藏矿工身穿裘皮衣。更何况,对于终生都未曾见过活的或死的西藏人的谢尔恩教授来说,他根据曾在蒙古见过西藏人的帕拉斯所作的介绍,而认为西藏人的面目都具有“与猕猴面目几乎是令人不可相信的相似性”。这一切都会取悦于最早的神话爱好者们,也可能几乎会使西藏人感到极大的恼火,因为西藏人恰恰把他们的先祖归于岩罗刹女与猕猴之婚合。如果谢尔恩知道这一神话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联想到他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我们还应补充说明:该教授继续解释了他们奇特的风俗习惯,如伸舌挠耳以表示问好,根据班智达辛格的描述,他们睡觉的姿势是俯在膝盖和胳膊上,也可以说是倚四肢睡,头扎在膝盖处,成群地住在外面。该教授继续写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面前的几百名西藏人,身穿皮衣,就这样互相挤在一起睡觉的情景。
另外一种吻合:西藏矿工更喜欢冬季工作,因为据辛格认为,当时没有塌方的危险。普林尼也曾指出,蚂蚁于冬季忙碌并于夏季睡觉。谢尔恩也引证了斯特拉波书第15章第1节中的一句话,它被归于梅加斯特纳。据后者认为,这些蚂蚁于冬季掘洞并如同鼹鼠一样在洞口堆土。此外,这些印度蚂蚁(始终据同一种史料认为)以狩猎为生。谢尔恩又补充说,那位班智达确实向我们指出,这些西藏矿工也以猎狩野牦牛和其他野兽为食。此外还有,矿工们常常受到强盗的攻击,因而才豢养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看门狗。许多旅行家们都讲过这一故事,班智达又重复了它。难道这些如此凶暴和如此疾奔并扑向印度人(希罗多德的看法)的动物不正是西藏人的藏獒吗?
但还有一个小难题:角的问题,即如同厄利特里亚的海格立斯庙中的角,大家也认为这是一种抄写错误。据沃尔(他也支持把这种动物考证为鬣狗)认为,不应将该词读作Cornua(角),而是Coriá(经加工的皮革)。也可能他们把Cornua理解作了“长牙”的意义,如“象牙”。严格地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里确实是指角,由于大自然的功力而使之很奇特地生长在一般是无角动物的头上了(我们确实可能应回顾一下所有这些假设)。总而言之,“角”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棘手。谢尔恩的解释认为,西藏人完全可以穿裘皮衣或兽皮,并且上面钉有该动物的角,很可能是作为装饰物或帽子使用的。他举出了一个例证,有人已向他证明,这里恰恰是指西藏人。在谢尔恩看来,这件事不仅是合乎情理,而且他还直言不率地宣布:“我们丝毫不能怀疑这种典型西藏人的头戴,并不是向参观厄利特里亚寺庙的人讲叙的故事中,所说的那些头饰”。
他在最后的总结中排除了怀疑的苦恼:“我们认为这一故事中再没有任何故弄玄虚的地方了。掘金的蚂蚁原来既不像古人所想象的那样是真正的蚂蚁,也不像许多著名学者假设的那样为较大的动物(由于其相貌及穴居生活方式而被误作蚂蚁),而是有骨有肉的人,即西藏的矿工。其生活方式和装束,在非常古老的时代就完全如同他们在今天一样了。”
我们不应忘记,对于像谢尔恩那样的欧洲史学家来说,西藏就如同月球一样无法进入,当时尚不存在有关其民族的照片。
但在今天还可以记得起的异议中,首先应该是一种笼统的原则性反对意见。我至今可以谈到的有关该问题的论据,都假设认为,西藏在2400或2500年以来,没有或几乎没有变化。当然,西藏人的保守气质是众所周知的,大家可以把近2—3个世纪以来的普遍稳定性作为根据,但我仍认为在这一方面走得过远是不谨慎的。我们对希罗多德时代西藏人的外貌一无所知。现在所知的西藏人历史仅从10或12个世纪之后才开始。他们是否始终都具有同一种体型呢?哪一个民族集团在哪次民族大迁徙之后,出没于和印度最近的地区呢?
大家还可以提出把这一著名描述定位于西藏的另一种反对意义。谢尔恩也如同其他人一样,把普林尼所说的Dardoe人考证为达尔德人,把希罗多德所说的帕克提人考证为阿富汗东部的帕提亚人,把卡斯帕提洛斯城考证为克什米尔。时至今日,尚未出现过反对意见,虽然人们也可能会受把卡斯帕提洛斯城比定为木尔坦做法的吸引,即大大偏向南方之地,这是由坎宁安提议的。同样,希罗多德指出一片沙漠的事实,则与对托克雅伦所处的荒凉高原的描述相符合。斯特拉波也提到了一片非常辽阔的沙漠,正如谢尔恩所指出的那样。但这其中却有一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现象,正如我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那是因为该高原由一片无垠的高山地与达尔德人相隔开,该山地是一个海拔高达4000—5000米的山口,那里有山谷、悬崖、堑谷、大雪、冰地,以至于自从有人写该地的游记故事以来,没有一个人不长篇强调穿越该地区的艰难和危险。有许多人都对其旅行保留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忆。许多人提到了事故的受害者,跌打、雪崩、严寒、严重高山病等事故。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却丝毫没有提到这一切,在至今所引证的有关古代的其他文献中,也没有这一切。希罗多德仅满足于提到一片无法居住的沙漠。这就把我们引向了上文所提到的有关母驼,以及它们在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动物面前的狂奔问题,甚至还包括矿址和出发点之间的可能距离问题。如果“蚂蚁”在西藏高原上,生活在一个诸如托克雅伦那样的地区,那么骆驼的印度主人之出发点,就应位于喜马拉雅山关隘的同一侧,这就是说同样也位于西藏高原。所以希罗多德所说的印度人,并不是普林尼所说的达尔德人。
我们在所有这些资料中还应补充一种属于气象方面的观点。辛格过分强调了托克雅伦甚至在8月间也出现的严寒气候。相反,希罗多德却强调了炎热,其文中含有许多奇特的资料。据他认为,该地区每日间炎热的高峰时刻,是黎明而不是正午。他提到了一种极端的炎热(而且他还是一名希腊人,已习惯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下游可怕的热浪),它肯定是属于最炎热之列。无论他对气候的描述多么充满奇异性(这一点似乎没有引起上文所提到的任何评论家们的注意),这种描述使得将其地望定于西藏西部冰天雪地的高原之想法,已变得不可能了。
此外,我还应指出,如果这种将其地望定位于西藏西部的做法,在30多年间占主导地位(大家在印度经济地质学问题上最严肃作家们的著作中,也会发现这种做法),那么它在1900年左右又被放弃而更主张为拉达克。当然,这场辩论始终未作结论。
19世纪的那位欧洲人谢尔恩,往往表现为推理主义者。他极力想找到一种具体的、合乎逻辑的、在任何方面都是合情合理的解释。他在研究其希腊文化的起源时,是以逻辑推理的方法进行的。他想根据手中掌握的论据,而具体确定古代文献中叙述的插曲之发生地。所以他高度注意类似某种证据的一切现象。如果缺乏证据,那么对文献的分析就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论。他们至此在某种意义上是玩弄了考证和推理的手法。这恰恰可能是一种过分推理的做法,一种对待传说过分“19世纪化”的观点。这种“蚂蚁”很可能是大家所需要的那些动物,甚至是一种已灭绝的动物。它们既在拉达克,又在西藏高原或附近的许多地区采金,因为当地不缺产金区,无论是含金片的河水,还是可以从事这项工程的动物,都不乏其例。就我们所知,达尔德人自2500年以来可能曾多次迁移过,曾经到过距那里远近不等的地方,古代地理学有时是朦胧的。但大家还应记得,在世界上存在着相当多有关矿藏的传说,有些传说认为金矿系由动物或其他危险生灵看守。人们必须冒很大危险,才能向它们夺取黄金,阿里马斯匹人的狮身鹰头鹰翼怪兽,在狮身上长着翅膀和长爪尖的大蹄子。它们被绘在希腊的容器上。希罗多德认为向它们争夺这种黄金的阿里马斯匹人,是世界上最为身强力壮的人。汉地的矿区也有它们那并非是好同伴的龙。长有黄发绿眼的金魔威胁着加利福尼亚职工。我们很想把采金的蚂蚁看作是同类的一种神话,一种被也是从中插入的具体事实所掩饰的神话,这一具体事实就是,确实有些动物在某些地区提供金土。在具有推理思维的欧洲观察家来看,这种具体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传说故事的结晶,从而使它产生了一种根本无需大惊小怪的现象。人们由于找到一种勉强符合逻辑的现象、一种表面的证据,所以就使这一神话传播开了。
我还将指出,如果有关采金蚂蚁的传说起源于印度(史诗《摩诃婆多罗》)、希腊或波斯(希罗多德及其后继人),但在汉地却没有相似的故事,虽然在汉地可以发现某些典型的西藏神奇动物。《唐书》指出在吐蕃有一种会飞的草,如同鱼一样长鳞,身大如犬,使人感到非常恐惧。但一切都与有关黄金的动物没有任何相似处。我还将指出,在托尔沙漠(我们也可以把本处涉及的神秘印度人去过的地方置于那里)中,似乎也不存在有关这些动物活动的传说,而且也不产黄金。在《摩诃婆多罗》中提到的蚂蚁和黄金,明显应确定在北部山区很远的地方,喜马拉雅山一侧或以远地区,绝对不会在托尔沙漠中。
因此,作为权宜之计,那些具有推理思维的人应满足于拉达克一地,唯有那里才存在有物资证据。诗人和这一神话的诠释者们,都有权想象一片更为辽阔的地域。
我现在再回头来谈一个较晚的时代,也就是在谢尔恩教授的论文已传播开,我们的那位班智达辛格又出发前往印度时。班智达于1873年9月在西藏新发现了已开采过的金矿遗址,即托克多拉克巴地区(位于东经85°—87°和北纬31°3′—33°之间)。他的地图连同其由特洛特作序的报告,于1877年出版,其中注有托克多拉克巴、托克丁令、托克持场、托克玛什拉、托克达克尚,托克吉穆利、当绒和萨迦夏尔等地。
那位班智达发现该地的采金规模比托克雅伦要小得多。那里矿工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在托克多拉克巴,他们几乎都栖身于在地下挖掘的土洞中。大家称这种住处为“洞穴”(Phukpa)。他共计算到32个,按照主人的财产状况而各自由5—25人棲身。这是由于他们迫不得已才选择了生活在这些土洞中的,因为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康巴人和游牧人中的强盗出没,他们习惯于杀死那些不慎居住在帐篷中的人。他们于夜间前来砍断帐篷的牵线,当那些不幸的人与强盗搏斗时,便会被从上面落下的帐篷绊住,强盗们便轻而易举地砍断这些人的脖子。那些地穴则比较保险,一个全副武装的人就可以对付大批进攻者。
但那里也有七八顶帐篷,属于流动商人或新来者。这些矿工们来自位于该矿区东部和东南部的纳仓,或者是西藏西部和“布拉马普特拉河畔的一座距日喀则以西有5—6日行程的重要城市羌格拉什”。
“地穴”(或“地下居室”)的主人开采他自己的金洞(而在托克雅伦,工人们则在一个共同的大洞中劳作)。班智达又具体解释说,开采工作只能于白天进行。那些相当坚硬的岩石都被用筐篮运出洞口,然后将之粉碎成小块,最后再将它们放入铺在一倾斜度不大的斜坡中的布片上,布片用石头固定,但不能使之形成一平面。这样就可以向上浇水。水将较轻的泥土微粒冲向远方,黄金便滞留在故意造成的高低不平的凹凸中。那些探险者在多拉克巴见过的最大金块约重达1两。但令人遗憾的是那里在距矿区1600米处才有水,必须用毛驴驮皮囊来运水。该地区如此寒冷,以至于为了不使毛驴被冻死,则必须在夜间把它们与其主人一起圈在洞穴中。
虽然矿工们向拉萨当局纳税很少(每人每年纳一砂金袋五分之一两的黄金,约为6克),但采金似乎也不是一种很赚钱的生意。这名习惯于印度生活方式的班智达还写道:采金人的收入“似乎比维持生活的全部必需略多一点……牧人比金矿工要富裕得多,而且还过着一种更为自由、更为舒适和更为独立一些的生活”。虽然采金非常艰苦,因为土地坚硬而水源又远,但多拉克巴的黄金要比托克雅伦的好得多。班智达认为那里有一块面积辽阔的产金区,但由于缺水却使其开采无重利可图。
他也解释了低税率的原因并补充说:“西藏金矿的规模和价值似乎被大大高估了。”
我刚才长篇引证的辛格之描述,明显使人联想到了上文已引证过的16世纪米儿咱·海答儿所说的“西藏金地”。米儿咱书的内容很久以来,就在不同程度上于西域传播,并于1895年用英文刊布,而辛格的记述在18年前才发表。其中的相似处是显而易见的:地下穴居、受侵袭之危险、严寒等。这就导致译文的诠释者爱莲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思考,我于此仅作以简单追述。“西藏的金地”是海答儿研究过的第一个金矿,由杜尔巴部开发。我们于此之前还可以读到,杜尔巴人共包括5万户,属康巴或游牧部的组成部分(他们也从事前往印度斯坦出售黄金的营生)。所以,开发该金矿的是杜尔巴游牧部的一支,而且也位于游牧民的领土上。
但据那位诠释家认为,我们在波斯文中读到的Dolpa一词,也可以用其他几种不同的方式读音:Dulia、Bulia和Pulba等。我们甚至还可以认为应把L读作K,以至于也可能读作Dukpa或Pukpa。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引向辛格所说的Phukpa了,指一批批金矿工为防盗贼而生活的地穴或地下住宅。所以,在大家似乎都倾向于认为,一个词的发音在历史发展中永不会变化的时代,这样领会文献是对的。
无论是从地理学角度还是从语言学角度,我们都不能非常严格地把古代与现代的金矿址相比较。这批金矿中有一些是众所周知的新矿,所以我们可以在上引蒙哥马利文中读到一条很可能并不是由辛格,而是由蒙哥马利本人所作的注释(因而是1869年):“据先前的资料认为,似乎是在8—9年之前(因而是1860年左右),首次发现托克雅伦地区盛产黄金”。但人们却在东经81°—82°和85°—87°、北纬32°25′—33°和31°30′—33°之间,发现多处矿藏的事实证明。至少在19世纪时,西藏高原就存在一个辽阔的产金区,从喜马拉雅山一直向北延伸到这个高原最远的地方(由于其海拔高度、寒冷和缺少植物,甚至在某些地方缺乏淡水,因而很难使人类居住)和从拉达克到拉萨的经度之间。据当地人向班智达的介绍来看,沿从拉萨到日土的路途一线,有一系列金矿,即沿紧傍布拉马普特拉河的分界线(很可能位于该江以北的低洼地)的沿途。昆仑山北麓同样也产金,但它不属于我的论著详细研究的范围。
这一产金区的存在,于20世纪初又得到了证实,它当时由一些英国人以及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于1905—1906年考察过,即在辛格探险近40年之后,当时进入西藏刚刚开始变得略为容易一些了。1906年8月,托克雅伦矿址又首次由一名英国人——库卢经纪人助理考察,该地于1906年又由斯文赫定考察。斯文赫定这一次从拉达克出发从事了一次探险旅行,使他从北到南穿越了整个托克多拉克巴金矿区,发现了一些近期开发过的痕迹和一堆堆确实含金的泥土。它们位于拉雄错附近高原上的一块非常荒凉的地区,介于东经85°和北纬34°15′之间。那里似乎仅于夏季才能工作。同一位探险家指出了东经86°线上的另一矿址,距拉雄错的边界有9日之行程,那里的黄金不是由淘洗获得的,而是粉碎岩块后经手选和风选才获得的。斯文赫定的探险路线从中间穿过了托克多拉克巴地区。他还横穿过伦格马—托克或格萨伦(北纬33°45′和东经82°10′)采金矿址;在令冲错东南(东经83°和北纬约33°20′处),有人挖掘了一些可达1米深的矿坑。他为自己的行程画了一幅详图。
另一方面,班智达辛格于1865年获悉在距拉萨有6—7公里的托蒂扶山存在有金矿和银矿,该山是穆斯林们的朝觐地,但那里的金矿尚未被开采。在哲蚌寺和小昭寺附近,还有由喇嘛们开采的金矿;或者是在日喀则以南24公里处的茂密山上的金矿,那时尚未被开发。
如果取一幅西藏地图并使用已引证过的文献以及分别由蒙哥马利、斯文赫定所提供的地图,由麦克拉伦在1907年6月22日的《矿业学报》中绘制的地图,而将至今所提到的全部金矿开发遗址都标出来,那就会得到20世纪初的一幅重要的和令人可笑的金矿图。其重点被置于托克雅伦、托克多拉克巴和萨迦夏尔3个主要地区。由于明显的历史原因,主要是英国的出版物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地区、阿里、羌塘、西藏西部高原的情况。因此,在近代并不仅仅是一个产金区,而是恰恰相反。我还应该指出,托克雅伦和托克多拉克巴也曾在1935年赫尔曼的中国历史和商业地图(《近代西藏的政治和经济》一书的插图)中,作为金矿址而出现过,但它们后来却从经济地图中消失了。现在我们再来谈西藏的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那里产金的盛名很早就被古文献证实,其中最古老者则应追溯到唐代。在19世纪和20世纪时,我们在那里又重新发现了天主教传教士和汉族官吏。
西藏的东部,从青海到云南边境,自1700年以后数年间被逐渐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了。青海地区自1710年向清政府纳贡,巴塘于1718年被平定,理塘至少从1729年起就真正处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这些地区的政治动乱不乏其例,省划曾有多次变化,民族边界始终不明确。青海成了蒙古诸旗的辖地,萨尔温江、湄公河和扬子江的上游以及云南边界地区,在数世纪期间都是使汉族人和藏族感到畏惧的地区。因为这都是一些被森林覆盖的高山峻岭,遍地布满凶残的野兽,居住有互相仇视的居民,他们或是“令人可怕的蒙昧”,“嗜血成性”,有时甚至是“食人生番”,他们时至今日还是一些“未完全受归化”的少数民族,其先祖们几乎被18世纪的清朝军队杀绝。但这些山岭中遍布金银,就如同阿萨姆,云南和缅甸的交界地区一样。西藏人居住的康地,同样也因强盗的出没而著名,那里也产金。在西藏的这一东部地区,有许多汉族和藏族人在相对有足够安全的地方,到处都淘金,这就是人们在18世纪对该地区的看法。
古伯察神父于1844—1845年间从西宁到拉萨而穿过了西藏,他指出曾遇见过在牛粪温火上铸金币的牧民。他写道:“在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方面如此贫穷的西藏,在金属方面却超过了我们的任何想象,在那里可以非常容易地采掘金银,以至于普通牧人也懂得纯炼这些贵重金属的工艺。”他提到青海及康地诸省是产金区。康地首府察木多城“也能养活其居民”(尽管在该地区缺乏农业、工业和艺术),“这是由于金矿、蓝色宝石,麝香、野牛皮和大黄”。
柔克义在他发表《有关西藏的汉文史料》的同一年(1891年),他个人的西藏游记《喇嘛之国》也出版了。他于书中多次提到在理塘地区存在着丰富的金矿。他在扬子江上游亲眼看到掏金工们在工作。此人断言,一般来说,在西藏到处都盛行淘金:“淘金是整个地区流传最广泛的职业之一,因为所有水流中都似乎蕴藏有贵重金属的细微沙粒。虽然每个淘金工所采集的数量无疑极其微薄,但一年的全部采量也不可避免地会达到某一可观的数字”。
1886年左右发表了一部有关西藏地理的汉文著作,当时赢得了许多读者。这部《西藏图考》完全重复了18世纪末《卫藏图识》中的资料,后者已由柔克义于1891年作了译注:“说板多山后有金厂”,或者是“达隆宗金粉”。无论是在这本地理书中还是在柔克义翻译的书中,都明确指出黄金出产于说板多山附近,而不是在从行政上讲的说板多地区。其中指出的行政区域是达隆宗。这同一地区同样也是作为蕴藏金矿的地区而被提及的。此外,《西藏图考》用两个不同的词区别了“金粉”、“金石”和“金厂”等。至于柔克义(我上文已提到),他可能参阅了一部比较古老的著作而作出了解释。据他认为,达隆宗的金粉就是在说板多提到的那一种,而《西藏志》(其作者于1721年在西藏)仅仅指出了说板多山区的金矿。
位于理塘和巴塘等地以南的云南边境地区,于1870年左右由赴西藏的天主教传教士德格丹修道院长作了描述。他在《1855—1870年的西藏传教区》一书中,特别是在有关金矿的一节(根据德格丹修道院长及另一位传教士丁硕沃主教提供的资料)中,有关于该地区黄金财富的详细描述。曾长期在该地区旅行和居住的这名传教士写道:“在西藏东部的所有河流中,甚至在最小的溪沟中,都蕴藏有金沙。”我于此仅从专写矿藏的这一章中摘录了有关经营黄金、金矿或矿砂的记载,它们都位于扬子江、怒江或萨尔温江、澜沧江或湄公河流域。
(译自巴黎1983年出版的《西藏的金粉和银币》中的《历史和传说》一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