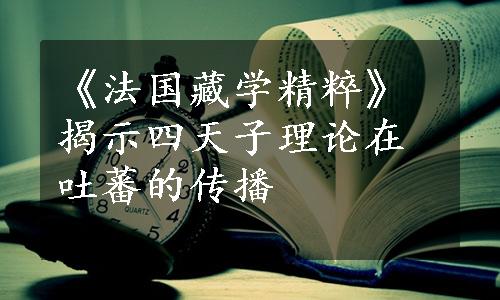
“四天子理论”在吐蕃的传播
A.麦克唐纳
在《汉藏史集》的目录中①,以下4个地区的前面都带有形容词:
神圣的尼婆罗(本处似指于阗)
智慧的汉地
英雄的弭药
法王的吐蕃。
它们可能是更为具体地指这些地区各自的国王的,完全如同其中把吐蕃称为法王地区所提示我们注意的那样。对各个地区的如此分类,以及选择与它们有关的形容词,似乎是对统治四方的四主之内容的追忆。自从伯希和的文章发表以来(载《通报》第22卷,第97—125页),人们都同意称之为“四天子理论”或“四天子说”。石泰安先生最近在他的论文(《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第241—314页)中用了最为言简意赅的一章,来论述这个问题。在《汉藏史集》中,当论述到选举的国王及其选举方式时,也阐述了这一内容(第5页)。这一内容与《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第244页中提到的《国王遗教》中的提法相近似。我已在他处转引了这段文字(《曼陀罗》第37—39页);在同一部《汉藏史集》下文第6页中,当谈到南赡部洲边界的时候,又重新提到了这一梗概:4个地区环绕吐蕃,吐蕃居中央,是世界的肚脐,汉地和契丹位于东方(参阅《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第259页和序言第31页),南部是印度和迦湿弥罗,西部是老虎部和豹子部(为了与其他各包括两个地区的方向相似,而玩弄了“大食”的字眼),北部是冲木和格萨尔。
“四天子理论”在吐蕃传播的开始,尚不大为人所知,石泰安先生认为这一理论是通过佛教的媒介而传播的。他还补充说(第253页):“虽然中国的取经进香人在印度遇到了这个问题,但至今尚没有任何一部印度文献(更谈不到以藏译本而著称的一部印度文献)向我们提供楷模。由于9—10世纪穆斯林作家们所赋予这种分类法的重要意义,以及他们当时与吐蕃人的接触(尤其是在于阗等地),我们还可以想到把上述观点在吐蕃的传播归于这些中间人。”有一卷敦煌文献值得我们于此引证,以支持这种假设。这卷文书在拉露小姐所编的《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中被编为Pt.958号。全文书共由三页组成,这是对佛教宇宙论某些观点的概述,这些观点可能引自某一部阿毗达磨的经文,因为此文献被称为《阿毗达磨》。写于左部第1行以上,3侧都有一条线所环绕。在下文所翻译的那段文字中,又重复了上述资料:“薄伽梵所说的这些话引自阿毗达磨的一部经文:《阿毗达磨论藏佛尊之言》。”虽然其中没有编页码,但这部经文明显是完整的:第1页是由上文所指出的标题而开始的,最后一页仅仅在正面写了4行。在简述了与“三毒”和在六道中转生之间存在的关系之后,以3条双短线结束。而这些双短线又两次以三个小圆圈分隔开来。
下面就是这卷文书中所触及到的内容:
1.阿修罗居住的四台,从须弥庐山脚下开始一直到达海洋中四万踰延那(yojana)的深处。四类阿修罗分别与饿鬼、人类、天神和动物相联系(第1页正面,第1—4行)②。
2.八部龙王:那些积累功德最多者居住在无热恼池。接着是对该池以及源出该池的4条河的描述,对赡部洲得以获名的阎浮树的描述(第1页正面第4行,背面第7行)。
3.八部龙王所居住的不同地区(第1页背面,第7行,第2页正面,第1行)③。
4.列举几个地狱(第2页正面,第1—2行)④。
5.世界的各个地区——四大洲的森林和墓葬、地狱、动物、人类、天神等,饿鬼根据其思想状态而分别与它们相联系(第2页正面,第2—3行)⑤。
6.列举在三界之中25类各种可能存在的类型,这些存在分为转生六道⑥(第2页正面,第3—6行)。
7.大、中、小三种娑婆世界。在该段文字之后才出现了“阿毗达磨论藏佛尊之言”这种表达方式(第2页正面,第6行;第2页背面,第2行)。
8.劫之轮回:成劫、住劫、坏劫、空劫这四个阶段。人体高度在劫中与寿数之关系(第2页背面,第3行;第3页正面,第1行)⑦。
9.转生的众生的“三毒”(贪欲、瞋恚、愚痴)与他们在六道中的命运有关(第3页正面,第1—4行)。⑧
本处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对无热恼池的描述,它开始于第1页正面,第5行:
无热恼池位于赡部洲的边界,
地处香山大山之南,雪山之北,
两山之间。
池周长100踰延那,
池水有八德……
一条河在该池四方的各自一方流过。
东河出自一只牛口,
河名叫作博叉河。
大河流向汉地皇帝处,他控制了“人宝”,
占有东地。
南河出自一只象口,
河名叫作私多河。
大河流向印度国王处,他控制了南部
摩揭陀国的智慧和“象宝”。
西河出自一只狮口,
河名叫作恒伽河。
大河流向冲木格萨尔地区,他是西方
狮子国大批商人的国王。
北河出自一只马口,
河名叫作徙多河。
大河流向默啜部,流向突厥和大食国王处,
他们占有了“马宝”,
是北国大批快马之主⑨。
东河和南河实际上没有向外流,它们已经就地消逝了,赡部洲就是通过它们而保持潮湿的。西河和北河各自绕无热恼池一周而后注入了向西南方向流去的大洋。无热恼池的北部生长有阎浮树,树高达4万踰延那,树枝树叶荫蔽全池。从树枝树叶上落下的汁液掉进了向东流去的大河。因为被树汁液滴触及到的石头和沙子都会变成金粒,所以当它们被运到汉地时就被称为‘阎浮树金’,赡部洲即由此树而获名”。
(原文书的藏文转写文略。——译者)
归根结蒂,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一段奇怪的文字,看作是提到了“四天子理论”的“译作藏文的印度文献”呢?如果这卷奇特的文书确实是引自阿毗达磨的一部经文,那就很可能是指《世间设施论》(对世界的描述),该经文连同《因设施论》和《业设施论》共同形成了《施设论》。据传说,这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7卷中唯一的曾被译成藏文,并被收入《丹珠尔》中的一卷。但是,为什么要把一部“论”称为“经”呢?另外,如果《世间设施论》是这一文献的史料来源,那么它本身是否在敦煌文书的时代就已经被译成了藏文呢?或者它是以一种汉译文为基础呢?
有关《施设论》经文的汉译本和藏译本资料,已由高楠顺次郎汇编进他1905年的文章中了,此文至今仍是比较研究根本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的基础⑩。拉·瓦累·普散(La Vallée Poussin)在《世亲和耶索密多罗》以及《〈阿毗达磨俱舍论〉概论》第29—42页中,又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穆斯(P·Mus)在《六道之光》第17—14页中,又都重新研究了这一问题 。
。
对于《佛说立世阿毗昙论》所提出的问题之一,出自以汉文本保存的《施设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538号)这一事实,译经时间为11世纪,其中仅仅包括《对法大论中世间设施门》的标题,并且在一条注释中指出其梵文原本已失传。高楠顺次郎当时曾建议到558年由真谛所译《佛说立世阿毗昙论》的另一汉译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44号)中,去寻求11世纪译本中所阙的部分。然而,在托玛斯先生的帮助下,经过对558年的汉译文与《丹珠尔》中的《佛说立世阿毗昙论》进行比较之后,高楠顺次郎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对同一内容的两种译本,虽然彼此之间在细节问题上有所不同”(同上引文,第77页注释,参阅《六道之光》第125页)。瓦累·普散也认为,从由高楠顺次郎所译之南条文雄目录第1297号来看,此经文与藏文本没有任何关系。这首先是由于汉文本是以“经”而出现的,其次是由于这两卷经文虽然在所论述的内容上有共同之处,但另外一些却不同,而且内容顺序和安排方式也都不同(《〈阿毗达磨俱舍论〉概论》第31—40页)。至于穆斯先生,虽然他反对瓦累·普散的观点,其意见也由根本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文献中所使用的文学手法,与巴利文校勘本手法相比较的研究,而得到了支持,因而认为“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中,仍保留了经文的外部特征”(第135页)。然后,在通过研究原文而校正对某些篇名的解释和对巴利文、汉文及藏文文献相应段落进行比较时,他又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藏文本与此(指真谛的汉译本)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字面上的相似性”(第137页)。然而,对于两部文献的内在比较,不能进一步推向深入,以谈到更多的问题。
因而,就问题的现状而言,正是由于在558年的译本与《丹珠尔》文本之间的比较,才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断代。但完全与穆斯先生在其文第123页所说的情况相反,藏译本并非是完全没有时间的。在组成《丹珠尔》中的《施设论》的3部经文中,唯有后两部附有译师的名字。但正如考狄(Cordier)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从索引和题跋来看,这3部经文似乎代表着一部统一的经文《施设论》的同样章节”。事实上,北京版本的《目录》也明确指出(第125页):“在第2卷中有一部由尊者大目乾连所著的《施设论》,其中包括由9卷组成的《世间设施论》(而据《大目录》认为则是6卷),由胜友、智慧铠和译师益西岱(智军)等人翻译的6卷本《因设施论》、由胜友、坛戒和智军等班智达所译的《业设施论》。毗婆娑论师们把这些经文看作是佛言,而修多罗部的经师们则认为它们是论。”我们暂且对提到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958号的《阿毗达磨经》的最后一点置之不顾,因为它已由瓦累·普散和穆斯(同上,第121页)所指出,而且也广为人知了。现在还有另一事实值得注意,即这3篇经文形成了一个整体,从逻辑上来说这三者是同时被翻译的。这一点已由布顿法师所证实,他在对《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分析(形成了《善逝教法史》的续篇,见本人所拥有一册的第155页,奥贝尔莱没有翻译)中宣称,“《世间设施论》共有7卷,《因设施论》也分为7卷,《业设施论》分为5卷。这些经文已由智军所译。毗婆沙论师们声称这都是佛言,在《大目录》中也把它们归于了佛言一类;但修多罗部的经师们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论’,我的分类与后者相同” 。
。
我们是否可以考证这一《大目录》呢?它把7卷归于《佛说立世阿毗昙论》,又把《施设论》分在“经”部。这里也可能是指《登迦目录》,图齐认为它修纂于公元812年。因为我们也从中发现,把7卷本的《世间设施论》和《因设施论》以及5卷本的《业设施论》都纳入了小乘经文一类,并一一列举 。这就是布顿所提供的数字。(www.zuozong.com)
。这就是布顿所提供的数字。(www.zuozong.com)
简而言之,如果不认为这些变化是在9世纪的译本与《丹珠尔》之间出现的,那就不容置疑地肯定,《施设论》中的3篇经文是在9世纪时译作藏文的,并且被分在了“经”一类中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到《世间设施论》中去寻找Pt.958号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中有关无热恼池段落的史料来源,其条件是如果它确实是引自其一部阿毗达磨的“经”。然而,我们在《世间设施论》中确实发现了对该池以及由此而出的江河的描述,不过却没有任何关于“四天子理论”的内容。由于普散在《世亲和耶索密多罗》中没有强调这一段文字,所以我于此根据北京和纳唐版本(它们是相同的)的《丹珠尔》而译出:“在赡部洲以北,有3座黑山。在这3座黑山以北,又有另外3座黑山。在这另外3座山以外,有一位被称作雪山的山王。在雪山山王以北,便是一位被称为香山的山王。在香山以远10踰延那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为‘水’的大湖,人们也称之为无热恼池或阿耨达湖。该湖有40踰延那宽和50踰延那深,周长为200踰延那。此湖形状漂亮,看起来很悦目……遍布鲜花。4条大河出自此湖,即恒河、辛都河、博叉河和私多河。恒河出自东部一只象口,它自右部绕水湖一周,连同500条河流一并注入了东洋。辛都河出自南部一只牛口,从右部开始而绕被称为‘水湖’的大湖一周以后,连同500条河流而注入了南部大洋。博叉河出自西方一只马口,它绕湖流了一周之后连同500条河共同注入了西部大洋。”
我们由此便可以看到,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958号的作者对无热恼池的描述,并不是以《世间设施论》为基础的,后一部经文在这一问题上与世亲的《阿毗达磨俱舍论》(卷3,第147页)相吻合,但稍有发展。然而,我们可以认为《丹珠尔》中的译本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可能与9世纪的译本不同。但还存在有其他包括有描述佛教世界的敦煌文书,如拉露小姐所编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966号。此经文在印度语中叫作Lo-Kapradna,即《说世间形成史》。其中没有提到无热恼池。相反,紧接着的967号伯希和敦煌写本也引自《世间设施论》,它以下列方式提到了无热恼池(第12页背面):“在该赡部洲北方很远的地方,距被称为香山山王以远处,有一大湖叫作无热恼池。其周长为200踰延那。从此大湖源出4条大河。都有哪些呢?即恒河、辛都河、私多河和博叉河。从此河中可以掘出金砂和绿玉片 、珍珠和各种各样的宝贝。每条河又由500条河而扩大,注入一大洋”
、珍珠和各种各样的宝贝。每条河又由500条河而扩大,注入一大洋” 。此文献似乎是概述了《世间设施论》的资料,但也没有包括比后者发挥得更多的有关“四天子理论”的内容。换言之,虽然此文书表现得似乎为一部阿毗达磨经的摘要,而且似乎还要归纳到《世间设施论》。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部《世间设施论》,也没有任何一部阿毗达磨经文把“四天子理论”与对由无热恼池发源的4条河的描述联系起来
。此文献似乎是概述了《世间设施论》的资料,但也没有包括比后者发挥得更多的有关“四天子理论”的内容。换言之,虽然此文书表现得似乎为一部阿毗达磨经的摘要,而且似乎还要归纳到《世间设施论》。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部《世间设施论》,也没有任何一部阿毗达磨经文把“四天子理论”与对由无热恼池发源的4条河的描述联系起来 。完全如同常见的对阎浮树的描述,不能说明由于与树汁接触而变成黄金的石块,是由东河冲走并流到汉地的一样
。完全如同常见的对阎浮树的描述,不能说明由于与树汁接触而变成黄金的石块,是由东河冲走并流到汉地的一样 。
。
然而,把无热恼池与四天子两种内容结合起来的现象,却由普祖鲁斯基在有关柬埔寨那榜的一座建筑的问题上所承认并提及。此建筑包括一个中心坑,通过石渠沟与位于4个方向的4个小盆坑相沟通,石渠沟中的水从4个雕刻的动物头中流出。普祖鲁斯基在他对动物头的描述中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4条大河正是从这4只动物头中流出来的,唯有牛头除外,本处由一个人头所代替,这是出于假设在这一建筑的设计中,“四天子理论”与对无热恼池的描述重合起来了 。在说明了那榜的建筑中结合了两种内容之外,现在Pt.958号写本又说明,对无热恼池的描述可能成了四主理论的传播工具。这肯定是由于在这两种情况下,世界的各个地区都与一种动物相联系,唯有东部除外。在对无热恼池的图解中,东部与一只牛相联系;而在四天子理论中,则与人类相联系。由Pt.958号写本所得出的下表,也完全可以说明东部的特殊情况。唯有在这一方向,从其嘴里流出一条河的动物,并不被看作是统治该地区的国王的财富。我们尚可记得,在那榜正是于东方雕刻了人头。
。在说明了那榜的建筑中结合了两种内容之外,现在Pt.958号写本又说明,对无热恼池的描述可能成了四主理论的传播工具。这肯定是由于在这两种情况下,世界的各个地区都与一种动物相联系,唯有东部除外。在对无热恼池的图解中,东部与一只牛相联系;而在四天子理论中,则与人类相联系。由Pt.958号写本所得出的下表,也完全可以说明东部的特殊情况。唯有在这一方向,从其嘴里流出一条河的动物,并不被看作是统治该地区的国王的财富。我们尚可记得,在那榜正是于东方雕刻了人头。
我们根据某些常见的描述 (如《世间设施论》中的描述),而可以制订出相差甚殊的表:
(如《世间设施论》中的描述),而可以制订出相差甚殊的表:
马口位于西方,狮口位于北方,而在Pt.958号敦煌藏文写本中,这一方向正好颠倒。至于4条河,恒河一般位于东方,于此却位于西方,而博叉河由西至东流。塔里木河(私多河)和印度河(徙多河)一般均认为在北方和南方,而于此却相反。除非北部的徙多代表着弘多的汉文对音,但这似乎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我们应承认私多河相当于印度河,汉文之对音为“辛都”河(参阅《热恼池大会》第177—180页)。
有关四主的问题,东部和南部与大部分分类是一致的。其中的藏文术语“人宝”、“象宝”以及下文不远处的“马宝”,似乎都是暗示圣王的七宝。释觉月在由石泰安先生已经指出的一篇文章中,把这一系列宝与4位国王的内容相比较。虽然“人宝”不属于这一类。正如石泰安先生向我指出的那样,圣王的七宝应作为一般所使用的“宝”这一术语的出发点,与康泰在他对天子的分类中使用的“群”字稍有相似 。在Pt.958号敦煌藏文写本中,唯一没有与七宝相联系的一个方向恰恰正是西方。人们一般都认为该方向是宝石地区。这也导致人们联想到“宝”字在其他情况下并没有用于其真意,而似乎更应该将此看作是圣王一系列宝的某种模糊回忆
。在Pt.958号敦煌藏文写本中,唯一没有与七宝相联系的一个方向恰恰正是西方。人们一般都认为该方向是宝石地区。这也导致人们联想到“宝”字在其他情况下并没有用于其真意,而似乎更应该将此看作是圣王一系列宝的某种模糊回忆 。
。
据记载,西方商人国王冲木格萨尔可能为至今所知的有关“四天子”的最早记载。它似乎说明这些机构要早于北方军队国王格萨尔的组织 。它也提出了一个要知道,在什么时候和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的问题。还应指出,冲木格萨尔是唯一一个没有伴随提到“王”的名字,如果是格萨尔于此具有“皇帝”的辞源学意义,那就是指冲木的“皇帝”。如果看一下《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第254页的表就会明白,冲木格萨尔在其名字的形式和指给他的方向方面,都继承了罗马的恺撒,也就是东罗马的伊朗语形式Frōm,道宣在7世纪时将之考证为波斯。据我所知,这一事实与商人国王冲木格萨尔,形成了我们即将看到的、有关Pt.958号写本中的亲子关系的假设的标志。
。它也提出了一个要知道,在什么时候和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的问题。还应指出,冲木格萨尔是唯一一个没有伴随提到“王”的名字,如果是格萨尔于此具有“皇帝”的辞源学意义,那就是指冲木的“皇帝”。如果看一下《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第254页的表就会明白,冲木格萨尔在其名字的形式和指给他的方向方面,都继承了罗马的恺撒,也就是东罗马的伊朗语形式Frōm,道宣在7世纪时将之考证为波斯。据我所知,这一事实与商人国王冲木格萨尔,形成了我们即将看到的、有关Pt.958号写本中的亲子关系的假设的标志。
已经有人指出,如果“四天子理论”肯定为相当古老和其原则是一成不变,这种原则就是把世界分成了4部分,那么国王们与他们所统治的方向之间的地理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进行这样分类的那些人的观点、地理知识和时代。然而,根据在Pt.958号写本中位于北方地区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这不是一个具体时间的话,至少也是这一文献由此而开始的一个起点。北部包括突厥人地区,同时也包括大食人地区波斯,人们一般都认为后者位于更靠西方;他们与默啜部的关系不太明朗。这一术语曾多次出现在敦煌文书中 ,特别是出现在由巴科先生发表在《5位回鹘使节对高地亚洲的考察》(载《亚细亚学报》,1956年,第137—153页)中的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3号中。突厥默啜地区是5位回鹘人报告的出发地,据说它共包括12部(第141和145页)。克洛松先生也写了一篇论文分析这一文书(《论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3号》,载《亚细亚学报》,1957年,第11—24页),他是以下列方式考证默啜的:“毫无怀疑,这里是指北突厥第二汗国,由颉跌利施(即骨咄禄可汗)于公元628年复兴,在由第4篇报告所描述的背景中灭国。在有关‘默啜’一名上,也丝毫没有怀疑,它相当于一个可汗王号的汉文对音,即颉跌利施的弟弟和事业的继承人,于691—716年即位”(第12页)。稍后不远,克洛松先生又在第18页中考证了这一地区的12部中的几个部族。因此,很明显,Pt.958号写本不可能早于8世纪初叶,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不会晚于8世纪中叶,因为阿波干可汗之汗国在744年就落入了回鹘人手中,从此之后再用“默啜”一名就会犯时代的错误了。这种猜测很有冒险性,因为汗国的名称的使用时间,也可能推迟到阿波干之后。然而。大食人和突厥的联盟,也可能是暗示突厥人在8世纪初叶占据了粟特人地区
,特别是出现在由巴科先生发表在《5位回鹘使节对高地亚洲的考察》(载《亚细亚学报》,1956年,第137—153页)中的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3号中。突厥默啜地区是5位回鹘人报告的出发地,据说它共包括12部(第141和145页)。克洛松先生也写了一篇论文分析这一文书(《论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3号》,载《亚细亚学报》,1957年,第11—24页),他是以下列方式考证默啜的:“毫无怀疑,这里是指北突厥第二汗国,由颉跌利施(即骨咄禄可汗)于公元628年复兴,在由第4篇报告所描述的背景中灭国。在有关‘默啜’一名上,也丝毫没有怀疑,它相当于一个可汗王号的汉文对音,即颉跌利施的弟弟和事业的继承人,于691—716年即位”(第12页)。稍后不远,克洛松先生又在第18页中考证了这一地区的12部中的几个部族。因此,很明显,Pt.958号写本不可能早于8世纪初叶,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不会晚于8世纪中叶,因为阿波干可汗之汗国在744年就落入了回鹘人手中,从此之后再用“默啜”一名就会犯时代的错误了。这种猜测很有冒险性,因为汗国的名称的使用时间,也可能推迟到阿波干之后。然而。大食人和突厥的联盟,也可能是暗示突厥人在8世纪初叶占据了粟特人地区 。
。
现在我们再回到Pt.958号写本的史料来源问题上来。阿毗达磨的经文似乎并不是把有关四主的理论与对无热恼池的描述混合起来了。但《世间设施论》还包括有其他可以与这一内容进行比较的观念。最明显也是最著名者便是把世界分成四个洲的观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四个洲分别位于四个方向。在汉文中就分别叫作: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这种传统的分类法也出现在敦煌文书中的两卷《世间设施论》中,出现在Pt.966写本和第8页和9页,以及Pt.967号写本的第1页中。我们知道,藏文的《世间设施论》也长篇描述了四大洲居民的财富、服装、城市、度量衡、两性习惯等等。可是,如果对《世间设施论》这些段落的释读,可以通过联想作用,而使某个了解这一情况的人联想到“四天子理论”,但这种释读尚不足以产生这种理论。
如果本处似乎并没有直接牵涉到阿毗达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针对这一写本的前后演变关系而提出一种假设。当时确实存在有一篇重要文献,它在描述了阿那婆答多池(即无热恼池)以及由此池而源出的河流之后,立即导入了“四主”理论,这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序》 。完全如同Pt.958号敦煌藏文写本一样,这位大取经人也把阿那婆答多池置于“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这一位置相当奇特,所以拉摩特先生在《大智度论》译本第1卷,第450页注②中,又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敦煌文书和《大唐西域记》又都一致把商人归于北主的居民。从石泰安先生在其著第254—261页所列的表看来,这主要是玄奘的独创,除此之外还有比较晚期的《喜地呼尔》。另外,对于源出该湖的4条江河的描述,也转载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中的描述,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部经文是由阿毗达摩大专家玄奘亲自翻译(见上引威特文第34页注②,上引普祖鲁斯基文第492—493页;戴密微:《古典印度》第2卷,第443—446页)。
。完全如同Pt.958号敦煌藏文写本一样,这位大取经人也把阿那婆答多池置于“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这一位置相当奇特,所以拉摩特先生在《大智度论》译本第1卷,第450页注②中,又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敦煌文书和《大唐西域记》又都一致把商人归于北主的居民。从石泰安先生在其著第254—261页所列的表看来,这主要是玄奘的独创,除此之外还有比较晚期的《喜地呼尔》。另外,对于源出该湖的4条江河的描述,也转载了《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中的描述,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部经文是由阿毗达摩大专家玄奘亲自翻译(见上引威特文第34页注②,上引普祖鲁斯基文第492—493页;戴密微:《古典印度》第2卷,第443—446页)。
由于玄奘是第一个把四天子的内容与对无热恼池的描述联系起来的人(在他之前,4世纪末的《十二游经》也强调了四天子理论,但却没有与无热恼池联系起来。译者声称这部经文译自梵文,但其真实性值得怀疑) 。我们是否可以承认,玄奘和Pt.958号敦煌写本史料有着共同的来源呢?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印度文献来看,这一点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可能更应该认为,在玄奘经过西域之后,阿毗达磨的这些译本就得以传播开了。这位唐朝法师或那些受他影响的弟子们,就强调了其中有关四天子的理论,完全如同《大唐西域记序》一样。如果是通过这一部经文的媒介作用,对于无热恼池的描述适用于向9世纪之前的吐蕃传播这一理论。那么近代西藏人再也不相信联系上述两大内容的纽带了。因为吐蕃人不会不知道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至少在晚期是这样的。1748年的《如意宝树史》在有关佛教于汉地传播的一节中,在提到玄奘的名字时称之为“唐僧”,在罗开什·阐德拉的版本中,于第120—126页中概述了他的生平和西游。另外,在1820年的《世界广说·南赡部洲》有关于阗国(李域)的一卷中,又把《大唐西域记》看作是其史料之一(见达斯于1886年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第201页中的解释)。但玄奘主要是由于贡布杰的努力,才在西藏为人所知,后者在《汉地教法史》中概述了玄奘的生平(18世纪中叶,见《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第39页),他将《大唐西域记》摘译作藏文。巴黎收藏有该书的胶卷,叫作《大唐西域记目录》
。我们是否可以承认,玄奘和Pt.958号敦煌写本史料有着共同的来源呢?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印度文献来看,这一点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可能更应该认为,在玄奘经过西域之后,阿毗达磨的这些译本就得以传播开了。这位唐朝法师或那些受他影响的弟子们,就强调了其中有关四天子的理论,完全如同《大唐西域记序》一样。如果是通过这一部经文的媒介作用,对于无热恼池的描述适用于向9世纪之前的吐蕃传播这一理论。那么近代西藏人再也不相信联系上述两大内容的纽带了。因为吐蕃人不会不知道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至少在晚期是这样的。1748年的《如意宝树史》在有关佛教于汉地传播的一节中,在提到玄奘的名字时称之为“唐僧”,在罗开什·阐德拉的版本中,于第120—126页中概述了他的生平和西游。另外,在1820年的《世界广说·南赡部洲》有关于阗国(李域)的一卷中,又把《大唐西域记》看作是其史料之一(见达斯于1886年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第201页中的解释)。但玄奘主要是由于贡布杰的努力,才在西藏为人所知,后者在《汉地教法史》中概述了玄奘的生平(18世纪中叶,见《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第39页),他将《大唐西域记》摘译作藏文。巴黎收藏有该书的胶卷,叫作《大唐西域记目录》 ,从其第2页来看,此标题译自《大唐西域记》。该文于第151页结束于有关娑摩若僧伽蓝的历史,以及那位可以用手举起窣堵波并置诸掌中,以将舍利骨放于下面的人的故事处(儒莲译文第2卷,第237页;毕尔译文第2卷,第318页;沃特斯译本第2卷,第297页)。其中有一行字终于提到了由王妃所建的一座伽蓝,此寺以东有一条大流沙河,但贡布杰犹豫不定,难以定夺是否应将此河考证成玛曲河(黄河)。紧接着是题跋:“第二卷终。大乘天、大唐大译师、精通三藏者的传记刊印于同一卷,即本章之末。因为大译师的这部传记可以收入了我的《汉地教法史》
,从其第2页来看,此标题译自《大唐西域记》。该文于第151页结束于有关娑摩若僧伽蓝的历史,以及那位可以用手举起窣堵波并置诸掌中,以将舍利骨放于下面的人的故事处(儒莲译文第2卷,第237页;毕尔译文第2卷,第318页;沃特斯译本第2卷,第297页)。其中有一行字终于提到了由王妃所建的一座伽蓝,此寺以东有一条大流沙河,但贡布杰犹豫不定,难以定夺是否应将此河考证成玛曲河(黄河)。紧接着是题跋:“第二卷终。大乘天、大唐大译师、精通三藏者的传记刊印于同一卷,即本章之末。因为大译师的这部传记可以收入了我的《汉地教法史》 ,我认为不需要再翻译一次了。此书叫作《西域记》,载汉文《论藏》中,已由贡布扎布译成藏文”等。
,我认为不需要再翻译一次了。此书叫作《西域记》,载汉文《论藏》中,已由贡布扎布译成藏文”等。
“大乘天”是玄奘的梵文名字之一(见《拉萨僧诤记》第11—12页注释)。汉文的《西域记》共包括12卷(《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087号),而不是10卷(沃特斯书第1页;戴密微:《古典印度》第406页、456—457页)。但沃斯特也强调了来自华北的一种10卷本,此本可能就是贡布扎布摘译本的底本,因为他在第1—2页中还指出:“下面就是《大唐西域记》……由大乘天以汉文修撰,来自一部十卷本。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而概述了其最明显的特点,并用藏文编写。”
在其摘译本开始处,贡布扎布接触到了四天子问题(第2页),“据非常著名的阿毗达磨的经文来看,其教理观点如下:一般来说有娑婆世界,具体来说又有四大洲世界。更为具体地来说,其中基本涉及到了赡部洲的组织,分别乘金轮、银轮、铜轮和铁轮而来到和将要出世的四圣主。这里又对真正的上师之国(印度)及其附属地区[唐朝的喇嘛或和尚(指玄奘)亲自前往],以及对他旅行中沿途经过的许多大地区所作的某些解释。据他的解释来看,当在这一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圣主的时候,众所周知的是人类的四大圣主就已经在赡部洲出现了。第1位圣主统治了赡部洲南部潮湿和非常多雨的地区,由于他的财富取自大量象群,所以人称之为象主。第2位统治了赡部洲西部,濒邻大洋,因为在那里可以发掘许多种宝,所以人称这第2位为宝主。第3位统治了北部一个非常寒冷的地区,由于那里马匹很多,而且财富也多来自马匹,所以人称为马主。第4位统治东方,那里民法特别发达,集聚了大量的人群,所以称之为人主。人们也按照顺序而分别称之为印度教法王、香巴拉宝王、大食霍儿王、汉地民法王”。
在这一摘要本中,贡布扎布把佛经中的宇宙论资料,与由玄奘所提供的关于四主的资料分割开来了(有人甚至认为他几乎是将之对立起来了)。前者诸如对苏迷庐山附近各洲的描述和圣主的出现;后者是对圣主内容的延续,贡布杰似乎认为这些资料是玄奘在取经朝圣途中所搜集的某些观点之结果。贡布扎布甚至没有提到无热恼池,这也可能是由于作者无意地将之包括在赡部洲的地理中了,因为他认为赡部洲在阿毗达磨的经文中太多见了,不值得于此重新描述。
贡布扎布在提出考证方向和各个具体地区时,离开了《大唐西域记》(完全如同道宣和958号写本一样)。他把南部考证成了印度,把西部考证成了香巴拉,这是拘理迦国王的地盘 ;把北部考证成了大食的霍尔人,也可能就是作为旭烈兀的后裔波斯蒙古人;把东部考证成了汉地。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肯定,这种对应关系根本不存在于贡布扎布所使用的10卷本的《西域记》汉文原文中,然而这很可能是贡布杰本人的解释,他在对待汉文文献中采取了某种自由态度。因为他在上文所引的那段译文之后,便是引自《国王遗教》中的一段话,这在玄奘著作中肯定没有。总而言之,18世纪的《西域记》译本并不能证明我于上文所针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958号的原文而提出的假设。换言之,如果这两种相距1000年的资料中,同一内容又产生了同样的联想,那才会令人感到惊奇。
;把北部考证成了大食的霍尔人,也可能就是作为旭烈兀的后裔波斯蒙古人;把东部考证成了汉地。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肯定,这种对应关系根本不存在于贡布扎布所使用的10卷本的《西域记》汉文原文中,然而这很可能是贡布杰本人的解释,他在对待汉文文献中采取了某种自由态度。因为他在上文所引的那段译文之后,便是引自《国王遗教》中的一段话,这在玄奘著作中肯定没有。总而言之,18世纪的《西域记》译本并不能证明我于上文所针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958号的原文而提出的假设。换言之,如果这两种相距1000年的资料中,同一内容又产生了同样的联想,那才会令人感到惊奇。
如果说Pt.958号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的前一种用藏文所写的关于四天子理论的文献,同时提供了证据,即正如石泰安先生所认为的那样,说明“四天子”理论的传播(或者至少是这种理论传播的渠道之一),是借助于佛教和通过西域而进行的,那同样不无道理。
注释:
①见本人所著:《〈汉藏史集〉初探》,即将发表于《亚细亚学报》中。
②这些等级与《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45号)卷9中的描述相同,它似乎就相当于藏文大藏经中大谷目录的第800号。与此有关的一段已摘要发表于《法宝义林》第1册,第12页中了。有关阿修罗的问题,除了发表于《法宝义林》第40—41页的一段文字之外,我们还可以参阅S.烈维:《〈罗摩衍那〉史》(载1918年《亚细亚学报》,见第46页);毕尔:《佛教经典之连锁》第50—55页;拉·瓦累·普散:《世亲的〈阿毗达磨俱舍论〉》第2册,第3卷,1926年巴黎版,第11页注②;穆斯:《六道之光》,1939年巴黎版,第154—183页;林藜光:《正法念处经》,1949年巴黎版,第25页。
③一般人都认为龙王是8个整体,而不是八部。参阅A.麦克唐纳:《文殊师利根本仪规的曼陀罗》第117页注①。
④有关佛教地狱的情况,见《六道之光》第93—113页、295—316页以及其他各处;《正法念处经》第3—14页。
⑤《正法念处经》第16—23页;《六道之光》第248—261页以及其他许多地方。
⑥见耶索密多罗对《阿毗达磨俱舍论》的疏注,其中第3卷涉及到了宇宙论,它已由普散用梵文和藏文发表。该部经文一共区别出了24种,作者确实认为在转生中有五趣而不是六道。参阅瓦累·普散:《佛教研究和资料、宇宙论、众生的世界和世界的汇集处》。世亲和耶索密多罗:《阿毗达磨》第3卷,1914—1918年伦敦版,原文第3—4页,译本第1页。
⑦瓦累·普散:《宇宙学和佛教宇宙论》,发表于《东方学研究》第4卷,第137页;《佛教宇宙学的年龄》,载同一刊物第1卷,第187—198页;《世亲的〈阿毗达磨俱舍论〉》第170—175、185—190、192—193页注
⑧见《法宝义林》第21页;韦曼:《佛教中有关毒的观念》,载《东方学报》第10卷,第1期,1957年,第107—109页。
⑨我没有翻译该词,因为从上文提到的那个并列句来看,我认为它可能是指北方—个重要省份或城市的名称。
⑩高楠顺次郎:《根本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文献》,载《巴利文献学会会刊》,1904—1905年伦敦版,第67—146页。
 我们还可以参阅由拉摩特所汇辑的所有文献,《龙树的〈大智度论〉》第1卷,载《比利时卢万大学博物馆丛刊》第18期,1944年,第106—113页;有关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普遍情况,见巴罗:《小乘佛教诸宗》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38卷,1955年西贡版,第131—152页。
我们还可以参阅由拉摩特所汇辑的所有文献,《龙树的〈大智度论〉》第1卷,载《比利时卢万大学博物馆丛刊》第18期,1944年,第106—113页;有关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普遍情况,见巴罗:《小乘佛教诸宗》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38卷,1955年西贡版,第131—152页。
 见布顿:《善逝教法史》第115页。高楠顺次郎已经引用了这段文字(同上引书,第77页注释),这是由切尔巴斯基为他翻译的。这引文的出处第173页很可能有一个印刷错误,因为我所拥有的这一本书两页中,一般都与他所使用的那一本相同。切尔巴斯基所泽的Prajnasen明显就是智军的名字。这位大译师可能确曾与噶瓦拜则和属庐·路易坚赞共同邀请胜友、宦利那黎提拿菩提、坛戒等赴吐蕃。正是他们这些人于9世纪初更新了译语。参阅《桑耶寺古史—〈拔协〉》,石泰安译本,1961年巴黎版,第73页。
见布顿:《善逝教法史》第115页。高楠顺次郎已经引用了这段文字(同上引书,第77页注释),这是由切尔巴斯基为他翻译的。这引文的出处第173页很可能有一个印刷错误,因为我所拥有的这一本书两页中,一般都与他所使用的那一本相同。切尔巴斯基所泽的Prajnasen明显就是智军的名字。这位大译师可能确曾与噶瓦拜则和属庐·路易坚赞共同邀请胜友、宦利那黎提拿菩提、坛戒等赴吐蕃。正是他们这些人于9世纪初更新了译语。参阅《桑耶寺古史—〈拔协〉》,石泰安译本,1961年巴黎版,第73页。
 拉露小姐:《墀松德赞赞普时代的佛经》,载1953年《亚细亚学报》第325页,第275—277号;图齐:《小品佛典》第2卷,1958年罗马版,第46—48页。
拉露小姐:《墀松德赞赞普时代的佛经》,载1953年《亚细亚学报》第325页,第275—277号;图齐:《小品佛典》第2卷,1958年罗马版,第46—48页。
 《丹珠尔》,北京版本第2卷,第19页,纳塘版本第20页。
《丹珠尔》,北京版本第2卷,第19页,纳塘版本第20页。
在吐蕃,权限随着时代不同而有差异。如在乌坚巴的传记中,辛都河从狮口流出,他甚至还叫作“狮泉河”(第61页;图齐:《经苏婆伐窣堵河流域前往吐蕃进香旅行记》,1940年加尔各答版,第48页和注[36],第75页和95页)。如在19世纪时于1820年的《世界广说·南赡部洲》中可以发现一些有关把阿耨达湖考证成玛法木错湖的讨论,同时讨论了有关动物头颅的合理化看法,它们实际上可能是一些成动物头状的岩石,位于环绕冈底斯山的四座大山的山脚下。参阅韦利:《关于〈世界广说〉中的西藏地理学》,1962年罗马版,原文第4—6页,译文第56—59页,注释60—64。一部冈底斯山和玛法木错湖(于此被说成了是无热恼池)地区圣址的导游指南的时间,为第15甲子循环的丙年(1896年),它在依照同样的顺序而讨论了一番之后,又以与《世间设施论》列举资料的相同方式,提到了4条河名。恒河在东部,被称为“象泉河”;辛都河位于南部,被称为“牛泉河”或“孔雀河”;博叉河(博刍河)位于西部,被称为“马泉河”;私多河位于北部,被称为“狮泉河”。对这些河和地区准确程度不同的描述混合在一起了,其目的是用神话地理学来掩饰该地区的真实地理学。
 这段疑问甚多。
这段疑问甚多。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967号。有关诸如《大智度论》这样的史料,赋予4条河各500条支流的情况,见拉摩特:《大智度论》译本第1卷,第450—451页;其中所示各条河的方位与《世间设施论》相同。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967号。有关诸如《大智度论》这样的史料,赋予4条河各500条支流的情况,见拉摩特:《大智度论》译本第1卷,第450—451页;其中所示各条河的方位与《世间设施论》相同。
 上引世亲和耶索密多罗经文第77—78页:《世亲的〈阿毗达磨俱舍论〉》第3卷,第147—148页;霍芬格:《阿热恼池大会》,1954年鲁汶版,第177—180页。我于此仅仅引证大藏经经文,它们很可能是958号写本的史料来源。
上引世亲和耶索密多罗经文第77—78页:《世亲的〈阿毗达磨俱舍论〉》第3卷,第147—148页;霍芬格:《阿热恼池大会》,1954年鲁汶版,第177—180页。我于此仅仅引证大藏经经文,它们很可能是958号写本的史料来源。
 参阅威耶诺特夫人:《古印度对树的崇拜》,载《大亚细亚综合研究丛书》第59卷,1954年巴黎版,第76—77页和102—103页。
参阅威耶诺特夫人:《古印度对树的崇拜》,载《大亚细亚综合研究丛书》第59卷,1954年巴黎版,第76—77页和102—103页。
 《鹿野苑柱子的象征主义》,载《东方学研究》第2卷,1932年巴黎版,第494—498页;还可以参阅图齐:《印度—西藏资料集》第1卷,1932年罗马版,第80页。
《鹿野苑柱子的象征主义》,载《东方学研究》第2卷,1932年巴黎版,第494—498页;还可以参阅图齐:《印度—西藏资料集》第1卷,1932年罗马版,第80页。
 见上文注
见上文注 。
。
 见释觉月:《佛陀游云生涯12年》,载《大印度学会会刊》,1943年,第10卷,第1期,第26—27页;石泰安:《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3卷,1959年巴黎版,第254页。
见释觉月:《佛陀游云生涯12年》,载《大印度学会会刊》,1943年,第10卷,第1期,第26—27页;石泰安:《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汉学研究所文库第13卷,1959年巴黎版,第254页。
 《世间设施论》,北京版本,第9页。它却发挥了四大洲居民财富的问题,而且又以本义提到了一些珍贵物资:如金、银,或者是在许多洲的铜。
《世间设施论》,北京版本,第9页。它却发挥了四大洲居民财富的问题,而且又以本义提到了一些珍贵物资:如金、银,或者是在许多洲的铜。
 《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第270—272页和572—575页。
《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第270—272页和572—575页。
 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2卷,1950年伦敦版,第276—280卷;石泰安:《汉藏走廊古部族》,1960年巴黎版,第4页。
托玛斯:《新疆藏文文书资料集》第2卷,1950年伦敦版,第276—280卷;石泰安:《汉藏走廊古部族》,1960年巴黎版,第4页。
 格鲁塞:《草原帝国》,1948年巴黎版,第165—167页;吉罗:《蓝突厥汗国》,1960年巴黎版,第49—52页。
格鲁塞:《草原帝国》,1948年巴黎版,第165—167页;吉罗:《蓝突厥汗国》,1960年巴黎版,第49—52页。
 儒莲:《西域记》译本,第3卷,1857年巴黎版,第76—78页;毕尔译文,1904年伦敦版,第11—15页;译本第1卷,1904年伦敦版,第34—38页。
儒莲:《西域记》译本,第3卷,1857年巴黎版,第76—78页;毕尔译文,1904年伦敦版,第11—15页;译本第1卷,1904年伦敦版,第34—38页。
 伯希和:《四天子说》第97—106页。
伯希和:《四天子说》第97—106页。
 这是一卷由152页组成的写本,收藏于大谷大学图书馆,汉学研究所已收藏有胶卷。
这是一卷由152页组成的写本,收藏于大谷大学图书馆,汉学研究所已收藏有胶卷。
 这句话的意义不太清楚。
这句话的意义不太清楚。
 《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第264和305页注
《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的研究》第264和305页注 。这种定位方法是错误的:香巴拉始终位于北部。我们也可能应该把东西方向颠倒一下,但其中的一句“他们也依次被称为印度法王等”说明,这些考证确实指上文所提到的四个方向的国王。
。这种定位方法是错误的:香巴拉始终位于北部。我们也可能应该把东西方向颠倒一下,但其中的一句“他们也依次被称为印度法王等”说明,这些考证确实指上文所提到的四个方向的国王。
(译自1962年《亚细亚学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