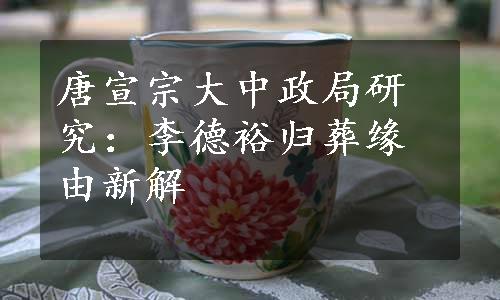
附文三 李德裕归葬缘由新解
会昌六年(846)三月宣宗登基后,重用牛党白敏中等大肆迫害会昌朝宰相李德裕,将其远贬为崖州司户,大中三年(849)十二月十日,李德裕病死于崖州贬所。李德裕死后,宣宗君臣宿怨未解,不许其葬归故里。但是大中六年(852)三月,在朝廷的特敕下,李德裕之子李烨最终获许护送李德裕及其亲属、家仆等六人灵柩自崖州归葬洛阳。关于李德裕归葬的缘由问题,陈寅恪先生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中提出李德裕归葬得力于大中五年(851)白敏中因延资库进言的观点。陈先生此说影响甚广,其后傅璇琮、王炎平等先生在相关著述中均赞同此说[1]。笔者认为,陈先生对李德裕归葬之事多有发明,但也略有武断之嫌,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以就各位方家指正。
《通鉴》卷二五〇懿宗咸通元年九月条下《考异》引《金华子杂编》云:
宣宗尝私行,经延资库,见广厦连绵,钱帛山积,问左右曰:“谁为此库?”侍臣对曰:“宰相李德裕执政日,以天下每岁备用之余尽实此,自是已来,边庭有急,支备无乏者,兹实有赖。”上曰:“今何在?”曰:“顷以坐吴湘狱贬于崖州。”上曰:“如有此功于国,微罪岂合深谴!”由是刘公邺得以进表乞追雪之。上一览表,遂许其加赠,归葬焉。[2]
关于《金华子杂编》的此段记载,司马光在《考异》中曾有驳斥。司马光言:“宣宗素恶德裕,故始即位即逐之,岂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岂合深谴’!又刘邺追雪在懿宗时,此说殊为浅陋,今不取。”司马光所说甚是,但是司马光只是据情理驳论,并没有得到史料上的佐证。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洛阳李德裕家族的一些墓志陆续出土,李德裕归葬缘由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唐代墓志汇编》咸通〇一六李濬《唐故郴县尉赵郡李(烨)君墓志铭》略云:
大中初,公三被谴逐,君亦谪尉蒙山十有余载。旋丁大艰,号哭北向,请归护伊洛。会先帝与丞相论兵食制置西边事,时有以公前在相位事奏,上颇然之,因诏下许归葬。君躬护显考及昆弟亡姊凡六丧,洎仆驭辈有死于海上者,皆辇其柩,悉还。
我们知道,延资库本名备边库,为会昌末李德裕为防备党项、回鹘所置。大中初党项内扰,西北兵食之事颇令朝廷头疼。从字面上看,墓志所云宣宗与宰相论兵食制置西边事与《金华子杂编》所云延资库之事似乎是同一事,如此一来,被司马光否定了的《金华子杂编》千百年后忽然又得到出土墓志的印证。陈寅恪先生据此墓志倡言:“然则《金华子杂编》之说虽有传述过甚之处,要为宣宗所以特许德裕归葬之主因,则可决言。”并进一步推测道:“夫当日敏中既判延资库,又为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使,则烨志所言之丞相自非敏中莫属,故疑德裕之归葬,敏中实与有力焉。”笔记小说与出土文献互证是陈寅恪先生治史之一大特色。这里陈先生有两个创见:其一,李德裕得以归葬是因为宣宗观游幸延资库,感念旧勋;其二,当日为李德裕论功的宰相是白敏中。
陈先生之言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细推敲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难以自圆其说。首先,宣宗素恶李德裕,李德裕贬死,宣宗是主谋,不可能直至到了延资库,才知其人蒙受不白之冤。另外,大中三年(849)宣宗将备边库改名延资库,不久改由宰相直接兼判,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宣宗绝无可能直至大中五年(851)才偶尔知道延资库的存在。《金华子杂编》情节荒诞,与史实多不吻合,应系唐末文人伪作,陈先生将其与《李烨墓志》相比附是有欠稳妥的。陈先生进一步又推测当日进言者是宰相白敏中,在逻辑上也存有较大问题。白敏中既已出为“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使”,也就是说他已不在朝中,判延资库之职当转由他人执掌(据《会要》,续判者为崔铉),何以复言此“丞相”非白敏中莫属呢?
我们可以断定,李德裕归葬与延资库无直接关系,但是《李烨墓志》明确无误的记载“会先帝与丞相论兵食制置西边事,时有以公前在相位事奏”,为李德裕求情的应是某位宰相无疑。大中初,白敏中权倾一时,有没有可能如陈先生所推测的那样,进言者就是白敏中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李德裕归葬的确切时间有个准确的把握。李德裕《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后李烨所作《附记》记归葬事甚详,《附记》略云:
大中戊辰岁冬十一月,烨获罪窜于蒙州立山县,支离顾复,念切蓼莪,欲报之恩,昊天罔极。己巳岁冬十月十六日贬所奄承凶讣,茹毒迷仆,岂复念生。匍匐诣桂管廉察使张鹭,请解官奔讣,竟为抑塞。荏苒经时,罪逆釁深,仍钟酷罚,呼天不闻,叩心无益,抱痛负冤,塊然骨立。阴阳至寇,棣萼尽凋,藐尔残生,寄命顷刻。殆及再期,乃蒙恩宥,命烨奉帷裳还袝先兆。烨舆曳就途,饮泣前进。壬申岁春三月,扶护帷裳,陪先公旌旐发崖州,崎岖川陆,备尝艰险,首涉三时,途经万里,其年十月方达洛阳。十二月癸酉迁袝,礼也。呜呼天乎!烨迫于谴逐,不能终养,劬劳莫报,巨痛终天,有生至哀,瞑目已矣。[3]
刘氏为李德裕嫡妻,大中二年(848)随德裕之贬而同至崖州,大中三年(849)八月二十一日先李德裕三月而卒[4]。李烨《附记》云“殆及再期,乃蒙恩宥”,这表明李烨得到朝廷特许归葬在大中五年(851)。墓志云大中六年(852)三月发自崖州,李烨自蒙州赶往海南崖州亦需月余(刘氏八月二十一日卒,由于刘鹭等横加阻挠,李烨十月十六日始得讯),故李烨在蒙州得到朝廷特许应在大中五年末。通常情况下,制敕自长安至岭南(蒙州)需要一两个月时间,可逆推此赦令自朝中发出的时间约在大中五年十月左右。而白敏中大中五年三月即已拜都统出镇邠宁,当时并不在朝廷,陈先生谓《李烨墓志》中宰相“非敏中莫属”在时间上是不能成立的。
不仅如此,从现存史料看,咸通初,懿宗诏复李德裕官爵,白敏中本人并没有将李德裕归葬之功据为己有之意。《通鉴》卷二五〇懿宗咸通元年九月条下《考异》引宋敏求《实录》注云:
白敏中为中书令,时与右庶子段全纬书云:“故卫公、太尉,灾兴鸺鸟,结怨江鱼,亲交雨散于西园,子弟蓬飘于南土,尝蒙一顾,继履三台,保持获尽于天年,论请爰加于宠赠。”全纬尝为德裕西川从事,故敏中语及云。
咸通元年(860)新君初立,朝野为李德裕恢复声誉的呼声甚高。白敏中是个反复无常之人,刘邺奏请追赠德裕官爵,白敏中“尝蒙一顾”,其入翰林本由李德裕举荐,为笼络李德裕故吏,助成其事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白敏中信中没有半字提及宣宗大中初李德裕归葬之事。这表明即便白敏中掠美平反之事,也仅限于在李德裕赠官上曾有力助,而不敢妄言此前有功于李德裕归葬,此亦可间接证明李德裕归葬与白敏中没有任何关系[5]。
除去白敏中外,大中初,最有资格与宣宗商讨军国大事的另一位宰相就是令狐绹了。巧合的是,关于德裕归葬缘由另一较有影响的说法,进言的宰相正是令狐绹。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中载:
太尉、卫国公李德裕,上即位后坐贬崖州司户参军,终于贬所。一日,丞相令狐绹梦德裕曰:“某已谢明时,幸相公哀之,放归葬故里。”绹具为其子滈言,滈曰:“李卫公犯众怒,又崔、魏二丞相皆敌人也,见持政,必将上前异同,未可言之也。”后数日,上将坐延英,绹又梦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还故里。与相公有旧,幸悯而许之。”既寤,召其子滈曰:“向来见李卫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祸!”明日,入中书,具为同列言之。既于上前论奏,许其子蒙州立山县尉烨护丧归葬。[6]
《东观奏记》此说为《新唐书·李德裕传》所采纳。陈寅恪先生对此说持否定态度,认为“德裕之是否见梦于绹,及其归葬之是否由绹之所请,则无从判明”。今按,李德裕托梦之说虽属悠茫,但亦非无迹可寻。李德裕远贬崖州后,白敏中等仍不肯就此罢休,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安插亲信出任桂管观察使,用以监视李德裕与外界的消息往来。据李德裕妻刘氏墓志,大中三年(849)桂管观察使为牛党成员张鹭[7]。大中四年(850)张鹭为令狐定所代,令狐定为令狐绹叔父,岑仲勉先生言“《东观奏记》所载令狐绹代请归葬,岂得讯自叔父而托之梦欤?”[8]此语虽简,但是颇有启发意义。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考证》卷下云:
《桂林风土记》:迁莺坊,本名阜财,因曹邺中丞进士及第,前政令狐定改为迁莺坊。《唐才子传》:“曹邺,大中四年及第。”杜牧有《赠令狐定礼部尚书制》:“去载桂阳,虽闻旱耗,闻其风俗,馨若芬兰。”牧以大中五年为舍人,大中六年卒。以此考之,定卒在牧之前无疑。旧《纪》大中十年十月桂管令狐定卒,误。
吴廷燮考订令狐定卒于大中四年曹邺及第之后,大中六年(852)杜牧病卒之前,而我们知道李德裕恰好在大中五年(851)得朝廷许以归葬,二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另据缪钺《杜牧年谱》,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十二日尚在湖州,可进一步推知朝廷得知令狐定卒讯应在八月以后。笔者颇疑旧《纪》中“大中十年十月”本为“大中五年十月”之讹误。若将令狐定之死同李德裕托梦之事联系起来,此事来龙去脉或可揣知一二。盖大中三年(849)八月李德裕妻刘氏卒,时李德裕子李烨欲解官奔丧,为桂管观察使张鹭抑塞,十二月李德裕亦在穷苦中病死,牛党同样不许李烨归葬。巧合的是,新任观察使令狐定到任后不到两年时间也染病去世(据《方镇年表》,张鹭桂管任期仅一年,抑或也卒于任)。大中五年(851)十月,令狐定死讯传到长安,令狐绹素惮李德裕,谓其叔父令狐定之死为李德裕鬼魂作祟,极为忧惧,故而出现《东观奏记》所言的一幕。令狐绹虽欲奏李德裕托梦之事,断不能直诉于宣宗,终需缘他事方可进言。大中五年,用兵岁久,国用匮乏。令狐绹先言李德裕制置兵食之功,再过渡到托梦之事,较为合理。李濬《李烨墓志》所记宰相言兵食事同李德裕托梦并不矛盾。陈寅恪先生指出“烨志盛称烨当父为相时避嫌守正之事,殆李濬特举此以刺令狐滈者”。李濬对令狐绹、令狐滈父子招赂擅权尤为不满,其不肯直书令狐绹名氏也不足为怪。
除李德裕归葬同令狐定之卒在时间上前后吻合外,以下一些理由或证据亦可以用来说明李德裕归葬缘于令狐绹惧德裕魂魄索命。
其一,从材料的真实可靠性来看,《东观奏记》所记并无任何漏洞。
《东观奏记》所记皆裴庭裕耳闻目睹,故记李德裕事较为可信。例如李烨贬所两《唐书》皆误为象州,独《东观奏记》不误。我们知道,令狐绹素无主见,大事尽谋于令狐滈,《东观奏记》所记令狐绹欲向宣宗进言,两次谋于令狐滈,这与令狐绹行事风格完全一致。令狐滈云当时朝中宰相除令狐绹外,尚有崔铉、魏謩二相。检得大中五年(851)十月戊辰至大中九年(855)七月间崔铉、令狐绹、魏謩三人同朝为相,时间上亦大致相当[9]。崔铉、魏謩皆为大中初竭力诋毁李德裕者,令狐绹直到大中二年(848)才由湖州刺史入朝,没有过深介入迫害李德裕之事,顾虑较少,由其出面求情也较为合理。(www.zuozong.com)
其二,从归葬细节来看,李德裕归葬之事似应为令狐绹等人一手包办,若非是对自己“性命攸关”的大事,令狐绹等恐不致如此用心。
李德裕归葬时极为隆重,“公躬护显考及昆弟亡姊凡六丧,自仆驭辈有死于海上者,皆辇其柩”。大中三年(849)六月,宣宗敕云:“先经流贬罪人,不幸殁于贬所,有情非恶逆,任经刑部陈牒,许令归葬,绝远之处,仍量事官给棺椟。”[10]李德裕当日并未公开平反,不在官给棺椟之列,即便宣宗特许官给棺椟,但沿途雇佣脚力等花费亦甚为巨大。李德裕贬至崖州时资储荡尽,病无汤药,时告饥馑,只有谏议大夫姚勖曾遣使馈饷候问[11]。李烨亦坐贬蒙州立山尉,俸薄禄微,以其境遇,绝无赀财千里北返。若非令狐绹等大力支持,李德裕归葬断难成行。李烨附记言“先卫公自制志文,烨详记月日,编之于后,盖审于行事,不敢诬也”。李烨“审于行事”,不敢言及其他,恐亦为当时形势所迫。盖宣宗君臣惧怕李德裕索命,故不得不尽快了却李德裕“魂魄”归葬心愿,但又不肯公然为其平反,所以归葬是在一个相当低调的状态下进行的。陈寅恪先生认为大中五年(851)李商隐受柳仲郢差遣,往渝州迎候杜悰,同时又径由渝州往江陵,顺道祭奠李德裕归柩。事实上,大中五年柳仲郢始镇东川,似乎不可能预知归葬之事,李商隐祭李德裕恐非柳仲郢所遣,应该是在迎候杜悰时不期而遇的。此时刘三复之子刘邺衣食无落,正以文章客游江浙,更是无由得知归葬之事,故其咸通元年请复李德裕官爵时尚有李德裕“孤骨未归于茔兆”之言[12]。
其三,从此后令狐绹对李氏子孙的态度来看,令狐绹虽然没有改变抑塞李氏子孙的政策,但亦不敢过于刁难迫害。《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附柳仲郢传》载:
大中朝,李氏无禄仕者。仲郢领盐铁时,取德裕兄子从质为推官,知苏州院事,令以禄利赡南宅。令狐绹为宰相,颇不悦。仲郢与绹书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愧于昔人;吴咏自裁,亦何施于今日?李太尉受责既久,其家已空,遂绝蒸尝,诚增痛恻。”绹深感叹,寻与从质正员官。
柳仲郢此时应已从李商隐处得知令狐绹许李德裕归葬之事,故敢公开庇护李德裕兄子。令狐绹虽极不情愿,最终还是默认事实,并授其正员官,此亦可视作李德裕托梦的后续影响。
李德裕生前嫉朋党,抑浮华,同牛党斗争了三十年,终遭宣宗君臣陷害,贬死崖州。然而唐宣宗、令狐绹等虽然阴谋得逞,对李德裕仍畏惧之心,令狐绹竟屡在梦中为李德裕魂魄相逼,最后不得不许其归葬。有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此恰为李德裕生前身后之写照。宣宗君相只许李烨归葬其父,在护送灵柩归葬后随即返回立山贬所,宣宗朝历次赦宥均不得量移。李烨妻郑氏大中九年(855)亦卒于蒙州,因无宣宗特赦,也不得归葬[13]。从宣宗对李德裕子嗣的冷酷态度来看,尽管宣宗君臣惧怕李德裕魂魄作祟,不得不许其归葬,但是对李德裕的仇视却始终没有减轻。宣宗君相怯懦若此,但又顽固若此,大中之政亦可知矣。
【注释】
[1]分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8—540页;王炎平:《牛李党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167页。
[2]今本《金华子杂编》此条佚,《唐语林校证》卷三《赏誉》此条“宣宗”作“懿宗”,又《玉海》卷一八三“唐延资库”条亦作“宣宗”,故知《唐语林校证》中“懿宗”乃后人所改。
[3]《唐代墓志汇编》大中〇七一《李德裕妻刘致柔墓志》。
[4]刘氏本为李德裕妻,陈先生《辨证》中误题为李德裕妾,详考见岑仲勉《唐史余渖》卷三“李德裕妻刘氏及其子女”条。
[5]王炎平《牛李党争》中对陈说进一步发挥,推测大中五年(851)白敏中出为都统即是因此遭谗的结果,离真相似乎更远。
[6]《南部新书》卷庚亦载此事,但其传误甚多,对李德裕多有猥琐之词,或经过晚唐牛党文人改造。
[7]《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载:“初,僧孺闻德裕代己,乃以军府事交付副使张鹭,即时入朝。时扬州府藏钱帛八十万贯匹,及德裕至镇,奏领得止四十万,半为张鹭支用讫。”张鹭正是与李德裕有宿憾者。
[8]《唐史余渖》卷三“李德裕妻刘氏及其子女”条。
[9]陈寅恪先生《辨证》文中以三人同相时间为大中三年四月乙酉至大中九年七月丙辰。今按,大中三年四月乙酉崔铉拜相,但魏謩拜相在大中五年十月戊辰,陈先生所言不确。
[10]《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本纪》。
[11]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别集》卷六《与姚谏议郃书三首》,第520页。此处姚郃当作姚勖,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第668页有详考。
[12]《通鉴考异》及陈寅恪先生皆以刘邺上书为后人伪造之史料。但表中诸事与李烨墓志皆合,则未可遽断言其伪,或刘邺不知其事,故重复言之。
[13]详见《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五七《李烨妻郑珍墓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