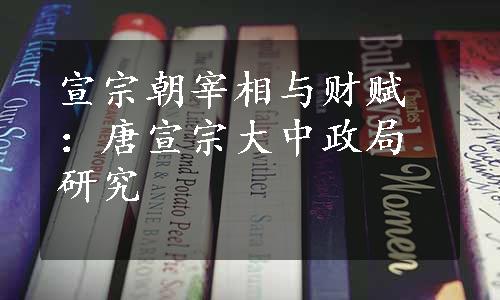
唐代中后期财政中枢逐渐由尚书户部四司主掌演变成度支、盐铁、户部三司分掌的格局。宪宗以后,朝廷始以宰相兼领财赋。到了宣宗时期,以计臣入相的情况较为普遍,计相的广泛存在是宣宗朝宰相之制的显著特点[40]。宋代洪迈《容斋续笔》卷一四“用计臣为相”条云:
唐自正(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谨(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非宰相事,请以归有司,其识量宏正,不可同日语也。[41]
宣宗朝新除宰相共18人,而由财政三司使入相者高达13人,占到总数的72.1%,计臣入相的问题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就洪氏所列宣宗朝马植、裴休等13人的情况来看,虽然此13人都由三司入相,但是具体情况差异很大。有的入相时即已罢使,有的入相数月内罢使,有的则入相一二年后方罢使,由计臣入相者未必入相后仍兼判财赋,洪迈笼统地称之为计相是不妥当的。为了对宣宗时期计臣入相的问题有更直观的了解,兹列表如下:
唐代宣宗朝三司使入相情况简表
续表
注:本表以《新唐书·宰相表》为依据,同时参考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及《东观奏记》中相关记载而制。计相时间是指以宰相兼判三司的时间。[1][2][3][4][5][7][8][9]采自严耕望先生《唐仆尚丞郎表》,[6]据《东观奏记》卷上补。其中裴休使职,万斯同《唐将相大臣年表》作裴休八月入相,仍判度支,无盐运,误。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宣宗朝计臣入相大致可分为前后两阶段。会昌六年至大中三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多入相即罢去使职,卢商、崔元式、周墀、魏扶等虽然以计臣入相,但入相时即已罢去使职,可以称为计相的只有马植1人。大中四年至大中末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由计臣入相者除崔慎由外都曾作过计相。整体上说,宣宗朝新除宰相18人,由三司入相者13人,其中仅有马植、崔龟从、魏謩、裴休、萧邺、刘瑑、夏侯孜、蒋伸等8人曾作过计相,约占入相总数的44.4%。而这8人之中,任相期间兼判三司的时间多仅有数月,超过一年的只有魏謩和裴休二人。(www.zuozong.com)
当然,三司使入相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不可能仅用一张表格或一组数字来表明财政三司同宰相的关系。宣宗朝财政三司使入相者除了人数多、比重高等特点外,尚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由财政三司入相者,虽得以参政言政,但是其职务重在财赋,故在其他庶政上权力比较有限。令狐绹拔擢裴坦为知制诰,裴休极不赞同,但力不胜绹,裴坦致谢时,裴休道“此乃首台谬选,非休力也”,当场拂袖而去。魏謩任相期间颇得宣宗信任,一次魏謩欲以杜濛为左拾遗,遭到裴庭裕父裴绅的坚决反对,最后也不了了之[42]。其他诸计相中,卢商因误判死狱,周墀因言收河湟之事,马植因宦官赠玉带之事,裴休、崔慎由因言立储之事而遽遭罢免,即使一度深受宣宗信赖的魏謩也因言辞过于刚直,遭令狐绹排挤而罢相。由计臣入相者若过于热心政务,反而会给自己的仕途带来意想不到的厄运。在执掌朝政方面由计臣入相者确实无法同白敏中、令狐绹等人同日而语。
其二,由财政三司入相者入相时间多比较短暂,除魏謩和裴休外,多数仅只有数月或一年左右,这表明由计臣入相者地位极不稳定。计臣入相后地位不稳同当时牛党内部新的权力之争有一定的关系,大中后期执政的令狐绹怙权自专,“尤忌胜己者”,由三司入相者多遭到令狐绹的排挤打压。但是周墀、马植、崔慎由等都是微有过失即遭罢黜,毫无回旋余地,我们认为,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宣宗对计臣的态度问题。大中以后,随着朝廷财政收入日益萎缩,宣宗不得不提高财政之臣的政治地位,直至官拜宰相,但是从强化君权的角度来看,若宰相将相权和财权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势必造成权倾天下的局面。宣宗喜欢玩弄权术,一方面以入相激劝计臣为朝廷卖命,另一方面在计臣入相后又时常寻找借口将其罢去,这是大中时期计相任期多短暂的重要原因。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三司使入相只表明三司使地位的提高,对相权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事实上,宣宗时宰相在财政方面的权限确实有所扩充,但这个变化不是三司使入相,而是首辅宰相兼判延资库[43]。《唐会要》卷五九“延资库使”条载:
会昌五年九月,敕置备边库,收纳度支、户部、盐铁三司钱物。至大中三年十月,敕改延资库。初以度支郎中判,至四年八月,敕以宰相判,右仆射平章事白敏中、崔铉相继判。其钱三司率送。初年户部每年二十万贯匹,度支、盐铁每年三十万贯匹。次年以军用足,三分减其一。诸道进奉、助军钱物则收纳焉。[44]
会昌五年(845),李德裕置备边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边境的紧张形势,并试图为用兵河湟积累财赋[45]。《册府元龟》卷四八三《邦计部·总序》载:“[大中]四年因收复河陇,诏渑池盐令度支收管,仍以灵州分巡院官专勾当。又诏以宰相判延资库,于是白敏中、崔铉相继判。”因此,大中四年(850)宣宗改以宰相兼判延资库,实际上是朝廷因河湟戍边费用激增而采取的一个应变措施,若从此点看,宣宗朝宰相职掌财政较前朝是有所扩大的。延资库收入完全仰仗三司率送,随着三司使税收的日渐枯竭,三司应转割给延资库的财赋时常不能兑现。咸通五年(864),延资库使夏侯孜奏称,户部每年合三、九月两限送延资库钱264,285贯匹,但自大中八年(854)至咸通四年(863)九月,除已纳收外,尚欠1,505,714贯匹[46],仅完成总数的43.03%。大中三年(849)八月,宣宗赏收复河湟诸军镇绢二十万匹,并以户部产业物色充(是时备边库尚未改名),大中末岭南用兵,又多支户部钱物,延资库并没有实现备边的初衷。终宣宗之世,延资库在朝廷财政体系中的地位尚不突出。懿宗咸通以后,延资库使凭借首辅之相的权威,逐渐割取财政三司的某些税收权益,成为可直接向地方征收财赋的财务收支系统,直到这时延资库才在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